亦论宁夏吴忠市有无古城湾村——与白述礼先生商榷
2013-10-20艾冲刘冬
艾冲 刘冬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北部边疆的重要城市——灵州城的地理位置问题,近年受到学界的关注,引起较为热烈的讨论。其中,也存在似是而非的说法。《宁夏史志》2012年第4期登载了刘冬撰写的 《关于唐代原州的三个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唐代原州》)。该文的一句话,即“开元九年(721)十二月,唐廷建朔方节度司(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引起了白述礼先生的注意。白先生认为:今宁夏吴忠市并无“古城湾村”,所谓古代灵州城不在“古城湾村西侧”,遂在《宁夏史志》2012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村吗?》的文章(以下简称白文),与《唐代原州》作者刘冬商榷。[1]我们读过白述礼先生的文章后,觉得白文所列诸证据过于牵强附会,且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无法证明“古城湾村”并不存在,而且与其过去的说法存在自我矛盾之处,难于自圆其说。这当然不能令人信服。说到底,题为《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村吗?》之文是一个伪命题。因此,我们愿在此回应白文的商榷。
一、所谓“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村吗”毫无意义
刘冬在《唐代原州》中主要论述唐代原州军政机构的变迁等问题。白述礼先生若对其主要内容有不同的见解而提出商榷,我们欢迎并愿意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白文对《唐代原州》仅说了一句客套话后,就对其主要内容再只字未提,却盯住“古城湾村”这个枝节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并非学术商榷的正确方式,其所论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白文开篇就着重强调“特别是,作为一位外地学者,能够与时俱进,文中决然抛弃昔日‘灵州在今灵武西南’的旧观点,欣然认同宁夏多数学者‘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的新观点,把唐代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城的位置,定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
然而,白述礼先生的这一句话存在两点失误。其一,即所谓“昔日‘灵州在今灵武西南’的旧观点”,白先生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实际上,古代“灵州在今灵武西南”的说法并无不妥之处。这种说法是以今灵武市旧城区作为参照坐标,判断古代灵州城址在其西南方向。在未具体确定古代灵州城的地望前提下,这是正确的表述。即便在目前,也属不错的表达。这一表述相比于“在今宁夏吴忠市”的笼统说法更为可靠。[2]白先生将“在今灵武西南”方向错误地理解成“在今灵武西南”部,显然是大错特错了。错在何处呢?错在将“在今灵武西南”方向误判为在今灵武市境内。其实,古代“灵州在今灵武西南”之说并无此意。所谓古代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的说法显得过于笼统宽泛。今吴忠市是地级市,下辖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和盐池县,如此广大的区域成为古代灵州治城所在,岂非太空泛吗?这种提法比起古代灵州城在今灵武市境(县级市)更为无稽。
其二,就是白述礼先生铸下断章取义之舛错。刘冬的原文是“开元九年(721)十二月,唐廷建朔方节度司(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而白先生刻意将“古城湾村西侧”六字割断,仅以“今宁夏吴忠市”来证明刘冬认同所谓“宁夏多数学者”的“新观点”。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式断章取义的做法,违背了作者刘冬的本意,毫无参考价值。这种将对自己有利的字词保留且予以肯定、而将与其观点不合的字句割断且予以否定的做法,在学术上是很不道德的投机行为。
如果说刘冬在唐代灵州治城位置上有所认同、采信与引用,就是采信引用了艾冲关于古代灵州城址变迁的研究成果——唐代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的结论,并非“欣然认同宁夏多数学者‘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的新观点”[3]。而艾冲的这一研究结论,白述礼从未提及,即使他最新发表的论文也是如此。[2]更别说其他宁夏学者是否论及了,此乃白先生借“宁夏多数学者”之名以兜售其不靠谱的说法。就是说,刘冬绝非认同所谓“宁夏多数学者”的“新观点”,那是白先生个人的断章取义之说辞。究其实际而论,所谓“‘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的新观点”也只是白述礼的提法,并非“宁夏多数学者”的观点。
白述礼先生刻意将“古城湾村西侧”六字割裂下来,就是要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因此,所谓“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村吗”的命题,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可言。尽管如此,白文涉及“古城湾村”有无问题,还是应当辨析明白。兹在下面试作辩论,以期达成学术共识。
二、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境有个古城湾村
白述礼先生声称:“……其中,‘开元九年’和‘朔方节度使,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所表述的结论完全正确。只是朔方节度使设置时间的‘十二月’和灵州今址的‘古城湾村西侧’的表述,似略有误。”遂以之作为批评的对象。[1]
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究竟有没有古城湾村?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在利通区境内。下面分作三个方面予以辨析。
(一)“古城”只是“古城湾村”的省略称谓
白述礼先生为说明今宁夏吴忠市并无“古城湾村”,列举出三个证据。
其一是举出2000年出版的 《吴忠市志》所附《吴忠市1998年行政区划表》的记载“吴忠市有‘古城乡’,古城乡管辖有7个村,其中有‘古城’村,没有‘古城湾村’”。
其二是举出宁夏民政厅2004年编制的 《吴忠市利通区行政区划统计表》所载“吴忠市利通区‘古城街道办事处’管辖有11个村,其中有‘古城’村,也没有‘古城湾村’”。
其三是“2007年7月10日,宁夏吴忠市又将古城街道办事处撤销,改建制为古城镇。新设立的古城镇辖原古城街道办事处的11个村,其中包括原‘古城’村,仍然未见‘古城湾村’”[1]。
我们并未否认在当今政府文件、出版的著作(包括地方志)中,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存在专名为“古城”的政区或聚落名称。但是,这只表明“古城”是“古城湾村”的省略称呼,也是“古城湾”的省略称呼。这种省略称呼在宁夏地区是习以为常的传统称道,由来已久,遂成为被官方沿用的政区名称,甚至出现将错就错的现象。可是,这并不等于民间没有称村庄为“古城湾”的地名。
首先,我们来审视一下宁夏地区的地名省略称谓、甚至误写的实际情况。
在白述礼先生熟悉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列举为数众多的堡寨和屯堡名称,其中相当多的屯堡名称迄今仍存,但被今人省略称道,甚至写成错字或别字,而目前依然将错就错地使用着。而今人的错误书写,并不等于正确的地名根本不存在。倘若这样思考,就大错而特错了。
譬如《嘉靖宁夏新志》列出的“王鋐堡”,今人省略为“望洪”,且完全写成别字,此是长期口口相传而转音使然;“王泰堡”, 而今省称 “王太”;“叶升堡”,而今省作“叶盛”;“邵纲堡”,而今省作“邵岗”;“王佺堡”,今作“王团”;“张政堡”,今作“掌政”,将“张”字错写成“掌”字;“蒋鼎堡”,今简称“蒋顶”;“李纲堡”,今作“立岗”,“李”误作“立”;“姚福堡”,今作“姚伏”;甚至“周澄堡”,今人误作“周城”。 其中,“堡”字皆被省略。还有“分水岭”,今人误作“烽水岭”,等等。①管律(明)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五卫》,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62-63页、第68页、第71页、第74-75页、第78页。《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图册》,永宁县、青铜峡市、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诸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1版。[4]
其次,了解到这些客观存在的省用、误用地名的实际情况,就可知白述礼先生所举“古城湾村”不存在的三条证据毫无说服力。“古城湾村”被省称为“古城”,其起因应是地图编绘人员为压缩图面字数而采用习惯使用的简称使然。一旦这种简称落在地图上,遂成为政府部门、专业人士使用的工具。“古城”之省称在纸面上取代“古城湾村”之全名,就易于理解了。但这样的错误并不能掩盖真实存在的“古城湾村”,它就是现今书面上也被省称为“古城”的村庄(如今正被拆迁而面临消失的结局)。犹如宁夏大学被省称为“宁大”一样,当然不能因为大家习惯上简称“宁大”,似乎真正的宁夏大学之名就不存在了,其全名依旧存在。北京大学被省称为“北大”、清华大学被省称为“清华”,其中的道理亦然。白先生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二)白述礼的“古城”村之说,与其此前的见解存在尖锐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白文也说“昔日宁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古城湾乡’……1950年(县级市)吴忠市建立后,1955年以前,仍然有过‘古城湾乡’,但是,也未曾有过‘古城湾村’”[1]。可是,按照地名学常识来说,“古城湾乡”的得名源于其驻地“古城湾村”,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古城湾乡”之名。
依照命名规律,乡级政府驻在的村庄名称通常就是乡级政区及其管理机构的专用名。这在宁夏地区相当普遍,迄今依然如此。例如:永宁县李俊镇政府驻地就是李俊堡村,望洪镇政府驻地就是望洪堡村,望远镇政府驻地就是望远桥村;贺兰县立岗镇政府驻地就是立岗堡村,常信乡政府驻地就是常信堡村,姚伏镇政府驻地就是姚伏街(即姚福堡);青铜峡市邵岗镇政府驻地就是邵岗堡村,瞿靖镇政府驻地就是瞿靖堡村,诸如此类。古城湾乡的得名,当然也来自驻在的村庄“古城湾村”之名无疑。至于其驻地后来有所移徙,则另当别论。这就表明:白述礼先生所谓“也未曾有过‘古城湾村’”的说法并不可信。
不仅如此,白述礼先生在2012年11月前也认同有个“古城湾村”。第一个证据是白先生的《一石惊天 古灵州浮现吴忠》一文。[5]在该文中插有一幅《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地吴忠绿地园位置图》,在该图的吴忠市区西北、黄河东侧标有一个村庄——古城湾,其位置就是白先生如今所谓“古城”村。[5]这就是说,白先生当时也认为存在“古城湾村”。否则,怎能标在其文章的线图之上呢?更有意思的是,白先生在“古城湾村”名称之下又加标一行注记“古灵州城故址”。该文最初发表在2004年6月23日的《新消息报》上。既然如此,白先生如今为何声称吴忠市没有“古城湾村”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说辞吗?白先生不会说此图不是他的吧?既然其文章的线图绘有“古城湾村”,请问白先生,究竟是你的那篇文章表述正确、还是白文正确呢(图1)?需要着重指出,白先生在寄给刘冬的《古灵州在今吴忠 专家学者认同》一文中,私自将《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地吴忠绿地园位置图》上的“古城湾”篡改为“古城村”。之后,竟公然篡改该线图名称,插在《宁夏史志》2012年第6期刊登的白文中,请各位读者参阅本文的图1。这种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做法是极不严肃的投机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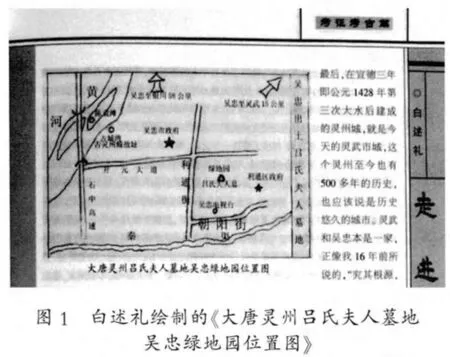
同时,第二个证据是:白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吴忠城建 古城灵州显真容》中也插有一幅线图《宁夏吴忠市唐墓葬群分布图》。在该图的同一位置也标出“古城湾”村之地名,其下也有一行注记“(古灵州城)”②白述礼著:《走进灵州》,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4页:《宁夏吴忠市唐墓葬群分布图》。[5]。他依然承认“古城湾”村的存在。该文最早发表在2004年10月18日《吴忠日报》上,后收入其《走进灵州》一书。虽然他现在不承认“古城湾村”,却早于八年前就在地图上将之清楚地标绘出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倘若白先生现在认为八年前自己搞错了,那就痛快地承认吧!然而,“古城湾村”是实实在在的聚落,亦即所谓“古城”村(按:实际是省称)。无论白先生承认与否,“古城湾村”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聚落(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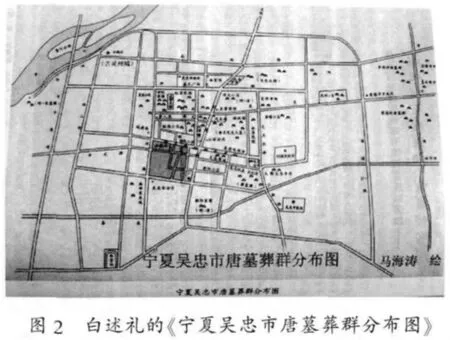
讨论至此,白述礼先生应该缄口无语了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白述礼先生所谓“古城湾”村即“古灵州城故址”、或者“古城湾”村就是“(古灵州城)”的认识也是很不恰当的。这种表述不仅与其文章的空泛论述不相符合,显露出自我矛盾的状况,而且跟历史实际相差一定的距离,不符合实际地理形势。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文献记载:明代洪武中古灵州城就被黄河洪流侧蚀冲刷殆尽,至今找不到任何遗迹。古城湾村根本未发现任何遗存。白先生凭空将古灵州城置于古城湾村的位置毫无依据,因为古代黄河从该村西侧流过,被冲毁的古代灵州城的位置应在今古城湾村之西侧、今黄河河道附近。实际上,“古城湾村”只能充当判定研究对象空间方位的客观的地理坐标角色,即起到参照物的作用。因此,所谓“古灵州城故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村”的说法,是不妥当的;所谓唐灵州城“即今宁夏吴忠市古城镇境内”,更是一种空泛之说。[1]都不如“古城湾村西侧”的表述更为具体准确。确如钟侃先生在《灵州的历史地位》中所指出:“墓志的发现,具体指明灵州城址当在今利通区绿地园以西的古城乡境内。城址虽遭河水崩陷而不复存在,但灵州城址所在的具体地方当可由此确定。”钟侃先生并未明确点出唐代灵州城址的具体地方在哪里,仅言“当可由此确定”。而“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就具体地指出明代以前灵州治城的地理位置,将此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并非白文所谓“其中‘西侧’的表述也欠妥”。请注意,钟侃先生采用“当在”、“当可”的措辞,这是较为谨慎的不十分肯定的表述。白述礼先生若因个人的需要将之视为“定论”,显然违背了该文作者的本意。[6]
(三)“古城湾村”的地名依旧存在
2010年8月,我们来到古城湾村进行实地考察。看到在该村南侧公路附近耸立着一座清真寺,其建筑物顶部赫然树立着“古城湾清真寺”六个大字。该清真寺毗连该村庄,就是以所在“古城湾村”命名的,这难道还有疑问吗(图3)!

白述礼先生在白文末尾所写“作者追记”文字,更从反面证明古城湾村的存在。即吴忠市正在建设“古城湾新村”工程,“是吴忠市古城镇所属新增加的第12个村:‘古城湾新村’。‘古城湾新村’并不是‘古城湾村’,与刘冬文中所说‘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村’,不是一回事”[1]。我们并未说过两者是一回事。然而,白先生不知道的是,早在2010年,古城湾村就处在被拆迁状态。旧古城湾村被拆除后,建立古城湾新村就势在必行。因此,“古城湾新村”虽然并非古城湾旧村(在旧村之南),但它与古城湾旧村被拆迁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是白先生并不清楚的。可以肯定,“古城湾新村”替代了旧“古城湾村”,但两者相距不远,“古城湾”之聚落名称仍旧得到保留与沿袭。鉴于此,所谓“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新村’,仍然没有‘古城湾村’”之说,显然是不成立的误判。因此,在今后,关于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时段灵州城位于“古城湾村西侧”的方位表述依然有效。
综上所论,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境的确存在一个“古城湾村”,“古城”只是它的省略称呼。这犹如“宁大”是“宁夏大学”的省略称呼一样的道理。白述礼先生的见解难于成立,也毫无学术意义。唐代灵州治城在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村西侧。其位置并非白文所谓 “今宁夏吴忠市古城镇”、“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村”、“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三说中的任何一说。
三、关于朔方节度司的始置年月
白述礼在白文中避开刘冬论述的主要内容,又抓住朔方节度使司创立于“开元九年(721)十二月”的时间不放,大发议论。这就给人一种吹毛求疵的感觉,或者叫鸡蛋里挑骨头的印象。
他认为 “……遗憾的是该文似乎都没有参考,朔方节度使设置时间表述为‘开元九年十二月’,其中‘十二月’,亦似欠妥”[1]。意在否定此时间。
首先要说明一点,对于朔方节度使司的创置年月,必须以原始文献记载来判定,绝非主要依据当代其他学者的论述确定。那么,指责刘冬未参考其他学者的论著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唐代原州》的表述是否错了?回答是:没有错。刘冬依据《资治通鉴》开元九年十二月的记载,将朔方节度司的始建时间判定在是年是月,这是正确的表述。[7]至于《新唐书》所谓“开元九年”、《唐会要》所谓“开元元年十月六日”,刘冬也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作了分析,并未采信。这也是正确的。其理据是,《资治通鉴》的年月顺序编排得清清楚楚,可以信服。而《新唐书》所谓“开元九年”与《资治通鉴》所载年份一致,却无月份,不必引用。至于《唐会要》“开元元年十月六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年份有误,不可采信;二是既然年份错误,其月日就难于令人相信。
其次,白述礼先生将《资治通鉴》开元九年十二月的记事,刻意改称作“开元九年末”,是十分无理的做法。[1]难道“开元九年末”不就是“开元九年十二月”吗?即便“开元九年末”是指开元九年十二月最后一天,那还是在十二月啊!这和刘冬的说法是一致的,为什么偏偏声称后者“亦似欠妥”呢?白先生不会没有这点常识吧!这种作法是十分可笑的!
第三,研究者是否采用其他某个学者或专家的观点,那是其自由,别人不得强求。何必非要别人接受某一种学术观点,而那种观点又很不靠谱。诸如白述礼所谓“专家学者比较一致考证确认:唐玄宗于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古城镇)设置朔方节度使的时间,应为‘开元九年(721)十月六日’”。关键问题是,既然年份已经出错,他凭什么相信其月份、日期是正确的呢?因为《资治通鉴》“开元九年(721)十月”并无相关记载呵。正确的做法是不采信《唐会要》所谓“开元元年十月六日”的记载,更谈不上将其月日与“开元九年”生拉硬扯在一起。这种“拉郎配”式作法是不严肃不靠谱的。
白述礼先生说这句话的依据是李鸿宾同志的《唐朝朔方军研究》,但显然误解了其意思。李鸿宾的原文如下:“《会要》的‘开元元年’经岑仲勉先生辨证,系‘九年’之误。倘若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一年的十月六日就应当是朔方节度使设立的具体时间”。[8]李鸿宾在此使用“倘若”、“应当”的措辞,也是表示不完全肯定的意思,至多只算是倾向于岑仲勉的辨证结论,并未完全采信之。不知白先生从何得出“专家学者比较一致考证确认”的结论呢?这仍然属于偷换概念的做法。即使退一步说,李鸿宾是“肯定”岑仲勉的意见,但我们不认为这是可信的说法,因此不予采纳。
其原因就是,白述礼完全忽略了《唐会要》的一个关键词,即“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敕”之“敕”[9]。“敕”者,皇帝的诏书、命令也。换言之,所谓“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敕”即唐玄宗于此日颁诏书或发命令,决定“改为朔方节度使”。做出决定与实际成立该使司之间需要一段筹划准备时间,因此实际设立朔方节度使司之举,必在其后的开元九年十二月。无论如何,绝非“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或白文所谓“开元九年(721)十月六日”。
我们认为:朔方节度使司始建于开元九年十二月,《资治通鉴》记载得清清楚楚,并无疑问。
尚需指出,白文中存在诸多的字词、句读、标点符号等方面的舛误和疏漏。例如“1950年(县级市)吴忠市建立后”的表述不合乎语法,本应是“1950年吴忠市(县级市)建立后”云云方妥。再如引用钟侃的论著时漏掉“绿地园”三字,引文并不完整。将《唐史余瀋》误作《唐史余藩》,白述礼作为老教授实在不该犯此低等错误呵。引用刘冬的“朔方节度司”刻意篡改成“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司”是指机构,“朔方节度使”是指职官,两者的意思有异,白先生又在此偷换概念。我们出于对白述礼先生的尊重,就不再逐一指出了,真诚期待白述礼先生能认真自查校勘其文章,别再出错啦!
四、关于白文对宣德《宁夏志》的误解
白文不仅否定《唐代原州》涉及的“古城湾村”,已见前述。还要否定“古城湾村西侧”的方位词“西侧”,认为“其中‘西侧’的表述也欠妥”,为其“唐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的提法进行辩解。[1]
白文提出的证据有四:明代宣德年间成书的《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绿地园出土的《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以及钟侃先生的文章《灵州的历史地位》。
首先,钟侃先生在文章中采用“当在”、“当可”的措辞,是较为谨慎的不十分肯定的表述,并未确定“灵州城址所在的具体地方”。而白先生视之为定论,违背了作者钟侃的本意,当然无法证明其所谓“古城”说。
其次,《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的出土,提供了唐代灵州治城的具体方位,而“古城湾村西侧”正是唐代灵州城的具体地方。但是,白述礼坚持所谓“即今宁夏吴忠市古城镇境内”的空泛说法,无力深入探究其具体所在地,没有意义。
再次,《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洪武年间灵州城被黄河洪水冲蚀殆尽,“唯遗西南一角”。既然与宣德《宁夏志》的记载存在明显的不同,根本无法证明白述礼先生关于古灵州城在今“古城”的提法。因此,引用该书毫无用处。
第四,宣德《宁夏志》关于灵州城故址的记载,既与《嘉靖宁夏新志》所载相左,且文字舛误甚多,只要认真读读吴忠礼先生的《宁夏志笺证》即知。因此,虽然其成书较早,但其可信性就需谨慎推敲定夺。而白述礼先生绝对相信其记载,且多有误读误解。为说明问题,在此转引《宁夏志笺证》原文如下:灵州“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击崩圯。洪武间筑城於故城北十余里,永乐间也被河水冲圯。今之新城,宣德间陈宁阳、海太监奉旨,相度形势,卜沙山西、大河东,西去故城五里余,命平凉卫指挥钟瑄、左屯卫指挥王刚督工筑者。地土高爽,视旧为胜”[10]。在这段关于古代灵州城遗址的记载中,出现了三个“故城”。第一个“故城”就是宣德年间仍可见其遗址的明代洪武年间迁建的灵州城址。第二个“故城”才是洪武年间被黄河大洪水冲没的“唯遗西南一角”的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时期的灵州城址。“洪武间筑城”之“城”则是永乐年间被黄河洪水再次冲坏的灵州城,即第一个 “故城”。第三个“故城”则是指永乐年间放弃洪武中所筑城池后再次迁建的灵州千户所城,亦即“视旧为胜”的“旧城”所在。而“今之新城”就是宣德间迁建的今灵武市老城区。白述礼先生却将第一个“故城”视为唐代灵州城,这是完全的误读误解。
因此,由此引申的见解难于成立。例如“古城一词是古灵州城的简称,古城西侧是黄河”。这一说法是建立在曲解《宁夏志》记载的基础之上,是无效的判断。前已申明“古城”是“古城湾村”、“古城湾”的省略称呼。而“古城湾村”、“古城湾”则是民间对不知其名的古代城址附近的黄河曲岸和村庄定下的地名。白先生硬说《宁夏志》的作者“朱栴还曾经亲眼见到过”、“古灵州城遗址”,记载于《宁夏志》中,但是,他曲解了《宁夏志》的相关记载。宣德年间犹存的 “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击崩圯”、“今犹存其颓垣遗址”的灵州“故城”废址,那是永乐中被黄河洪水冲坏而放弃的洪武中所筑灵州城,并非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再说580年前的明代宣德年间见到的洪武“故城”废址,能否保存下来实为悬案,因为明代黄河迫使灵州城三次迁徙是史实。白先生偷换概念,将“古城”省称强指为“古灵州城”,却非“古城湾村”,借此否定“古城湾村西侧”的正确定位,这是徒劳的。
至于所谓“朱栴还曾经亲眼见到过”古灵州城遗址,不知白先生有何确凿证据?
纵观白述礼先生关于古代灵州城址的研究过程,其结论总是飘浮不定。起初,他声称“明初以前被黄河水淹没的古灵州的城址,应在今吴忠市东北之东塔乡石佛寺村”[11];其后,他改口说“所以古灵州城应该在吴忠市西北原古城乡”[5];最近,他再次改口称“古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2]。总之,白述礼先生越说越空泛,从最初较为具体的地理位置——东塔乡石佛寺村逐步倒退飘移至古城乡(或古城镇),最后泛指整个吴忠市境。这样的所谓研究没有价值,还是具体一点、深入一点为妥。
况且,无论白述礼先生持何种说法,所指位置皆在今灵武市城区西南方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否定灵州城“在今灵武西南”之说呢?更有甚者,白先生并未探明古代灵州城的迁徙过程,就顽固地坚持所谓古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的片面认识。其实,古代灵州城址发生过四次迁移,因而存在过五座灵州城。第一座州城是北魏灵州城,在今青铜峡市瞿靖镇新林村附近;第二座州城才是存在于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初的灵州城,在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村西侧;第三座州城是明代洪武十七年迁建的灵州城,在今吴忠市管区北缘、山水河西侧;第四座州城是明代永乐中迁建的灵州千户所城,在今灵武市旧城西偏南五里处;第五座州城就是宣德三年迁建的灵州新城,即今灵武市老城区。[3]因此,今灵武市境内至少存在过两座古代灵州城址。至于“今宁夏吴忠市”之说,有失偏颇。
讨论至此,孰是孰非,相信读者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自然能分辨清楚的。
最后,我们奉劝白述礼先生,看一篇其他学者的文章要着眼于宏观大局,商榷要以其主题内容为讨论对象,不要老是抓着别人文章的枝叶大放厥词,更何况这枝叶并无不妥之处。他的文章中常识性问题是非常之多,如果我们像他那样做的话,尽可全盘托出。出于对老者的尊重,我们不提罢了。希望白先生在批评别人文章之前,先想想自己的文章有无问题吧!
[1]白述礼.今宁夏吴忠市有古城湾村吗?[J].宁夏史志,2012(6).
[2]白述礼.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考[C//].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8).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3]艾冲.灵州治城的变迁新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4).
[4][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5]白述礼.走进灵州[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
[6]钟侃.灵州的历史地位[C//]吴忠与灵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9][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吴忠礼.宁夏志笺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1]白述礼.古灵州城址初探[J].宁夏史志研究,198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