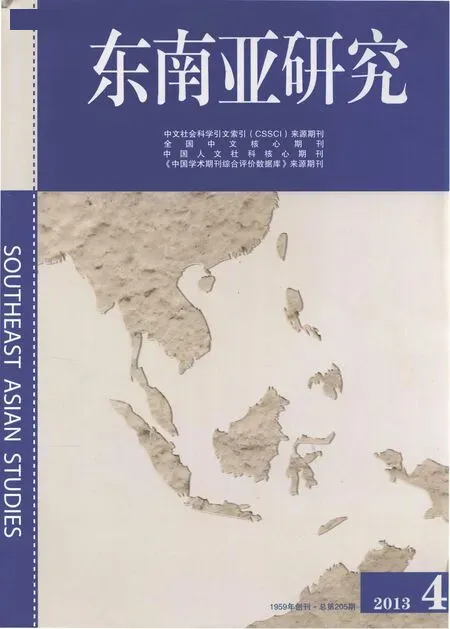跨国华人社会场域的动力与变迁:新加坡的个案分析
2013-09-27*刘宏
* 刘 宏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新加坡)
引言
过去的30年来华人新移民的数量增长迅速,已经有超过800万人散居于世界各个角落[1]。新移民社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明显的跨国流动性,这也促进了他们和故乡联系模式的多样化。目前,华人新移民已经通过多种机制与自己的祖籍地/国建立有效的联系,并藉此为海外的华人建构起一种集体性的认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华人的社会组织在建立华人的跨国联系和华商网络方面扮演了关键的制度性角色,这一功能在全球化时代也得到了承续和加强。
孔飞力教授 (Philip Kuhn)认为,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参照系,“祖籍国 (homeland)”的概念“既是客观事实 (中国革命和现代华人国家)……又是海外华人思想中的主观意象”的必然认识[2]。本文以新加坡作为学术案例,尝试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分析“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并探寻“祖籍国”概念是如何在后殖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被想象、拷问和重构的。笔者选择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作为深入的研究对象,乃是基于两重考虑:第一,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社会和商业网络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点之一,并且通过它的特殊定位把东南亚的华人与中国(尤其是华南)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有机地联系起来。第二,在过去的20年中,新加坡成为华人新移民在亚洲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数十万的华人新移民成为本地社会和文化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而对海外华人认同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们与“祖籍地”联系的范围 (不论是个体、家庭或商业上)也更趋多样化。本文主要关注制度性联系,集中研究那些已经在新加坡和移民的祖籍地之间建立和维持的制度化横向联系,并纵向考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殖民地/后殖民国家和本土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作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全球化在解释亚洲政治经济的发展动力方面让不同学者的论证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化被视为“全方位削弱国家权威”的重要力量,“蒸发、缩水、有缺陷、空洞”等概念已经成为描述当代国家特征的典型形容词[3]。然而,对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角色定位也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认为“国家安全依然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关切”, “没有其他类型的政治机构(无论是地方的、地区的、还是跨国的和全球的)可以像国家这样有着完全的多维度能力”[4]。
聚焦于跨国社会场域的角色,可以使我们超越在全球化时代对国家—社会二元关系的传统认识。目前对于全球性互联网络和族群等媒介的研究(如对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群的性别研究)揭示出跨国公共领域研究的重要性[5]。杨国斌就提出跨国华人的文化网络在华语世界本身就是“开放的交流空间”,而“这些空间在中国内部和外部的世界中是共同存在的”。然而,“从技术层面或者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这些空间与全球网络相连接,有着明显的全球性。它们的话语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跨越国家边界的限制将公众联结起来”[6]。
本文通过强调网络和制度的角色来聚焦跨国华人场域的发展和演进,展示现代亚洲从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到以社会和经济为中心的路径转变。换言之,作为纽带力量的华人社会组织已经将祖籍地的“客观存在”和华人的“主观意象”有机联结在一起。本文中所论及的“主观意象”就是由海外华人通过诸如报刊、网媒和文物等媒介建构起来的关于祖籍地或故乡 (侨乡)的认知和想象。这些意象有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可能并不能如实反映中国已经取得的快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是却彰显着海外华人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该认同反映了移民在移入国社会内部所拥有的归属(或缺失)感。
通过对过去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不间断联系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海外华人和其祖籍地之间的多层互动导致跨国华人社会场域的出现,并体现出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为海外华人和故乡/祖籍地之间的常规和持续扩大的人口、观念、商品和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有效的空间;国家(包括中国和海外华人所在的国家)在推动这些流动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二,作为横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领域的动态范畴,跨国华人社会场域已经并将继续如社会性和商业性的网络 (通过共同的族群活动)那样推动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的发展与演进 (通过建构对祖籍地的“主观想象”)。第三,目前跨国华人社会场域已经形成涵盖地域性、血缘性的宗乡社团以及专业性机构的制度化组织体系,并为全球华人的社会和商业联系搭建起有效的桥梁。
跨国社会场域的概念化和目前的国际移民研究紧密相连,它将跨国移民视作是在流动的社会性空间里发生的现象,并通过在多个社会的同时嵌入而得到持续的重构[7]。目前,对“网络”的研究已经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两家顶级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上所发表的以“网络”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从1980年的1.2%到1990年的2.2%,再到2000年的7.8%以及2005年的11.6%[8]。经济学家杰克逊指出,“关于‘网络’的研究文献增长非常迅速,该领域的多学科属性令人激动,很难想象其他研究领域也可以像诸多学科那样如此容易地来获取和应用”[9]。简单地说,华人跨国场域主要通过与祖籍地的联系来建构并维系制度化的网络和双向交流与互动。
下文中将重点讨论新加坡华人和他们 (想象的或真实的)祖籍地之间的跨国联系的形成与转型。这一联系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5年)展示了非殖民化和民族国家建构两个进程,新加坡华人社团此前与“侨乡”的密切联系在该阶段被瓦解,而他们与处境相当的邻国(区域内部)之间的联系则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中国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祖籍地的想象而存在,已经不再是先前开展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地实体了。第二阶段 (1965—1990年)过渡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在该阶段新加坡华人与祖籍地 (地方与国家的双重层面)的制度化联系被迫中断,中国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新加坡华人的“祖国”,然而东南亚区域内在的华人网络却因此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第三阶段 (1990年至今)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此时随着冷战后新加坡与中国的建交和关系的热络,两国之间的跨国网络得以重构和加强,新加坡华人与祖籍地的纽带也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而被紧密联结起来,但它也同时也影响了新移民同新加坡国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历史上新加坡华人社会与作为祖籍国的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增进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认知,同时跨国华人社会网络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对于更好地理解“跨界亚洲”[10]的发展也将做出一定的贡献。
一 故乡联系的新动力 (1950—1990年)
笔者认为,20世纪末叶之前,新加坡在亚洲社会与商业网络中的角色——及其与祖籍地的联系——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
(1)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从全球层面来说,新加坡是东西方交通的战略要冲,从地区层面来看,它处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交汇的十字路口。新加坡所处的马来半岛南端这一战略位置,使其在海路、空路和陆路 (通过新柔长堤)交通中拥有多条线路可以抵达该区域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比如印尼、大陆东南亚和中国。新加坡的重要地理位置和网络容量并没有被外部观察家所忽视,20世纪30年代,一份提交给民国政府的官方中文报告这样描述新加坡: “座落在南洋群岛 (海洋东南亚)的中心,是欧亚之间的重要通道,它在商务方面的重要性在本区域的诸多城市中无出其右者。”[11]
(2)转口贸易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性地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悠久历史和冷战的环境赋予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全球性城市国家的命运[12]。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起飞之前,其经济主要集中在转口贸易领域:诸如根据海外市场的需要从事对热带产品进行分类、分级、处理和深加工的贸易,以及进口大宗西方产品然后根据亚洲分销商的需要进行小容量分装等。
这一经济形式充分体现了贸易伙伴关系和社会/商业网络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相关性。如新加坡立法会议195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其转口贸易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商人之间的贸易联系”[13]。作为西方贸易公司和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大大小小的华商不论是在大规模的贸易还是小规模的零售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主要活跃在托收用于出口的本地产品以及销售进口来的制成品等领域。
总之,浓郁的跨国和跨地区特性——与基于籍贯和方言群的多种跨国网络联系在一起——很早就作为华人商业活动的标签而存在。新加坡的华人在组织这些跨界联系纽带方面非常积极,因为这一纽带不仅凝聚着大量深具代表性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掌控着本地的经济生命线。
二 从故乡联系到地区化的推动(1950—1965年)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就在新加坡建立了与本地华人社团拓展联系的重要联络机构。这些社团以“政治参与者、社会保护者、商业信用护卫者和文化行动者”的角色推动跨国与跨洋沟通桥梁搭建,服务于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本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开始转型。一些年轻的华人被新中国作为潜在的世界大国的崛起趋势所鼓舞。然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东南亚新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对华人的同化/歧视政策也受到支持,最终推动华人社群所形成的侨居心理向本地认同转变[14]。与1949年之前相比,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华社影响祖籍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程的尝试锐减为寥寥数例,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努力也仅限于特定的问题领域。作为文化符号的“侨乡”纽带也在此时被显著削弱。1941年以前,还有相当多的华人社团热心于提升和促进源自遥远的华南故乡的传统文化在南洋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华社在该议题上的关注点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意识到应该给予本地 (东南亚)文化以同样的或更多关注度[15]。
简单来说,50年代早期新加坡华人社团/网络已经和中国——既作为民族国家,也作为故乡——渐行渐远,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所驱使。二战以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冷战大背景为本地区的国家关系与身份认同搭建起全新的框架,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必须在政治和文化的取向上适应并推动认同的本地化。然而,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瓦解趋势是迫于外部敌对环境的压迫,所以华人社团的内部结构以及他们与“侨乡”之间的既有联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保留。因此,海外华人才能借助于这一制度化的基础,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在区域和全球层面重建与祖籍地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华人与祖籍国之间关系纽带的弱化所造成的损失,最终借助新加坡作为本地区网络中心地位的加强而得到部分的补偿。加上诸如地缘性和方言群联系等原生性的纽带在华人社会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华人社团也得以借助地区化的推动来巩固和拓展已经积累的金融资源和会员势力。
以新加坡台山会馆为例,台山县坐落在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四邑地区的一个县城。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该县有接近一百万人口,包括大约20万海外侨胞 (他们当中约有一半是生活在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在八个台山会馆的支持下,1947年泛马来亚台山会馆联合会在新加坡举行了开幕典礼,联合会旨在推动共同的族群团结,“(处理)有关 (同胞的)教育、文化、经济、互助和福利等方面的所有事务”。而提升东南亚地区台山同胞之间的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议程,例如,联合会鼓励台山同胞通过集资联营来创立企业,并力主通过此举“在南洋地区建立和增进台山同胞之间的合作,就像北美地区已经实现的那样”[16]。
华人社团在地区化趋势的推动下,逐渐对与新加坡和东南亚相关的事务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推动这些议程和事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该会馆三十多年的议事日程对比,可以清晰地展示这一转向 (参见表1)。

表1 潮州八邑会馆的主要议事日程 (1929—1965年)
“客观事实”与“主观意象”之间的互动在战后的东南亚一直存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当地方化进程导致新加坡华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在身份认同上逐渐有了同胞的亲近感时,祖籍国的概念得以再次浮现。另一方面,中国在与海外华人产生联系与互动时,其角色已经转换为“民族国家”,而非此前的“侨乡”。下文将详细讨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如何在战后积极推动重建与中国的关系这一典型案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减弱,并且随着1951年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强制执行对诸如橡胶、锡等战略物资的禁运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华商所从事的经济贸易活动主要是基于橡胶的进口、贮藏、深加工、分装、再出口等等领域,所以这项禁运的实行沉重打击了华人商业社会。为了摆脱困境,华商便由其代表性组织中华总商会出面,尝试重建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联系。
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政府新政策的支持。当时的中国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国内建设需要大量的橡胶、锡等原材料,而马来亚又是世界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在50年代中期,中国调整了它对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的政策,外交上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6年8-10月间,中国的外贸部长邀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的14个省份和十多个大城市。代表团在中国受到包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和欢迎。这次访问收获颇丰,代表团最终与中国签下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经贸合同,包括从新加坡出口7000吨橡胶给中国的许可。此行也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在提交的报告书中指出,所有总商会会员 (包括那些曾经是国民党领导成员的会员),都被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深深感染[17]。
总之,新加坡独立以后,基于本地会馆的社会网络在1950—1965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与中国的联系渐行渐远 (不论是侨乡还是国家这两个层面),但是众多本地会馆在地区化的推动下加强了联系,并逐渐在重新定位它们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祖籍地的概念在特定的场域中曾经被“侨乡”所代表,或者被作为民族国家的“祖国”所代表,虽然中国的民族国家定位使它在政治上与新加坡华人不断地疏离,但是在经济上它却与这个南洋岛国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三 跨国联系的再兴 (1965—1990年)
从新加坡人的立场来看,二战结束后的20年间,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化联系主要由社会力量发起和推动,很少或没有国家的干预。在中国,国家的作用则重要得多。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国家开始注重其在跨国联系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国家对跨国议程的管控能力在不断增强,而且国家也深深卷入到跨国进程中,并参与塑造个体与故乡之间联系的属性。1965年以后在新加坡本土出生的大多数华人,都把新加坡视作他们的故乡。1970年,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总和超过总人口数量的97%,其中新加坡公民占到93.1%[18]。20世纪80年代末期,海外华人力图重建与祖籍地联系的努力与全球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新加坡华人形塑对中国新的主观想象提供了机会。
新加坡独立以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推动下,逐步打破了西方在本地区内的航运垄断,拓展了华人社团运用政府和商业网络的力量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航运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中心内容,早在国家独立之前,航运就被远东航运公会 (FEFC)所垄断,其他的航运公会不得不接受西方大国的强有力控制。由于长期垄断,造成运费高的离谱,甚至比那些非航运联盟要高出20%-50%,这一局面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都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独立以后,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一个旨在结束远东航运公会垄断地位和取消高昂运费的运动被有效地发动起来。中华总商会确立了两个主要战略:一是积极与马来西亚其他的华人商会建立联系,二是努力争取获得国家的支持。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陈永裕在1967年倡议总商会和政府共同组织,一致行动,时任新加坡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1971年,中华总商会的一个代表团以低于远东航运公会1/4的运费在中国成功赢得了它的委托权。在70年代早期,中国总共有38艘船只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则抓住机会,与香港及菲律宾的华人运输公司展开积极合作,加强海外华人之间的商贸联系。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新加坡逐渐打破了远东航运公会在该地区的垄断,增强了新加坡与西方航运公会谈判的话语权[19]。
20世纪70年代许多新加坡华人将中国视为是族属与商业联结的契合点,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中使这一想象得到了加强,经济活动与中华文化和华人性等元素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华人社团已经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中,由全球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组成的制度化轨道已经形成,而新加坡则处在这一全球性华人跨界网络复兴的核心位置。尽管国家仍然在继续推进新加坡本地社团与祖籍地的跨国联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社团自身在组织全球联系时变得更加积极。
在国家推动社团跨国联系的背后还存在很多因素。首先,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依靠国际 (特别是亚洲)市场。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发展积极寻求建立所谓“区域之翼”的政策。为了这一议程,政府尽力去恢复华人社团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制度性联系。李光耀资政1993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宣布说,“我们如果不利用华人网络来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这将是愚蠢的”[20]。其次,虽然政府已经在国内建立起诸如民众联络所和社区俱乐部等多种基层组织,但是它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范围非常有限,无法满足跨国网络议程和拓展的需要。从社团领袖的视角来看,参与祖籍地所举行的国际性恳亲大会或者确保维持与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等都是避免社团人数和影响力降低的有效方式。前任贸工部部长杨荣文准将说:“新加坡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如果新加坡能够孕育它的文化内核,它的经济主干将变得更加强壮,而它的枝叶会伸展得更远更广。”[21]
因此,复兴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被国家和华人社团共同驱动,其目的是要让一个愈加全球性的新加坡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这里,诸如地方化和宗族关系等原生性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相关。换而言之,“主观意象”就是在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战略相结合的情况下的产物。
另一方面,“客观事实”的新变化对新的“主观意象”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通过改变旧政策,推出新政策来为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跨国制度化联系的复兴提供额外的推动力,这些变化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层面[22]。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事实和扩大,海外华人的定位逐渐从原来被认为的“历史包袱”转变成为经济发展所需的“优势资源”。作为海外华人全球性经济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华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努力“抓住机遇,善打‘侨牌’”。
中国政府重构与海外华人联系的政策转变与后者所推动的复兴与祖籍地之间联系的努力相契合。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组委会主席陈永裕指出,华商大会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就是“华人的共性”。此后各届大会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2011年10月第11届大会再次由新加坡主办。大会一直遵循的一个传统就是强调文化在海外华人商业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华人性”已经被确定为华人国际商业网络的起始点。海外华人的这一信念已经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张松声说:“经济发展催生了中国的崛起,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到亚洲,华人在商业事务中的优势也开始提升到世界范围”[23]。
新加坡福清会馆可以说是本地会馆中参与祖籍地建设和凝聚内部族群联系的代表性机构。1988年世界福清恳亲大会之后,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成立,总部设在新加坡。联谊会的目标是为会员提供“规划、组织和领导力”,并出版《融情》杂志。该季刊主要介绍世界范围内的福清人在社会、经济等领域的详细信息,每期大约有4000份的发行量,传播范围很广,阅读量也很大 (目前已经有网络版供在线阅读)。
总之,在新加坡和中国政府新政策的共同推动下,新加坡华人社团与祖籍地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得到了重构和加强,该联系在持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发展中已经创造了切实的经济成果。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劳奇 (James Rauch)和崔林德 (Vitor Trindade)的研究显示,“华人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国家之间差异化产品贸易的发展,这一现象在东南亚非常普遍,我们最小的估计 (1990年保守的看法)是,华人网络推动了近60%的双边贸易增长”[24]。
四 新移民及其与中国的新联系(1990—2013年)
前文对新加坡华人社团和“祖籍地”之间的跨国联系进行了分析解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团的领导和会员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华人移民,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就来新加坡拓殖,并已经把这里视为是他们永远的“家”。而刚刚过去的20年见证了一个不同类型华人移民的快速出现,即所谓的“新移民”。他们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中国移民到世界各地。他们优先选择的目的地是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是他们在亚洲的主要选择。本文接下来将考察新加坡新移民的特性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制度性联系的建立。其中,国家将继续在塑造祖籍地的映像以及与祖籍地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新加坡的新移民
较大规模华人新移民社区的形成受益于新加坡指导性的移民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主要是源自新加坡人口下降所造成的压力。过去的20年里,新加坡的人口持续走低,使其成为世界上有统计的人口总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4.93(1960—1965)到2.62(1970—1975)、1.57(1995—2000),再到2009年的1.2,这一数据已经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标准所需的2.1[25]。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将灵活的移民政策作为实现人口更新的重要途径。1999年吴作栋总理指出:“没有人才,我们就不能成为第一世界经济体和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家园,必须从海外引进优秀人才以弥补本地人才的不足”[26]。李光耀也确信新加坡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将放缓经济增长,并把增加本国人口数量视为政府必须解决的主要任务。李光耀以日本忽视引入移民而造成经济停滞的事实作为比较,并坦率地指出,“不管你是否喜欢,除非我们可以生育更多的婴儿,否则我们需要接纳更多的新移民”[27]。1992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提供全额奖学金给来自中国的高中生,帮助他们进入本地的初级学院和大学。奖学金所附加的一项主要条款就是他们毕业以后至少要在新加坡服务6年。在经济方面,国家给新移民企业家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启动资金总额达到1300万新元[28]。这一发展战略与支持来自大陆的中国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联系在一起。到2011年1月,157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市场资本接近495亿新元 (387亿美元),第二波上市的公司价值则达到45亿新元 (35亿美元)[29]。

表2 新加坡人口及其增长率(1990—2012年)
在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引进“外来人才”的灵活移民政策的推动下,过去的10年中,外来的永久居民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它代表了新加坡人口的最快增长区段 (见表2)。截至2012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有531万,包括382万新加坡居民,其中有329万新加坡公民和53万永久居民,还有149万非居民的外国人,他们持有一年以上的工作准证或长期访问签证。一般认为,新的永久居民中有很大比例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或者相关的专业技术经验。当给予他们永久居留权时,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教育学历证书和薪酬水准进行严格的审核。
没有官方统计显示华人新移民的具体数量,因为这对于多元族群社会的新加坡来说被视为敏感话题。据初步估计,新加坡的这类移民总数 (包括短期居留者,诸如短期合约劳工等)大体介于50万-60万之间[30]。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与其他地方的华人群体开始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这些新移民已经不仅仅来自华南侨乡,他们在中国的家乡已经扩展到了全中国。李光耀就承认当今的华人移民有不少“来自北方,或者说是长江以北。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到来让新加坡获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31]。那些有着先进的专业技能的新移民,一般来说都比本土人口的教育程度高,他们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部门占有较大比例。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在1671名全职教职员工中 (2000年数据,此后的数据没有公开),有 887名(53%)是新加坡公民,其余的784名 (46.9%)是外国人,这其中又有110名 (14%)是中国公民。在842名全职研究员中,只有221名 (26%)是新加坡公民,外国人则有621名 (74%),其中329名 (39%)是来自中国大陆[32]。
(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组织:超越地缘与血缘
华人新移民在新加坡人口总量中的比例在增加,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组织起来的呢?他们与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前辈之间是否存在不同?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有什么新特征?笔者认为,对于新来者而言,“祖籍地”的概念已经从明确的地域符号向文化或者族群符号转变,以代表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和作为民族国家或一种文明的中国。
与传统的华人社团相比,新移民社团涵盖面更广,他们从一个更加宽广的多样化的地理和社会背景下吸收会员,涵盖的范围也摆脱了诸如地域和血缘等原生性纽带的束缚。比如,在美国的新华人社团更倾向于双文化,并且在会员吸收和机构组成上遵循“独特的混杂”标准,要“同时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了解深刻,并在这两种文化下受到良好的教育,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他们大多由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专业性团体和校友会组织起来[33]。日本的新移民团体也是如出一辙,他们也是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技术和其他经济因素,取代了此前所依托的原生性纽带[34]。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那些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美籍华人的祖籍地的社会化在塑造他们的政治观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5]。
同样地,在文化与象征意义方面的相似发展趋势正在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中发生。新加坡华源会(后来更名为“中国新移民总会”)成立于2001年,由出生于大陆的华人专业人士组成,从成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新移民中吸收会员,同时也在持有长期学生准证或工作准证的中国大陆公民中吸收“准会员”。根据它的章程,该组织有六个主要使命:“协助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促进会员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促进会员与其他社团的友谊及交流;通过各类活动丰富会员及家人的业余生活;促进新加坡和中国两地商贸往来。”作为代表中国新移民的最大的社团组织,华源会有5000名左右的会员[36],其来源地广布中国各省,其中超过80%的会员拥有大学学历。
非地域性是华人新移民社团的另一个特征。与华源会一样,成立于1999年的新加坡天府会则以一种更为符号性的方式代表其成员的故乡。虽然天府是四川省的别称,但是该会的成员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地缘组织性原则 (即名义上的出生在四川和讲四川方言者),而且还包括那些曾经在四川学习、工作或者从事商业文化活动的人。“同乡”这个词自2006年从天府会的名字中拿掉 (最初名为“新加坡天府同乡会”),同时成立了附属机构天府商会。天府会会员大约有2000名,来自中国各地[37]。
在这些社团和他们故乡的联系中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会馆被新中两国政府共同认可,李显龙总理在2010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以这是“一个好现象”高度赞扬了新移民社团在新加坡国民融合中的作用[38]。如天府会的顾问中就包括新加坡国会议员和四川省副省长,而且国家对新移民社团的扶持已经在多个领域实施:第一,当新加坡政府旨在通过诸如华源会这样的制度化机制来吸收和融合新移民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样对通过新移民组织建立跨国社会和商业联系非常感兴趣。第二,这些新移民社团与中国的互动,已经不再是将中国仅仅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故乡”,而是看做为民族国家。他们的活动范围并不会侧重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如四川省、天津市),而是从整体着眼,加强与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密切联系。这些新移民社团所举办的具体的活动主要包括文化展览、庆祝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庆祝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作为一项历史遗产的延续,新移民社团也热衷于通过完善的制度化机制来为新生代移民企业家的社会和商业活动提供服务,协助他们与中国以及其他更多的跨国群体在一个更广的领域里合作发展[39]。在这层意义上,这些社团组成了一个联结新加坡和中国的跨国网络。第三,新移民社团与传统会馆的联系比较有限,而且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诸如一些联办的典礼活动。不同的组织原则(传统会馆倾向于以“祖籍地”或本土联系为主,而新移民社团则建立在“祖国”或国家联系的原则之下)意味着他们为不同的客户和事务领域服务,他们不可能重叠。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新移民更好地整合进新加坡的社会结构中,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作为一家拥有超过200家地缘和血缘团体的联合组织,于2012年1月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华族文化中心来整合新加坡的新移民,以帮助他们融入本土社会,并且展示本土的华族文化认同[40]。
值得指出的,由于近年来新移民人口的大量和迅速涌入,新加坡民众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包括就业、交通、学校、医疗等等。出于对这一现象以及政府移民政策的关注,一些新加坡人通过不同的方式 (包括选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言论、集会等),表达其不满,强调新加坡人 (而非华人)的身份认同。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大选后也发生重要调整,提出新加坡人优先、提高移民门槛、加快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41]。现在评估这些融合的努力是否成功和有效还为时过早,不过,它们对华人跨国场域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结语
对于新加坡华人和祖籍地 (祖国)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还将继续,其互动的模式以及特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总结前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看法:
第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华人与祖籍地之间关系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推动了跨国社会场域的形成,并通过持续的互动和联系将海外华人与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的同胞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 (临时性的)与中国联系的削弱被中国作为新加坡 (老一代)华人的共同祖籍地的出现而抵消。然而,全球化和新加坡的经济地区化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之间非正式制度化联系的重建。这一重建随着流动性更强的华人新移民的到来而得到加强。这些新移民把中国视为民族国家和重新崛起的文明的观点要比他们的“故乡”情感来得强烈。正在发展的“客观事实”(中国自身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转变)和正在建构的“主观意象”(由海外华人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变化的图像)塑造了他们与祖籍地联系的新的特性。而且,新加坡和中国两个国家都在参与祖籍地的意象建构方面深思熟虑。当新加坡政府鼓励以重建与祖籍地的联系来推动它的全球商业网络和国民融合议程时,中国政府也与海外的新移民及其社团接洽,并将此作为跨国议程中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和增强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建设的重要途径[42]。
第二,通过移民的持续嵌入,流动的社会网络已经在一个以上的社会中被不断建构和重构。在联结新加坡和中国华人的跨国社会网络中,制度化联系充当着一个关键性的媒介,这些制度基于诸如地缘、方言群、次族群等内容,而中国作为一个集体想象的场所而存在。跨国性的社会网络为国家和市场提供了介于共同的族群、经济以及社会政治互动的交流空间。作为一个跨国实体,该场域也通过新闻通讯、网站和不同的文化与庆典活动等来推动关于祖籍地的理念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创造和传播。如本文引言中所分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分法不能有效地分析诸如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力量这样的新兴模式。跨国社会场域的形成和演进 (包括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之外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分析工具。
第三,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跨国社会场域的案例研究也揭示了重新思考亚洲研究固有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亚洲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全球冷战对抗的时代背景使我们对跨国力量和跨 (次)地区行为体缺乏足够的关注。通过对国家—社会交叉点的外围和地区安排的边缘的管理,跨国行为体可以在塑造国内和地区的转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揭示了跨国因素在塑造现代亚洲历史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43]。我们需要引入多样化的概念工具来解释新的现象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在这些概念体系中,对于国家机构的权威的纵向建构将被放置到横向跨国网络的宽广轨道上,以便于在公共领域和私人舞台的交互空间内发展和运作。
【注 释】
[1] Hong Liu,“An Emerging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Historicity,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2011,pp.813-832.
[2] Philip Kuhn,“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Fifty-eighth George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7;“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in Hong Liu ed.,The Chinese Oversea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vol.1,2006,pp.67-97.
[3]Peter Evans,“The Eclipse of the State?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World Politics,50,1997,pp.62 - 87;T.V.Paul,“States,Security Function,and the New Global Forces”,in Paul,Ikenberry and Hall eds.,Nation-State in Question,2003,pp.139 - 165;Linda Weiss,State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4]T.V.Paul,“States,Security Function,and the New Global Forces”,in Paul,Ikenberry and Hall eds.,Nation-State in Question,2003,pp.139 -165;John Ikenberry,“What States Can do Now”,in Paul,Ikenberry and Hall eds.,Nation-State in Question,2003,pp.350-371.
[5]Mayfair Yang ed.,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Yu Shi,“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Ethnic Media Use,Community Formation,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Activism”,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Cultural Studies,19,2005,pp.55-72.
[6]Guobin Yang,“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Media,Culture & Society,25,2003,p.484.
[7]Peggy Levitt and Nadya Jaworsky,“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3,2007,pp.129-156.
[8] Mark Rivera,Sara Soderstrom and Brian Uzzi,“Dynamics of Dyads in Social Networks:Assortative,Relational,and Proximity Mechanism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6,2010,pp.91-115.
[9]Matthew O.Jackson,“Networks and Economic Behavior”,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1,2009,pp.489 -511.
[10]参见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Hong Liu,“Singapore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Business Networks”,in Hong Liu and S.K.Wong,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Business,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1945 -1965,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4,pp.229-272.
[12]Paul Kratoska,“Singapore,Hong Kong and the End of Empi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2006,pp.1-19.
[13]Hong Liu,“Singapore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Business Networks”,in Hong Liu and S.K.Wong,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Business,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1945 -1965,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4,pp.229-272.
[14]Wang Gungwu,Don't Leave Hom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2001.
[15]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161页。
[16]Hong Liu,“Singapore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Business Networks”,in Hong Liu and S.K.Wong,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Business,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1945 -1965,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4,pp.229-272.
[17]详见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章。
[18]Shirley Hsiao-li Sun,Population Policy and Reproduction in Singapore:Making Future Citizens,London:Routledge,2012,p.13.
[19]Hong Liu,“Singapore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Business Networks”,in Hong Liu and S.K.Wong,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Business,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1945-1965,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4,pp.229-272.
[20]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1-265页。
[21]“Treasure what's uniquely S'porean - BG Yeo”,Straits Times,2004-03-26.
[22]Mette Thuno,“Reaching Out and Incorporating Chinese Overseas:The Trans-territorial Scope of the PRC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The China Quarterly,168,2001,pp.910-929;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第79-93页。
[23]Teo Siong Seng,“Message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at the 11th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WCEC)”,http://www.11thwcec.com.sg/en/01about1.0.html,October 19,2011.
[24]James Rauch and Vitor Trindade,“Ethnic Chinese in International Trad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4,2002,pp.116-130;Rosalie Tung and Henry Chung,“Diaspora and Trade Facilitation:The Case of Ethnic Chinese in Australi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7,2010,pp.371 -392.
[25]Shirley Hsiao-li Sun,Population Policy and Reproduction in Singapore:Making Future Citizens,London:Routledge,2012,pp.20-29.
[26]《吴总理:建立第一世界经济体 发展全面有活力世界级家园》,《联合早报》1999年8月23日。
[27]Rachel Chang,“Shrinking population will hurt economy,says Mr Lee”,Straits Times,2012 -02 -04.
[28]刘宏:《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9]“Chinese firms looking beyond Singapore for public listings”,Global Times,2011-02-22.
[30]谢美华:《近20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及其数量估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1]Leong Weng Kam & Teo Wan Gek,“Immigrants needed as fertility rate dips further:MM”,Straits Times,2011-01-19.
[32]刘宏:《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3]Min Zhou and Rebecca Kim,“Formation,Consolidation,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thnic Elite: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2,2001,pp.227-247.
[34]朱慧玲:《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35]Pei-te Lien,“Places of Socialization and(Sub)ethnic Identities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S:Evidence from the 2007 Chinese American Homeland Politics Survey”,Asian Ethnicity,9,2008,pp.151-170.
[36]Jessica Cheam,“Wang Quan Cheng:Chinese-Singaporean divide a'mindset issue”,Straits Times,2012-05 -19.
[37]潘星华:《“天府会”成立商会 欢迎新移民及本地人加入》,《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6日。
[38]Lee Hsien Loong,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National Day Rally 2010(English Text of Speech in Mandarin),August 29,2010,http://www.pmo.gov.sg/content/pmosite/mediacentre/speechesninterviews/primeminister/2010/August/_2010_8_29_.html,October 20,2011.
[39]Hong Liu,“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2005,pp.291-316.
[40]Rachel Chang,“Chinese clans plan centre for new citizens”,Straits Times,2012-01-25.
[41]刘宏:《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Md Mizanur Rahman and Tong Chee Kiong.,“Integr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A Transnational Inclusion Approach”,Asian Ethnicity,14,2013,pp.80-98.
[42]Hong Liu,“An Emerging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Historicity,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2011,pp.813 -832.
[43] Grant Evans,“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There are Regions,Culture Areas,and the National States: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33,2002,pp.147-162;刘宏、廖赤陽:<ネットワー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華人研究:二十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を再検討する>,『東南アジア研究』(京都大学),2006年第43卷,第四期,第346-373页;Hamashita Takeshi,China,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London:Roultledge,2008;刘宏: 《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