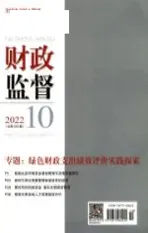睿智的学者 民生的使者——访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国贤教授
2013-09-19
●本刊记者 尹 情 杨 卡
他去过祖国最西边当支边青年,是当时财科所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许毅老前辈。学有所成,潜心学问,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我国最早洞悉绩效管理方向的学者,致力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和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为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不懈奔走献策。
他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为人谦和低调的马国贤教授。

最后一站:上海
所谓聪明,并不是说你什么都行,而是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每个人都会栽跟头,但是聪明人会总结经验。
——马国贤
记者:马老师在业界很低调,关于您的个人报道不多,主要是从专业角度解读财政领域热点。请讲讲您的经历。
马教授:我的经历非常简单。1963年在江苏无锡上的高中,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农场当支边青年,属于农业工人。1972年,我从巴楚总场调到巴楚县财政局。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计、财政相关知识基本都靠自学。当时,我对政府的运作很好奇,想知道在政府这么大的机构里资金是如何运行的。后来自己看了一些书,有一本是于光远写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之后觉得学习经济学很有意思。那时候两派武斗,但都不冲击财政局,因为财政局要管发工资。为此,我白天要上班,而且经常加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看书。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我是1980年参加的研究生考试,在财政部科研所上了三年研究生。我比较喜欢研究学问,研究生毕业后,正好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不久,缺教师,我就过去了,在那里教了五年书。后来调到浙江财经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2000年来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在这里教了12年书,上海是最后一站。
记者:从您的经历来看,读书改变了命运。考研对于您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马教授:说起来,参加考研很偶然。1980年我因公负伤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看报纸,有一个广告吸引了我:财政部科研所招收研究生。当时想也没多想,觉得自己学了不少知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报名试试。能考多少分完全没谱,当作是考着玩,看看自己的水平。当然,报了名之后观念就不一样了,既然要考,就不能考得不好太丢人,于是开始正儿八经地准备考试。
当时主要考英语、政治和财政学三门课,没有教材,也没有指定书籍,主要靠自身积累。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书都翻出来看,由于县城里没有考场,南疆考生统一在喀什市考试。考完之后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一点劲都没有,三公里路程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老乡家里喝了点稀饭,住了一晚,才坐他的车回去。最后考试结果出来总体还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那年财科所财政学专业在全国的招生人数是5名,我是其中一个。当时的财科所所长许毅老前辈说,这个学生这么远,考得还可以,英语差点可以再学,算是破格录取了。许老后来就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现在想想,考上研究生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记者:工作了15年之后,又重拾课本,从新疆转到北京继续学习。在财政部财科所学习期间,面临哪些困难?
马教授:我在财科所读研时已经35岁了,在所有研究生里面年龄是最大的,压力非常大。英语一直是我的软肋,我的基础太差,记忆力也不好,当时一起进来的年轻人学习很快。为了补上英语这门课,毕业后我跟另一名研究生一起翻译了一本英国的《税收经济学》,获得了中国税务学会的二等奖,这是最早的税收译著。
在财科所学习的三年,是我对财政学知识全面系统学习的开始。财科所的老师很好,讲稿都非常具体,那时没有教材,主要靠老师讲。课余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因为之前在财政局工作过,财政学知识学起来相对容易些。我们是1980年初招进去的,9月份才开学,在北京读了一年之后转到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财经学院)学习了一年,财大的学习比较规范。在财科所,除了本所的老师授课外,还邀请了人大等著名教授,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学习专业知识。
记者:从江苏到新疆,再从新疆到北京、江西、浙江、上海,这么多年辗转于祖国东西部之间,您有什么感悟?
马教授:去了这么多城市,但是教师的身份是不变的,到哪里都是讲课、做研究,只不过换了地方,办公桌搬了个家而已。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已经退休两年了,博士生的论文还是认认真真指导,与他们讨论,提出修改建议。相对而言,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研究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包括国际性问题,接触的知识更加广阔,视野也相对宽广。这也是我最后选择留在上海的原因。2012年8月,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了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我是高级研究员,帮他们做一些课题。
“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一个家庭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国家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马国贤

记者:2006年,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成立,您作为中心主任,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绩效研究的学者。起初怎么想到做绩效研究?
马教授:1993年,美国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1997年我看到这个法案,预感到它将是中国政府管理的改革方向,于是就开始研究它。2005年,我编著出版了《政府绩效管理》,这本书从研究政府管理和财政管理的原理开始,收集了我在2003年以来开展绩效研究的相关案例,并介绍了绩效评价方法。它在财政部第一届许毅财经科学基金评审时,获得一等奖。
我是从2003年开始参与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当时全国义务教育矛盾非常大,财政政策不清晰,中央财政收入有限,地方政府不愿出钱。为此,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课题做调查并形成方案。从2003年到2005年期间,我们一直在做这项调查,河南、安徽两个省基本都跑遍了,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甘肃,特别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调查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路径,将教育经费分为三个部分:教师工资、公用经费、建设和修缮费。提出的基本观点为:义务教育应该是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可以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缺钱的问题。对于教师工资,由于农村教师也涉及乡镇干部工资,因而这个问题应该由地方政府解决,而财力上困难的县,应通过一般转移支付来解决,以保证教师工资高于公务员工资(至少账面上是这样)。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公用经费,这也是办学最困难的。我们提出了按生均标准,也就是按在校的每个学生标准来计算和拨付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款。这有四点好处:一是与学校的支出匹配,也容易计算;二是通过国家确立最低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县给予转移支付,有利于实现最低公平的均等化目标;三是随着财政收入增长,标准逐年提高;四是对不同财力水平的省,中央与省可以按不同比例分担,以发挥省级政府的作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生均标准的最低公平”的概念。就是说,国家保障最低标准,地方若要做得更好,可以超过这个标准,但要自己掏钱。对于教育危房,我们建议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承担,县里也出一点。这项政策为国家采用,并沿用到现在。现在看来,这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政策。
记者:这实际上解决了义务教育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问题,理清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您正式开展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马教授:在我看来,在解决义务教育财政投入问题之后,下一步就是提高教育质量,办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什么叫“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这就要通过绩效评价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是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拿了钱而没有用于义务教育上。这是我们开展义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的理由,它得到了财政部和教育部的支持。
我们首先从西部找一些地区摸底,调查学校的管理现状。跑了几个地方之后,确定在宁夏的银川市开展调查。由于该市周边县比较贫困,教育管理比较薄弱,假如这套义务教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在这里行得通,那么全国其他省市也就能做到。在宁夏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我们确定了一套基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毛入学率、教育质量、家长和教师满意度、实验室配备、图书馆等标准。指标建立起来之后,2005年财政部在全国选了4个地区开展试点:江苏无锡、河南郑州、宁夏银川和甘肃庄浪县。围绕这些指标对4个试点地区进行评价,反映出他们在资金投入、教育管理、教育质量上差异很大。这项试点不仅使大家认识到绩效评价的价值,也弥补了我国在引入绩效的理念后在政策实践上的不足。通过绩效评价试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城市教师严重超编,而农村教师短缺;同时,经费管理上也存在着问题。这项研究成为财政部、教育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记者:前面讲的这些是2006年之前开展的研究,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在教育支出绩效研究方面又有哪些成果?
马教授:中心成立以后,我们评价了国家的一些重大专项,也在各省做了一些项目,比如福建、河北、江苏等省开展的义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通过近年来持续推进教育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各部门对义务教育的责任心增强了,财政投入的钱也增加了。对孩子们来说,教育不光是要让他们读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读好书,学到东西。我有一句话:一个家庭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家庭的未来;一个国家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如果能让全国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80年代末期,浙江与湖北等省的财政收入差异不大,发展水平也基本差不多。但二十年后,两者的经济发展差异非常明显,财政差距一下拉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浙江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尤其是基础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因而农民的素质比较高。这是潜在因素,改革开放使能量释放出来了,在大家还不理解时,他们就能敏锐地洞察市场前景,率先办起了工厂。老百姓主动要求致富,而不是靠政府。这说明了教育跟未来发展的关系,希望在孩子们身上。
记者:您在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方面做出的成果,对其他领域开展绩效研究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除了在教育领域开展绩效研究,有没有向其他方向扩展?
马教授:我们不仅做了义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还做了高等教育支出绩效和继续教育支出绩效研究,这些都是前几年开展的国家重点课题。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做卫生支出绩效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卫生医疗上投入了很多钱,如何用好这笔钱是关键。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卫生院。政府往往攀比投入,认为投入越多,机构越庞大,配备标准越高,政绩就越大,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卫生支出绩效评价既要求卫生院配置达标,也要求统计他们的看病工作量,即有效公共服务,包括医务人员的人均服务的工作量,以及服务质量,并综合评价每个卫生院的绩效,平均计算出县市的卫生支出绩效。这样的评价有利于防止机构的官僚化,促进卫生院搞好管理,发挥自身优势,增进为病人服务的质量。这个项目最早是在江苏省开始的,通过对全省的卫生院进行绩效评价,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我们往往将乡镇都建设卫生院视为政绩,但有些卫生院没有人去看病,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往往这样,于是我们建议撤消这些卫生院,将钱用于办好边远乡镇的卫生院。同时,它也促使卫生院通过开设家庭病床等服务项目来增加工作量。
记者:您持续做了这么多年调查研究,跑遍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开展绩效评价有哪些结论和感受?
马教授:通过近十年来的调查,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结论:一是农村教育投入比较低,中央政策没有落实到位;二是教师工资问题很大,农村干部和教师工资问题都比较大;三是普遍存在教育质量不高,大多数学校只重视语文、数学,不重视外语,特别是农村地区英语学习很差;四是教育基础设备配置不足,包括初中、高中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以及图书馆等。这些基础配备不够,设备使用也不足,该做的实验没有做。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向财政部反映了,并且提出了解决对策。
我的感悟是:国家应该在教育上多花一点钱。2003年冬天,我们到河南省去调查时,当时学生住的地方条件真差,宿舍的门关不住,窗户没有玻璃,用砖头堵起来的。宿舍没有热水,要学生自己去打水。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就这种学习环境。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向财政部领导反映说,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这种条件,是因为国家穷。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富裕了,我们有条件让学生们过得好些。我的理解是,无论国家如何困难,也要筹钱搞好义务教育,这是能够做好的。
另一个感悟是绩效管理很重要,全世界政府都重视它,是因为它包含着政府科学管理的因素。比如,十八大指出,腐败问题治理不好将亡党亡国。而腐败的核心是两点:一是人事腐败,二是财政失察。它表现为财政无效率。如果我们抓住了绩效,就会将制度中的问题揭示出来。又如,我国的法律、机构并不比西方少,而且看起来都很忙碌,但政府运行得不好,许多事没人管,官僚主义、腐败、浪费三大难题始终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大家忙于做事,而没有绩效观念,因而工作效果相互抵消,剩下的有效公共服务不多。再如,绩效管理提出的以有效公共服务来评价政府职能,就颠覆了“只要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事就好,有没有效果无所谓”的行政观念。绩效管理的核心是“一观三论”,也就是花钱买服务、买效果的预算观,公共委托代理理论、结果导向管理理论和为“顾客”服务理论。这些既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观念,也是转变我国政府行政的关键。总之,在我看来,绩效管理将是21世纪我国政府建设和科学发展的关键。
然而,绩效管理能不能搞好,不只靠领导重视,更需要科学方法。只有按照科学方法建立的绩效指标和标准,才能真实地评价出各项支出业绩,起到促进管理的作用,而目前在这方面,财政还做得不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建设绩效指标库,十分必要。
改革也是一种“试错”
目前,国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很多,矛盾也很多。改革者要有恒心,要运用方法。宁可走慢一点,想清楚了再做比匆匆忙忙开始要好。
——马国贤
记者: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您写文章深入浅出,擅长用浅显的语言道明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对于财政监督,您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呢?
马教授:其实,研究财政监督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监督的原理,这是一个薄弱环节。无论是财政监督,还是人大监督、审计监督、人事监察等,都存在着为什么要监督,监督有什么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监督事与监督人等关系的研究,这些是必须弄清楚的。我认为:一是财政监督有独立性,为此支持他们设局,以减少行政干扰,独立发挥作用;二是监督有自身规律,应当研究监督的原理和方法,厘清这些,才能按规律办事;三是科学监督是必然,所谓科学监督,也就是全面发挥纠偏、威慑、促进三大作用的监督。说到这里,我要讲两个故事。
我在贵刊《新年展望:坚持科学监督的正确方向》一文中曾经讲到一个故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经研究过为什么在非洲草原上,羚羊与猎豹都是跑得最快的动物。经过研究他发现,羚羊跑得快是因为猎豹要吃羚羊,猎豹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跑得慢的羚羊了吃掉了,剩下的是强壮的、跑得快的羚羊。而猎豹跑得快是因为羚羊,那些老弱病残跑得慢的猎豹,因为抓不到羚羊而饿死了,剩下的当然是最好的。竞争的结果是,虽然这两种动物都跑得快了,但猎豹的速度始终略慢于羚羊。在这个故事中,若是没有了猎豹,羚羊就没有了天敌,会过度发展,遍布非洲草原,个体也会弱不禁风,传染病蔓延。可见,猎豹是推动羚羊种群发展的动力。
这是自然界的“共生现象”,实际上财政监督也有“共生现象”。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犹如羚羊与猎豹,如果财政监督是“实质性监督”,也就是“吃羚羊的猎豹式”监督,而不是像花瓶一样,充当“形式”而不起作用,那么,它才能成为公共资金的“看护者和守护神”。“实质性监督”只会清除官僚机构中的腐败者,并不会阻碍政府依法行政和改革。这与猎豹只会吃掉老弱病残的羚羊是一样的道理。
另一个是古希腊的历史故事:达摩克利斯之剑。相传,西西里国王有一个朋友叫达摩克利斯,他经常埋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而国王多么富有。为此,国王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招待他。达摩克利斯在吃饭时,抬头看到自己座位正上方有一把用马鬃倒悬着的锋利长剑,眼看就要掉到自己头上,吓得离席而逃。这则故事讲的是威慑作用。威慑能用低的成本去阻止某些人的行为。财政监督应当发挥威慑作用,使觊觎者不敢去做。但是,它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财政监督必须是实质性监督,而不是走形式,“监而不督”。也就是真的有柄锋利无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是监督信息应当公开,使达摩克利斯看到剑就悬于头顶。若是剑锁在国王箱子里,就起不到威慑作用。这一故事说明,实质性监督和信息公开是搞好财政监督的关键。
记者:虽然您现在退休了,却一直在进行学术研究。平时除了做研究,还有其他的什么业余活动和爱好?
马教授: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平时就看看书,锻炼身体。我想做的事有三件:一是研究预算绩效评价,建一个绩效指标库,把绩效评价引向科学,这也是英国等国家做的;二是写一本财政监督的书,对监督的原理和方法做一系统研究,告诉大家怎样才是科学监督;三是写一本关于王安石的书。王安石是北宋的改革家,文学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在历史上很有争议,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坏。林语堂把王安石说得一无是处,而康有为、梁启超却为他“平反”。我想写一本通俗的小说,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王安石。
王安石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却非常马虎。有一次别人请他吃饭,在他前面放了一盘鹿肉,他就把这盘肉吃完了,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大家在猜,王安石是不是喜欢吃鹿肉。有人说不对,于是第二天就把一大盘青菜放到他面前,把鹿肉推到一边。他只把青菜吃完了,却不知道还有其他菜。从这点可以看出王安石在生活上是很马虎的。
但是他在政府改革上却全然不同,当时北宋的财政问题很大,国家到了崩溃边缘,士大夫尊古训,不思改革,怕担风险。王安石却不同,一心想拯救这个国家。他在鄞县当县令时,为解决水利问题,进行了一个月调查,有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有时住寺庙,甚至荒野。他做地方官时政声很好,经欧阳修等推荐,仁宗皇帝三次调他做京官,他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神宗时才奉诏。主要是朝廷保守势力太强大,怕做不出名堂。
我想通过他的故事说明一点:改革是不完美的,是有风险的,但是社会也只有在改革中前进,否则国家就会衰败。这是千古道理。
记者:现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如火如荼。从王安石这个改革者身上,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马老师: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国家的问题很多,矛盾也在深化,改革才能渡过困难期。在改革上我有两点想法:第一,改革者一定要有恒心;第二,改革要注意方法。王安石的失败是在方法上过快过急,致使“煮夹生饭”。我的理解是,改革宁可走慢一点,想清楚了再做,要比匆匆忙忙做好。
实际上,王安石改革对我们的指导性很强。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所谓聪明,并不是说你什么都行,而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每个人都会栽跟头,但是聪明人会总结经验。社会改革也是一样,很多错误都不可避免。实际上,改革也是“试错”。现行制度、体制和机制不行的,就得改革,通过改革寻找出路,而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栽跟头,停滞不前。这也是我学习十八大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