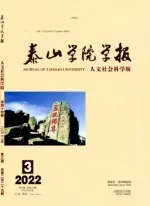论鲁迅的文学选择及其本质特征
2013-08-15靳新来
靳新来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鲁迅的文学观是丰富和充满矛盾的,他曾经一度非常看重文学的审美特性,认为它并不涉及国家的兴衰存亡,也和个人的利益得失相离。他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视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1]这一观点与王国维关于“纯文学”、美之“独立价值”、美之“第二形式”等观点遥相呼应,两相合拍。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开始呼应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儒家美学的单向社会功利要求中挣脱出来而纳入现代性的审美要素。但同时鲁迅又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他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增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这种作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2]。后来他又进一步将文学看作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立志要利用文学来改变国民精神。而且愈到后来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愈在鲁迅思想中占居上风。一直到1930年代,鲁迅还这样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4]鲁迅的这种文学选择绝对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是体现并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历史选择。关于鲁迅文学选择意义和价值,也只有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也才能够获得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从近代开始的中国文学的变革是与中国消除亡国危机、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必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学承担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文化变革的历史使命。蔡元培就曾经指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5]当然仅仅把文学视作思想“传导”的工具,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独立性,这确实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就当时中国文化的情形而言,首先在文学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排斥科学的伦理文化,而规定其形式规则及其特点的主要是文学。要破除旧文化的形式结构,则文学上的突破无疑应是首选。蔡元培在当时不过是指明了这样一个特定的事实。将文学看作传导思想的工具,并进而呼唤与新思想相适应的话语形式的变革,固然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传统在新形势下的高度发扬与延伸,从根本上说则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融入全球化浪潮的表征,因为正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将一直封闭自足的中国文学抛入了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使其固有的价值标准、美学旨趣、艺术形式同新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刺激了文学自身的调节机制,推动中国文学走上了变革的道路。鲁迅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持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以文学为利器来改造国民性、建构“立人”的思想体系,可以说顺应了文化变革转型时期历史的要求,也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众所周知,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的,这是鲁迅独特的人生选择,却也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方面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梁启超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鲁迅对中国变革方向的认识也经历了由器物到文化的渐进过程:他接触西学,最早是路矿,后来是医学,都属于现代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立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具有不证自明的现代性,不仅能够富国强兵,还有助于“维新的信仰”。这种对科学的尊崇态度在《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中有充分表现。但鲁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深入下去,由科学而及人,其中的《科学史教篇》指出:“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指出人类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皆在于“致人性于全”。当然,在这里他并没有对为什么要“致人性于全”进行深入的逻辑论证,这一过程在其后的《文化偏至论》中得以完成,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由“物质”而入“精神”,由“科技”而入“人性”,鲁迅完成了思想的升华。但鲁迅并不是要放弃科学,而是在深刻认识科学局限性基础之上,将疗救愚弱国民的重心锁定在精神层面。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6]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弃医从文,不单纯是顺应时代要求对社会使命的承担,更来自于他的内在生命自觉,是他听从内心召唤、回归自我的必然结果。从小培养起来的对于文学艺术的兴趣爱好、内在的文学气质,决定了鲁迅属于文学、文学也属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不在于鲁迅选择了文学,而在于他回到了自己;不在于他从此开始了自己作为思想启蒙者的一生,而在于他首先完成了一种自我启蒙,明确表达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学态度。可以说,鲁迅选择文学既呼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又遵从了自己的内心需要。
鲁迅从事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开始的。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绍介,在翻译,而尤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7]这正好也说明了他从事翻译有着明确的文化目的和选择意向。对此,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有更清楚的阐述:“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国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8]鲁迅是想通过自己的译笔,让自己的同胞从“同一样命运”的异邦民族那里,汲取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彼此建立起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最初的辛劳凝结为两册《域外小说集》,于1909年印行,其中他亲自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从“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出发,鲁迅高度赞赏19 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9]所以,“五四”以后,他将翻译的重点集中于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翻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契诃夫的《坏孩子与别的奇闻》、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爱罗先珂的《童话集》、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论艺术》、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除了苏俄以外,鲁迅文学翻译涉及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十余个国家,作品类型丰富多样,主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这些译作总计达300余万字,直与他的文学创作等量齐观,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长达30 余年的翻译生涯中,不管是选择什么国家的作家,也不管是选择什么体裁的作品,鲁迅都是从现实斗争需求出发,怀着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奴隶的目的,企望通过翻译的作品以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激发他们奋起反抗的意识。鲁迅曾经明确表示,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10]。他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看作是“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贴泻药”,用以狙击“中国的病痛的要害”[11]。可见,作为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一翼,外国文学的译介承担了传播文化火种、转移国民性情,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为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鲁迅认为翻译还有一个实际功用,那就是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示范与借鉴,他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12]鲁迅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读了百余篇外国小说基础上尝试进行的。鲁迅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与文学翻译一样,文学创作在鲁迅那里也是有着“为人生”的明确目的的。当初弃医从文的初衷就在于痛感国民精神的病态,而立志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一直到1930年代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他还这样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3]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小说形成了独特的视角:“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4]因此,对于国民精神状态的关注也就成了鲁迅小说关注的焦点。他重点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其中也包括孔乙己一类滑落于社会底层中的落魄文人。鲁迅也像其他作家一样关心他们的物质贫困,但他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精神困境,从中发现精神解放的重大意义。《药》中的华老栓救子心切,却把人血馒头当作良方妙药;在《故乡》里,闰土辛苦得近于麻木,却将自己命运寄希望于毫无意义的香炉与烛台;《祝福》中的祥林嫂行动上不服命运而抗争,思想上却也恪守传统礼教。她抗婚只是想做一个节妇,而捐门槛也只是出于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精神恐怖。《离婚》中的爱姑大胆泼辣,敢骂敢斗,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知书识理”的七大人身上……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将中国人精神的千疮百孔揭示得触目惊心。最能充分体现鲁迅小说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即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 正传》。鲁迅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 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 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回避的态度,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阿Q 形象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阿Q 形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民的魂灵”已经愚昧、麻木到何等可怖的境地,思想精神上的启蒙主义革命在现代中国是迫切而不可或缺的。而充当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在鲁迅笔下他们一个个陷入精神的迷途和困境而不能自拔。《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曾经血气方刚,热心改革,十年下来却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尽是认真地干一些十分无益无聊的事,借以填补空虚的心灵。《孤独者》里魏连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向着他身受的一切进行无情的复仇。“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样的告白饱含着他多么深重的心灵创伤。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曾经面对旧道德的阻挠高歌猛进,却经不起小家庭灰色生活的淘蚀而日渐破碎,退回旧家庭的子君在无爱的人间凄惨死去。这些人物本来是承担启蒙的改革者,却带着累累的精神创伤在现实的荒原中一个个死灭。在这些无路可走的梦醒者身上鲁迅看到了启蒙者的悲剧命运,看到了置身于荒原的孤独。鲁迅的这些描写,不是旁观,也不是俯瞰,而是渗透着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一种自审,是鲁迅拷问灵魂之深的极致。如果说这在小说中还包裹着一层社会主题的外壳,那么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则表现为直抵心灵深处的开掘突进。
《野草》虽薄,内容却是厚重和复杂的,其中最为特别和重要的则是作者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无情拷问。作为独战多数的战士,鲁迅经过痛苦反思深刻体验到一种生存的困境,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为“两难”的整体结构:《影的告别》中的影子是沉没于黑暗还是走向光明?《墓碣文》的“我”面对追问是回答还是离开?《死火》中的火是冻灭还是燃烧?《过客》的“我”是走还是停?……这些都是鲁迅精神苦闷、彷徨的真实表现。鲁迅逼视自我灵魂,拷问出灵魂里的“鬼气和毒气”。可以说《野草》是鲁迅给自己设置的一座心灵炼狱,它锻铸了鲁迅的心灵的诗,也催生出鲁迅独特的生命哲学: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都会使影子消失,无论是冻灭还是燃烧结局都是死亡,无论怎样走下去前方都是坟……“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3]——这就是鲁迅对世界的认识,然而他依然希望通过对“行动”的选择改变世界“虚无”的事实。他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4]这就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从《野草》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变革中的精神苦痛和心灵律动。
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随感录”命名的最早的鲁迅杂文,本来就是新文化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表明鲁迅一如既往秉持“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从开始杂文写作起,他就将这一文体与“五四”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在鲁迅那里有相当自觉的认识,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15]而他认为:“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16]鲁迅充分发挥杂文这一新型文体的优长,投身“五四”启蒙运动,对旧传统、旧文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也构成了鲁迅前期杂文的思想内容。鲁迅在上海十年几乎倾注全力投入杂文创作,看重的仍是这一文体“匕首”、“投枪”的战斗功用,文化战士的本色可谓有增无减。这一时期杂文增加了不少政治色彩,社会内容也更加广泛,而笔锋所向,尤其集矢于落后腐败的政治在社会各个领域对广大民众施行的精神奴役与愚弄。鲁迅将社会百态万象笼挫于笔端,却不止于就事论事,而是尽量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入手,挖掘现实社会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的精神根源,这样就把一般的政治评论转换和提升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在杂文写作后期那样一种“切迫的”、“不从容”的时代,鲁迅洞穿纷繁世事的表象,依然如故地关注国民大众的灵魂,进行冷峻而深刻的文化批判,所以他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17]
鲁迅感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文学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从翻译到创作,从小说到杂文,30 多年如一日始终守持“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不动摇。鲁迅的确十分重视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但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中都突破了附属于政治社会需要的“实用”层面,而是特别关注人的生命状态,探究灵魂的奥秘,传达自我生命体验,因而具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始于近代的文学变革并不是文学自身产生,而是政治变革带动的结果,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文学也一直依附于政治,这成为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这样的文学自有其历史合理性,却不得不付出审美价值失落的代价。多少文学作品就像随着流水飘转的浮萍,虽鲜光一时却最终风吹雨打去。而鲁迅的文学因为根植于中国大地,连通着中国人的精神血脉,经过数十年历史潮流的淘洗更加焕发出其蓬勃生命力。
[1][2]鲁迅.坟·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书信·331220 致徐懋庸[A].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A].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 集)[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6]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13][1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鲁迅.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坟·杂忆[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鲁迅.译文序跋集·《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A].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鲁迅.两地书·四[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鲁迅.书信·250411 致赵其文[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华盖集·题记[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鲁迅.两地书·三二[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准风月谈·后记[A].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