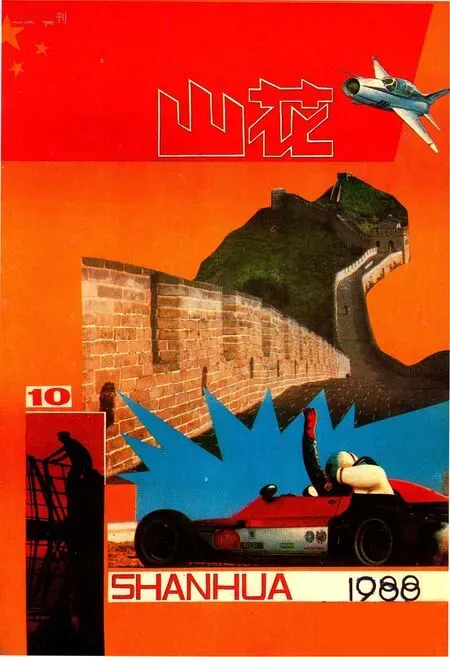浓缩的叙事:论方方小说中“标示”符号
2013-08-15刘碧珍
刘碧珍
真正的文学艺术品都应该被看作一个为某种特别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和符号结构。而且按照韦勒克的观点,文学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对于这样关键性的文字符号,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中提出“标示”这一概念。他认为:叙述叙事作品的作者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听懂”故事,会在文本中设置各种标示,以引导读者按既定意图把握。因而标示可定义为文本中出现的起“标志”、“显示”等作用的叙述手段。同时,他还进一步给标示分类:题旨标示与人物标示,他认为“前者提示创作动机、作品宗旨和主题思想等,后者或隐或现地透露人物的人格特征。”可见叙事文本中的标示符号可以起到帮助叙述,促进作者与读者交流的作用,是浓缩的叙事。
卡勒认为文学既是文化的杂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叙事过程本身也是作者带着自身的情感从事的写作活动,包含着其审美趣味和价值体验,是一种与文字和潜在的读者交流和抒发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过程。所以,作者在叙述中运用标示可以使叙事文本有双层意蕴,既让读者的注意力关注形式表面的修辞魅力,又引导他们投向内容层次,关注文化意蕴。
方方是当代文坛富有个性的一位女作家,熟知叙事就是一种交流,其本身就会预设两个参与者:发出者与接收者以及二者所包含的隐含作者、叙述者、隐含读者和受述者等。所以她能成功地处理隐含的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与读者的关系,并巧妙控制这几组关系之间的距离。她通过有效的技巧“说服”读者接受其观点和立场,影响读者的思想行为。标示在方方的小说中运用得非常普遍。例如《乌泥湖年谱》、“三白”系列、《看不见的地平线》、《桃花灿烂》、《风景》、《夏天过去了》等。它们通常是以隐喻式的标题、象征性的意象、哲理化的题记形式出现。或者揭示主题,或者显示人物命运,或者揭露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引导读者阅读文本,与作者对话,并在无形中接受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
以隐喻式的标题作为标示
标题往往包含着文本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常以隐喻的语言通过标题形式把文本隐含的信息传达给读者。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符号标记组成的巨大网络。语言作为符号的价值与语言的复制功能是重叠在一起的。隐喻采取了以人拟物,以物拟人的手段,避免直接地并列受喻者和施喻者,而以词语间非逻辑或超逻辑的方式,使两个存在系统互相干涉而发生意义的变化,并加入感情色彩和道德判断,从而产生多义性的联想,打通了世俗人间、神话、动植物世界的界限,达到“不喻而喻”的效果。方方的生活与武汉这块土地紧密相连。她在《方方:行云流水的武汉》中描述武汉的地理与文化,并表达自己对武汉的热爱。因而武汉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会无形中成为她小说中的意象来源。
小说《江那一岸》和《看不见的地平线》以“岸”和“地平线”为题,文中多次出现“江那一岸”与“地平线”这些意象,它是故事中的地理空间,也是故事发展的线索。“岸”与“地平线”都是理想与浪漫的写照,同时又标示着一种视线之外且无法靠近的虚幻。如短篇小说《江那一岸》,在女搬运工的想象中“江那一岸”是一派花红柳绿的景象,因此她一直渴望到江那一岸去。而当她真正到达江那一岸,发现其实不过如此,一如她所生活的彼岸,同样是布满纸屑、瓜子壳与果皮的泥泞小道,于是她有些后悔当初的行为。再如《看不见的地平线》讲述几位待业青年:蛮子、“我”、豆豆想去草原看地平线,不顾其他朋友的劝说,并为此付出努力。但当他们找到工作,忙碌起来之后,又都认为“地平线”是与己无关,玄而又玄的东西。同样《夏天过去了》也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夏天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又喻指人生的风华正茂期。可见,在此类作品中,题旨标示着人们心中对理想的追求,充满着青春时代的激情与豪迈,但在现实面前理想逐渐变为幻灭与空虚的写照。
《风中黄叶》和“三白”小说系列(《白驹》、《白雾》和《白梦》)也运用了隐喻性的题旨标示。隐喻性的题目传达出文中人物命运漂泊不定、精神世界无所依托的悲凉气氛,以及普通人面对厚重而又虚幻人生产生的无奈情绪。“风中黄叶”隐含萧瑟、凋零之感。而“白”、“黄”两种颜色更加重悲凉氛围。因为,白色与黄色本身就蕴含衰败的人生景象。可见,作者用特定的文化符号作为小说标示来揭示她的创作主旨和复杂情感。如小说《白驹》中没有一位作者予以赞扬的人物。小说情节围绕“小男之死”展开,令人惊异的是朋友家人对小男的死没有丝毫悲伤,叙述者——“我”调查死因,也只是出于记者职业的猎奇之心。人的生命异常脆弱。人们对生命价值应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小男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生命被轻视,即便在他的亲朋处也得不到任何爱怜之情,充分地暴露出在快节奏的世俗社会中人情的日益淡薄。《风中黄叶》中主人公黄苏子长得非常漂亮,大学毕业后还拥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在中学时,身为高中教师的父亲曾经粗暴残忍地处理了男生给她写情书的事件,黄苏子心灵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外在的成功也抚平不了她内心的悲凉。黄苏子因人格扭曲过起了白天是白领夜间为暗娼的生活,最终惨死。黄叶的“黄”一方面指向苏子及其父亲的姓氏,另一方面也暗示出黄苏子的生活状态。而父亲圆滑世故的作风和社会世俗气息则加速了黄苏子的死亡。
以象征性的意象作为标示
方方除了使用隐喻式的标题作为题旨标示,象征性的意象也是作者刻意安排用来提示主要人物命运或者故事走势的标示。意象的运用,可以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它是中国人对叙事学与诗学联姻所做出的贡献。它在叙事作品中的存在,往往成为行文的诗意浓郁和圆润光泽的突出标志。它作为文眼,具有凝聚意义、贯穿叙事结构的作用;还具有保存审美意味、强化作品的耐读性的功能。例如《桃花灿烂》、《何处是我家园》。
《桃花灿烂》题目就已是标示,取名来源于《诗经》中“桃之夭夭,其华灼灼”。小说中提到一片桃林,每当春暖花开之时桃花灿烂,引起人物的无限遐想,也象征着青春、爱情与生命。故事中粞与三个女人因为欲望、爱情与工作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可惜却由于无尽的欲望都无果而终。另外,粞这个名字也已经预示了人物最终的命运。作者为了让读者明白她的用意,在故事中提到了两次。“粞”的字义是碎米,多用来做牲口的饲料。故事中提到在粞死了之后,骨灰撒入江中被鱼虾吞噬。叙述者借星子之口又有这样一段议论:“在此之前,又是谁一口一口地吃着他呢?是生活本身,还是他自己?或是他们相互联系?再不,是人类这一类生命未曾进化得完美而自携的弱点一直细细地咀嚼着他?”这段文字无疑表明了作者对故事人物性格的关注,她用“粞”这样的名字象征性地揭示出人在无限地追求之后终究要回归本真的现实。所以桃花灿烂绚烂一时,正如人生的顶峰不可一世,但对于个体而言,最终都会曲终人散,这是生活的本真,亦是社会普遍的规律。
《何处是我家园》讲述一个叫秋月的女人的悲剧一生。文中多次出现“风筝”这一意象,秋月的命运随着风筝的出现而改变,而且她的命运也如风筝一样漂泊不定,孤苦无依,没有归宿。叙述者明确告诉我们:“她想自从那一天,那是哪一天呢?她看到了那只风筝,她的命运就如这只风筝一样只有沉浮之空间而没有归宿之陆地。”而且小说取个哲学意味的名字“何处是我家”就带有作者试图探讨人生的用意,秋月的名字也同时寓意着人物一生悲苦、清冷的结局。秋月命运的几次改变中都出现了风筝,所以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在结束故事时,借秋月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晓得我是从哪里出发的,最后还要到哪里去。”可见作者想告诉我们,普通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的无助。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作者、叙述者以及故事中人物的悲凉无奈的心态。
以哲理性的题记作为标示
题记也通常是文本中很重要的部分。作者煞费苦心,安排了一些哲理性的词句,既为故事确立了一个基调,又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暗示。如《落日》题记引用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风景》开篇引用了波特莱尔的话“……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的世界……”这些标示的话语含蓄地告诉了读者:叙述者将要讲述的是一个人性蜕变与伦理失范的故事。“家”在许多人的心中都应是爱的港湾,是充满温暖、弥漫温情的地方。《风景》中却通过小八子冷静地观察并叙述了二十年来他的父母在汉口贫民区河南棚子的一间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抚养七男二女,一家人打骂嘶咬、互相诅咒,彼此伤害的过程。《落日》中的家庭关系更令人啧舌:丁老太含辛茹苦抚养了两个儿子,带大了孙女,晚年却成为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阻碍,被活活送进了殡仪馆。而且本应悲伤地送祖母归乡的旅途却成为一家人难得的一次郊游。家的温馨在此两部作品中早已荡然无存,留下只是人人互为工具,互相利用的残忍。在小说《风中黄叶》开篇就引用一段摘自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文字作为题记“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足音在记忆中回响/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通往我们不曾打开的那扇门/进入玫瑰日中。”结尾再次引用“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燃尽的玫瑰留下的一切的灰。悬在半空中的尘土/标志着一个故事的终结之处。”正如小说所讲述的黄苏子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孩,她的名字和生长的环境就暗示她的命运,她的开始就是她的结束。所以这篇小说还有一个名字叫《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再如,作者在《乌泥湖年谱》每一章节前面都安排了一组诗句,如曹操的《短歌行》、张养浩的《山坡羊》、范仲淹的《苏幕遮》等,借诗词传达了叙述者讲述不同时段故事的感情基调以及主人公经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同时也为整个作品增添了某种故事外的意义,增加了故事内涵的参数值。如1957年,主人公丁子恒与同事正在为修建三峡工程而激情满怀时,政治运动的苗头就已悄悄出现。这一章的题记就是傅玄的《云歌》“白云飘飘舍我高翔,青云徘徊为我愁肠。”第二章,政治运动正式开展,科学工作者为三峡工程的修建忧心忡忡,此时题记就变为李元膺的《洞仙歌》“百紫千红花飞乱,已失春风一半。”最后一章,1966年,主人公及故事中人们都饱尝政治运动之苦,尽管都有满腹才学和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因此这时作者设计的题记为《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衰”。 可见,哲理性的词句既为故事确立了一个基调,又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暗示。
可见,叙述中所使用的技巧和手段都是为了交流服务的。总之,标示可以是一个意象,也可以是一句话或一段文字,它关系着叙述者意图的表达,是一种“浓缩”了的叙事。因而,它会出现在文本中引人注目的地方。作者费尽心机地设计它,目的就是促进读者阅读的兴趣,更好地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本论文是江西省2012年社科规划课题《叙事学泛化现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8.
[2]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157.
[3]乔纳森·卡勒著.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3.
[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