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毁灭与希冀——读解安勇小说
2013-10-20张春梅
张春梅↓
“你想躲,却无处可躲,只能眼睁睁硬挺着。他已经来到你的身边,发出恐怖的笑声,两只巨大的巴掌把你夹住,一点一点,慢慢地压扁。……你失去知觉了,你没有意识了,你感觉自己死了。你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像条死狗躺在地上,被他拖着往前走。”
——《一九八五:性也》
上面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有酷刑加身的感觉,只不过这里的“身”却是“精神”。这种精神受刑、人性被挤压直至甘愿处在“死亡”的状态,在作家安勇笔下几乎可以说是一条暗流。穿越这条暗流,“人”怎样从“个人”被规训和惩戒成为“类人”,摆出的“死狗”架势是否意味着被挤压成饼的“个人”已经失去“爱”与“美”的能力,人要怎样才能从“死了”发现生的希望,所有这些精神的图谱,是安勇在简约而不失反讽的叙述中反复讨论的地点。他有代表性的几部作品:《蚂蚁戏》、《青苔》、《软肋》、《一九八五:性也》、《钟点房》,向读者展示了残酷的成长历程,并带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严肃的怀疑精神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现今的文学创作中是稀少的,弥足珍贵。
读解安勇的小说,要从他有意选择的不可靠的叙事者开始。《蚂蚁戏》是这样开篇的:“那年冬天,知青们浩浩荡荡开进村子里时,我正胯下骑着一根木棍,驰骋在村中的土路上。”这个开头很有意思,历史的表征与民间话语合而为一。我们看到,作为观看者和叙事者的“我”从一出场就并不比一般人的智力和眼界高。而《一九八五:性也》这样开了头:“一九八五年,我十四岁,还是个啥事都不懂的混小子”。类似的,《青苔》中的女人莫丽雅因为社会位置的不稳固始终处在患得患失之间,“心里乱糟糟的”;《软肋》里的小伙子们统统参加到了冲动的情场之战。这样一来,在安勇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可靠的叙事者,或者不在事内能客观呈现事件的人物。每个人物都被欲望裹挟而去。而正是这种不可靠,使一种主流历史之外的微观历史得到真实的表达。欲望、权力、性、嫉妒、革命……,一个个文化表征在看似不可靠的叙事者口中完成了自己的微观史描述。

叙述者虽不可靠,叙述中的时间差则有助于事件在对比当中达致客观。更重要的,是呈现一种心灵的真实。安勇总是以回忆的笔调记录一段关于美与丑的往事,随之将叙事推入事件的深处。这种今与昔彼此观照的距离感始终存在。如《蚂蚁戏》中:“但从那天开始,她一下子黯淡无光了,光芒四射的小赵老师从此走进了我的心里,直到她死和死后的许多年,我都无法把她赶出去。”再如《软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储艳天。之后的好多年里,我不时就会想起那一幕情景”,这记忆,关乎这几个“人”内心的美被毁灭和美之如何的命脉。进而言之,这些触景生情的自动回忆是烙在心灵深处的,在审美距离的观审之中,在经年的挤压之下,最终完成美的被发现和被认识的历程。而我们也逐渐清晰地知道,美在被发现和被感知的一刹那已经和欲望分不开了。欲望无分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只要在人组成的社会结构之内,它就是存在。
《蚂蚁戏》的主人公叫小小,岁数不大,刚上学的年纪。作者的确是通过小孩的视角展示出小小眼中美丽的代名词——小赵老师的美来。但他并没有赋予这个主人公多余的德性和光环,相反,这个“小”人物身上,比之毁灭美的成人世界并不少什么世俗的痕迹。除此之外,就是人所自带的罪恶本性。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用世俗的儿童眼光展示了人被社会蹂躏和吞噬的现实,也不仅仅说明社会对人之精神的改造功能,他还承载着安勇对这个会毁灭美的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希望。尽管作者只是用淡淡的一句“我突然意识到,她的处境可能与我有关”,关于美的思索却就此敞开。《软肋》的回忆在退休谕示下的晚年和叙事者的青年时代之间开启,就像“猴子、蝈蝈、大头、一斤”这些绰号一样“一直延续下来,跟随我们走到退休后的时光里”。它同样向读者展示了美在特殊时空的悲剧命运和美在人们心头划过的印记。所以,安勇一方面在沉重地书写美的毁灭,另一方面却也在呈现美的被发现历程,虽然美湮没于世界,也必将在世界中被发现;美被毁灭,也被锻造。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欲望及其势不可挡的社会性。
安勇的作品关注“性欲”之于人性的根本意义。由于他作品的叙事者常常是不可靠的,或者说,正处在被社会塑形的过程中,所以,性意识的被建构就成了叙事的重点。正如福柯所言,“重要之处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及其后果又能够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在《软肋》,“猴子”等几个青年男子关于性的“启蒙”是由“覃远志”这个“把女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并最终招致毁灭的男子来完成的。覃远志和储艳天的恋情与“性启蒙”一样,非常具有社会性和语境性。关于“红色”的一切成为这二人爱情的中介和调味品。前者因为“红宝书”、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诗词赢得了“政治水平高”的象征资本;后者则成为此象征资本的臣服者,义无反顾地拜服在“红色”的光芒之下,并完成了自己的“性启蒙”。这就解构了爱情的独立存在可能。权力成为有意识地控制人性的工具。由此看,覃远志和储艳天都是被社会化、政治化和语境化的。他们最终的毁灭性结局正是社会化人格和人性矛盾的大爆发,这既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同时是对被建构于“软肋”之上的爱情的彻底颠覆。《一九八五:性也》里的老师薛德松、班长胡立伟等看似清醒,却未必不是被成功训诫的文化符号。而正是这种疯癫和荒诞,令人们看清了某种事实。
阎连科的《受活》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同样建立在革命狂热之上,并最终在革命+性欲的决绝之中完成了特殊语境中的表演。与之不同,《软肋》加入了“美”这一关键元素,并使之贯穿于一切社会活动之中。有了美这个介质,使欲望、政治、权力等等变成了被观看之物,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观念或价值。而需要我们关注的,这起事关“软肋”的爱情是由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我们”完成的,这再次证明:美与欲望相关。如《软肋》中一处颇有意味的细节,“见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活照样干不出来,老龙只得向大队长请求援兵。”此处可谓安勇反讽艺术的一大典范。他有意识地在“思想政治工作”、“流动红旗”、“竞赛”这些具有鲜明社会色彩和主流集体文化意识的表征间进行对比。这里没有谁比谁的境界高,也没有谁比谁更加卑劣,主导行动的终极力量是欲望和对美的占有。只不过,必须看到这欲望的发生总有个“美的希冀”在里面。对于跳南大沟的“小赵老师”(《蚂蚁戏》)、杀死覃远志的储艳天(《软肋》)、冲进湖里仅为一朵荷花的小顾(《青苔》)而言,却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美的坚守”并最终获得自由。

除去以回忆的方式坚守内心美的希冀,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尖锐地提醒这些参与到“美的毁灭”过程中的人们?《青苔》里弱智“小顾”没有任何华丽语言的简单行为给了世俗的、自以为正常的人们重重一击。从这个角度看,小顾就是他者,在众人存在的世界之外,因此,他的热烈,加上他的破坏行为,就构成了“他人就是地狱”的明晰镜像。这个长相像“明星”的“傻子”,与自信“总能”控制局面的莫丽雅,构成了鲜明的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安勇的智慧是在其中浸入了人性中的感性力量,也正是感性的不断堆积,莫丽雅的“冲动”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其结果,理性的理由变得可疑,而非理性反倒成为一把利剑划向看似端方的理性世界。如果说《蚂蚁戏》《软肋》的反思与对美的发现相关,那么,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介入却是从头到尾始终存在的。然而,只有在“疯癫”的世界里,“爱”与“美”才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所以,恰恰是看似不起眼的“小顾”,给了所谓的“理性”和“正常”一记重拳。富有隐喻意味的安格尔的《泉》同样发挥了镜像功能。小顾视之为“宝贝”,莫丽雅却觉得这“裸体的外国女人”“恶心”。如此一来,小顾对爱与美的执着,就与作者反复言说的“主动权”、“制造快乐”、“分寸”、“正轨”形成巨大的反差。莫丽雅的理性,也变得可疑。小顾的挚诚,反衬出莫丽雅的虚伪,准确说是一种看似清醒的虚伪。或者,莫丽雅们的生活是以假为真,而小顾无功利的真,自然被视为“假世界”的“威胁”。可靠的是,安勇并没有将莫丽雅描写成残忍和完全异化之人。莫丽雅的“欺骗”,既是对“假世界”的维护,同时也是理性堤坝开始溃败的显影。北湖已“铺满厚厚的青苔”,可莫丽雅们心上的青苔已经长得遮蔽了心的痕迹。小顾的出现以及最后的死亡,是回返内心的荆棘满布之途。只是,以众人眼中心中的“不正常”来引导“正常人”审视自身,是何其讽刺和怪诞的事情。面对这个充满悖论和问题的世界,这却是安勇开出的一剂良药。
关于性的被建构、美的被毁灭过程和成长的艰难,安勇总是将其放在社会化的特殊语境之中,这也使他全部的小说连缀起来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中的一系列死亡,弥漫着悲伤、无奈。显然,安勇是在写人性——被压榨、被挤压的人性。在他最新的作品《钟点房》中,他将笔触伸向青春已逝却极度渴望“生活”的中年妇女。这个女子同《蚂蚁戏》里的小小、《青苔》里的小顾、《一九八五:性也》里的袁金利等人比起来,虽已差不多完全社会化,却同样希求获得个性和爱。她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怀疑和不确定,她那飘忽的思绪注定叙述同样是不可靠的,却无比真实和残酷。
《钟点房》讲的是覃晓雅内心深处对美的希冀,虽一点一滴被生活和岁月磨砺,却始终存在。“钟点房”的寓意在于,主人公覃晓雅“要做的事和任何人(甚至包括綦连安)都无关,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事,也许这辈子就只有这一件事如此。”这件事情可以让她的人生纸牌有“属于自己的内容”。换而言之,她在寻找生活中的自我。结果,来钟点房的男人一直沉浸在自己关于“小师妹”的暧昧回忆之中,那是他对自己逝去岁月的装点。这使覃晓雅关于男欢女爱的浪漫故事显得乏力而尴尬收场,想要借助外力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内容”的打算以失败告结。这犹如“蚂蚁戏”中“两只蚂蚁想不明白世界为什么突然变得面目全非了。”覃晓雅们的人生在社会森林之中失去了自我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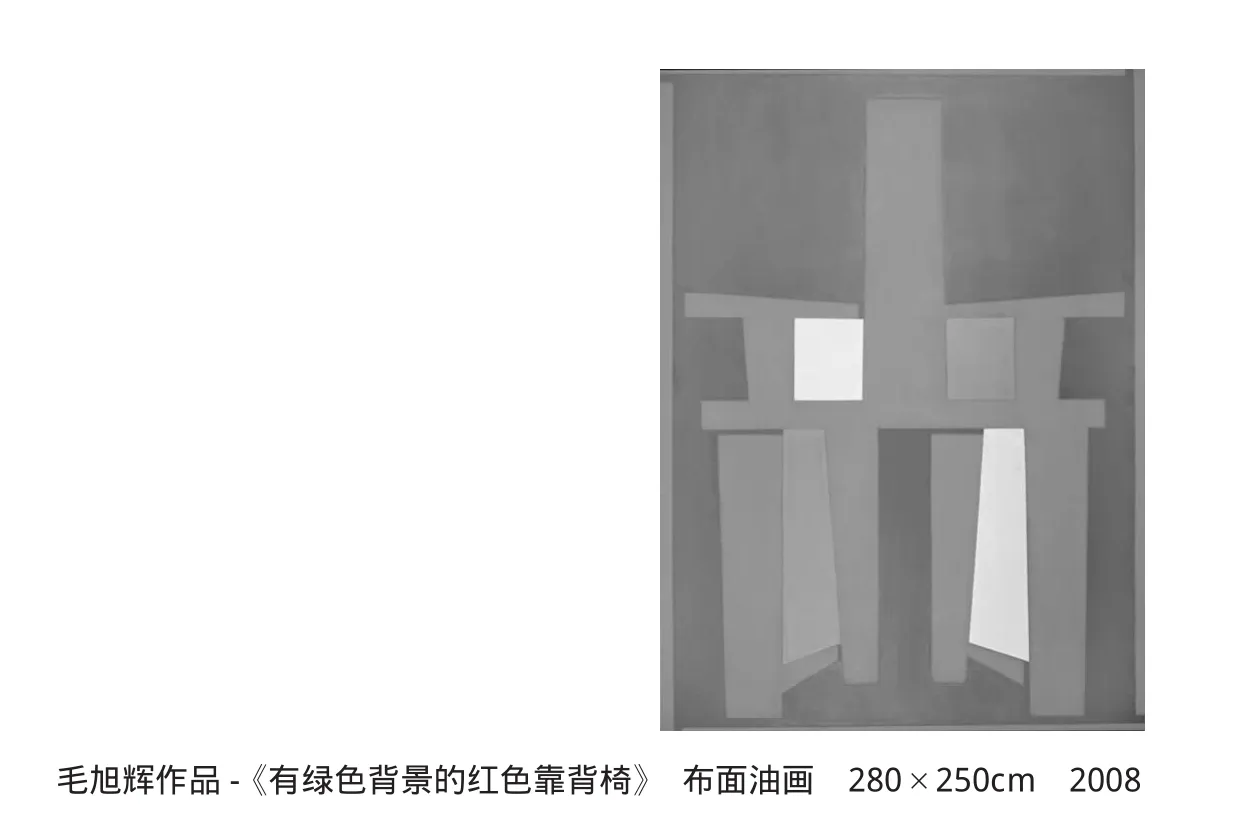
福柯说,“相似性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符号世界”。安勇却没有放弃相似之外的诸种可能。他看到,在生活的咬噬和磨砺下,每个人仍然或多或少有属于自己的想象。虽然覃晓雅在无力的话语独白之中“又能像从前一样生活了,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侍候儿子和老公,到了晚上就准时等着看那部宫廷剧……”,这一刻,英国著名漫画家的“读图时代”,遽然出现在大众面前:一只猴子看着雷打不动的肥皂剧,看着看着变成了人,而没多久,人就在无限的复制、重复过程中变为猴子。在这样一个人变猴的过程,覃晓雅的“钟点房”承担了“人”拒绝变成“猴”的希望,焚烧的《泉》改变着莫丽雅自以为是的世界,只是在重复和习惯的压迫中,青苔已无处不在,这愈发显示出发见自我的艰难。
在精神暗流的反复言说系统里,特定语境下的话语狂欢在安勇笔下十分突出。他对并不高尚、也并不智慧的普通民众生活,有意识地选择了铺排和展示,构成对特殊语境下现实生活的详尽描述,同时,又因正儿八经的叙事语调使全文充满了反讽的气息。令人安慰的是,这反讽的背后,无时无刻不透着沉重的反思,从而在重重包裹的洞穴之中隐约透出一丝光亮。在这种氛围下,《青苔》里的小顾以其含混的存在构成对世人“当头棒喝”的本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