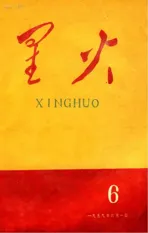杨铁匠
2013-08-15阿微木依萝
□阿微木依萝
杨铁匠一句话也不说地站在那里,我以为他应该说点什么。
“杨铁匠,你是哑巴不是?你怎么把我的锄头打成这样?我打的是锄头不是镰刀!”气愤的客人在杨铁匠身后大骂,但是杨铁匠好像听不见他的声音。
“杨铁匠!就算是赊账你也不能这样。赊账是暂时的,我早晚会把钱算给你,你这样子算他妈的什么意思!”那人向前走几步,追着杨铁匠继续骂。
杨铁匠终于恼了。这是他忍耐很久才突然发怒,吼道:“我没饭吃了!你他妈准备赊到几时!”
我站在山洞外面的石堆上,杨铁匠的吼声差点把我从石堆上震下去。
杨铁匠和客人扭打起来。我不会去劝架。我才十岁。
杨铁匠是从外地搬来的,他来那天是个中午,两只手各牵一个孩子,左边是女孩,右边是男孩。他的肩上架了一捆被子,用红花的床单罩住,像一朵大花开在身上。手臂上还挂了几件衣裳,与唱戏的一般。那时我站在村口的草垛子旁边,正巧看见杨铁匠牵着他的两个崽子进村。我就像看见怪物一样朝着我家的厨房大喊——“妈!洋鬼子进村啦!”——前一天晚上,我在邻家蹭电视看,电视里有个洋鬼子和他长得一模一样:长头发,毛胡子,穿一条短裤。唯一的不一样大概是鞋子的区别,那洋人穿的是皮鞋,杨铁匠穿的是草鞋。可惜我当时并没有多注意杨铁匠的鞋子,所以我认定他是洋人。
“喊你妈的魂!”我妈是这样回答我的。她的脑袋只在门边晃了一下就缩回厨房。
“嗨,小娃娃,你们这里可有打铁的?”
他喊我小娃娃,这使我心里大不舒服。在我想来,我可是个大人了。“你!是哪个?”我斜着眼问他。阳光有些强烈,把我的眼又逼回正位。
“铁匠。”
“不懂。”
“打铁的。”
“不懂。”
“哎,跟你一个娃娃有啥好说的。说啥你也不懂。”
“你不是洋鬼子?”
杨铁匠哈哈大笑:“我不是洋鬼子。我是杨铁匠。”
杨铁匠没有和我多说,他领着两个孩子朝村子的边缘绕了一圈,最后,他在一个斜坡的山洞前三下两下搭了个偏棚,住下了。在偏棚过了些时日,他才在山洞边起了一所草房子,一个人建,用墙板装满泥巴,一天砸一板,慢慢将四面墙壁立起来。他是个死了老婆的硬汉。但也有人说他是个死了老婆的软汉。他喝醉了会哭。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杨铁匠,还有他的两个孩子。我常去他家蹭饭。当然,我悄悄去,在那里吃个半饱,回来再吃一顿,这样不会被父母骂。杨铁匠的厨艺很臭。
杨铁匠住在村里快要两年了,听村里的女人们传言,说他打铁挣了一簸箕银子了,我们村子以及附近村子的钱都让杨铁匠挣光了。所以她们在打铁的时候,不是砍价就是赊账。“应该这样!”她们齐声表示。我是挤在她们中间听来的,她们说什么从来不避开我。当然,有时候说到什么要命的事情,也会把耳朵凑近了说,不敢让我听到。
现在,这个挣了一簸箕银子的人和他的客人扭打在一起,我在想要不要上去帮忙。我的牙齿一向好使,只要我跳得足够高,就可以准确无误一口咬掉他的耳朵。
但是杨铁匠和那个人显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打得满身泥灰,对立着站在那里,牙齿咬住下嘴皮,眼睛瞪得跟马脖子下挂着的铃铛一样大。很快,他们的姿势变了一下,就像两只好斗的老公鸡,在阳光下张开爪子,红着鸡冠子,“呀”地一声,朝对方狠扑过去。
杨铁匠的小儿子来了,他叫大老熊,我远远地瞄了他一眼,不清楚杨铁匠为什么给他这样干瘦的儿子取个猛兽的名字。大老熊瘦巴巴的,走起路来就跟喝多了一样,飘来飘去。
“你爹跟人干架了。你看。”我将手抬得高高的,生怕大老熊的小眼睛看不见。
大老熊听见我的话哭了。面向着我,好像是为了我指给他看才哭。他哭给我看。
杨铁匠听见儿子的哭声,一下子就软了气,不打了。他吼道:“老子不跟你计较了,这几天之内把钱给我准备好。都一年了,算对得起你!”他灰扑扑爬起来,筋疲力尽,好像要栽倒,他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口水里含着血丝。他的牙齿出血了。
那个人恨恨地离去,一路骂骂咧咧。
杨铁匠十分疼爱大老熊。大老熊就是他的命根子。有一次,杨铁匠喝醉了,他在打铁的山洞里和一个老者讲他的往事。我和他的大女儿小花针在铁匠炉子边烤火。我们抽那架打铁用的风箱玩,看火焰像金色的蛇一样往上蹿。
杨铁匠和老者的谈话跳进我的耳朵。
“……你说我怎么结的婚?”杨铁匠望着老者,“农村人,能怎么结呢!我给了老丈人两挑谷子,就把他的女儿领走了。那时候的人,不值钱。”杨铁匠咂巴着嘴,表现出一副无奈的洒脱。
“也对,我那老婆子就是白领来的,不仅这样,他爹还倒给我一只年轻的母羊。说留着下崽。老人家糊涂,只有母羊没有公羊怎么下崽呢?我也糊涂,家里没有公羊还不晓得去借一只么?家的没有,野的还没有么?你看看,那时候的人,不仅不值钱,还笨。现在好了,一看你家大老熊就很聪明,这么一点大的娃,就晓得爬灶头上煮稀饭。”
老者夸赞大老熊聪明,小花针有点不高兴,她嘟着嘴,把风箱拉得怪响。
杨铁匠抹起眼泪来。他喝醉了。老者叫他不要哭,他说他止不住眼泪,是眼睛自己想哭,不是他想哭。他说:
“大老熊出生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雷,我当时很高兴,因为传说中那些了不得的人物出生时,都打雷下雨,所以我认定大老熊将来会是个人物。我想我杨铁匠一辈子,祖上打铁,到我这辈还打铁,也应该出个不打铁的人物了。想想我很快就是这个人物的爹,我简直站在那里想大笑几声。但是屋里的人喊天叫地,把我吓着了。接生婆一会子跑出来,一会子跑进去,她被雨刷湿了,看起来像一只肥胖的落汤鸡。我也不敢问她屋里的情况。有会子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想进去看看生下来没有,我的一只脚刚跨进门槛,接生婆一脚就把我扫出来了。
“我站在雨里等消息,当时也顾不得躲雨,也不担心一个炸雷把我干掉。接生婆再跑出来的时候,她在雨水中摊开一双血手说:‘你赶紧进去看看,该怎么办?’很无能的样子。”杨铁匠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肩膀一颤一颤的,好像扛着一件什么东西。老者没有说话,但是很认真地在等杨铁匠继续讲。
我和小花针也被杨铁匠的话吸引过去。我感觉他的故事讲得比我奶奶好。
“我当时气得发疯。揪着接生婆的衣领,‘你他妈咋搞的?’我当时一定在哭,声音沙哑得我自己都不认识。那接生婆也慌了,她说:‘接了一辈子生,没遇见这样的!’‘你废话!你说生二胎就像老母鸡拉屎一样容易!’我急得想跟她打架。接生婆一把甩开我的手,她朝我大吼:‘我说的是屁股大的人!你婆娘那扁平的屁股,能像拉鸡屎那么容易吗?’接生婆抹了一把湿答答的脸。”
老者忍不住嘴唇上扬,发出一阵短促的笑。杨铁匠被这笑声阻挡了话,往旁边闲看的时候,才发现我和小花针也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听他讲话。
“出去玩!”杨铁匠黑着脸把我和小花针撵了出去。这样,他之后和老者讲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他很疼爱他的大老熊。刚才大老熊一哭,他立马就不打架了。
“哭啥哭?不要哭。你爹我好好生生在这儿的。”杨铁匠朝大老熊走来,一把将他抱在怀里,转身走了。他的脚肯定被踢坏了,走路像个瘸子。
我们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里面栽了许多白菜。白菜已经长得很好了。我悄悄跑进菜地,想拔一棵白菜送给小花针。小花针躺在眠床上已经一个月了,她病得不轻。我跟她说我们家的白菜长得太好吃了,不煮熟看着就好吃。她眨着眼睛表示她的高兴,她已经不能说话,好像病成了哑巴。但是我说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她会不停地给我眨眼睛,表示她愿意听,或者对那些东西很感兴趣。我说到白菜的时候,小花针的眼睛眨出了许多眼泪,我就想,她可能想吃点白菜,或者想看一看白菜。
十天前,我听杨铁匠说,他已经给小花针请了好几个仙家来跳神,但是没见着效果。病没有好转,好像越跳越严重了。
“鸡也用来祭神杀光了,现在是鸡无毛,狗无踪,光杆杆的了。要想再请仙家来跳神,我得再打几把锄头才能挣到买鸡和请神的钱。”他说得很用力,恨不得现在就有人找他打锄头。
“你家有只瘦狗。”我赶紧纠正他说错的话。因为他家并不是“狗无踪”。
“那瘦狗也算狗?”杨铁匠狠狠朝地上吐一泡口水,说:“它不算!给它吃再多饭食它也瘦得跟鬼样!”他说到什么激动的事情,总喜欢往地上吐口水。
我对他打锄头不生什么兴趣,我对那些仙家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仙家是什么东西。他说仙家不是东西,仙家是可以通神的人,当然,他们还可以看见鬼,甚至还能看见活人的魂。我没有听明白,越问越多,越听越糊涂。他懒得理我,吩咐大老熊在家照看小花针,他上山干活去了。
杨铁匠上午忙坡上的活,下午就到山洞里打铁。他的铁匠铺开在山洞里。
杨铁匠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也不止他一人这样,村里许多大人对小孩都不是十分热情。他们在路上遇着你,就跟遇着小猪小狗没什么区别,高兴了嘿嘿一声,不高兴时,就跟没长眼睛一样飘过去了。这也使我养成一个习惯,他们不先与我招呼,我绝不主动与他们招呼。这样的习惯在他们身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我身上就不行,他们会跑到我的父母那里告状,说这娃儿一点礼貌也没有,看见长辈连个招呼也不打。我父母的耳朵是用豆腐做的,他们先骂我没有家教,接着就实行他们的家教,把我狠揍一顿。
我已经好几天没去看小花针了。我担心去得越多,杨铁匠抓住我的缺点越多,如果他也学那些长辈向我的父母告状,那我的屁股就得开花。但是昨天我还是忍不住去看了小花针。看完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要给她送一棵白菜去。
“她喜欢老点的?还是嫩点的?还是不老不嫩的?”我放下昨天的闲事不想它了,在菜地里翻着白菜叶子自言自语。我无法确定小花针喜欢哪种口味的白菜。
“叽咕叽咕什么?”我妈突然站在我背后,她走路一点响声也不带。
“小花针家没有白菜。昨天我去看。我听说。”我不敢提送白菜的事情。因为慌张,话也说不明白。
“咋可能。上个月和杨铁匠干架那个人不是给了他家一麻袋白菜抵账了吗?就吃完啦?”
“啊?”
“啊什么啊?回去!”
我刚转身准备回去,妈又说:“拔棵嫩点的。病人喜欢吃。”原来她早就猜透我的心思。
从村里通向杨铁匠家的路十分难走,一路上有不少石头横挡着,要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冬天这样跳没什么问题,夏天稍不注意就会踩着蛇,刚开始我很喜欢走这样的路,摔了几次跤,踩着几次蛇之后就不喜欢了。这也是我逐渐不去他家蹭饭的原因。如果不是小花针生病,我才不愿意抱着一棵白菜在石头上跳来跳去。
我刚走到杨铁匠家门口,他家那只瘦狗就来迎接我了。它甩圆了尾巴,还轻快地跳起来蹭我的腿。
“你好点了没有?”我刚一进屋,来不及喘口气就问。
房间很暗,我过了好一会子才看得见东西。
小花针没有回答我的话。我走到床前,看见她睁着眼睛,眼角红红的,眼里有血丝。
“你来啦?”她轻微地抬起头,想要坐起来,但是没有足够的力气,她又喘喘地躺回去。
“你可以说话啦?”我有点兴奋,已经好久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了。
“早上和晚上严重,中午要好些。啊!——白菜呀!”小花针看见白菜了,她显得十分激动。好像她从来没有见过白菜一样。
她把白菜接过去放在她的枕头边,好像她自己就是一片菜地,那白菜是刚刚从她身上长出来的一样。“一定很甜吧?”她问。
“不甜。有点甜。”
“那是甜还是不甜?”
“甜吧。”我又补充道,“如果往菜汤里洒些白糖。”
“你有妈妈,真好。”小花针突然哭了,她的泪水从红色的眼角淌出来。
“你没有吗?”我这样问的时候,心里感到难过,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要难过。我没有看见她的妈妈的缘故吗?杨铁匠来村里的时候,只带了她和大老熊。可是我明明听杨铁匠说起他的老婆,说生大老熊怎样怎样,虽然我没有听到更多,但我确定小花针是有妈妈的。
“她死了。”小花针哭得更凶。虽然她病着,但是她哭的力气却很大,“昨晚我梦见她了……她问我想不想她。我说不想。其实我很想她。但是在梦里那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又好像是我说的,我搞不清楚……”小花针刚刚揩干的眼角,很快又被新的泪水滚湿了。
我也受了她的影响,眼泪也跟着落下来。
我忘了问小花针的妈妈是怎么死的。我给她煮了一碗白菜汤,她们家没有白糖,所以我撒了一些盐巴进去。
“晚上不回去了吧。你就在这里住一夜。好不?”
“好。 ”
我走到她家门口,隔着几百米朝家里喊话,我妈还是听清楚我的意思了。我告诉她今晚不回去了。
杨铁匠在傍晚回来了,很疲惫的样子。他不问我这样晚的天色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脱了鞋子,鞋口朝下,从鞋嘴里抖出许多黄泥巴。
“晚上要请神。仙家都找好了,天再黑点就来。花针,你想吃点啥,我去给你煮。”杨铁匠靠在门板上问。
小花针因为白天的那碗菜汤有了点力气,她居然可以撑起来坐着,然后笑笑地望着杨铁匠说:“爸,不要请神了,我感觉快要好了。我想吃点白菜炒饭。”
杨铁匠被小花针的好转惊喜了一下,他说:“看来请神是有作用的。花针,不要担心,我们再请一回,病肯定就彻底好了。你等着,我去给你做饭。”他的样子没有先前那样疲累了。
天黑了许久,杨铁匠请的仙家还没有来。他坐在门口张望,那条弯道上只见夜鸟飞窜。
“该来了。为什么还不来?”杨铁匠说。
“爸,我想吃鸡肉。”大老熊知道请神要杀鸡,所以撑着没有回房睡觉。在往常这个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再等等。”
“不想等。”
“你——”杨铁匠原本想发火,他的脸色刚刚沉下去,立刻又缓和起来,并且带着几分喜色:“总算来了!”他指着远道上的一个黑色的影子,“那仙家走路的样子就是不一样,像飘。你们看!”他立马站起身,先是指给我和大老熊看,接着就招呼站在门口的我帮他烧火煮水。“要请仙家洗洗脚,解一解乏。”他说。
杨铁匠的厨房很矮,我一个不高的孩子站在里面也险些碰头,杨铁匠就更不用说,他每次做饭都弯着腰杆,好像一支藏在厨房里的弯弓。我想这样的矮房子让老鼠住进来更合适。小花针肯定也和我想的一样。她说有一次在堂屋里发现一窝鼠崽子,刚出生的,有着红嘴唇,浅灰色的毛,脚爪和脑袋嫩得就像透明的,眼睛就跟空气一样好看。她把那窝鼠崽子悄悄挪到厨房,放进矮墙连接处的一个草窝里,过了些时日再去看,它们已经不知去向了。
想到那窝鼠崽子,我一边烧水,一边往厨房的草窝里看。为了不让鼠崽子突然伸出脑袋吓着,我轻声地哼起歌来。
“奇怪呀,刚才明明看见仙家来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莫非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杨铁匠走进屋,神情疑惑。
杨铁匠刚刚说完话,仙家就站在门口了。仙家说:“我来了。”
我没有看见仙家的样子,杨铁匠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听见仙家的声音。那声音和杨铁匠以及更多的人的声音差不多。“仙家也说人话嘛。”我这样想了一下,对这个仙家也就失去了一半的好奇。我以为仙家要说仙家的话,会是我听不懂的一种发音,就像老鼠和鸡的叫声。
就在声音响起的一刻,杨铁匠的脚软了下去,就像一颗果子撑不住从树上掉下来:“哦哟喂,我的神仙亲爹,你吓着我啦。”
杨铁匠半蹲下去,我看见仙家的样子了。“是个人嘛。”我说。
“不然还是个啥?”那仙家看我是个孩子,也不和我计较,原本升上脸去的怒色也换成了一副笑容。
“我以为仙家是个别的什么东西呢。”
仙家的笑容僵在脸上,就像庄稼地里的草站到枯黄,一派败坏的摸样。杨铁匠转身喝斥我:“小娃子不要胡说八道。好生烧火!”
“本来嘛,那瞎子算命的,他就不喊自己是仙家,他只说自己是干迷信的。你要说干迷信的我就懂,你要说仙家,我不懂。我爸说仙家在月亮上。我没有乱说。”
“还说?”杨铁匠更生气,做出要把我扔出去的模样。
仙家低头走进厨房,放下他的蓝布包,往小凳子上坐下来。
仙家因为上了年纪,看起来苍老,有股我说不出的神秘的感觉藏在他的面色之后。
“哎哎,不要和娃娃吵嘴。我有自己的道号:黄先人。不是仙家的仙,是先人的先。”黄先人又对我说:“你爸说得对,仙家就是住在月亮上。我只会把仙家请下凡。但我不是他们。”
“娃娃,你几岁了?”黄先人穿上他的鞋子,又问我。
我懒得和他说话。
虽然受了杨铁匠的喝斥不敢做声,但我还是可以偷偷地瞄几眼黄先人。黄先人长了一张黑黄的脸,脸上爬满斑点,他的手也是蜡黄的,眉骨有些高,两条眉毛却生得稀疏又浅短,好像是谁家不要的废猪毛让风给吹去黏在那里。他跟杨铁匠说话的时候,那两条短眉毛就像是无法在眉头上站稳脚,看着就要往下掉。
“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一个生魂,哎——”黄先人神秘地说,接下去的话他却不说出来,想让我们自己去猜。
“生魂是活人的魂,谁会知道自己的魂在哪里瞎逛呢?”杨铁匠表示他无法猜得出来。
“娃娃,你猜。”黄先人望着我说。
我正在生他的闷气,看也不看他一眼,佯装没听见。
“在猜啥?哈哈。”王婶子来了。她也低头走进厨房,看到我在,和我打了声招呼,看到黄先人也在,也和黄先人打了声招呼,最后才和杨铁匠说话:“我来找你帮忙,明天帮我挖一天地。换工。不会亏你。以后你有活忙不完也来找我。”王婶子说得很爽快。
杨铁匠想了一想,说:“可是可以,但是要晚一些来,大概要到上午十点左右。你晓得,花针病着,老熊还小,我得煮饭喂猪,打整完了才有时间出门。”
“晓得晓得,那就这样定啦。对啦,过些时候,还要麻烦你帮忙打把镰刀。收秋后卖了粮食再给你钱。”王婶子说着就站起身,扫一扫她衣角上的灰尘,准备离去。
“耶,你不回家吗?走吧,跟我一起。”王婶子走到门边,她朝我招手。
“姐姐不回去的。你自己走吧。”大老熊来厨房端水给花针喝,碰巧听到了王婶子的话。他替我回答了。
王婶子走了。
黄先人没有再继续刚才猜生魂的话题。他脱了鞋子,把那双沾满黄泥巴的脚泡进水盆中,水有些烫,他又将脚抽出来放在盆边吸一吸凉,再放回盆里。
晚上没有月亮,正适合黄先人请神。黄先人说,月亮就是鬼神的太阳,我们看见的月色越好,鬼神越感觉热。
“这样说来,我们的太阳就是鬼神的月亮吧?”杨铁匠问。
黄先人用一根指头轻轻抚过他的短眉毛,说:“你这样说也有点道理。就算是这样的意思吧。”接下来,黄先人就开始请神了。他把桌子上摆好的所有的东西都看一遍,确定没有缺少哪一样,才稳稳地蹲在凳子上准备请神。
“公鸡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是公的吧?”
“公的。”
“嗯,对头,莫整错了。我上次去的那家,憨婆娘不分公母,逮了只母鸡站在桌子上,那神仙生气,最后用了两只公鸡。你说亏不亏?原本一只就可以,偏要再搭一只。你可不要弄错了。对了,我看你家鸡圈里好像是没有鸡?”黄先人说得自己就跟树上的黄鼠狼一样,从鸡圈门口路过一下,并且还是在没有月亮的晚上,都能凭感觉知道杨铁匠的鸡圈里没有鸡。
“鸡圈里确实没有。昨天晚上连夜去村外买来一只,我把它装在背篓里,放在堂屋里了。怕它跑掉。”杨铁匠说。
先人点一点头,坐在那里放心地请起神来。他开始全身发抖。
我见过请神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招数。其中一些请神者是坐在桌子上,摆露出一张要笑不笑的脸,他们一旦是这个样子,就证明神上身了;那个样子不是他的样子,那张笑脸也不是他的笑脸了。反正请神的人在神完成任务离身清醒后,他会说:“那刚才的神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只是一个传话的壳子,刚才的我被神借用了,啥也不知道。”他这样问的时候,(一般请神的人家会邀请几个亲戚朋友来观看)就会有观众告诉他,那神问了他们什么,他们又回答了什么。请神者也会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他说的意见也是根据结果而来。假如结果没有使人明白神仙的意思,请神者就会说,你们太糊涂,应该这样问,应该多问一些;假如结果很糟糕,他就很无奈地告诉你,是你们问得太多了,这样会使神仙不高兴。
我见过一次因为问得太多而使神仙不高兴的场面,那神仙抖着抖着就站起来,砸了那家的碗和甑子,还有一条长得非常漂亮的胶板凳。吓得那家人战战兢兢,说那神仙的脾气真是不好惹,下次若再请来,一定少问一些。那家的女主人只敢偷偷地抱怨,说自己花了一只大花公鸡,希望能让神仙多指点迷津,不想赔了碗和甑子,外加一条好凳子。那时我比现在还小,我就坐在女主人的身边,她的抱怨从嘴巴里轻声地滚进我的耳朵里来。
还有一些请神的人,他们像是一只只会跳舞的公鸡,先是围着桌子跳,接着就围着房子跳,后来大概是跳累了,跳回屋里就躺在地上,好像是死了一样。正当你以为他死了,他却在那里突然哼起调子来,那调子当然是请神的调子。听不懂。哼完了那些调子,他清一清嗓子,才会问这家人要请他的目的。
黄先人就是跳来跳去的神。现在他就躺在地上,调子也哼完了。说的却尽是些听不懂的人话。我以前见过的那些请神的人,他们说的话还是能听懂的。难道黄先人的道法更高吗?
先前,黄先人就告诉杨铁匠,说如果是生病的人家请神,那么请神的人都会介绍一位医病的神仙下来。所以,他也会介绍这样一位神医。那位神医问的就是关于病人生病的日期,以及病人的生辰。但是现在杨铁匠发懵了,他刚才给黄先人喝了半瓶子好酒,现在黄先人请的神在他身上也像是醉神,说话不清不楚,听不明白。而那张“壳子”,也就是黄先人本身,他躺在地上说着说着好像要睡过去。
“爸,我听着像醉话。”大老熊说。
“小娃子不要乱讲话!”
“我听着也像醉话。”我也忍不住说。
“这本来就是醉话。”小花针也扭头望着黄先人,并且十分惋惜的样子,“我就说不要请了。上次也这样。”她咳嗽两声。
我赶紧凑到小花针的床边坐下,悄悄问:“上次也是黄先人吗?”
“是。来跳了半夜,也是喝醉了,睡了两个多钟头,醒来发了一阵子酒疯,吵得人睡不着。我爸偏不认为那是酒疯,他说那就是神仙在作法。”小花针低声告诉我。
“不要给他喝酒嘛。”
“我爸说,是黄先人要求的。不喝酒请不来神。”
我仰起头仔细搜想,确实,我见过的请神的人都喝酒。他们每次要将自己的脸喝得像鸡冠子一样红,才开始请神。但我没有见过谁喝得这样醉,还连带着把神仙也灌醉了。
杨铁匠显然是见识过黄先人请神的道道,他一点也不着急,坐在墙边静静地等黄先人问话。大老熊想要睡觉了,但是他又惦记着鸡肉,所以他站着。站着不容易瞌睡。
“鸡准备好了吧?”
黄先人躺了大约一个钟头,总算说得清话了。
“嘿,这次他醒得早。”小花针感叹。
“准备好了。”杨铁匠急忙回答,生怕怠慢了仙家。他又战战兢兢追问:“请问是哪一位仙家?”
“杨八姐!”黄先人躺在地上,像鱼一样抽动一下身子,喉咙里发出女人的声音。
“啊,杨仙家!真好真好——”杨铁匠赶紧往桌下烧了三张纸钱,表示欢迎杨八姐的到来。过了大约两分钟,杨铁匠又烧了三张纸钱,才继续问:“请问仙家,我姑娘花针的病可有得改?是有什么关口吗?”杨铁匠问得很清楚,看来前几次请神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似乎真把黄先人当成了女的,问话的时候脸色发红,看也不敢多看黄先人一眼。
“说一句话就烧三张纸钱,我爸好笨的。反正他躺着也看不见,不能少烧一张么?”小花针虽然说得小声,还是被杨铁匠听见了。他严厉地瞪着小花针,示意她不要乱讲话。
“鸡,摆上。 ”
黄先人发话了。这时大概不是杨八姐在说话,声音不同先前。
杨铁匠飞快地往堂屋的角落凑去,摸着那只公鸡的脚,倒提着出来。他不知该摆在哪里,又慌忙地跑去烧了三张纸钱问:
“仙家,鸡来了,摆哪里?”
杨铁匠的脸上汗水都出来了。他大概是怕仙家发火。
“桌上!”这时又是杨八姐的声音了。
杨八姐哼着我们听不懂的调子,好像是专门哼给鸡听的。鸡听了调子后,站在桌子上转了一圈,然后沉静地蹲在桌面上。杨铁匠坐到我和花针的身边来了。大老熊也跟了过来。杨铁匠擦了一把汗对我们讲:“鸡也听神仙的话,这要是平时,它还不飞走?”
杨铁匠又说了些赞美的话,赞美鸡的时候也把神仙赞美了一番。说杨八姐就是有能耐,不说人话的东西在她手里都这般乖巧。这样说了一会子,又蹲回桌子的一边,给黄先人当下手,专门负责烧纸钱给仙家。现在黄先人是暂时剔在一边的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杨八姐。”杨铁匠怕我们不识神仙,特意在耳边低声强调。
黄先人的魂应该在屋子的某个角落,因为喝醉了酒,也许在睡觉。
“公鸡在打瞌睡!”大老熊尖声道,好像他从来没有见过鸡打瞌睡。
“瞎说!”
“真的!”
“神仙控制的鸡怎么会打瞌睡!现在看到的是鸡壳,鸡魂是清醒的!青沟子娃不懂轻重!”
杨铁匠居然像孩子一样和他的大老熊争执起来。若不是他十分溺爱大老熊,我想他会动手。
黄先人从地上爬起来了。并且盘腿坐在地上,全身抽动,发出一阵精怪的笑。然后正色道:“凡间之人杨铁匠,你女花针三魂七魄少一魂,隔山隔水归不了门,你要准备公鸡喊魂,连喊三夜——”黄先人停了一停,吹出一口长气,拍一下令牌说:“凡间之人杨铁匠,你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你就回个话,莫浪费我杨八姐时间。”
杨铁匠赶忙烧了三张纸钱。反正在说话之前,他都要先烧纸钱。为了不烧漏一张或烧多一张,他每次都要认真数一遍。他说黄先人跟他讲过,少烧或多烧都是不灵验的,仙家收不到你的诚意,他给你解关口就会蛮干,不管准是不准。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仙家救命。”杨铁匠脸憋得通红,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完他的谢意,于是他推开凳子,双脚着地,在桌前给杨八姐叩了个响头,又慌忙喊花针下床来叩头。
“快点快点,来叩头感谢仙家救你的小命。”
花针本不想起床,但是被大老熊催促起来了。大老熊十分喜欢叩头,所以他自己也跑去叩了一个头,也不管杨八姐领不领。
杨八姐走了。黄先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和其他的请神者一样,神仙一离开身体,就开始问刚才的事情。
“请的是哪位仙家?”
“杨八姐。”
“嗯,杨八姐神力大!”黄先人竖起大拇指。
杨铁匠也鸡啄米似的点头:“确实确实!”
“问好了吗?什么毛病?”
“和上次不一样。上次说丢了一魄,这次说丢了一魂。那一魄刚回来,你看,这——”杨铁匠非常懊恼地看着花针,“这娃子,就是不让人放心!身体好时乱走乱逛,搞得不是丢魂就是丢魄。”
“杨八姐说怎么改?”黄先人又问。
“喊魂。”
“嗯。”黄先人一边点头,一边举起那只公鸡,用嘴咬掉鸡冠子,在门框上,门槛边,床头,柜头,桌角上,墙壁上,还有杨铁匠的弯拱拱的香火板上点鸡血,最后再回到桌前,往铺开的红布上也点了几滴。黄先人嘴里咕噜咕噜念一些法咒,围着桌子转了一圈,才将一碗汪着纸钱灰的水端给花针喝。
“是法水。喝一口。”黄先人半闭着眼睛继续念咒。
花针抿了一小口。
“好了。今晚喊一喊魂。明晚你照我的样子喊。这只鸡今晚得杀。”
“行行,我明天另外买一只。这只肯定是要杀的。我懂。”杨铁匠边说边准备去烧水。
黄先人在门背后盖一个背篓,鸡在背篓里,他拍着那只背篓来回地重复着喊:
“花针花针,你快回来。你爹喊你回来!花针花针,外面路黑,外面风大,外面山高,外面路远,花针花针,你快回来!——”
花针躺在床上,偷偷望着黄先人笑。大老熊听着黄先人的有节奏的喊魂,也跟着悄悄念。
鸡肉很快上桌子了。黄先人不动筷子之前,谁也不能动。但黄先人显得十分大度,他说:“现在这只鸡的任务完成了,它就只是一只普通的鸡,你们不要担心,哪怕是只小鬼呢,它现在也是煮熟了的。吃!不要怕。”他把鸡脑壳挑进自己的碗,挽起衣袖,好像要跟谁打架,“这个不能给你们吃,这个只有我能收拾它!”黄先人露出一嘴黄牙。
吃完饭,已经是深夜了。大老熊打着瞌睡吃完了一只鸡翅膀,一只鸡腿,还有半只鸡屁股。鸡屁股是吃到一半才发现的,他原本不爱吃,所以当他发现自己正在啃鸡屁股时,发出了一声怪叫。要不是杨铁匠手快,那半只鸡屁股已经飞到猪食锅里。“简直是浪费!不吃不要糟蹋了!”杨铁匠可惜地望着鸡屁股。他还是把残破的鸡屁股放进了嘴里。
杨铁匠嚼完那只鸡屁股,就去黄先人的红布下压了五块钱。那是对黄先人请神的酬谢。黄先人收红布往口袋里装的时候才发现那五块钱,他说:“你看你,又客气了不是。算啦算啦,这次就算啦。”他拿着钱,远远地递给杨铁匠。他不能上前去递钱,非常慌忙地收拾他的东西,很走不开的样子。杨铁匠也远远地往外推着手,好像黄先人的手并没有隔着多远,而是在他的眼前,他极力地往外推手说:“不行不行,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你的脚的。它走了这么远的路,难道不要买双鞋子感谢它吗?请你一定收下,不嫌少就行。”
黄先人收下了。
黄先人整理好了东西,顶着夜色要回去。他说:“我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这样对病人不好。不管多晚我都得走,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杨铁匠说:“好,好,我也不敢破坏你们的规矩。一路小心。”他递给黄先人一把松明。黄先人拒绝了。他说他长着夜眼,干这一行的人,晚上走路就跟白天一样。
黄先人走了十几步,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站在那里问杨铁匠:“今晚的神请得还让你满意吧?”
杨铁匠赶紧回答:“满意满意,很满意。”
“满意就好,你要心里服气才行,你服气了神仙才会高兴,今晚的迷信也就没有白干。你要是心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神仙就不高兴了,你今晚的鸡也白死,迷信白干,病人的病情可能会拖延,也可能会加重。所以我要问清楚你,服气是不服气?你要是不服气,可以再备齐东西,我做到让你服气为止。”黄先人十分诚恳地说。
“黄仙家,我服气。我真的服气。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有那些烂心肝的想法。”杨铁匠赌咒似的保证。
黄先人这回真的走了。
晚上我和花针睡一张床,先是各睡一头,后来被她的哑屁——我把不响的屁都称作哑屁——还有她的臭脚熏得无法忍受,干脆和她睡一头。病了几个月,她说话满嘴臭气。
“我的魂好像回来了。”
“嗯。”
“你说黄先人真的知道鸡脑壳有几对骨头吗?”
“不知道。”
“你说他真的长夜眼了吗?”
“不知道。”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嗯?……”
我睡着了。满肚子的鸡肉都在做梦。
黄先人的迷信还真管用,花针好了。但是她病好后没几天,王婶子喝药死了。为了不让花针沾染晦气,杨铁匠不让花针去王婶子的丧事上玩。
听说王婶子死前突然后悔,拉着她的男人说她喝了药,赶紧救她。王婶子的男人没有当真,以为她开玩笑。
“你晓得为啥她要喝药?”那天下午,花针神秘地问我。
“不晓得。”
“听说她喜欢我爸。那天去帮忙,她跟我爸说她喜欢他,还主动拉我爸的手。羊贩子晓得了,打了她一顿,她老婆婆晓得了,又骂了她一顿。听说她生的那个大娃儿不是羊贩子的。第二个才是。”
王婶子的男人做羊生意,所以大家都喊他羊贩子。
“不是羊贩子的,是哪个的?”
花针摇一摇头。
“不会是你爹的吧?”我惊叫。
“你爹的呢!我们搬来的时候,羊贩子的大娃儿都会走路了。”花针掐了我一把。
“你咋知道她摸你爹的手?”
“我偷听的。我爸和张老爷喝酒聊天时,我就在门口弄猪草。”花针压低声音道,“还有,是王婶子隔壁的周二婶子说,王婶子被羊贩子打了,都打来挂在猪圈杆子上,是她去帮忙劝架的,要不然,王婶子那天就被打死。”
我想起王婶子丧事上那天,周二婶子也在,她当时还跟着陪哭。我看她哭得那样伤心,也跟着莫名其妙掉眼泪。我并不想哭。杨铁匠确实在丧事上不怎么受欢迎,他去挂礼钱的时候,羊贩子也没有给他好脸色。但是没有骂他。王婶子的老婆婆当时坐在墙角,手里握着一根拐杖,在看到杨铁匠从她面前经过,她就“笃笃笃”地敲着拐杖,并且不停地朝地上吐口水,好像她被鱼刺卡了喉咙。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哈!你的书拿倒啦!”
我坐在草垛上,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书,心里却在想王婶子丧事上还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花针突然说话,把我的思路打乱了。
“我教你唱山歌。”花针兴致很好地说。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那条从鼻孔下方横过去的鼻涕印子像路一样飘在脸上,平时看不顺眼,但现在看来也不讨厌了。
“不唱。”我说。
“你在想啥?”花针有点不耐烦。
我正想告诉花针,那天虽然杨铁匠不受欢迎,但他至少没有挨打。另外一个外乡人被羊贩子打了一顿,那个人气咻咻走了,还扬言,等到有机会,要把羊贩子打出羊屎来。我刚想这样说,看见周二婶子和黄先人来了,他们走在一路,肩并肩,在讨论什么事情。
“哟,花针,好完全了吧?”黄先人走到花针跟前。
花针说,好完全了。黄先人又问杨铁匠在做什么,花针说她爹什么也没做,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路边和张老爷喝酒,喝得烂醉了。黄先人拍拍腿,坐在草垛上,他让周二婶子也坐。“这咋行呢?喝酒可以,不能喝得烂醉!再说,这事情不关他。”黄先人让花针去把杨铁匠喊来,他有话跟他说。
“其实吧,要真是人家的娃,给人家也就行啦。我看那外乡汉子也够可怜,他那天的衣服穿得像个讨饭的。他要是在平时来也好,偏生赶在人家的丧事上来,多少也有点欺负人了。你说是不?”周二婶子撇了撇嘴。
黄先人睁着一双小眼,叹气道:“这是关乎这里的事情——”他用两根手指拉起他松弛的脸皮。
“也是。就算不是自己的,也养出感情来了。也不是一碗米喂大的。再说那娃娃也不愿意跟他去。王氏自己躺在地上,她是一事不知了,但是那娃娃的眼神,那么多人都在闲说,他会一点不知道吗?他肯定也怀疑羊贩子不是他亲爹了。听说有一回羊贩子把钱藏在蜂窝里,那娃子找着了,偷了一百块。”说到这里周二婶子笑了一笑,“那娃子也够聪明,藏在蜂窝里的钱都能找到。”
“羊贩子真会藏。”黄先人漫不经心道。
“肯定是不想给那娃子花钱,才这样折腾。不就是几块钱的事情吗?”周二婶子反复地掐着一根干草。
“反正我是看出来了,羊贩子不会把娃儿给他的。那个外乡崽子也是,早干啥去啦?现在羊贩子把娃儿养到这么大了,他说是他的,要领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他不能老是把一顶绿帽子翻来翻去给羊贩子扣上!这么多年了,兴许羊贩子都要忘记那娃子的身份了,准备把那娃子当亲生的了。他这一来,又把那娃子的身份抖亮出来。羊贩子生气是对的。”黄先人清明地分析着。
“对。”
“羊贩子没打断他的腿,他就该烧高香去。”
“对。”周二婶子表示赞成。突然她又小声道:“羊贩子也不是啥菩萨心肠,听说当年那娃儿刚落地,他就抱去扔在厕所板上,摆在厕所里三天三夜,他骗王氏说,那娃儿被他扔在草丛里,让野狗吃了。王氏只是哭,不敢说话。王氏跟我聊天时,还这样哭着当时的委屈。”
“哦?这个我还真没听说。那后来呢?”黄先人表示惊讶。
“后来是羊贩子的老妈听见厕所里有娃儿哭,才知道他的孙子出生了,并且被丢在厕所里。你知道,她身体不好,年纪又大,常年只待在自己的房间——包括解手。该那娃子不死,被她救了。羊贩子也不敢再扔,就这样不疼不恨地喂大,他说就当家里养了只不能宰杀的小猪崽。其实羊贩子也不算狠,下不得手,他希望那娃子自己死在厕所板上,而不是他亲手将他扔进粪池。如果他当时直接扔进粪池——”
“现在那猪崽的爹来了,他又舍不得给了。说起来还不是他羊贩子自己找的麻烦,王氏和那个外乡人好他也不是瞎子,但是他装瞎,天天去勾引王氏。听说那外乡人的老妈嫌弃王氏,王氏心灰意冷才会嫁给羊贩子。我猜他当时是想娶进门再说,只是没有料到,把人家的儿子也娶进来了。”黄先人冷笑一声。
“是这样简单倒好,关键是,娃子的亲爹亲妈又勾搭上了。还让那憨实人杨铁匠撞上,偏生他嘴不关风,喝了酒说漏了,传来传去,传进了羊贩子的耳朵。王氏也笨,咋就选在杨铁匠打铁的山洞里呢?难道别的什么地方就没有合适的?”周二婶子说到这里脸红了一下。
“山洞里安全呀。他们也不会想到杨铁匠大半夜突然去打铁。你说那疯子,也活该他背黑锅。人家羊贩子以为他杨铁匠收了好处,特意撮合的——我该称呼他们露水夫妻吗?”黄先人这回哈哈大笑。
我听到这里,心里好像明白很多事情,但又什么也不明白。我不愿意这样一直听他们讲话,迫不及待地问:“我觉得那天就猪耳朵拌香菜好吃。你们说呢?”我指王婶子丧事上的宴席。我说得太快,也许没有表达清楚。
黄先人和周二婶子这时候才想起我还坐在他们后面的草垛上。他们没有表现出惊讶。在听到我的话时,他们同时笑了几声。
“反正这事情老小都知!不管她。”黄先人对周二婶子说。周二婶子点头同意。
杨铁匠来了。他提着一只酒葫芦,摇摇晃晃像根稻草一样飘来。后面跟着花针。
“我呸!她确实暗示些眼色给我,还拉了一下我的手,但我没有,我啥也没有做!黄仙家,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把她的魂喊回来问。周二,你得相信我。她死不死与我有啥关系?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那天喝多了半夜想起去打铁,我哪晓得她在?这事情扯了一个多月了,还扯不清。越扯越扯不清。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看鳏夫门前是非更多。
“就因为老子没有再讨婆娘,所以哪个的婆娘有奸情都是我搞的鬼!我哪有那个闲功夫?我一天要打多少把锄头,要烧多少火炭,要挖多少地,要割多少草,我一天忙不完的事情,还有心情嫖人家的婆娘?”说到这里他红了一下脸。周二婶子也把眼睛移到别处。
“你莫生气。”黄先人说。
“现在倒好,不直接说我嫖,说我帮别个嫖,我他妈傻子啊?我都能帮别个嫖,我还不如自己嫖。关键是老子没有嫖也没有帮别个嫖!他羊贩子要怪我,我能解释得清楚?”
黄先人和周二婶子刚刚说完他们先前的想法,杨铁匠就耐不住性子吼起来了,吼了一大串。
“想开点。人都死了。”周二婶子劝他。
“就是,人都死了。你还记得我上回给花针做迷信不?我说我看见了生魂。”黄先人问杨铁匠。
杨铁匠并不像花针说的那样烂醉,他其实没有醉,只是走路有些飘。他望着黄先人摇头,表示不知道。
“那个生魂就是王氏。她那天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她活不成多久。果然是这样。”
“那你咋不救她?”
“她的魂飘得太高,抓不回来了。”
“看来仙家也有办不成的事情。”杨铁匠哀叹道,“就像我打铁,有时候一块好铁,硬是打不出一把好镰刀。”
“你说得对。”周二婶子拍了拍杨铁匠的肩膀,又说,“你干脆合适点找个人算了,这样下去,哎——”
“我又不是一只种猪,母猪起草都要赖在我身上?”杨铁匠把酒葫芦摔在草垛上。黄先人又把酒葫芦捡起来还给他。
“你们!远点去玩!”杨铁匠挥着手,把我和花针赶开了。
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话,我没有听见。
秋天了,村里的人都在地里忙着收庄稼,王婶子的事情好像过去了,我也忘记了。虽然是秋天,她的新坟上却长了许多青草,还有一个新鲜的耗子洞,好像花针放在她家厨房草窝里的耗子都搬进了这里。王婶子像是死去多年一样,我有时候在她的坟墓边上割草,看不见一点供品。按照规矩,应该有点供品。
这几个月,花针不常来我这里走动,我也很久不去了。
杨铁匠的山洞里照常有打铁的响声传来,每天清早和傍晚,铛铛铛——沉重的声音,把太阳从早晨的天边敲出来,又在傍晚的黄昏里敲回去。我感觉杨铁匠才是仙家。我心里有个想法,希望找到一块好铁,让杨铁匠给我打个红彤彤的太阳。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守着这个太阳了。
但是前一个月,杨铁匠没有打铁。他只喝闷酒。
这段时间虽然平静,也有很多事情发生。这个村里的人讲什么事情不会背着小孩子,所以我总是放心地支着我的耳朵听。我听见周二婶子说,黄先人犯了什么法,被一个贵人用绳子捆着带去受罪了,因为他给那贵人的老妈请神,结果没有两天,那老妈子死了,贵人怪黄先人请错了神,害了他老妈的性命,要黄先人还他的钱。他给了黄先人很多钱。黄先人把钱花光了,他买了一匹黑色的瘦马,想着喂胖了再转手卖掉,赚一些草料钱。可惜瘦马还没有喂得胖起来,那贵人的老妈就死了。黄先人把瘦马指给贵人看,希望他可以接受那匹瘦马,拿它抵债,贵人不干。周二婶子说,黄先人一直在棺材前跪着,现在他就像一匹黑色的瘦马了。
我又听到张老爷子说,黄先人不是因为请错神,而是那贵人请他算命,问自己的官运可有得升,黄先人说有得升,给他多少多少钱,就帮他搭一座鸿运桥。可是那贵人没有两天就被降职了,他怀疑黄先人在鸿运桥上做了手脚。
这几个月来,我就这样想着这些杂事,很少去花针家蹭饭。我听见他家隔壁的小光头说,花针家杀了一头小猪,伙食好得很。
“你一贯都喜欢去蹭吃蹭喝,这阵子咋这么安静?”我妈在院坝里筛豆子。太阳下,她的脸色和暖,飘着笑。
“不想去。”我说。
“花针家要走了。你也不去看看吗?”妈抬起头来看我。
“啊?……”
就在这天下午,杨铁匠提了一挂小猪肉来我家。他是来和我的酒鬼老爸告别的。花针和大老熊都没有来。“小娃娃家,带着走人户啰嗦。操心。”杨铁匠说。
杨铁匠把那挂猪肉递给我妈,我妈把猪肉递给我爸,我爸用两根手指试着猪膘,“不错嘛,有点样子。”他赞美那块猪肉。猪肉被挂到墙上去了。它旁边吊着一把宽口的菜刀。
杨铁匠喝了半瓶子白酒,醉了。一喝醉,他就开始讲他的往事,他的往事我听完了一半,所以在他讲前半段往事,也就是他的大老熊出生的那一段,我就没有耐心听。我跑出去和一只小狗打闹。等我掐准了时间进屋继续听杨铁匠的故事时,杨铁匠正在抹眼泪。
“杨铁匠,你是杨铁匠,不是杨泥匠。拿出男子汉的脾气来,不要哭嘛。”我爸咂着烟,慢腾腾说。
杨铁匠摇一下头,他说:“男子汉的脾气,老母猪的价格!我算是看透了。”他抹了一把眼泪,又继续讲他的往事。
“……我跑进去一看,不得了,花针他妈已经不行了,我也着了慌,又跑去院坝里找接生婆。但是接生婆吓着了,又被我吼了几句,已经生气走掉了。”
“生下来没有?”我妈也紧张地问。
“废话!没生下来,那大老熊是啥?”爸瞪了妈一眼。
“娃儿是下来了。大人没了。——带着娃娃在老家淘了几年日子,抓罚款的又来了。因为我和花针他妈没有办结婚证。你们晓得,结婚要去盖几个章才算是合法的,你自己说结婚不算数,摆了酒席也不算,必须要有证明。我拿不出证明。更拿不出钱。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娃娃离开那里。听说现在又不抓了。”
“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咋又想起搬回去呢?”
“父母的坟,还有婆娘的坟都还在那里。虽说是死了,也不能那样丢着不管。再有就是……”杨铁匠无奈何的样子道,“这里要求上户,可是我来的时候,没有敢去迁户口。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能背着户口去哪里呢?去年我回去迁户口,那里的人换了一批,他们说我可以回去,现在村里正在搞什么种植,需要人手,要把户口迁走是不行的,因为那边给我派分了任务,要迁户口也得完成任务再迁。这样又何必呢?我任务完成了,再走,那不是傻子吗?所以说,等于是我自己跑回去找了个麻烦。我在哪里都找麻烦。你看,我接触的人都惹上了麻烦。黄先人,请神那个,现在请在拘留所去了。人家告他宣传迷信,迷惑人心。要是我不去请他来请神,也就不会有那些个罪名。还有王氏,我要是不答应去帮忙,她就不会想着来摸我的手,我要是深更半夜不去山洞打铁,我就看不到她的事情。现在倒好,她下土了,我还背着黑锅。那羊贩子见着我就跟见鬼一样,羊贩子的老妈见着我,也像见着臭虫一样。”杨铁匠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得太累的缘故,他闭着眼睛靠在墙壁上休息。
“那是要走了吗?”
“是。”
“什么时候走?”
“后天。”
妈说走得太快了,冬天走也赶得及。爸也说走得太快了。但是杨铁匠说不快,就得后天走。后天日子好。当初他选个黄道日子搬出来,现在还是要选个黄道日子搬回去。
杨铁匠跨出了我家的门槛。那块肉当晚就被炒吃了一半。
“前一个月上吊没死成,这个月要搬家回去了。这算咋回事?”我妈在饭桌上说。她又提起上个月杨铁匠喝醉了上吊的事情。
杨铁匠上个月用自己的裤腰带上吊,他的裤腰带是麻绳做的。在他家门口的那棵弯树上,他把裤腰带拴在粗壮的树枝上,然后把自己的脖子往绳套里一伸,就像只破鞋一样悬在那里了。大老熊和花针当时在煮饭,他们从厨房里跳出来,大老熊飞一样地爬到树干上,用一把菜刀砍断了裤带,杨铁匠从树上掉下来,摔晕了过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勒死自己就掉下来摔晕了。那棵树也被砍断了,说它沾邪气。这是花针在路上找猪草遇见我说的。就是因为杨铁匠上吊,花针和大老熊要看着杨铁匠,他们没有时间出来玩耍,而我也不敢去。
现在杨铁匠好多了。并且,一说到回家,他的精神也抖擞起来。虽然他跟每个人讲他的往事都要抹眼泪,但一说到要搬回老家,那眼泪就变成笑容开在脸上。
“说白了就是命苦的人。命苦的人喂猪都不肥。和蚂蚁一样。他也是喝醉了一时想不开,不是真的想死。”爸用筷子夹起一小块猪肉,突然又放下了。“你们吃。我饱了。”他离开了桌子。
“打铁的钱怕是进了周二的腰包了吧!是因为这样才想去上吊。可是他死了又能怎么样?那货本来就不是好沾惹的。她自己是有男人的,还干这种事情。诓干了人家的钱,又不能……”
“不要瞎说!周二婶子听见又得吵闹。”爸打断妈的话。
“我怕她么?”妈收起碗筷,端着簸箕进了堂屋,不再说话。
门口刮起一阵狂风,这个山沟里,很久没有刮风了。
杨铁匠带着花针和大老熊走了。因为知道他搬家的日子,我早早就坐在路边等他们。
太阳刚刚从山尖冒出来,杨铁匠就背着一筐行李来了,他是从太阳的正对面走来的,所以他的脸上被早晨新嫩的阳光打扮得很有生气。花针和大老熊跟在后面,好像是杨铁匠分散的影子,一边一个,一人背上背一床铺盖。还有,那只瘦狗也跟着。但是那只瘦狗是卖给别家的了,大老熊和花针一边走,一边还往回扔石头,想把那只瘦狗打回去。花针在哭。
“你要走了,我没有东西送你。”我说。
“我也没有。”花针擤掉一把鼻涕。
“快走,不然要错过车子。”杨铁匠在前面催促。我又想起他刚刚进村时问我的话,那时候我不懂铁匠是干啥的,现在我听惯了他的打铁的声音,就像我听惯了村子里的鸡叫和狗叫,他却要走了。我想着以后再也不能听到打铁声,再也不能见着我的朋友花针,眼泪忍也忍不住地落出来。
“你只要看见我家的瘦狗,就好像看见我了。我走了。”花针退着走了几步,最后转身大步地跟着杨铁匠和大老熊。他们很快走出村子,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他们留下的那条瘦狗在新主人的喂养下日渐壮实。它很有希望变成一条胖狗的,如果不是被新主人放进了锅里。周二婶子也吃了狗肉,一连几天都在人前回味,杨铁匠家的狗,肉真香!那张被剥下来的狗皮粘在那户人家的篱笆上,晒干之后,就被走街的货郎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