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
2013-08-07■严苏
■严 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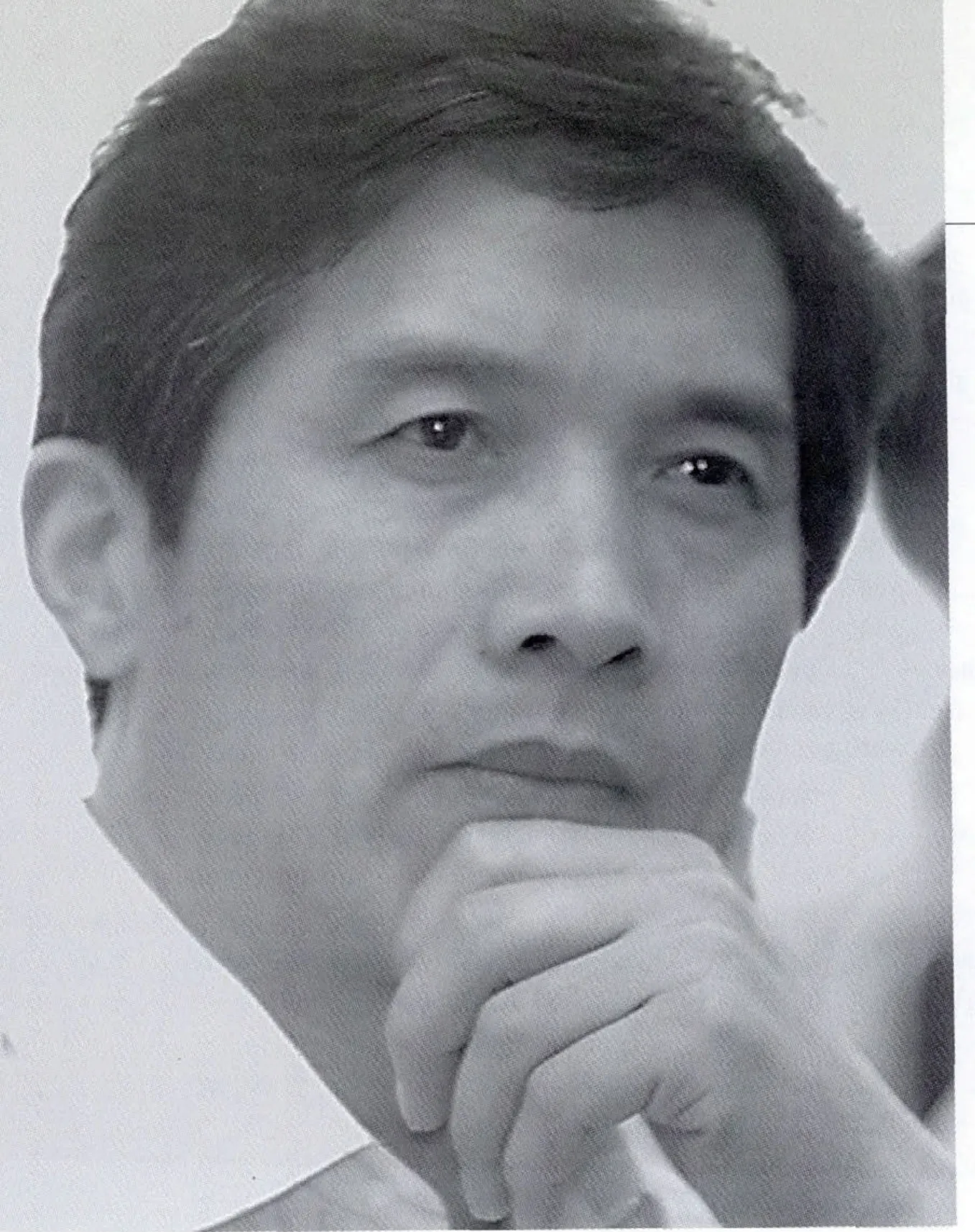
舅舅打记事起就没骂过天,这与外婆的教育有关。外婆在舅舅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要他不打爹娘,不骂天。舅舅记住了,这一记就是七十年。但今天破例了。早晨,舅舅起床后,听外面没有落雨声,鞋子都来不及穿好,趿拉着把门打开,伸出头想看看天,就这时吹来一阵风,雨星子劈头盖脸地打过来,舅舅的老眼被迷住了,鼻孔里也落进几滴雨,仿佛飞进一群小蠓虫。舅舅鼻孔痒得难受,连打几个喷嚏,眼泪鼻涕都出来了。舅舅抹一把脸,开口骂道:“这该死的天!这该死的天气预报!”
进入五月以来,老天就跟死了亲娘,整天哭丧着脸,眼泪说来就来,大时像瓢泼,小时像牛毛,一个月没瞅见过日头。这个月是小麦生长关键期,忙碌半年,收与不收都是这个月说了算。偏偏老天不帮忙,小麦抽穗、扬花、灌浆,正需要日头时,日头却躲在乌云里睡懒觉。舅舅每天定时收听天气预报,想知道黑云何时散去,日头几时出来。昨晚扭开收音机,听女播音员说今天雨渐止,转多云。舅舅当时想,多云就多云吧,总比下雨好。雨下得太多,沟满河平的,麦田里积了大量的水,想放无处去。舅舅看麦子站在雨水里,水已淹到脖颈处,麦穗随着风不停地摇晃,舅舅看那就是向他求救的一双双小手啊!舅舅急得抓耳挠腮,老脸皱得像苦瓜,肩上扛着铁锹,从田头跑到田尾,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子受煎熬。好比自己的孩子被狼群围困,而他却无法解救,舅舅的心像刀剜一样难受。撒眸四看,映入眼帘的全是茫茫雨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大伙嫌这一片地离家远,想抛荒。村干部不同意,于是用抓阄来解决这一难题。舅舅手气差,一家几口的地都抓在这里。这是命,怪不得旁人。舅母想埋怨几句的,一看舅舅阴得能拧出水的脸,赶紧把话咽进肚子里。舅母把抓阄的事悄悄打电话告诉两个儿子,两个小子无所谓,说话吊儿郎当的,他们对舅母说,地好也好,地孬也罢,他俩没工夫种。小子们给舅母算了一笔账,说一亩地最多收八九百斤小麦,按市场价一元一斤计算,也就八九百块钱。刨去种子、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开销,剩下小几百,不够一桌饭钱。碰上坏年成,麦子要是生了赤霉病、蚜虫啥的,那可要大减产,一季忙下来怕是连本都难保。他们动员舅母把地扔掉,就在家享老福,兄弟俩按月寄钱回来,保证不让她和舅舅饿肚子。舅母没好气道,才穿几天有裆裤子,就人模狗样地跩起来了!说后挂断电话。舅母把小子们的话藏在心里,没对舅舅吐一个字。
舅舅、舅母的两个儿子是敢吃螃蟹的人,多年前就去南方打工。起先是单个儿,待立稳脚跟,转脸回来接家眷,眼下小日子过得还不赖。知儿莫如父,舅母虽没把儿子们的话过给舅舅,但舅舅也能估计到。舅舅把两个小子看得像一碗清水,他们张开嘴巴,他就知道他们想说啥。小子们的心在外边,想叫他们在土坷垃里刨食吃,那是痴心妄想。不刨食就不刨食,舅舅本就没指望他们。离开胡屠夫,舅舅想他是不会吃带毛猪的。
天上的云像急行军,组成不同方阵,一阵过去,另一阵又急驰过来,始终不见太阳的踪影。中午时分云层又厚起来,天色阴暗,好像黑夜降临,竖起耳朵听,云层里“哗哗啦啦”的好像有流水声。舅舅仰起脸,有雨星子在飘,把脸挠得痒痒的。舅母说:“我开收录机听听,看有没有雨。”
舅舅“嘁”的一声,没好气道:“那东西说话跟放屁差不多,不灵!”
舅母说:“多数还是灵的。老话说的,‘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它真要变,天王老子都管不住。你骂人家,不是冤枉他们嘛!”
舅舅梗起脖子说:“气象台这帮混蛋一个个都是饭桶,他们端着国家饭碗,到月领薪水,却摸不准天上事,叫我说骂是轻的,往重里说应该下岗回家,给我修地球去!”
舅母不再言语,进屋忙自己的事去。
在家里,舅舅和舅母有着各自分工,泾渭分明,就像火车的两条钢轨,平行向前,永不交叉。具体说,就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舅舅有点大男子主义,在家里,他是甩手掌柜,油瓶子倒了不会伸手扶起,舅母要是怪罪他,他会振振有词地说,“老娘们的事别找大老爷们,自己扶去!”一句话把舅母噎在那里。舅母心里生气,却不能顶撞,因为油瓶还在那“咕嘟咕嘟”淌油呢,那流淌的可全是钱呐!舅母脚下生风,“噔噔噔”跑到灶台边去收拾。舅母一边忙碌一边生气,心里暗暗道:“哼!有初一就会有十五。咱走着瞧,你哪天用着我,我也拿捏拿捏你!”舅母说过狠话,心里感觉舒服一些,肚里的气仿佛戳破的猪尿脬,渐渐散去了。舅母没心没肺,还是老鼠性格,爪子落地就忘记自己曾起过的誓。在舅母看来,家庭就是一叶小舟,分啥舵手水手啊,保证小舟平稳前行,把日子过下去才是关键,讲究多了,就是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舅母这样想,就是僭越,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舅舅把舅母的行为看成是篡位,想参政议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舅舅对付舅母的最拿手办法是拔腿走人,把舅母一个人晾在家里。舅舅这一走就不见人影,他跑到镇街上和老熟人抽烟聊天,中午到小吃店下一碗青菜面,吃完了也不回。电子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地走,一圈又一圈,跑得挺欢。也就后半晌,舅母就火烧眉毛似地找来,像个犯错的童养媳,勾着头跟舅舅说软话。舅母不停嘴地说啊,说啊,好话说出几箩筐。舅舅听得很受用,舒坦得像喝下一碗糖开水,眯着眼把手里的烟抽完了,这才慢悠悠地抬起脸,睁开眼睛问:“告诉我,还多管闲事不?”舅母见舅舅开了尊口,头摇得像货郎鼓,赶紧回答:“不啦!不啦!再也不敢啦!从今往后我只管我的鸡毛蒜皮,不问你的家庭大事!”舅舅看舅母没敢掺假,说的话句句是真,这才慢条斯理地收起烟,站起来,把衣襟上的烟灰拍去,背着手往外走,边走边说:“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走到门口,见舅母还在原地待着,扯开嗓子就嚷:“还愣着干啥?回家啊!”舅母“哎”的一声跟上来,他们俩一个前,一个后,颠颠地回家去。
风波平息,舅舅舅母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舅舅的两个儿子从相亲到成家,都是舅舅一手操办的,舅母在幕后,只管后勤供给,接送亲眷等等杂活。
舅母把握分寸,绝不越线。
两个小子的婚事办得体面,也排场,好多年过去,舅母还感觉脸上有光,脊梁骨也挺得直。
舅舅干事喜爱铆足劲,出重拳。小子们结婚前一晚,他亲自上门,全村一户不落,把当家的都请来吃暖房酒,第二天正日又吃一顿。就是说,出一份礼喝两顿酒,这在全村史无前例。舅舅的豪爽、大方,全村无人能比。舅母今日想起这事,还要咂巴几下嘴,表示对舅舅的敬意。舅舅钱的来路,大部分是土里生长的;另一部分是两个儿子打工所得。舅舅常说,土地是他的小银行,更是养老儿,你想啥,撒几滴汗水,它就能给你长出来。
看来今年的汗水长不出粮食,麦子十有八九要泡汤。
这是几十年一遇啊。往年麦子抽穗扬花时也下过雨,但是下了两天,老天就天遂人愿地晴朗起来,就像天气预报说的,雨渐止,转晴。今年的天让人琢磨不透,像犯了肠道病,滴滴拉拉的,隔一会就下一场。
舅舅从屋里走出来,感觉雨星子密集起来,转眼间变成了毛毛细雨。舅舅不躲不避,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舅母见了说:“你转啥呀?老牛推磨啊?告诉你,衣服淋湿了没干的换了!”
舅舅叹息一声,进屋来。
屋子里湿度大,霉味一阵一阵往鼻孔里扑。舅舅坐下又爬起,把凳子放在门口,刚往下坐,老柜上的电话鬼叫似地嚎起来,把舅舅吓得一跳。舅舅知道电话是小子们打来的,所以不急着接。舅母见舅舅稳坐钓鱼台,催促道:“快接呀,那可都是钱啊!”舅舅睨视舅母,“嗤”地笑了,说:“外行了是吧?你给我记牢了,只要不拿起电话,电话局是收不到钱的!”说着起身向老柜走去。是二小子打来的,他说从电视里看到老家发大水了,问家里的几亩麦子遭淹了没有。舅舅不想让小子们操心,张口就说:“遭淹的是别人家,我们家好着呢!”二小子追问一句:“当真?我跟我哥都担心死了。”舅舅心里说,你们是担心,我可是痛心,痛到骨头里!但说出口的却是:“这还能有假?你们安心挣钱,安心过日子。记牢了,把孩子给我照看好,家里的事有我呢,不用你们操心!”二小子放心地说:“家里没淹就好。那我挂了啊?”舅舅说:“赶紧挂,我也挂啦。”临挂时舅舅又补上一句:“没事少打电话,有闲钱给孩子买东西吃!”说后才放下电话。舅母在旁边,电话里的话她一字没漏,全部听进耳朵里。舅母心存疑问,她弄不明舅舅为啥要对二小子说假话,淹就是淹了,又不是他们想淹的,瞒着干啥?舅舅走回门口,看着门外的雨,自语道:“远水不解近渴啊!”听了这话,舅母就明白舅舅心里想的啥了。是啊,两个小子要是天上的龙,知道家里遭淹了,张口就把水吸走。既然不是,你把实情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心挂两头,不安心做事。听说两个小子,还有他们的家眷,全部在流水线上干活,那活是一个萝卜一个眼,出不得半点差错的。
舅母抬眼看舅舅,心里对他又多了一份敬意。
舅母跟舅舅生活几十年,顺时也好,逆境也罢,从没听舅舅说过孬话,更没见他向困难低过头。
回想刚成家那会,舅舅兄弟俩分家,老屋一分为二,自留地也一分为二。舅舅在家排行老二。家分好后,老大对他说:“老二,那块地本来是我种的,耕田时我把肥料下进去了,你看咋办?”舅舅想了想说:“既然这样,你把肥料取走吧。”老大本意是想多种一季,待收了庄稼再把地还给老二,想不到老二让他取走肥料。老大闻后,点头说:“好。”说后就挥锹取土,把田里的熟土一锹一锹挖走。两天后,舅舅田里的一层熟土不见了。舅舅看着属于他和舅母的那畦坑坑洼洼的生土田,二话没说,挑起担子就下河塘。春种在即,舅舅要把老大取走的土还原。河塘土湿、沉,舅舅挑了一天,肩头先是红,后是肿,再后破皮出血了。晚上脱衣服,衣服和皮肤粘在一起,舅母用热水浸泡好久才把衣服脱下。舅母看舅舅的肩膀肿得像冻山芋,心疼得流泪,要舅舅歇几天,等伤好了再挑。舅舅说:“季节跟娘们生孩子一样,耽搁不得。”说后倒头便睡。第二天继续挑,连挑十天,田才与老大家的一般高。河塘土黑黑的,里面有腐物,挺肥沃,很适合庄稼生长。耕种时,有土坷垃滚进沟里,舅舅会当成宝贝似地捡回来——这土是他一担一担挑回来的,流失了实在可惜。当年播种的是玉米,虽然比老大家晚种几天,但出苗后没多日就追赶上。舅舅白天参加队里劳动,早晚到自家田里走走看看,有草就拔,苗密了就间。舅舅还别出心裁,在玉米的行距间种豆子,栽山芋。玉米在拔节长高,叶子又宽又肥,叶面发出蓝油油的光,仿佛利箭斜指天空。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开始扬花,腰间也钻出稖头,左一支右一支地别在腰间,像盒子枪,有的还别了三支,英姿飒爽,一副傲慢之气——好比孕妇,B超过了,知道自己怀的是多胞胎,昂首挺胸,把秘密嚷嚷出去。稖头顶上有一撮小胡须。当胡须由青嫩变成棕色,稖头就成熟了。第一年舅舅喜获丰收,产量比老大家高出一倍。舅舅和舅母偷着乐。有了粮食,舅舅碗里的饭由稀变厚,隔三差五还能做面疙瘩吃。
收了玉米,舅舅挥镰砍去玉米秸秆,阳光瀑布似地照进来,豆苗蹿高,山芋秧沿着土垄爬行。舅舅乐呵呵的,嘴巴整天合不拢。舅舅喜爱观察,发现谁家庄稼长势好,他就往那里跑,把好经验搬过来,这样做的益处是少走弯路,不受损失。舅舅常对舅母说,不会过日子看邻居。人勤地肥,舅舅耕种的几分自留田,长势一直比老大家好,老大一家看着既羡慕又妒忌。
土地承包后,舅舅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舅舅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分得十多亩责任田。两个孩子尚小,舅母要照管他们,还有一日三餐,田里的活基本是舅舅一个人干。舅舅是耕耙锄薅,播撒栽插样样在行。舅舅采取的是套种法,地一年四季不闲着。土地承包第五个年头,舅舅的大小子考入高中,二小子升入初中,两个小子玉米苗似地往上蹿。正是花钱的时候,舅舅突然病倒了。也不是啥大病,能吃能睡,看着跟好人一样,就是腿不听使唤,站起来先是疼,后是麻,想动一动,就是不听指挥。到乡医院,医生开来大包药丸,吃了不起作用,花了好多瞎眼钱。万般无奈,舅母陪他到县里的大医院去,先拍片,后做CT,两次检查结果一样,都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当即开单住院。舅舅拿着片子对着光亮瞅,眼睛瞅酸了也没瞅出哪里突出,哪里凹陷,一溜骨头跟肉案上的猪排骨差不多。舅舅把片子摇得“哗啦啦”响,问医生这病要命不要命。医生说:“不要命,但是比要命还难受!”舅舅一听不要命,就想回家撑着,要舅母扶他走。舅母做事从不越位,更不越俎代庖,但今天破例了。她没听舅舅的话,就在舅舅像落水般地伸出手,希望舅母搀扶他时,舅母毅然离开,走时竟然把手伸进舅舅的口袋,在舅舅毫无防范时拿走钱包,舅母跑出一阵风,到住院处把钱交了。舅舅像被施了定身法,想追挪不了步。大概是腿疼得厉害,他“咝咝”地吸溜牙花子,从牙缝里骂出一句:“臭娘们,反了你了!”话音未落,人就跌坐下来。
钱进了医院的账户,舅舅硬着头皮住下来。
这病有两种治疗方法,一是手术;二是推拿、牵引。舅舅见不动刀也能治病,当然选择了后者。
推拿安排在上午。来医院才知道,生这病的人挺多,推拿室里坐了一排溜,跟抢购紧俏物品似的。捺着性子等,快到中午才排上队,面朝下腚向上地趴在床上,医生的手便在病着的地方动起来,手法跟娘们揉面差不多。起先有点痒,继而是酸,酸得挺舒服。舅舅想酸的地方可能就是病菌驻扎的地方。他想请医生多用些劲,把病赶跑,或者就地弄死——弄死好啊,要不它还魂了还会祸害人。舅舅在琢磨说辞,腹稿还没打好,医生的手已停下,对他说:“到时了,下一位!”舅舅怕医生偷工减料,偷偷瞄一眼墙上的电子钟,刚好半小时——这时间是医院定下的。
舅母扶舅舅回病房。短短的路程,舅舅走出一身汗水。舅舅躺到床上,抹去额头的汗,叹息道:“我咋得这种病哦。这病是富人得的,我们耗不起呀!”
舅母安慰说:“心急吃不得热粥,既来之则安之吧。”
舅舅说:“眼看就要秋收,心难安唷!”
舅母说:“病根找到了,医生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舅舅把身体放平,直直地躺在床上——这样睡,腰才舒服。舅舅叹息一声,自语道:“听天由命吧。”
舅母没再搭理,拿上碗去食堂买饭,吃了饭就可以去牵引室牵引了。
来得正是时候,牵引室还有空床,不用排队就有位置。
牵引床头低脚高,人倒着睡,脚头吊一只沙袋——脚高,是防止牵引时人往下出溜。所谓牵引,就是将沙袋固定在患者的腰间,以沙的重量把身体往下拉,让突出的地方松弛下来,不再压迫神经。神经不受压迫,腿自然就不疼了。舅舅想,医生的话听起来有道理,细琢磨却有漏洞。你想啊,人睡在床上,身体被拉松了,突出的地方不压迫神经,腿自然成了好腿。问题是,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牵引,总要起来的。一旦起来,松了的地方就会还原。还原了,那病又会兴风作浪,为非作歹。舅舅把话藏在心里,待医生离开了才对舅母说。舅母听着有道理,但不敢顺着舅舅的意思来,于是说:“别瞎琢磨,你又不是医生!”舅舅摇摇头,说:“病魔未除,明摆着的道理!”
舅母说:“听医生的,不会错!”
舅舅就听医生的,上午推拿,下午牵引。一个疗程结束,病没见好转,钱却跟流水似的,全部淌进医院的账户。这天下午,护士通知交费。舅舅问:“来时交的1000多元,光啦?”
护士说:“差不多了,要续交,不交明天停止治疗!”
护士的话,像根棍子横在舅舅的耳朵里,舅舅听着难受,对护士说:“住院十天,我一没打针,二没吃药,一天一二百元,你这哪是开医院,是开旅店哦!”说后就吩咐舅母去办出院手续。
说出口的话,泼出门的水。舅母见舅舅态度坚决,知道劝也是口抹石灰——白说。于是就到住院处去结账。
舅舅和舅母是坐晚班车回家的。秋收在即,好多事等着他。舅舅顾不上自己的病,第二天就下田去。
腿还是疼。舅舅和舅母一起割稻子,腿疼了就蹲下来,一步一步往前挪。大片的稻子割倒在地,要用独轮车运回打谷场。舅舅忍着疼痛装车,车子刚装一半,舅舅的腿跟触电似地一阵麻木,人失去平衡,沙袋似地摔倒在田埂上。舅母跑过来扶他,被舅舅强行推开。舅舅咬牙站起,把车子装满,车襻套上肩头,挺身站立起来。腿疼不能走,他把车子压在肩上,昂首挺立,让腰承受车子的重量。舅舅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目张胆地与病魔叫板!豆粒大的汗珠从舅舅的额头滚下,经过面颊,蚯蚓似地钻进衣服里,不一会上衣就潮湿了。舅母捶胸顿足,请求舅舅放下车子。舅舅置若罔闻,就那么站着,直到人和车子一同倒下。晚上,舅舅来到打谷场,把稻子打了两个捆,用扁担穿上挑在肩头。舅母睡觉时不见舅舅,四处寻找,最后在打谷场找到他。还别说,舅舅的土办法真地管用,几天后,他的腿疼得轻了;又过几天,竟然不疼了。
舅舅对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对付办法。感冒发烧,嘴里寡淡不想吃饭,舅舅就强迫自己吃。三碗下肚,肚子里翻江倒海的,像用棍子搅,一阵恶心,舅舅想忍没忍住,“哇”地呕吐起来,吃下去的全部倒出来。过一会,舅舅端起碗又吃。再吐。再吃。反复几次,终于不吐了。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有了饭,就有与感冒对抗的力量。结果,舅舅的感冒不治而愈。
在舅母心目中,舅舅是个强人,从村东数到村西,无人能比过他。
舅舅虚龄七十三。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个年龄是个关,好多人就倒在这个关上。年前,舅母买块红布,一针一线地给他缝两条裤头,剩下的零布做一根裤带。舅舅不穿,也不扎红裤带,说大老爷们穿红戴绿的,给人看到,要笑掉大牙的。舅母劝说:“可不敢大意,穿上能避邪免灾呢。”舅舅说:“啥邪啊灾的?我种田吃饭,不偷不抢,不犯王法,谁还能吃了我不成?”舅母说不过舅舅,她把两件东西悄悄塞进舅舅枕头里,算是派上了用场。
野风吹老少年人。
在舅母眼里,舅舅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脸上的褶子一道连着一道,像新耕过的土地;腰有点弯;手大,骨节也大,看着像假肢;走路外八字,两脚一撇一撇的。舅舅平常都在田里,舅母看不到。自打下雨,舅舅被困在家里,舅母和他碰鼻子撞脸,这才有工夫打量他。
老牛闲下就倒嚼,为的是给养;舅舅坐下就打盹,给人感觉是累了,要睡觉,其实他是在养精蓄锐。只一会,舅舅就会睁开眼。眼睛睁开时,人跟充过电似的,浑身都是劲。舅舅站起来,摸起家伙就出门。舅母见了笑说:“做梦了是吧?雨还没停呢!”舅舅清醒过来,在雨里站了一会,才转身回屋。
雨是午饭时停止的,日头从云缝里钻出来,天地像拉开大幕似地突然亮堂起来。舅舅推开碗跑出去,打起眼罩往天空瞅,阳光把他的老泪都扎出来了。舅舅顾不上擦泪,扛起铁锹就走。舅母跟在后面喊:“你的饭还没吃完呐!”见舅舅不理睬,跑出门叮嘱他:“当心啊,路上滑!”
舅舅走在村路上,多日的雨水,把路基泡软了,走在上面像踩在棉花胎上。路面坡洼处,长出一层绿青苔,舅舅怕摔倒,把铁锹当拐杖,小步往前挪。云散得差不多了,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才一会工夫,路面被晒得热烘烘的,隔着鞋都能感觉到。下了村路,进入田间小道。道旁长着一溜巴根草,舅舅走在巴根草上,脚下稳当,不担心滑倒。
来到自家田里。田里站不住人,人停下就往烂泥里陷。舅舅撸下几穗麦子,在手心里搓,吹去麦皮,摊开手掌一看,全是秕粒,而且还生了赤霉病。看来今年是白忙活了。舅舅扛来铁锹,本意是把田埂挖开,让积水流出一些。天晴了,太阳晒几天,水很快就会蒸发掉,乐观看,多少能收获一些,不会绝收。现在看,自己估计错了。提步来到田头,放眼远看,舅舅就想把麦田改成水田,种一季水稻,把夏季损失弥补回来。另外,麦秸秆割回家,打不出粮食,晒干了可以喂牛,牛长肥了卖钱。想到这,舅舅的心像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芒种刚到,舅舅就开镰收割,把麦秸秆运回场上晾晒。忙了两天,两个小子带着家眷从南方回来。舅舅见了他们问:“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来干啥?”
大小子看一眼场上的湿麦子,说:“你在电话里说这里没遭灾,我们回来夏收啊!”
舅舅见老底被揭穿,也就说了实话:“我那是要你们安心挣钱,别惦记家!”
二小子抢过话说:“你把地扔掉我和哥就安心了!”
这话舅舅又不爱听了,他狠狠地瞪了两个小子一眼,骂道:“地把你们养大,你们却翻脸不要它,一对白眼狼!”说后,推起车子气呼呼地走了。
舅舅推车走出村,由大道拐上小道,抬眼往田里瞅望,心里的气即刻烟消云散,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脚下这片土地确是好哦,只要你舍得撒汗水,它就不会让你失望。好田是这样,田边地角也如此,你随手栽几棵瓜秧,丢几粒种子,到秋天,它就给你结一串胖瓜,长好多果实,叫你吃也吃不完。再往灌溉总渠那里看,水边的杂草长得高过人头,去年的还枯着,今年的又长出来,青的覆盖枯的,密实得像一道屏障,风吹不进,雨浇不透。这些东西砍回家就是好柴火,可惜无人要。现在烧饭不用柴火了,家家烧沼气,开关一扭,蓝火苗就蹿出来,一锅水眨眼就开,既干净又省事。想过去,青黄不接时,家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锅里没粮食,锅下缺柴火,走出去想拾一把都困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非昔比喽。舅舅慨叹着走到自家田头。放下车子,抓起一把湿土,用手掰开来,迎着太阳看,土黑黑的,发出一种油光,细瞅还有好多小细孔,跟发酵过一样。舅舅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知道手里的土劲头足着呢。土是熟透了的,就像好女人,男人一碰就怀孕。想到这,舅舅咧开嘴“呵呵”笑起来,自己骂自己老不正经。骂后动手干活。
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眷,把东西放回家里,转脸就到田里来。说到底还是年轻人啊,做事利索,多几双手做事,到晚上,田里就有了眉目。
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大小子把孝敬舅舅的酒拿出来,舅舅也不推辞,拧开瓶盖就往杯里倒。人老话多,喝了酒的老人话更多。两杯酒下肚,舅舅打开话匣子,掰着手指给两个儿子算细账,说他一年种庄稼收入多少,加上养的鸡啊鸭的,加到一块不比打工挣的钱少。说到这,舅舅把他的新计划说出来。舅舅说:“堆在场上的那些麦秸秆,那可全是宝啊。”
大小子伸长脖子问:“能派啥用场?”
舅舅说:“喂牛啊,那可是上等的饲料!”
大小子又问:“我们家养牛了?拴在哪里?”
舅舅喝下一口酒,用筷子点着大小子的脑袋,笑呵呵地说:“买啊!有钱啥都买到,瞧你笨的!”
二小子的眼睛本来就大,一听说要买牛,眼睛睁得更大,说:“大,你还没忙够啊?告诉你,我和哥这次回来,就是要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跟上时代!”
舅舅放下酒杯,眨巴着眼睛问:“做啥工作?又搞运动啦?”
二小子说:“下午说过的,丢地!”
舅舅没再骂,他笑着说:“一年两季庄稼我只种一季,就是听了你们的劝。你们得寸进尺,又要我丢地。真丢了,我和你妈喝西北风啊?”
二小子拍胸说:“放心,我们不吃,也要让你和妈吃个饱!”
舅舅冷起脸,声音也高起来:“宁可要人嫌,绝不要人怜。我和你妈有手有脚,不依赖你们!”
大小子抢过话说:“大啊!你都七十三了,还当三十七啊,不年轻了!”
舅舅冷脸说:“少废话!我把实话告诉你们,今年小麦绝收,我想种一季水稻,把损失补回来!”
两个小子,还有他们的家眷听了都急了,说:“栽水稻累死人,比种小麦辛苦多啦!”
舅舅对他们说:“那是老皇历喽。告诉你们,眼下水稻不用栽插,抛,站田头往里抛,跟打水漂差不多。”舅舅站起来,示范给他们看。
二小子看了笑说:“大啊,你莫不是说醉话吧?”
舅舅喝酒最怕人说他醉,二小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撞到舅舅的枪口上了。舅舅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他用手点着二小子,后又点大小子,气呼呼地说:“你俩明天就给我远走高飞,离开你们,地球照样转!”说后就离开饭桌,到灶屋打水冲澡去了。舅舅干了一天活,又喝了几杯酒,身子骨有点乏,早就想睡觉了。冲澡时舅舅想,明天要做的事是平整出一块田,把稻谷落下,等到秧苗长出半拃高,就可以往田里抛了。舅舅相信,这一季不会再绝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