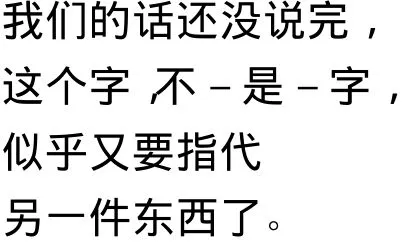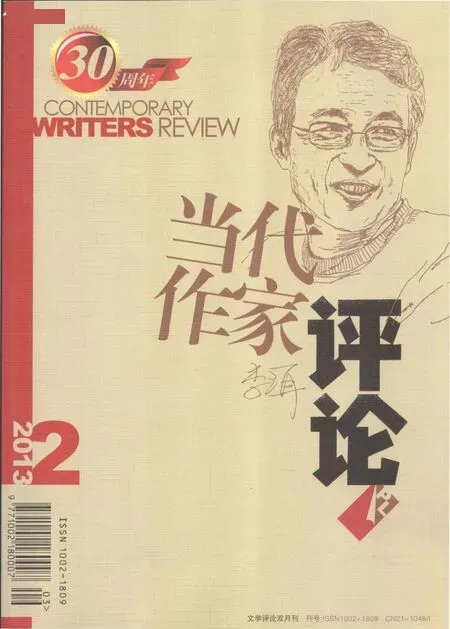抒情性与作为项目的诗歌——美国诗歌二〇〇〇-二〇〇九(下)*
2013-07-09迈克尔戴维森史国强
〔美〕迈克尔·戴维森 著 史国强 译
新近的抒情诗
我们讨论概念派、诗歌剧院、数字技术及新式类型,读者可能要问,更为传统的诗歌形式又将怎样,比如抒情诗。不少文章指出,抒情诗还远没有死亡,不过是发生了剧烈的嬗变,在更为灵活的身份印证方面,不断修改其原有的类型特点。斯蒂芬·波特(Stephen Burt)对过去十年他所谓的“新事物”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的抒情诗不仅与隐秘的自我相关,而且还可能从他人使用的言语中借来“腔调”。新式抒情诗的特点是,“严谨、简洁的描述、谦虚、低调的文字以及对物质的和社会的世界的那份执著,虽然诗人对这个世界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在雷·阿曼特洛特(Rae Armantrout)、乔恩·伍德沃德(Jon Woodward)、迪文·约翰斯顿(Deven Johnston)、约瑟夫·马塞(Joseph Massey)、伊丽莎白·特莱德维尔(Elizabeth Treadwell)和格雷厄姆·福斯特(Graham Foust)等人的作品里能找到上述特点。推崇经典的短诗和狄金生,接受来自威廉姆斯、格雷和客观主义者的暗示,这足以说明“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如关注日常生活的物质性,不同的是,新诗更强调接触目标后所创造的文字域(verbal registers)。请想象一下威廉姆斯《红色的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的第一行。
抒情诗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关的任何争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抒情诗的表现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二是抒情诗是不是没与社会性(the social)构成相反相成的关系,因为抒情诗总是引发“泪水无法承受的深刻思想”。然而,如阿多诺(Adorno)在《抒情诗歌与社会》里所指出的,要描述从物质性里摆脱出来的世界,这种欲望“实质上还是社会的”,因为“这种欲望要抗议人人痛斥的社会环境:敌视、疏远、冷漠、压迫”。面对几经创伤的历史,阿多诺视为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这十年的诗人却视为能指过程自身的无能为力。阿多诺将抒情诗的严谨与洗练视为个人反抗市场的退却,二十一世纪的诗人却从退却里发现了社会性的新形式。以最近的一首诗歌为例,马克·诺瓦克(Mark Nowak)在《停工关闭》(Shut Up Shut Down,二〇〇四)里借用日本的俳文形式描写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的散文式思考,之后用日本的俳句表现劳力外迁之后工人的不满。在诺瓦克的诗歌里,最后出现的俳句变成了小镇上失业的人数。《停工关闭》将抒情诗裹挟在社会环境里,所以,这首诗歌对内在性(interiority)的要求,先要依傍促成这一要求的社会影响,不然就无法存在。
与上文的角度稍有不同,伊丽莎白·威利斯(Elizabeth Willis)总结“新近抒情诗”的特点,称这些诗歌并非来自某种心理核心,而是来自其他地方:“这些新诗没有自我表现力,惟独自我思想或声音从未彻底摆脱语言的调性变化”。无论“其他地方”是一系列劳力外迁的社会条件,还是无法形容的神秘状态,总之,当下的抒情诗在描述精神变化方面,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一如更早的抒情诗或概念派。安德鲁·乔昂(Andrew Joron)在一首抒情诗里提到抒情诗的这一问题:
这里,第一人称还在继续:陈旧的发明,不知何故在其自身的速度里停了下来,其物资与自身又不相同——
其存在的时刻:一次没到来的运动的残片。
安·坎尼斯顿(Ann Keniston)在论述为“九·一一”创作的诗歌时写到这种经过思考的答复:其物资/与自身又不相同。坎尼斯顿注意到,世贸中心倒塌后出现了一大批诗歌,指出这些诗“描述近来发生的事件,描述的方式将注意力引向如何再现‘真实’这一问题上。但诗人们没有正面描述,相反,他们通过时间序列的不稳定性、距离、间接性及疏离感来观照字面说法和比喻说法的关系”。接下来坎尼斯顿继续探讨如何利用创伤理论,借助不同画面留下的记忆,在事件后人们经历危机的时刻,描写暴力事件发生后的迟来感(belatedness)。其实,“九·一一”之后大众诗歌的地位才是坎尼斯顿更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次事件促使诗人以公开的态度承认“这骇人的场面……/我们庞大的系统转而与我们作对”,这是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令人难忘的诗句。
作为研究项目的诗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唐纳德·赫尔(Donald Hall)、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丹纳·吉欧亚(Dana Gioia)与谢特利悲观地预言:没人阅读诗歌,但事实似乎与他们的判断相反。喜剧清口、轮流朗诵、赛诗会等表演形式出现后,诗歌读者未减反增。诗歌博客散发开来,将诗人变成了出版人、编辑、记者。马乔里·波洛夫(Marjorie Perloff)发现,到二〇〇〇年为止,罗恩·希里曼(Ron Silliman)著名的博客已被点击二百五十万次,他的网志提要(blogroll)与他人的一千二百个博客链接(Unoriginal Genius xi)。与诗歌相关的统发软件(listservs)、网站、聊天室有增无减,昔日锁在图书馆档案柜里的诗歌朗读录音材料,如今在PennSound、Ubu-Web、YouTube及其他网络服务器上唾手可得。自费出版、数字出版、短期数字出版等形式让 Edge、Meritage、Bookmobile、Salt、Jaded I-bis及Blazevox等不大的出版社在大社收缩的时候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克雷格·德沃金(Craig Dworkin)指出:“等新世纪来临时,诗歌因数量之大,已经走入死胡同:写出来的诗歌以几何方式激增,任何人读到的诗歌很快就能达到算数的极限。”结果原来出版方面的问题“从出版转向了发行……出版更多的诗歌集已不在话下,问题是如何把众多好诗……送到喜欢诗歌的读者手上”。所以互联网才成了“推出新发行范式的一大平台”。
批评家为诗歌的软弱状态感到惋惜,此时的他们很少哀叹读者的多少,他们说的是诗歌在文化领域风光不再,尤其是在学院派那里。所以我们没必要为缺少读者感到悲伤,最好还是改写一下下面这句话:“我读的诗歌没人读。”这个问题的部分成因是,有时诗歌与其他写作形式不分彼此,如把诗歌写成散文、说唱歌曲、新闻、批评理论,或者如在数字诗歌那里,还能把诗歌写成动漫或概念派艺术。不妨借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超越类型的倾向,这就是B.M.里德(Brian M.Reed)所说的“作为项目的诗歌”(Nobody’s Business)。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以“探索性诗学”的形式,用诗歌来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社会现象或政治问题。艾德·桑德斯(Ed Sanders)在这方面很有作为,一九七七年他与科罗拉多州的纳罗帕研究院进行合作研究,此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写作项目:杰克·凯鲁亚克空灵诗学学院(Jack Kerouac School of Disembodies Poetics)。在《派对》(The Party)里,桑德斯和他的学生们采访当地佛教社区和凯鲁亚克学院的成员,在采访过程中他们发现诗歌运动和精神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超出这所学院,演变成更大的矛盾。虽然引发这个研究项目的“事件”与诗人 W.S.默文(W.S.Merwin)和这所学院的创始人兼精神领袖 C.T.林珀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之间的矛盾有关,但这项诗歌研究还揭示出默文等主流诗人与凯鲁亚克学院麾下的反文化诗人之间更大的裂痕。这项研究推出了诗学、诗歌、新闻调查与人种学等超越类型的作品,其影响波及后来的不少人,因为他们希望让更多的历史和政治问题走入诗歌。
将诗歌作为项目来研究,这一倾向在詹纳·奥斯曼(Jena Osman)的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人物》(The Character,一九九九)、《加星号的文章》(An Essay in Asterisks,二〇〇四)和《网络》(The Network,二〇一〇)等作品里,她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混淆诗歌与论文的定义,将诗歌与学术研究合二为一。她的文本里点缀着视觉材料和不规范的页面,这些杂糅的作品已经抵达其他话语最幽暗的角落,如戏剧、化学、最高法院的卷宗、词源学、美国史、城市研究等领域。
在《网络》里,奥斯曼用一首有关投机的诗歌来探究历史与词源的轨迹。一些文字从好些语言派生出来,经过追根溯源,她发现一些词义意外地残存下来,使用至今。从词源的角度梳理文字,不难发现美国商业史、奴隶贸易、对外拓疆的根源所在。这方面奥斯曼的作品并非绝无仅有,此前查尔斯·欧尔森(Charles Olson)的《极限诗歌》(Maximus Poems)、苏珊·豪(Susan Howe)的《新教徒的纪念馆》(Nonconformist’s Memorial)、T.H.K.车(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听写》(Dictee)等,也是通过真实证据、视觉媒介、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来达到借诗歌考问历史的目的。在奥斯曼的作品里,各个部分(她称之为“网络”)都要安排一个字的变迁图,如,她对finance(金融)这个字追根溯源后发现,fine、finesse、fin及 finish在词源上与finance一脉相承。一个字的变迁引发出与金融资本相关的种种联想——荷兰人在纽约的殖民、蔗糖贸易及最后的奴隶制。每个网络写的都是奴隶制在新共和国建立时扮演的角色。在名为“金融区”的那部分里,奥斯曼望着早年华尔街的地图、那里的街道及当年的机构。奥斯曼利用各种原始材料(华盛顿·欧文的《纽约外史》、阿尔伯特·乌尔曼的《纽约史要览》、詹姆斯·库珀的《安家》),从历史的角度探究美国为人所诟病的投机性“投资”,因此,这一部分既是对国家起源的历史研究,也是对当下经济危机的评述。奥斯曼的作品虽然写的是金融资本、种族与城里人的投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她的研究从来也不是颐指气使的或说教式的。相反,她总是在官方史料掩盖之下,通过寻找一个字的来源,揭开金钱、种族和帝国的秘密。
新世纪的诗歌
杰罗姆·卢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完成的一大工程《新世纪诗歌》(Poems for the New Millennium)与二十世纪末的诗学传统大唱反调,重新描绘出一幅现代主义的版图,因为其中收入的先锋派诗人选自世界各地,不仅仅来自美国和欧洲。这部诗集在混合的艺术类型、人种学诗学、不规范的类型,乃至诗人的身份等方面也有所兼顾。在如何评价新世纪诗歌这一问题上,我们这卷《当代文学》专辑,是《新世纪诗歌》的继续。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已经触碰到新诗走向的脉动,他们的文章使我开始反省我与诗歌的关系,因此,当我为特刊挑选文章时,尤其希望收入这些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诗歌,就其构成、美学及走向来说,五光十色,特刊所选文章不可能将其一一囊括进来,但总的来说文章所指仍然是文化全球化和知识数字化造成的挑战。
特刊收入研究伤痕诗歌的文章,不过两位作者的写作角度有所不同。卡普兰·哈里斯(Kaplan Harris)写的是新叙述写作如何应对艾滋病。他先在文中回顾同性恋诗人的作品,虽然这些诗人占据着不同的美学领地,但诗歌所指无一离开艾滋病。之后他开始剖析新叙述美学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抗艾滋病运动才有了新叙述美学,作者以旧金山为例,尤其是凯文·基利安(Kevin Killian)在《阿金托系列》(Argento Series)里描述的旧金山,这部作品从杰克·斯派赛(Jack Spicer)的“系列诗歌”那里借来灵感,而“系列诗歌”又取材达里奥·阿金托(Dario Argento)的恐怖片。如哈里斯所说,这些诗歌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其他诗人说的话或作品,一般来说他们又是死于艾滋病的诗人,所以这些诗歌以文字的方式验证了斯派赛的提法:幽灵出没的诗歌。但这些幽灵是诗歌作者的朋友和同伴,因此幽灵在“诗里”“诗外”同时徘徊。
坎尼斯顿在文中承认,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基地组织发动攻击,以此为题材的诗歌深受影响,但这些诗歌还不足以表现悲伤的情感或愤怒,不过是在述说诗人自己的迟到感。从文学的角度表达迟到感,我们大概对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俄狄浦斯论”更为熟悉,他说“强大的诗人”确实要挑战他们的文学之父。坎尼斯顿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来自弗洛伊德的nachtraglichkeit,或“迟后的行为”,指的是对暴力事件迟后的记忆。她借用创伤理论分析了众多“九·一一”诗歌中的几首,作者是品斯基、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uck)、罗伯特·海斯(Robert Hass)、本·勒纳(Ben Lerner)等人。坎尼斯顿分析以美国历史事件为素材的诗歌,与此同时,她还探讨了诗歌方面更大的话题:大众诗歌的可能性及诗歌语言的角色。她提出的问题是,诗歌能不能或如何才能“再现这些打击及诗人的搏斗,进而让诗歌散发出意义来,此外,诗人如何驾驭诗的意象和比喻才能形成上述张力,这后一点尤为严峻”。
双子塔和五角大楼被攻击之后,诗歌领域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斯帕尔分析了这次民族主义的成因,再次提到“九·一一”的影响。这一次的民族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奥登(Auden)的《1939年9月1日》广为流传,网站和博客上涌现的大众诗歌,以及大众诗集的不断出现,这些足以证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斯帕尔希望透过这一现象,在艺术不断私有化的时代,研究大众诗歌的地位。她发现,克林顿执政时期联邦政府对基金会、艺术研究院所和文学机构的资助被削减下来,等到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公私开始联手,出现了她所说的“民族主义私人化”这一形式。乔治·尤迪斯(George Yudice)对公私分家大不以为然,斯帕尔引用尤迪斯的话说:“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公与私是相互开放的。”此外,斯帕尔还就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例子,她是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诗歌的泛滥,以及后来的诗人在英语之外进行的外语写作,这些诗人拥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显然,“他们试图摆脱民族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英语扩张,目的是‘疏离’英语”,暗指“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推行的所谓统一的民族主义。约翰·巴尔(John Barr)的诗歌《恩典》(Grace)就是用“另一个”英语写成的。巴尔既是诗人又是企业家,兼职诗歌基金会主席,因此也是露丝·莉莉(Ruth Lili)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馈赠的受益人。这首诗几乎是以加勒比海方言创作的,揭露出“一个帝国奇特的断言,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文学里,这个帝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大胆地为帝国辩护,而且并不掩饰这一目的”。巴尔身兼银行家与诗歌经办人,这一角色在一首诗歌里凸显出来,因为这首诗从种族成见的角度再次强调了民族主义。
坎尼斯顿对复杂的人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此相同,在抒情的“我”被人怀疑的时代里,J.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通过研究抒情作品,又继续了坎尼斯顿的关注。拉马扎尼发现,后来不少诗歌自称是“歌曲”,虽然这些诗歌与各种音乐形式存在赓续的关系,但阿曼特洛特、帕尔默、T.莫里斯(Tracie Morris)、弗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J.格雷厄姆(Jorie Graham)、凯文·杨(Kevin Young)及其他一些诗人写作的领域更为宽泛,所谓音乐不过是他们诗歌中的元素之一。按照 M.M.巴赫金(M.M.Bakhtin)的理论,诗歌是独白,是一元的,但拉马扎尼证明,上述诗人不仅使用多种语言,从一种口语逃到另一种口语,而且还借用他人的语言。他指出,阿曼特洛特在诗歌里填入歌词,而且还要让读者知道这些歌词有不同的读法。在阿曼特洛特的作品里,不同的发音要么相互覆盖,要么相互碰撞,以此来佐证作者对独白的怀疑。特兰斯·海耶斯(Terrance Hayes)的《希普逻辑》(Hip Logic)借助说唱(rap)和嘻哈构成诗歌的主题和强音节。虽然海耶斯的美学渊源有所不同,但其作品也在借用说唱里的歌词,同时还要捉弄嘻哈风格里的男人姿态。
B.M.李德(Brian M.Reed)撰文《千禧年后的诗歌与改道的语言》,作者在文中以借用与拼贴为例,继续探索拉马扎尼提出的语言杂糅(heteroglossic)的可能性。李德指出:“语言改道后的诗歌”在现代派那里早已有之,从庞德、查尔斯·莱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到苏珊·豪,他们在语言上无不以变化为要旨。但这些先行者与后来的概念派有所不同:双方的主体性在话语上嵌入得深浅不同。根据李德的分析,在现代派那里,拼贴发音的目的是要寻找以鲜明的语言表现特定历史的可能性,诗人频频接触的是“数据,也就是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通过电视、电话、MP3、电子书、电脑显示器传输出来的信息。”
李德在文中提到的实验性写作被非洲裔美国诗人用来达到不同的目的,因为这些诗人要面对漫长的种族压迫史。E.索克利(Evie Shockley)在文章里首先讨论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如何在《潜入沉船》(Diving into the Wreck)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借用沉船来指代父权弥漫的历史并将这艘船定义为奴隶船。罗伯特·海顿(Robert Hayden)的《贩奴航线》(Middle Passage)是这种历史反省的另一样板。之后索克利又开始分析道格拉斯·卡尼(Douglas Kearney)和M.菲利普(M.NourbeSe Philip),他们的诗歌《水中黑鬼的游泳歌》(Swimchant for Nigger Merfolk)与《轰!》(Zong!),讲述了“贩奴航线在方方面面造成的仍然发生的伤害与牺牲,断裂与缺席”。我在文中提到诗学断裂,坎尼斯顿提到诗歌里的迟到感,在那些连接历史伤痛与时下种族问题的诗歌里比比皆是。
这次蒂莫西·余(Timothy Yu)撰文分析亚裔美国诗人,其中反复提及历史问题。他注意到金咏梅、勃森布鲁格(Berssenbrugge)、李立扬(Li-Young Lee)及姚强(John Yau)等诗人形成的合力,暗示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裔美国诗人的实验,可能走入各不相同的方向。他对金咏梅研究种族问题的文集《平民》提出了合理的概括,因为其中不少文章“使以语言为代表的共同空间成为可能,但在文本那里,语言是为统治与生存不断挣扎的地方”。蒂莫西·余格外关注金咏梅对语言物质性表现出的兴趣,对散居海外的鲜族人来说,语言物质性关乎他们能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被接纳为美国公民。语言与民族属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林丁(Linh Dinh)、芭芭拉·雷耶斯(Barbara Jane Reyes)、C.P.洪(Cathy Park Hong)及林覃等人关注的话题,他们无一不把语言问题视为少数族裔完成社会化的工具。
诺伊尔从表演性的角度分析近来的拉丁裔美国诗人,指出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诗人所关注的是身份政治,如今他们已经转向交叉的、跨文化的话题。诺伊尔发现,老一代拉丁裔诗人强调“身体”的能见度,生怕读者不知道与压迫、斗争、移民有关的历史和地点。新世纪的拉丁裔诗人不再为传统所累,诺伊尔借用物理学上的反物质来讨论他们的身份,指出“那里没有基础;在身份的下面是差异,最终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other)”。诺伊尔将他们的诗歌视为他所谓“危机身份”的所在地,在这个身份的掩盖下,诗人们充分利用种族混合这一传统和移民经验,借助数字与网络实验,合作及其他形式进行诗歌创作。
丽塔·拉里(Rita Raley)在她的文章中指出,数字诗歌来到世上,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历好几次大变化。如果说早一些的艺术形式是与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网络结构发生联系的话,那么新一代诗歌似乎更倾向“自我反省,对自己在网络社会里的角色与功能,批判精神更强烈”。她从大卫·约翰斯顿〔David(Jhave)Johnston〕那里借来的例子说明,不同的媒介成分(文本、意象、视频、声音、数字)合成起来,创造出一个她所谓的“独特的媒介生态”。这一生态表明,数字诗歌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就要携手联合,大概这次联合令人颇感意外,但也从另一面说明,数字诗歌与生态批评,谁也不怀疑相互关联和杂糅共生。原来的数字媒介以关注自身运作为特点,与此不同,新近的作品开始面对环境与生态问题。约翰斯顿的诗歌就写到最近的环境事故——从深水地平线公司的石油泄漏写到福岛核反应堆外泄。《真相》(Sooth)是在蒙特利尔生化工厂之内创作的系列视频诗歌,如拉里所指出的,模拟的生态系统使人联系到对视频文件的操控。二进位的机器和大自然在作品中被解构,因为这些作品同时“清晰地表达了存在的独一性(singularity)与观照他者的道德要求”。
脚注:论旋生旋灭
我开始学术研究时,先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管理一大批当代诗歌档案。与身边的原稿为伴,总有稀奇的经验发生,我发现这些速朽的纸页和信件,一经我的触碰,就加速了原件的朽烂,哪怕是一点点地朽烂,这一发现更令我感到稀奇。诗歌写在低廉的大裁纸或学校里用的笔记本上,纸张已经开始变质,虽然我格外小心,但是一经触碰,放入无酸的赫林格文件盒内,纸片就开始脱落。这些诗歌大部分来自五六十年代,或是打在或写在那些纸上,对这批诗歌来说,上述经验也是为了让诗歌流传下去,不过是有点滑稽。这批战后诗人的作品,所关注的是经验的旋生旋灭和生活中感悟的可能性,以各种下划线、行距、日期来面对时下的问题。战后诗歌探讨社会不可逆转的恶化,所以,还有什么比使其速朽更合适的吗?
另一稀奇的时刻——在其他从事档案研究的人那里,这时刻可能很普通——是阅读诗人的通信。一个诗人写给另一诗人的信,我打开阅读,不免有震惊之感,这终究不是让外人过目的文字。不过,倾听(或目视)这位诗人不设防的、直接的称呼,这其中又少不了因偷窥引发的魅力。还有,与实实在在的纸页接触,也能发现诗歌要素的特点,因为此时的诗歌已是高度的个人化,几乎是无话不说的,然而,这信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所以才感人至深,如杰克·斯派赛写给朋友的诗,或弗兰克·欧哈拉(Frank O’Hara)写给乔、比尔、沃伦或格瑞斯的信。
上述经历与我阅读这一辑的文章联系起来。旋生旋灭、迫不及待、亲密无间,这些话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问题以更公开的形式再度出现——仿佛公与私之间再无障碍可言,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食谱或无意听见的对话,已经离开家庭的领地,进入公共领域。那么,在电子邮件和社会网络盛行的时代,又如何理解“个人的”这一问题。若是诗人不保存电子邮件的话,写下来的通信就没法变成资料被人研究;诗人的通信就可能被外部驱动器所取代。一旦纸质的文本被数字文档所取代,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又将如何改变数字技术才能读到必要的信息?社会网络、电子邮件、超大数据库出现之后,人们开始从公共关系的角度进入原来的私密空间,如,你可以与从未见面的人成为“朋友”,读者可以联络他阅读的诗人,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发表的意见,可以变成聊天室里激辩的话题。
我用稀奇两字描述诗人手稿将要发生的变化,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数字时代如何定义那些旋生旋灭的现象,我希望那些稀奇的现象能作为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再次回来,所谓稀奇的现象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与此同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同的表达形式凭借科技将原来地理上和文化上分开的诗歌连了起来。YouTube、Skeype及其他视频技术使诗歌传播在残疾的和失聪的诗人那里成为可能,此前这些诗人还缺少艺术平台。诗人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电子邮件相互见面,这些渠道又在官方的出版机构和学术论坛之外,构成了另一个活泼的话语空间。社会运动利用这些技术开拓新式的反公众(counterpublic)领域,这种能力把政治运动的阵地移到了党派之外。这些分散的文化生成形式能不能摆脱商业化的和政府的掌控,仍然是个问题。或者,如帕尔默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