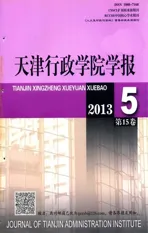英国保守党语境中“大社会小政府”的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
2013-05-16成晓叶
成晓叶,凌 宁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 南京210004)
一﹑英国“大社会”的起源、内涵与发展
(一)“大社会”计划产生的背景与起源
英国保守党于2008年6月发布了《一个更强的社会:21世纪的志愿活动》绿皮书。在2009年的秋天,戴维·卡梅伦在雨果·杨的讲座上阐述了“大社会”的概念,这次演讲明确了志愿活动与社区组织在实现“大社会”这一理念中的作用。“大社会”也是保守党2010年竞选的重要砝码。戴维·卡梅伦在雨果·杨讲座上发表了第二次重要的演说[1],该演说同时也构成了保守党的部分竞选纲领。2010年5月由保守党和自由党首相与副首相参加的联合政府政策声明就包括发布“大社会”的议程[2]。
“大社会”是英国2010年保守党大选宣言的标志性口号。《泰晤士报》将“大社会”口号称为重新塑造政府职能以及解放企业家精神的一个进步举动。现已成为保守-自由党联合政府协议中立法程序的一部分。“大社会”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将权力授予地方百姓和社会的政治环境,打造一个将权力从政治家让渡给人民的“大社会”计划。戴维·卡梅伦钦点作为华裔的爵士韦鸣恩来为“大社会”计划提供意见,外界也称他为“大社会沙皇”(Big Society Tsar)。而实际上真正在卡梅伦背后创造“大社会”概念的是保守党智囊——菲利普布隆德(Phillips Blond)——《每日邮报》称他为戴维·卡梅伦的“哲学之王”,《英国的电讯报》也称他为戴维·卡梅伦“大社会”计划背后的驱动力量。
(二)大社会的内涵
在大社会的项目中包括建设大社会的银行以及建立公民服务机构。“大社会”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给予社会更多的权利(强调地区主义以及权力下放)。大幅度地改革规划体系,公民更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所在地的发展状况;在社区中引入新的力量以挽救那些面临关闭的地方设施以及服务部门,给予社区接管国有服务业的投标权;培训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
2.鼓励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社区(强调志愿精神)。以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志愿者活动融入社区,包括推行一个全国的“大社会日”且将公民服务人员的评价系统作为关键要素并入其中;采取一系列鼓励慈善事业以及慈善行为的活动;建立国家公民服务机构。这项标志性工程会提供一项长达16年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成为积极并且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具有的技能。
3.将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积极推进行政权力以及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提高地方议会的综合能力;废除区域空间战略(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将住房与土地规划权的决策权交还给地方议会。
4.鼓励合作社、互助性组织、慈善机构以及社会企业的参与。将合作社、互助组织、慈善机构以及社会企业的运作与公共部门的运行相结合;授予公众部门的工人新的权利,形成雇工所有制的合作社以及接管他们所从事的服务业。这将会让上百万的公共部门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雇主并且有助于刺激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用休眠的银行账户建立一个大社会银行,这也能为社区组织﹑慈善机构﹑社会企业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5.公布政府数据,将政府数据透明化。提供“数据获知权”使得政府控制的数据集能被公众所利用,并且定期发布数据信息;授予警察每月公布地方犯罪数据的权利,因此公众能够了解到当地社区的犯罪情况,警察也要公布抓捕罪犯的情况。
(三)大社会的思想来源
那么“大社会”的构想来源于何方呢?戴维·卡梅伦常说“社会从来就是存在着的”。但这种说法听起来是社会的构成建立在公民之上,这与保守党传统的自由论相抵触。保守党在另一方面表示“大社会与国家的概念不是一回事”,而这一说法又很难解释新保守主义的家长式作风。由此同时又产生一个疑问:究竟“大社会”概念如何与保守党政策相结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的年代。在《利维坦》一书中,个人在寻求国家政府庇护的过程中丧失了自由。但是没有政府的话,人民处于一种生活孤独且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生活状态。社会契约是个人将自由永久性地让渡给国家来获得社会秩序和确定安全边界的一种理性选择。
《利维坦》虽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霍布斯的理论仍然有三个漏洞。首先,他有意忽略了人类感情、意愿以及兴趣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在他极端的个人主义学说中试图在个人之上寻求一种“公共意志”而忽视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媒介机构;最后,他在推崇国家的道德假定下抵制个人主义的概念。
《利维坦》问世一百年之后,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埃德蒙·伯克深入地批判了他的理论。埃德蒙·伯克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人类的自然状态独立于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公民社会。
霍布斯同时也忽视了相互信任、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埃德蒙·伯克则认为这三个概念是人性构成的基本要素。霍布斯强调个人意志的卓越作用,埃德蒙·伯克强调在公民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是天然互惠的。在缺乏约束的状态下,霍布斯视自由为消极因素。埃德蒙·伯克则认为自由作为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机能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社会”计划是埃德蒙·伯克针对霍布斯理论进行的深思熟虑的批判,修补了霍布斯遗漏的三处地方:相对于霍布斯,埃德蒙·伯克更关注人类的各种才能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将更多的关注视角聚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机构;更加关注社会与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任由国家摆布[3](p.95)。
二、英国“大社会”的主要特点
英国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从提出到践行均充满了不同于工党也异于撒切尔夫人时期保守党领衔的英国政治,可以说是英国政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做法,因此“大社会”计划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属于英国政党政治的产物
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政治做出了深刻的改革。她成功地削减了工会的力量,使工会彻底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量。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撒切尔夫人毅然地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主义理论。推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史称“撒切尔主义”[4]。而1997年5月1日英国大选之后,经托尼·布莱尔改造后的“新工党”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保守党,结束了18年的在野生涯。这也是二战后历次大选中工党所取得的最好的成绩[5]。而托尼·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便是走一条既不同于一元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元社会主义而又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保守党上台执政的前提是必须要填补之前工党政府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结合之后的空白地带。在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VS大政府”的演讲中,他提到这个国家现在被很多的问题所困扰:我们被“大国家”所困扰,受限于经济的迟缓增长,身上的债务让我们举步维艰,且生活在一个不能为我们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下[6]。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提出“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尝试着在个人和家庭的基础上鼓励人们独立自主。戴维·卡梅伦在他的主张中加入了“社会”的字眼,以此与撒切尔的主张相区分。然而戴维·卡梅伦对“小政府”偏爱的一面可以算作是撒切尔主义的一个继承者。“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提倡自由价值观,推行“民众资本主义”,用“小政府”来代替“大政府”,只是这种单位从个人和家庭转向了社会,但他们对自助意识的推崇也是显而易见的[7]。
(二)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意识形态自从被引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共同体这个领域以来,其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点就越明显,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政党重视意识形态是由于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法律、道德等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意识形态有助于阶级等共同体及其政治行为赢得支持,获得普遍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组织、创新的能力[8](p.7)。诸如撒切尔夫人与托尼·布莱尔这样的领导人将个人与意识形态的术语结合起来。因此,19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以及90年代中期的布莱尔主义便油然而生,撒切尔夫人与布莱尔都将这种意识形态的良知与他们的政党和政府糅合在一起。他们的远见卓识帮助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披上了一层道德使命的外衣,同时也让他们的政治追求的方向变得明确。然而并非每一个政治家都能将意识形态与政党的宣传运用得惟妙惟肖,戈登·布朗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致力于追求一种聚合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使他的声望受损也让他的执政有时看起来像一艘无舵的小船。戴维·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的构想正是基于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哲学,同时将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让渡给公民社会[9]。
(三)更广泛的权力下放
“大社会”的构想在戴维·卡梅伦作为反对党的领袖时就已经提出。2010年,戴维·卡梅伦带着“大社会”的口号走马上任。解读“大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在戴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的一次演说中,他着重强调了社区与志愿组织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工具,同时建立“大社会银行”为这些组织解决融资问题。完善社区志愿组织以及建立“大社会银行”都是英国政府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下放给英国公民的做法。在2010年5月政府发布的《构建大社会》报告中提出:“我们希望可以给公民、社区以及地方政府所需要的权力以及信息,让他们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让他们来建立一个理想中的英国。我们需要让家庭、网络、社区这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变得比以前规模更大、功能更健全。只有公民和社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多的责任,人们才能平等,社会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10]这份简短的报告也是旨在将政府权力下放到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同时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委托给地方政府。这种权力下放不同于托尼·布莱尔时期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地方议会,而是将权利交回公民的手中。
(四)自由市场与社区的有机结合
英国高校与科学国务大臣大卫·威利茨(David Willitts)认为当代保守主义的目标是将自由市场与社区相结合。虽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认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会以自私和贪婪取代公众对传统社会道德的尊重。资本主义越成功,传统道德受到的侵蚀也就越严重。而威利茨认为市场与社区不但能够相互兼容,同时双方的理论也能相互支持。
首先,市场经济中需要业已确认的社会信任网络[11](pp.80-97)。市场 机 构 有 时 受 到 国 家 的 监管,但在很多情况之下市场交易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管制与计划会破坏社会关系并且时常以国家导向来代替社会关系。市场机制的效应更能推动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因为买家与卖家在不停地进行交易的同时需要将市场和信任作为交换的一种工具。所以,市场便成了让人类从只为自己思考到为更广泛的社区利益思考的最有效转化媒介。
其次,传统观念和社区在定位消费者的动机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消费者表达他们自己的喜好。而这些喜好是由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市场在更广泛的集体智慧结晶下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此外,一些已有的社会习惯也划分了市场的疆界:“有些商品是你不能销售的,而有些商品是不允许销售的。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由一个社会组织来维系去支持这种市场经济”[12](pp.52-59)。
最后,威利茨提出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潜在经济变化将会形成新形式的社区。威利茨提出了一种共有社会的理念并且强调社区的新形式是由经济嬗变所产生的。比如工人社区的兴起源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浪潮。这些由经济变化带来的社区变化同样也会形成这些社区所独有的传统与机构。这类似于威利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观点,即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逐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新形式的社区。
三、小政府大社会在英国遇到的阻力与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期,面对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失灵等情况,保守党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领导人对英国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时隔14年之后,卡梅伦依靠“大社会”击败工党重新执政,然而两年后保守党的“大社会”计划逐渐从云端落到地上,它的神圣光环也慢慢褪去,而普遍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与“大社会”走到了一起。
(一)志愿精神难成“大社会”计划的顶梁柱
在21世纪,英国公民对社会活动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消极。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罗伯特·D·布坎南教授(Robert D.Putnam)在他的一本描述美国公民生活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以及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后传统》(1992)书中都呈现出一种公民不情愿参与公众事务的状况。在这两位学者的假设中,现代的公民可能更不愿意为了一个特定的集体意识而聚集起来。相反,他们可能会加入那些具有个性独特兴趣广泛的团体之中。英国前议员,同时也是欧洲事务评论者的大卫·马宽德(David Marquand)认为公共生活早已侵蚀殆尽。由于大部分的物品市场可以供给,因此公民没必要再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或去领取公共物品。
虽然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公民政治参与度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仍然不及前十年下降的幅度。十年前,尽管在工党执政时期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强化,但是公民的权力越来越小而且他们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也在降低。然而,英国公民调查表明前几年的政策在赋予公民权利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参见图1)。

图1 1945年~2010年英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变化
参与非正式志愿者的人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周期性志愿者在2003年和2009~2010年中分别下降了37%和29%。而正式的每月参与一次的志愿行为也在下降。2005年为29%,2009~2010年为25%(参见图2)。
公民参与(包括参与形式广泛的民主进程、参与公开游行与示威、签署请愿书)﹑公民咨询(意指积极咨询有关当地的服务或是通过参与咨询集团以及完成一份有关当地服务的问卷调查的行为)﹑公民行动(既包括直接参与当地服务的决策环节,也包括就任当地议员学校管理者、当地治安法官)都处于一种明显的下降趋势(参见图3)。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英美学者对公民未来的参与度持一种消极态度,在实践中英国公民的参与热情不但不高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因此,英国“大社会”计划如同水中捞月,缘木求鱼,难切实际。
(二)削减福利使“大社会”失去凝聚力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任之初,有批评者曾提出卡梅伦“大社会”的设想只是削减福利的一个“掩体”罢了。同时这些批评者指出,卡梅伦将“大社会”计划作为“大政府”对立的概念,他突出强调了工党“大政府”的官僚管理形式带来的不足。他也认为英国公民对福利国家的依赖也存在着问题。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提供的服务容易排挤私人服务,因此“大政府”是社会健康运行的一个主要障碍因素。从2010年英国便开始削减各项公共开支。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进行了大幅削减,以往新购电动车最高可获5000英镑补贴,但此数额现已锐减80%[13]。2010年10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削减并且提高退休年龄[14]。2012年,英国政府先是不顾大量的长期失业青年,缩减求职津贴[15]。在2012年8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保守党召开的年会上宣布,如果保守党能赢得2015年大选,保守党政府将在2016~2017年期间削减100亿英镑(约合161亿美元)福利预算支出[16]。因此卡梅伦提出“大社会”的计划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不同于工党执政时期的“大政府”主张,另一面是削减福利能使深陷经济泥潭中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长舒一口气。总而言之,不停地削减福利只会让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更加雪上加霜,削减福利的政策也会对卡梅伦的大社会计划产生“祛魅”效应。

图2 2001年~2010年英国民众在正式志愿者活动与非正式志愿者活动中的参与程度

图3 在过去十二个月中至少有一次公民参与、公民咨询、公民行动的经历(2001年~2010年)
(三)欧债危机对“大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
虽然欧洲央行在法兰克福,但欧洲的经济中心仍然位于伦敦,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在每逢金融危机时当然难逃它的魔掌,英国央行副行长以及索罗斯纷纷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与此同时,英国虽然不是欧洲债务主权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英国受债务危机负面影响也不小。评估政治风险的智库梅普尔克罗夫特全球风险顾问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最容易受欧元区危机恶化影响的非欧元区经济体中,英国名列榜首,这是因为英国与这个单一货币集团的贸易和银行业联系紧密。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说:“这些经济体所受的影响包括工业产值的下降、竞争力的丧失以及由于收益率上升而可能导致主权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报告称:“欧盟成员国英国的财政困境及其与欧元区密切的贸易关系令其对欧元集团经济危机加深时的应对能力极度有限。”[17]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英国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系统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这种信心的丧失集中体现在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以及英国议会上关于财政开支的争吵。公共部门在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主导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大环境下运行势必不会顺畅,公共部门及其相关的运行机构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社区项目也会遭到牵连。
目前,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联合政府正在试图减少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这将会直接影响一些志愿组织的融资来源。英国的发展信托协会预计60%的社区或社会企业可能会失去大量核心资助。对于志愿组织而言,政府资助的40%的援助也将大大减少[18](p.48)。而依靠政府融资的社区或社会企业以及志愿性组织在失去大量融资的情况下运行效率以及运行条件将会大打折扣。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以及欧债危机接踵而至的不利情况下,将融资转向民间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途径。
此外,政治冷漠积重难返。所谓政治冷漠是和政治参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不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某项政治活动,即对政治活动的“心理卷入”程度较低。根据欧洲睛雨表(Eurobarometer)对欧洲各国民主的满意程度来看,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英国民众对民主的满意程度最低。大社会计划也将受制于民众对政治活动冷漠态度的影响,英国社会意向(British Social Attitudes)调查显示,许多英国民众质疑保守党的社会政策,同时发现他们对国家供给(State Provision)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在大选后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7%的民众记不得“大社会”的内容,36%的人承认只记得一小部分内容,而 33% 的人对大 社 会 一 无 所 知[19](p.73)。因 此 在英国公民政治冷漠的大环境下,大社会的计划并没有深入人心,相反大部分人对该计划不是印象不深就是全无所闻。在西欧国家民众普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大环境下,大社会计划仍然面临着英国公民对大社会计划的认同困难。
四、中国是否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土壤——基于与英国的比较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治理理论发展以及各个国家推行政府改革的实践,公民自治的形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英国目前“大社会”计划也具有公民自治的色彩。但是这种“大社会”的管理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分析,尤其要研究中国是否具有“大社会”这种治理模式的社会土壤与政治土壤以及思想土壤。
(一)社会土壤:缺乏历史根基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历史悠久,其社会发展的模式与单元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江村和禄村等地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将人与人之间关系区分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20]。前者是建立在乡土社会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农耕文明。而后者是建立在商业社会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自始至今,都是属于一种关系社会[21],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社会中关系与信任紧密结合,形成了关系信任的独特文化。从孔子那里便有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说。即使讲公道、讲法仍然不能超越人伦之情。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中世纪以后,其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小共同体社会,人们隶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教会占据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基督教锻炼了西方人社会为本的责任观念[22](p.56)。正如张荫麟所说,“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庭的小群而尽忠于超越家庭的大群的要求,成了西方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因此西方家庭观念极为淡化,而集团生活甚为浓厚”。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社会的形态正在从农耕时代进入现代文明时代。有数据显示,我国现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每年大约有1500万人在向城市流动[23]。这种流动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这种转型中的社会体系还不够稳固,公民还未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还不能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当中,大部分仍然沉浸在农耕社会的环境下,这就犹如生长的作物,肥料充足但肥力缺乏。
(二)政治土壤:条件不够充分
英国“大社会”计划依托的社区概念已深深扎根于社会土壤中,而民主制度作为英国的政治土壤也为“大社会”计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英国地方自治传统历史悠久,素有“地方自治之母”的称号。近代以来,地方自治制度虽然发生重大变化,但其自治传统仍在。如1888年和1894年两个地方政府改革法都明确规定实行地方自治。1974年《地方政府法》也仍然保持了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在当今,地方自治制度已构成了现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4]。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组织,它的本质在于阶级统治。人类社会的阶级诞生以后,“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他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也不能跟着改变(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因此,国家不像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那样是全体居民的权力,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讲,国家是“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25](p.191),与西方不同的是,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原意是民之主,意为君主是人民的主人,就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到目前为止公布的民主指数而言,虽然有刻意贬低中国民主的嫌疑,但是从总体排名和各项指标的得分来看,中国与英国民主还存在一定差距。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随着阶级而消亡,民主也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是通向其理想的无国家无民主的必经之路[26]。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改革的道路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因此英国“大社会”计划可能会在中国未来产生,只是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参见表1)。

表1 中英民主指数差异
(三)思想土壤:养料充分
英国虽然在政策上最先提出了“大社会”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而是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廖逊在1986年5月的一篇学术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中,正式使用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尤其是建立省级银行以及设立统计局的概念与英国“大社会”计划的启用休眠银行以及财政透明政策十分相似。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玛丽娜·斯托得(Marina Stott)的《大社会的挑战》认为英国“大社会”计划是新瓶子里装着的老酒,她认为廖逊的这个概念就像是戴维·卡梅伦“大社会”的设计图纸。1987年,海南正式开始实施“小政府、大社会”体制。虽然该计划伊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诟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观念上的变迁,“小政府、大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一体制后来还被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所效仿。但德裔英国经济学者舒马赫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完成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的撰写,这本书在1973年至1979年六年间再版十二次,至今仍然是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反观中国廖逊一文的出现以后便再没有类似的人物写出类似的论文,更没有相关著述来阐释,因此虽然“大社会”在中国的思想土壤充分,但与国外英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五、英国小政府大社会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大社会”计划虽然听上去颇有些“乌托邦”的色彩,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这本著作类似,许多概念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大社会”作为党派竞选的口号,在竞选时的用途无疑是为保守党竞选造势,当保守党竞选成功之后,“大社会”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时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可能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大社会”这一概念起初得到英国选民的青睐,在英国社会运行之后却并未受到英国民众的充分肯定,因为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英国公众更关注的是就业以及社会保障问题。本身就具有“大社会”社会土壤、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的英国还没有表现与“大社会”的良性结合。目前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并非完全容纳不下类似“大社会”的公民自治计划,中国地域辽阔,国情十分复杂。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以及开发沿海沿江政策的做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是近40年来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最终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强势政府的有力治理。相比之下,英国相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较少。中新社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这一数字已超过英国、法国人口总数。因此,英国的治理相对于中国而言更加方便、更加有效,不用考虑地方差距、城乡差别等因素。此外,从思想土壤来看,我国与“大社会”有关的论文仅有廖逊《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一文,即使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领域公民治理,其理论来源仍然是西方学者的著述,目前推行以西方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大社会”恐怕会产生与初衷相反的祈愿。同年有报告显示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27]。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民主政治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官民共治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头等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打击腐败、造福人民等。
六、结语
2010年5月,卡梅伦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重新将保守党带回英国的权力中心。在他上任伊始,大胆提出了“大社会”计划,这项社会改革的计划是将政治家手中的权利交给民众。卡梅伦这种强调大社会小政府的特征具有强烈的“去工党化”政治色彩,并力图改变工党时期“任何事情都依靠政府解决”和工党时期“国家保姆”的形象。“大社会”这一具有浓厚变革色彩的社会改良计划特点鲜明但也存在着困境与阻力。就中国而言,英国“大社会”的计划所需要的思想土壤虽然较为充分,并存在基本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但仍然不成熟。在国情差异较大、民主基础不同的情况下,我国推行类似的做法未必可行。
(本文特别鸣谢英国约克大学James Barbe对文章中部分概念的解释)
注释
①合作社意味着工人所有并由工人运行的组织。参见Marina Stott.The Big Society Challenge 2011Keystone Development Trust Publications p87.
②互助性组织意为消费者或是顾客来承担所有权。
[1]David Cameron.The Big Society Rt Hon David Cameron[EB/OL].Tuesday,November 10,2009.http://www.conservatives.com/News/Speeches/2009/11/David_Cameron_The_Big_Society.aspx.
[2]Building the Big Society[EB/OL].http://www.cabinetoffice. gov. uk/media/407789/building-bigsociety.pdf
[3]Jesse Norman.The Big Society,the Anatomy of the New Politics[M]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Press,2010.
[4]陈建平.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浅析[J].历史教学问题,2003,(1).
[5]刘建飞.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及其一年的实践[J].当代社会主义问题,1998,(3).
[6]Matthew Eisner Harle.The Big Society Will Not Take Place:Reading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Conservative Discourse[D].MSc in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LSE,2011.
[7]Takeshi Nagashima.The Senshu Social Capital Review[J].The Idea of“Big Society”in Britain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ebate,2011,(2).
[8]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的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9]Heywood,Andrew.The Big Society:Conservatism Reinvented?[J].Politics Review,2011,(21-1).
[10]Cabinet Office.Building the Big Society [EB/OL].May 2010.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building-big-society_0.pdf.
[11]DavidWilletts.The Free Market and Civic Conservatism in K.Minogue(ed.)[M].London:HarperCollins Conservative Realism,1996.
[12]David Willetts.The New Contours of British Politics?[C]//Iain Duncan Smith.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Society,London:Politicos,2002.
[13]英 国 削 减 电 动 车 补 贴 [EB/OL].2010-08-02 .http://env.people.com.cn/GB/12319798.html.
[14][英国]政府将缩减福利支出、削减公共部门就业并提高退休年龄[EB/OL].路透社中文网,2010-10-21.http://cn.reuters.com/article/vbc_gb_economics/idCNnCT040333520101021.
[15]英国长期失业青年数量翻番 政府却缩减求职津贴[EB/OL].人民网 ,2012-10-17.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017/c70846-19295382.html.
[16]英国宣布将削减福利预算支出100亿英镑[EB/OL].2012-10-08.http://www.microbell.com/ecodetail_579601.html.
[17]英国受欧债危机影响最大[EB/OL].2012-07-2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7/27/c _123474118.htm.
[18]Marina Stott.The Big Society Challenge[M].Keystone:Development Trust Publications,2011.
[19]Hugh Bochel.The Conser Vative Party and Social Policy[M].Bristol:Poliuy Press,2011.
[2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李伟明,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22]张军,陈元刚.社会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23]田培良.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进程[EB/OL].中国农业信息网,2003-07-02.http://2010jiuban.agri.gov.cn/gndt/t20030702_96491.htm.
[24]张日元,王敬敏.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的历史考察[J].岱宗学刊,2007,(3).
[25]王浦驹.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6]俞可平.推进管理创新 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EB/OL].人民网,2012-10-01.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2/10/01/16566483.html.
[27]英国贫富差距拉大富人穷人差别对待引发民众不满[EB/OL].中国广播网,2012-09-26.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9/26/17915513_0.shtml.
[责任编辑:刘琼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