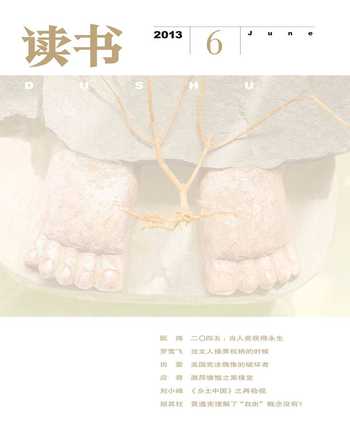学问的人生——怀张晖
2013-04-29胡文辉
胡文辉
张晖的追悼会,我没有去。听说,正在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多年来罕见的大雪。
我比张晖要整整大上十岁,可是我还没有见过雪。我错过了他的最后一面,也错过了这场离别的雪。
这些天来,我所能做的,只是留意着网上关于他的种种评论,也搜寻着自己关于他的点点记忆。
我跟张晖的交往并不早,也不算密切,可说是学问之交,君子之交,跟他的友人、同事相比,他给我留下的片断印象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于他短促的人生来说,些许的雪泥鸿爪,也是值得珍视,也是值得写出,作为他生命正文的一个注脚的。
回想起来,我们相交,应是由于我笺释寒柳堂诗,在《龙榆生先生年谱》里发现一些线索,遂贸然去函,希望他能提供有关资料。前两天检点过去的信函,找到他的两封信,一封写于二零零一年十月间:“陈、龙二人交往诗词不在手边,无法复印呈上。因为我明年六月毕业离校(拟去其他地方读博),故今年七、八(月)间已将在校的图书资料大部分搬至上海家中,陈、龙交往诗词亦已放在家中。拟于寒假再行复印呈上。乞谅!”一封写于次年二月间:“您需要的陈寅恪教授的一些材料已经找出,今寄上。手迹为龙榆生教授亲书。”
《陈寅恪诗笺释》所征引的史料,照我的印象,大体皆据已刊的文献,未刊的文献极少,张晖提供的这批材料,应是其中最大宗也最紧要的。考虑到龙榆生的学术地位,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陈寅恪交往的频密,若缺少这些参证材料,对陈诗的理解自不可能完整,《笺释》也就有很大的缺憾。前些时正在做《笺释》增订版的工作,龙榆生诗词的文本出处,已改从新刊的《忍寒诗词歌词集》,而删去初版时“张晖提供”的字样,但他的学术风谊,在我的记忆中当然是不会删去的。
张晖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敦厚,性格谦和,虽然头角早露,却绝无自矜之意,可谓人如其学,学如其人。不过,我们的初次见面,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当是他到了香港科技大学读博之后。只记得他说过科大所在的清水湾环境优美。后来他的夫人张霖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往还见面稍多。而较有印象的一次,是我们跟乔纳森(刘铮)、何家干(张文庆)一同去了香港的图书义卖。
我每逢到香港搜书,则写简单的日记。查旧日记,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提到:“长短句(张晖)在‘天涯告知香港要搞旧书义卖,问我来不来。”也就是说,那次“活动”可说是张晖引起的。第二天则提到:“早上九点正到中央图书馆。十点才开始,但已排了很长的队。五元一本实在太便宜。香港的电器、衣服虽然跟广州差不多,但香港一份报纸,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也要五元啊!……我抢得比较有节制。何家干第一轮买了三百元。张晖来晚了,也买了二百元。”不过我主要只是记书账,甚少记人,只在日记旁补了一句:“另有一本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送给张晖了。”
说起来,那段时期,我们都常去“天涯社区·闲闲书话”,他用“长短句”的网名(自然是源自他的专业)晒过书,也卖过书。当时我们多通过网站的短消息联系。可惜不知何时开始,“闲闲书话”逐渐扩张,趣味迁变,旧人星散,我久已不登录;好不容易想起密码,成功登录,却找不到短消息一项,张晖过去给我的信息,就此在“天涯”湮没。
以后他北上,我赠他七绝一首,似乎就是通过网站传给他的。现在仅记得最后一句:“只恐长安不易居。”而后来,长安是更加不易居了。
最后一次见张晖,是在二零一零年。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办了一次关于《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初识刘梦溪先生,会后又登门拜访刘先生,就叫了张晖同去。
此后我们就只是电邮联系。
就在我们最后那次见面未久,他曾发来一个邮件:“因××可能会拉到一些资助,我想借此机会点校一些近人的诗出版,初步在二十种左右。如各种条件允许,我很想出版汪琡、汪兆镛、兆铨、兆铭一家之诗,此外,黄秋岳、梁鸿志、李释戡、诸宗元、梁鼎芬、赵叔雍、李瑞清、汪东、胡翔冬、谢觐虞等,也有兴趣出版。限于视野,我大约总是以与汪政权有关者及东南一带诗人为两大宗。如何做才能较有意义呢?”我给他泼了点冷水,提醒他注意:“一、这是为人之学,对大家当然是好事,但所费时力恐怕很大,而对你个人,就未必都能转化成研究性的东西。二、能出汪精衛、梁鸿志、黄秋岳当然好,汪氏家集也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会有兴趣,但目前要正式出版恐怕不易——除非是像台湾那个(按:指台湾刊印的《民国诗丛刊》)一样,出个几十上百种,那就没有那么显眼了。但若要零卖,还是不容易吧。三、××拉的赞助是否可靠?……如果真有钱,倒可考虑办个杂志(丛刊性的也行),以近代诗词为重心,奠定一个阵地,推扬一种风气。过去龙榆生正是靠办词刊起家的嘛,刘梦溪先生其实也是靠办《中国文化》起家的,哈哈!简单说,编书不如办刊。”随后他回复:“所言极有理,受教受教。果然一时冲动靠不住。……还是专注南明和章太炎,把这两个成果弄出来要紧。办杂志有意思,当图一宏大的非专业的刊物。呵呵。”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他生前筹办《近代(文学)评论》,则仍与“当图一宏大的非专业的刊物”的志愿不无关联。他提到的“南明和章太炎”,应指南明之际的文学、章太炎的诗,记得他曾有笺注章诗的意思,但似无下文(按:闻已完成近百首的笺注稿)。尽管如此,这点滴思绪,很可见他的学术趣味的流泻,也可见他学术心灵的充溢。
也是在这一年,我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出版,张晖写了篇书评。我感觉好话说得太多,在他而言虽出于本心,在外人看来则不免阿私了。不过他也有一点批评:书中谈到卞孝萱以印章证史、周勋初以小说证史,他认为不太确当,因为古典文学研究界多以为卞氏更着重以小说证史。对此,我回应说:“我查了一下,卞孝萱强调唐传奇与政治的关系,其实是继承了陈寅恪之法(但在具体观点上他对陈颇有批评)。所以你指出小说证史问题,确应补入陈、卞两人,再列举周勋初的提法。”他答复:“所言甚是。卞先生文集行将出版,多考订旧学,若以兄标举之标准而言,卞先生实在算不上一位一流的学者。然而,即使成为这样的学者,也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一流其难哉。”张晖曾从卞先生学,故有此感叹。随后,他发了一个电邮并附件:“读大作,因无俞平伯,盖俞曾是我最喜爱的学者,所以近撰一文,谈俞之淑世情怀,亦偶寄感慨也。”此即收入《无声无光集》的《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读张晖中学同学维舟回忆文章,乃知张晖早年极喜《红楼梦》及红学,他自述曾视俞先生为“最喜爱的学者”,当与这重因缘有关。或许,这也可以视为他对《现代学林点将录》人选的一种含蓄批评吧。
张晖最后的主要工作,应是整理龙榆生遗存的往来信札,今年一月二十日,他来邮件:“最近在整理龙榆生遗物,有近人书信近千封。我和刘铮说了一下,想以某某致龙榆生函为题,陆续在报纸上介绍。其中有陈寅恪函十多封,其中一封信钞示通行的《阜昌》诗,明确作《题双照楼诗集》。……另有陈氏佚诗二首,照片两张,寄上供参考。”我为之大喜,因为《陈诗笺释》的增补已到最后阶段,正好来得及补入。当天他收到回复,又传来《新发现的陈寅恪给龙榆生诗函》一文,我提了几条意见;二十一日我又传去一则补充意见:“照情理,《阜昌》诗是因汪去世而作,《题双照楼诗集》不应当是原始的诗题,而且《吴宓日记》也只是说是挽汪诗,未记诗题,可作旁证。可能后来时过迁境,才改《题双照楼诗集》,这样因书而作,比因人而作,显得低调一些。”他当天答复:“颇有理。”——不过,此文稍后在《南方都市报》上刊出,关于《题双照楼诗集》题名一事,内容并无改动。或因文章已传,来不及改,或因事涉琐细,他觉得暂不必改吧。
“颇有理。”这就是他给我的最后的邮件,最后的通信,如此简短,就像他的一生。
对于张晖的猝逝,已有无数的感喟,关于生活压力,关于学术体制、住房、薪酬、职称,种种的不如意。此亦事出有因,也是应有之议。可是,我更愿意退后一步,从抽象的层面来看待这件事。
生命的脆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不论我们是学人,还是常人,总会有“既痛逝者,行自念也”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生命的脆弱?或者换个说法,作为一个脆弱的生命,我们应当如何做学问?
我的想法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业,未必只有做学问才是最了不起的、最神圣的,只是做学问也绝不低于任何一种事业。它是一种有趣味的事业。作为学人,做学问就是我们证明自身存在的方式,是我们感受生命、呈现生命、释放生命的方式,是我们与不断消逝的生命相对抗的方式——尽管是终归失败的对抗,可也是值得骄傲的对抗,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个老渔人,就像加缪笔下那个西西弗斯。归根到底,跟其他世间的事业一样,做学问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隐显必于是,贫富必于是。勤奋地治学,也就是在积极地生活。如果非要追问学问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吧。
生死无常,不是我们可以猜得到的;学问无边,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完的。那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但问耕耘,尽我本分,可矣。
汉朝的夏侯胜、黄霸由于勇于提出异见而系狱,黄霸要跟夏侯学习《尚书》,夏侯表示两人已是死罪,何必去学,黄霸乃引《论语》的话回答:“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觉得,这句话或许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话语之一,不仅代表了人类的求知欲望,更代表了生命的积极精神。我过去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的跋里,引用过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我仍愿在今天种下一棵小树。”这跟孔子、黄霸所言,也是意蕴相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晖是尽了本分的,应当说,他已超出了本分,尽可能呈现了他的生命,他的热力,他的光辉。
在诸多的已刊著作中,新出的《无声无光集》代表了他治学的广度,而《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二書,则代表了他治学的深度。后二种著作,或系联人事,或考辨源流,为不可无的踏实功夫,皆足以传世。此外,未刊者还有专书《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有文集《朝歌集》,有编著的《忍寒庐学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有用笔名“闻幼”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十多篇书评……他以篇幅无多而内容丰富的人生,践行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践行了“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我仍愿在今天种下一棵小树”的精神,对此,我们既应当感伤,也应当感奋。
我们应当为逝者的离去而伤怀,却不必为生命的短促而灰心。
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我写到几个早逝的英才:刘师培、刘咸炘,终年皆三十六岁;张荫麟,终年三十七岁。此外还有姚名达,得年也仅三十七岁;范希曾,甚至只得三十一岁。论年寿的不永,论学术的早熟,张晖是可以跟这些前辈相提并论的,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光荣。
据维舟回忆,张晖说过:“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几句话被转引得最多。话是有内涵的,但不免悲观,也许只是他一时的感触吧。我并不觉得张晖是个忧愤、愁苦的人,他已有所好,有所爱,有所成,有所得。
大约就是针对这些话,吴真在微博上回应:“深海鱼类,若不自己发光,便只有漆黑一片。”此系日本名导大岛渚最喜爱的和歌,用到这里,也恰当得很。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发光的方式,而张晖,一直在发出深海鱼类那种“非常幽暗的光”,他仿佛是感觉到命运的敲门声,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倾力发出了更多的光。
当然,张晖之逝,终究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刚刚看到最新发表的张晖遗文《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有一处说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试看学术史上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术的向上一路是怎么走的,而学者一旦将对政治、社会、文化的诸多不满内化为治学的驱动力,则必将大大提升学术的境界。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直到章太炎、陈寅恪,他们的研究莫不如此。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诞生于学者对于时代的紧张的思索之中,比如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陈世骧将《文赋》翻译为英文而将《文赋》的主旨理解为‘抵抗黑暗,均是明证。”这些话,我觉得说得相当透辟,是见道语。
严耕望曾批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透露出人文科学的两种不同旨趣:追求实证,追求兰克式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如严耕望者,可称“无我之境”;有情怀,有寄托,如陈寅恪者,可称“有我之境”(在此,我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著名概念,想必是早年专攻词学的张晖所乐意的)。但严先生似乎忽略了,他自己主要研治制度变迁和地理沿革,属于历史的客观问题,自不妨强调治学的“无我之境”;但陈寅恪辨析钱柳诗所隐含的政治寓意,探讨明清之际的史事人情,却不能不涉及人的主观问题,则其治学的“有我之境”,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若无“我”的存在,又谈何“了解之同情”呢?而张晖所理解的“古典文学的意义”,正类同于寒柳堂治史的“有我之境”,可见他阅历渐增,对治学的体会已有更深的进境,只可惜已来不及展开,来不及实践了。
在无尽的遗憾之外,我还有两个属于私人的遗憾,一个是学术旨趣方面的,一个是生活喜好方面的:
张晖去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系台湾版《诗史》的重刊,据说颇有增易,但张晖在邮件中只说:“近刊《中国“诗史”传统》,乃去年年底评职称,遂旧作新刊,不好意思再寄奉。”因此,我手头只有他签赠的《诗史》。此书原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诗史”概念》,是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诗史”内涵的衍变。张晖读博的方向是文学理论,从这一角度入手也属顺理成章,而且,这个角度本是“诗史”的主流,只不过至于今日,反倒为陈寅恪式的“诗史”实践所遮蔽了。当然,我更感兴味的,也正是陈式的“诗史”,也即历史学角度的“诗史”,故这部《诗史》,我并没有仔细看过。可是,从收录在《无声无光集》里的《诗歌中的南明秘史》一篇,从张晖的遗著《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的主题,我分明感到,他近年的论说已逐渐接近寒柳堂式的“诗史互证”,那么,在学术上,我们原本定会有更多的契合的。
维舟的长文《平生风义兼师友》,细腻地追述了张晖青少年时代的学术奋斗,悱恻感人,但情调似乎稍嫌灰暗;我更喜欢小旁写的《有声有光的老灰》,哀而不伤,泪中有笑,刻画了一个学人的世间风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一段:“除了醉心学术,老灰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尤其是甜品。彼时老灰在香港,老霖在广州,两人时常忙碌地穿梭在粤港之间,而探亲的频率多半取决于老灰冰箱里食物的消失速度……‘好吃得快要哭了,是老灰用来形容美食的最高评语,他治学方面如此了得,在对待食物的品位以及形容食物的辞藻方面却又十分幼齿。”难怪,我也记得,曾跟他、沈展云、乔纳森一同在广州文德路吃过甜品呢。我是一个港式奶茶的迷恋者,而张晖久居香港地,又好甜品,想来也是奶茶的同好吧?而北京那个地方,到哪里找一杯像样的港式奶茶呢?在生活上,我们原本也会就甜品和奶茶有更多的交集的。
可所有这些都无从谈起了。
在张晖故去的当晚,我写了一首悼诗,今亦附于此:
徒闻万壽塔,把臂已无从。
维港几番月,六朝何处松。
与时辩诗史,据实谱词宗。
不信声光歇,新编墨尚浓。
万寿塔,俗称玲珑塔,也就是张晖当日朝夕相对的那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塔虽久已无声无光,但历数百年尚存;如今,张晖也无声无光了,信亦如此塔,有那不朽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