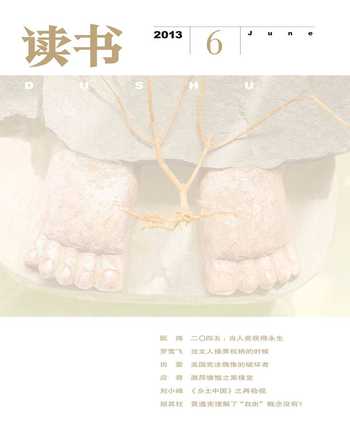“萧伯纳在上海”与当年媒体的言论运作
2013-04-29姚玳玫
姚玳玫
二十世纪前段,世界文化名人访华,都或大或小会酿成一阵言论热潮。与前此杜威、罗素、泰戈尔访华不大一样,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乘英国“皇后号”游轮抵达上海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有些来得不是时候。此前一年多,日本人的步步逼近,折磨着中国人的神经:“九一八”事变,锦州沦陷,“一·二八”淞沪战争,山海关失守,热河告急……亡国的阴影由东北关外漫至关内,犹如癌症患者病情之扩散,不可控制。
也许是对战争环境有所顾虑,萧伯纳对此次中国之行,一再犹豫:先是否认他有参加世界旅行团并访问中国的想法,之后“又起身作世界之游”。抵达上海,又“无意登岸”,并拒绝“一切闲杂人等”上其游轮。之后还是登岸,但为回避嚣烦,有意绕开守候在新关码头的四百多名迎接者而选择在杨树浦码头悄然登陆,给等候他数小时的人群,泼了一盆冷水。加上前此在香港的“赤化”言论,萧伯纳刚到上海,有关他的议论已经沸沸扬扬。
一、期待与回应的错位:“萧伯纳”的多重含义
身兼“和平之神”、“社会主义同情者”、“西方戏剧家”多重身份的萧伯纳此次访华,构成国人三重期待:一是萧的“和平之神”国际身份和声誉,对于危在旦夕的中国,会有帮助。因此,同是世界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盛邀萧访华,他们想借萧的正义之声,给肆无忌惮的日本政府、不愿意说公道话的西方列强、消极抵抗的国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而实际上,七十七岁的充满想象力和随意性、我行我素的萧伯纳,在中国的言论未必能让人满意。他与宋庆龄会谈,当宋谈及应该“消灭造成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时,萧说:“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为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让宋尴尬;他说当时联合国刚发布的袒护日方的《李顿报告书》“可称公平”,让国人哗然;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局势时,他说:“我说什么不重要,假如我是一个武人,杀死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让记者无言以对;他避而不谈中日问题,说“只要从中国安全地走出了一步去,就什么都说”。可见他不想得罪日本人。何况他在上海只停留八个小时,连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将军恳邀他参观上海“一·二八”战后废墟,也无暇顾及。可以说,萧伯纳在上海的匆匆之行及其随意发言,没有让中国局势发生变化。
二是前此萧伯纳到过苏联考察,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揄扬,引起各方关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萧抵香港,《申报》载香港路透社十四日电,称萧伯纳在香港对大学生说:“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落伍。”人未到,不俗言论已传遍上海。对此,左右翼人群有不同反应:对于正处于蒋政府剿共重于抗日的白色恐怖氛围中的左翼人士,是一种鼓舞和支持。如鲁迅,他对萧伯纳来华的关注,接连发表文章迎萧、颂萧、评论萧,他协助瞿秋白编辑出版《萧伯纳在上海》,都与他对萧的社会主义拥护者身份有好感不无关系。相反,右翼方包括正在为剿共焦心积虑的政府当局,对萧的言论则充满警觉,呈现一种神经质的敏感。萧伯纳“百万家财”、乘豪华游轮周游世界,与其同情无产者、揄扬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右派刊物讥讽他“借主义,成大名”的把柄。实际上,萧伯纳只是一位同情社会主义的费边主义者,他访华期间即兴的发言,那些经报刊翻译、摘引、转述而显得前言不搭后语的言论,成为左右双方各执一端、互相攻击的口实。
再者,萧伯纳是受“五四”新文学家推崇的西方戏剧家,他的《华伦夫人的职业》早于一九二零年搬上中国的舞台。这部剧最终不是以成功的经验而是以失败的教训,为中国早期话剧实验敲响了警钟,让话剧界有识之士意识到:“借用西洋著名剧本不过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一种方法。”至此,“五四”以来提倡引进西洋剧的观念受到置疑,以“爱美剧”倡导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话剧改革相继展开。一九二二年回国的洪深是这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而萧伯纳则对他构成一种遥遥的影响。此次萧访华,作为剧界代表,洪深(就像当年陪伴杜威的胡適、陪伴泰戈尔的徐志摩)是最有资格陪伴在萧伯纳身边的人物。但萧不经意的怠慢,洪深的一再“碰灰”,两人的对接呈错位之态。在短暂接触中,萧对哈佛毕业、话剧科班出身的洪深,颇不以为然:“听说你在美国某大学里学过编剧,这就奇怪了!在课堂里,从书本里,你学到什么没有?编剧要从人生中去学习的。我自己编剧的时候,我先认清几个人,把他们的行为言语,记录下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着,像一朵花的开放一样,那才是真正可以学会的编剧。”(《昨日下午两点半从孙宅到世界学院的途中一段谈话》洪深记,载《时事新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萧说话直率,那种长辈教训后辈的口气明显。相反,在中国笔会,萧伯纳对传统戏剧界代表梅兰芳却热情有加:“当介绍梅兰芳时,萧氏与之立谈颇久……萧谓英国戏剧演时无锣鼓等声音,盖演剧时一有杂声,损害观众之注意力,而中国演剧时颇觉过闹。梅氏答称中国戏剧有两种,如昆曲即为不闹之一。”“萧氏闻梅君有三十年之舞台生活,而注视其面容曰,君诚有驻颜术哉。”(《东西戏剧家两权威晤谈》,载《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梅兰芳不懂英语并没有妨碍萧、梅间做艺术乃至情感的交流。萧伯纳对当时剧界一新一旧、一西一中两位代表人物的不同态度,颇令人意外。
总之,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停留八个小时的萧伯纳,并不让人满意。言论界之所以被搅得这么热闹,与主客双方在期待与回应上呈错位之态不无关系,也与萧本人持反讽的、搅局的、揭出真相的说话方式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内外交困、多方矛盾复杂纠结的一九三三年中国社会背景下,萧的到来,成为各方表达政见、发泄情绪的一个端口。
二、以“萧伯纳”为借口:三路人马,各说各话
还是鲁迅说了大实话:“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蹩脚的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胭脂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家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萧伯纳在上海〉序》)每个人都想借萧伯纳说话,所有的期待,期待的落空,落空后的不甘、辩说、反唇相讥,说穿了都是一相情愿。数十家报刊报道萧伯纳访华,同一次谈话,几经转译转载,添枝插叶,按照自己的口径做褒贬延伸,各说各话。萧停留上海八小时有限的“谈话”被无限发酵,汇成一个巨大的言论泡沫。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之后那几天,上海各路文化人都卷入关于萧伯纳的言说中。近百篇文章大致呈三种态度:左翼文化人,如鲁迅、茅盾、韬奋、适夷、许杰、李翼等,持颂萧态度。右翼文化人,如张若谷、巴宁、杨昌溪、张资平、全增嘏等,持呸萧态度。一些立场中立者,如林语堂、郁达夫、傅雷、赵家璧,持论比较平和,就事论事,不带明显褒贬倾向。
一九三三年三月,萧伯纳离开中国半个月后,反刍“萧伯纳”的热浪再度掀起。其中有三组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野草书屋印行《萧伯纳在上海——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一是《论语》第十二期“萧伯纳专号”;一是《矛盾》第一卷第五、六期“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较之前段“颂萧呸萧”的杂乱无章,三组文章显得深思熟虑,有自己的思路和意图。将之放在一起,其本身则构成一场言论战。
署名“乐雯”剪贴、翻译及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是鲁迅、瞿秋白、许广平、杨之华合作编纂的一本小书(“乐雯”原为鲁迅笔名。《萧伯纳在上海》主要编者是瞿秋白,书中署名“乐雯”的文章,应是瞿秋白执笔)。结构上以颂萧、呸萧为界线,分别辑录“Welcome”与“呸萧……”两方面文章,每部分冠上标题、编者按语等。呸萧文章后面,附上比原文篇幅更长的编者述评,述评采用杂文笔法,以褒贬定性分明的修辞、冷嘲热讽的口吻,否定负面观点,调整舆论倾向,“颂萧”主旨明确。诚如编者所言,萧是“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真正为光明奋斗”,“他向着‘革命开步走”。此为该书的基调。
相比之下,《矛盾》第一卷第五、六期“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的编辑思路就没有那么清晰,有临时拼凑之感:既有巴宁恶搞式的文章,也有傅雷学究气的“评传”,以及杨溪昌的动态类短章。总体而言,这份得到国民党官方资助、倡导民族主义文学的刊物,对萧伯纳访华持冷嘲热讽态度,指桑骂槐的言辞里,藏着对萧的中国之行的深深失望。署名“巴宁”的《萧伯纳在上海》是特辑的重头文章。文章连萧伯纳在上海的时间都写错,说萧“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莅临上海”。却有意恶搞,称萧为“爱尔兰的‘现代古董”、“老怪物”、“萧老头子”,将前段报上报道萧伯纳几个细节添油加醋地重述一番:有意拎出萧对宋庆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说的反驳,借萧之口,称宋“你是一个说话天真得令人难堪的小孩”。渲染萧对洪深的冷落及其“自打锣鼓自下场”的尴尬。讥讽与萧倾谈甚欢的梅兰芳为“我们的‘邦家之光雄美人”。写萧在孙公馆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萧对上海印象时,“一群蠢东西张开了嘴等待着,却只听见回答是:‘恶劣!恶劣!恶劣之至!这下子可真完啦……记者先生们乘兴而来,结果是败兴而归。萧老头子呢?他是头也不点一下地走进洋房里去了……开口便是一顿狗血喷头的臭骂,我以为中国的新闻先生总可以‘知难而退了吧?老怪物终究是洋人啊?中国人而获洋人之骂,岂非已够耀祖扬宗之事……”巴宁当时未必在现场,却绘声绘色,用激愤、夸张及贬损的口吻,写萧的言行,以挑起民族义愤。如果说巴宁文章与乐雯《萧伯纳在上海》观点针锋相对,笔法却颇为相似,都采用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那种有失节制的挖苦和讽刺,裸露了这一时期言论表达理性的匮乏。
《论语》第十二期是一个有备而来的“萧伯纳专号”,突显的是《论语》与萧伯纳在“幽默”特性上的联系,立场较中立。既有鲁迅论战式的《谁的矛盾》、蔡元培抒情式的《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也有洪深澄清事实的《幽默矛盾萧伯纳》、邵洵美记事式的《我也总算见过他了》,更有全增嘏谩骂式的《关于萧老头子》等,显示刊物包容姿态。再者,所刊文章比较严谨,动态文章交代出处。如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文前有记者按:“本文手稿曾经孙夫人审阅,所载孙夫人谈话部分,皆经孙夫人手订无讹。”萧伯纳的《敬告中国人民》,由宋春舫翻译,中英文版同时刊出,可对照互读。不像《矛盾》只载此文中文版,译者也没署名。另者,林语堂《欢迎萧伯纳文考证》,转录《时事新报》二月十七日顾瑞民的《萧伯纳来了》,将顾文对林语堂《有不为斋随笔:读萧伯纳传偶识》的抄袭做了一番“考证”,用幽默方式揭出报界转相抄袭的真相。
三组文章,依据各自的逻辑,敷陈出关于萧伯纳的三种叙事。萧访沪期间说了什么话,其上下文关系怎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萧伯纳为由头,说自己想说的话。由于说话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各异,各说各话、互相攻讦的情况明显。在这场言论运作中,乐雯《萧伯纳在上海》尤为引人注目,值得另加分析。
三、汇编与统率:《萧伯纳在上海》的言论运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报刊运作已高度纯熟。一方面,政府当局言论管制的失效,政治文化势力的多元并立,言论炒作的推波助澜,报刊呈众声喧哗局面。另一方面,左翼言说在这一时期的深得人心,使其成为言论界实际的领头羊,潜在地统率言论走向。
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界两位铁笔人物鲁迅和瞿秋白,在这本小书中可谓配合默契。首先,他们将“萧伯纳”定义为一面“政治的凹凸镜”,“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式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其次,揭发“呸萧”言论是如何操作的。在《政治的凹凸镜——“比较翻译学”与“小辫子的科学研究”》一文中,乐雯追究两方面问题:(一)多种文字“转译”的问题。“……萧说的是英文,从英文翻成汉文,或者翻成日文,甚至于像大陆报似的,还会从英文翻成汉文,从汉文再重新翻成英文——这种复杂的过程之中,很可以做些手脚。这样转辗传译,就把萧伯纳的谈话翻陈出新,弄出许多‘修正、‘删改、‘补充、‘捏造的把戏来。”一再转译,萧的谈话已经被修改甚至捏造,可信度几近于零。(二)萧同一次谈话被不同报纸“转说”的问题。该文以“中国政府和革命”、“李顿报告”两个话题为例,比较《字林西报》、《大陆报》、《每日新闻》、《上海日报》、《大晚报》及其他各报对萧同一段话如何“转说”,如何“做些手脚”,从而得出结论:“萧伯纳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日本人要说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仿佛萧就说了‘中国政府不只一个;英国要说中国政府只听美国的玩弄,不能尽如大英之意,于是萧说中国民众不要戏子做政府的话,就记载出来了;国民政府要说自己是很好的统治者,于是萧说的话又变了:‘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没有好的名声;自由主义的幻想家要请政府少说些话……于是萧的话里又加了一句……责备中国政府多讲空话难于骗人的意思。”关于“李顿报告”萧的说法更是“‘因报而异,简直‘一气化三清,同时当了伦敦东京南京三个政府的外交总长了。”乐雯深谙言论操作背后的把戏,他说:“后台的‘戏子的把戏,比涂着花脸的前台姿态更不容易看见……”他采用转载、翻译、摘引、综述、评论多种方法,穿插进行,揭发把戏,戳破言论泡沫,最后来个“萧伯纳的真话”,以正视听。
问题是,《萧伯纳在上海》在揭发呸萧言论运作把戏的同时,自己也将这种运作发挥到了极致。与上述耍把戏的言论相比,它的抱团意识、舆论反攻意识、占领言论高地意识,都要自觉得多。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萧伯纳在上海只停留八个小时,却引起上海文化界一阵神经质的骚动。萧的多重身份牵动中国文化界的多条神经,其一言一行都有无穷意味,给予各方力量以锐利的刺激,由此引发的一场口舌战毕現了当时承受内外压力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躁动、茫然、偏执的内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