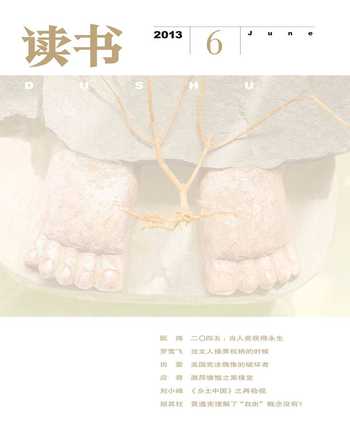深圳与故乡之间的行走
2013-04-29郭熙志
郭熙志
我先说说故乡和深圳两个城市之间的旅程吧,这是真正百感交集的旅程。深圳是一线城市,故乡铜陵是安徽最小的地级市,我住在深圳,从上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来,为了一部关于故乡大通镇变迁的纪录片《渡口编年》,一直来往于深圳与故乡之间,一开始是为了所谓“见证正在发生的历史”。
镜头似乎带着诅咒,有四五个乡亲,拍着拍着就死去了,现在拍摄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区域也由镇变成县变成市,最后是南方。关注的就是故乡那些国企的职工和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活过来的。他们从镇里走出来,口中骂骂咧咧,没有什么对幸福生活的幻想,只是为了混口饭。
我从扯东带西大汗不止狼狈不堪地赶火车,到衣着体面地坐高铁飞机,这个过程虽只有十多年,但恍惚之间,仿佛是飞渡了几个世纪,很焦虑痛苦同时又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大的时代(不一定是好时代),并记录它。一切都如此丰富。“转型社会”,当征兆还不十分明显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拍摄,这是我的得意之处。
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春运列车上因拥挤窒息休克而被抬进餐车的一张张苍白的脸,更恐怖的关于火车的记忆来源于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南下,我的同乡张有齐要搞一个“中国第一次选美”,让我到深圳写文案。那时我新婚,是利用婚假溜出单位的,临走没有告诉任何人,之前,我已吃过不少被同事告密的苦头。那时来深圳需要边境证,边境证的证明是在我采访单位重型机械厂开的。
就这样,先汽车再火车又转了几趟火车才到深圳。那时火车最大的特征,就是远远飘来刺鼻的尿味和难以下脚的厕所,要在车厢里来往行走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被死死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动弹,所有空间——包括行李架、座位底下以及厕所,都塞满了人,有些人还攥着自己撒尿用的塑料瓶子麻木地看着你。从鹰潭转车,来到站台,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出现了:站台是空的,两边的列车窗户上挂满了人的脚。
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来深圳,上海宾馆以西皆为黄土,东边,怡景路老电视台亦是黄土一片,但见小型转播车一辆停靠于旁,与今日之深圳比,差别巨大。深圳《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楣说:每一个深圳人都想把自己变成一卷钞票;搜狐网刘春说:深圳的青年女子都有二奶的冲动,有些已经实现,有些正在努力中。一位女同事说,在北京,你说你写诗有女孩子喜欢你;在深圳,你说你会写诗,所有女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疯子。
一九九九年,我来深圳时,天瓦蓝瓦蓝,现在香港都要出巨资改善空气改善环境,因为香港一年也有半年阴霾。
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体验,而不是大小的区别。比如深圳,除了罗湖区,其他区,依我个人的体验,皆为未完成之城区。道理很简单,城市需要若干年才能成熟,人气不是一天聚起来的。没有人生活的城区就是鬼城区。
深圳是什么?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桥头堡、第一张股票、城中村、王石房地产?还是公关小姐、二奶村、香港后花园?铜陵是什么?三线城市、计划经济堡垒、资源枯竭型?还是文明三千年、山水秀江南?一九九二年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二零零零年第一家麦当劳在故乡铜陵开业,相差八年。二零一二年底我回銅陵,江南文化园可以和深圳比肩的影院、桑拿、茶楼、宾馆一应俱全,就局部而言,铜陵的享乐甚至超过深圳。如果你在时间或空间的剪辑上发生错乱,你将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一个城市还是两个城市。这是我在深圳与故乡之间的十几年行走中感悟到的,故乡回不去——因为熟悉的已经变成陌生,时间永远是一次性的,没有办法预演,没有办法打草稿,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