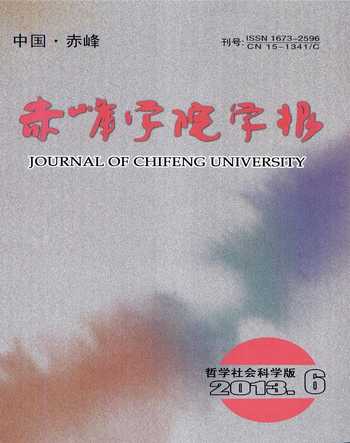通假字与古今字、假借字关系说略
2013-04-29杨毅华
杨毅华
摘 要:通假字、古今字、假借字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字的存在,造成了古书中用字的分歧,给人们阅读古书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为此有必要弄清这几种字的概念,并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通假字;古今字;假借字;概说;关系
中图分类号:H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98-04
在古代汉语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词,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而同一个词也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记录,这就是古汉语中特有的一些用字现象。这种现象也是古汉语中客观存在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通假字、古今字、假借字。这些字的存在,造成了古书中用字的分歧,给人们阅读古书造成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这几种字的概念几乎是混淆不清的,教师们一般都统称为通假字,即以通假字涵盖了古今字和假借字。其实这是几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我们有必要弄清这几种字的概念,并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古文字教学提供一点借鉴。
一、通假字和古今字
(一)通假字概说
通假字指的是古汉语中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通用或借用的现象。即某个字本来已经有专门的字表示,但古人在书写时没有使用这个字而是借用了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记录它,这就形成了通假。“本有其字”是通假字的特点,其中被代替的字是本字,用来代替本字的字则被称为通假字或借字。而古音相同或相近是通假字产生的前提,如果本字和借字的读音没有联系,就不能构成通假。例如:
例(1)畔,本义是“田界”,《说文解字》:“畔,田界也。从田,半声。”在《孟子·公孙丑上》:“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中被借去记录“叛”。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古多假畔为叛”。“畔”和“叛”在古代声母和韵部相同,构成同音通假。
例(2)“伸”是记录“伸展”、“延伸”的本字,但古人在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却借用了与之读音相近的“信”来记录它。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一奋其气,威信邻国”中,“信”就是“伸”的通假字。“信”和“伸”在古汉语中同属“真”韵,构成了叠韵通假。
通假现象在古汉语用字过程中是经常出现的。通假的基本原则是语音是否相同或相近,而不管字形和字义是否有联系。相同指的是古音相同,而且是汉代以前的古音,而不是现代的读音。因为,有些字的读音发展到现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衡量通假不能以现代音为准,要以古音为标准。例如“罢”和“疲”在古代就是一对同音通假。“罢”的本义,《说文》解释为“遣有辠也”,是“罢官”、“免去”、“解除”义,音“皮”,和“疲困”的“疲”读音相同,故在《过秦论》:“率罢散之卒,将数万之众,转而攻秦”中,借去表示“疲”,构成同音通假。若用现代读音去衡量,这两个字声母韵母都不相同,好像构不成同音通假,而在上古音里,这两个字同属于并母歌部,声韵完全相同。因此,准确地说通假应是“古音通假”。
通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通假字和本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同音通假,如前面举例的“畔通叛”、“罢通疲”;二是音近通假,即通假字和本字之间或声母相同(双声),或韵母相同(迭韵)或者声母相近(发音部位相同)。如上例的“信、伸”就属于音近通假中的叠韵通假。
(二)古今字概说
古今字是指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字形来记录。先用的那个字,叫古字,后用的那个字则叫今字。而且古和今的时间是相对的,若以周秦为古,那两汉以后就为今,以汉为古,那么魏晋以后为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曾说道:“凡读传,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它和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古文字和今文字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古今字是汉字在发展衍生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文字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上古时期,汉字的数量较少,而新词不断增加,不少字除表本义外,经常被借去表示假借义,再加上词义的引申发展,就形成了一字兼表多义。后来,为了把其本义和假借义以及引申义区别开来,人们就另造新字来表示其中的某一个意义。这样,在这个义项上,就形成了和古字相对应的今字,这个字又叫做“后起字”或“区别字”。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古今字就是区别字,是以不同的字形来区别不同的意义。人们有时称古今字为“分化字”,其原因即在此。例如:“竟”和“反”的本义分别是“乐曲终了”、“完”和“翻转”,但在《左传·晋灵公不君》:“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中,“竟”记录的是“边境”之义,“反”是“返回”之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字记录多个词的现象,难免表义含混。所以,汉代以后,人们在表示“边境”和“返回”义的时候另造“境”和“返”来以示区别,“竟和境”、“反和返”就形成了古今字,在表“边境”的意义上,“竟”先用,是古字,“境”后用,是今字。
古今字形成的途径,概括起来主要有二种:
1.由于词义的引申,一个字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意义,为区别词义,后人或为本义另造新字,或为引申义另造新字,以分担原字的部分意义,这样原有字和后起字就形成了一对古今字。例如
例(3)“文”本义是“花纹”,《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彩色交错”、“文字”、“文辞”等意义。后来,为区别词义,就另造“纹”表示本义,而原有字反表引申义,“文和纹”形成一对古今字。通过这种途径形成的古今字还有:“益溢”、“尊樽”、“止趾”、“奉捧”等等。
例(4)“责”的本义是“索求财务”,《说文》:“责, 求也。从贝朿声。”如,《吕氏春秋·慎行论》:“往责于东邑”,用的就是本义,由此引申出“债务”、“责备”、“责任”等意义。为区别词义,后人为其引申义“债务”另造“债”字表示,而原有字仍然表示本义或其他意义,于是,在“债务”这个意义上,责和债就形成了古今字。这样形成的古今字常见的还有:“昏婚”、“景影”、“取娶”、“赴讣”、“知智”等。
2.由于古代文字数量少,有的字在表本义的同时又被借去表示另一个意义,使得假借义与本义共用一字,后人为区别词义,或为本义另造新字,或为假借义另造新字,从而形成古今字。例如:
例(5)队,本义是“坠落”。《说文》:“队,从高陨也。俗字作坠。”在《左传·庄公八年》:“公惧,队于车”中,即为本义,后借去表示“队列”、“军队”等意义,于是,另造“坠”表示本义,“队坠”就形成一对古今字,《说文》:“俗字作坠”中的俗字其实指的就是今字。这种情况的古今字常见的还有:“莫暮”、“孰熟”、“其箕”、“然燃”、“自鼻”、“要腰”等等。
例(6)采,本义是“采摘”,《说文》:“捋取也。从木从爪”。本来与色彩的意义没有联系,由于当时没有替色彩的“采”造字,于是就借“采”来表示,如《孟子·梁惠王上》:“抑为采色不足视於目与?”中,“采”就是“彩色”义。后人为区别词义,就另造了一个“彩”来表示假借义“彩色”,于是“采彩”也形成一对古今字。类此的古今字又如“与欤”、“戚慽”、“辟避”等。
这些后起的新字和原字均构成古今字的关系。古字表示的意义多,今字只是表示古字的部分意义。
(三)通假字和古今字的联系与区别
通假字与古今字都是古书中的用字方法,二者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们有一个相同之处,即二者都有字与字的对应关系,通假字有本字和借字的对应关系,而古今字是古字和今字的对应关系。除此,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古今字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
古今字的古字和今字不是同时代存在的,产生的时间有先有后,都是古字在前,今字在后,它们之间是纵向历时的关系。如“县”和“悬”,“县”本义是“悬挂”,《说文》:“繫也。从系持。胡涓切〖注〗臣鉉等曰: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爲州縣之縣。今俗加心,别作悬。”由此可知,“县”后被借为“悬挂”义,另在本字的基础上加“心”,形成今字,“县”比“悬”产生得早,是“悬”的古字。
而通假字的本字和借字是同一时代同时存在的,不管时间的先后,是书写人临时借用,以此代彼,本字和借字是横向共时的关系。
2.从意义上看,古今字意义范围有大小之别。
古今字的古字和今字之间在意义上大多有联系,今字或表示古字的本义,或表示古字引申出来的意义。且古字和今字的意义是包容关系,古字意义范围大,今字的意义范围小,今字承担了古字的某个义项,今字的意义一般包含于古字当中。如《吕氏春秋》:“澭水暴益。”中“益”是“溢”的古字,“溢”表示的就是“益”的本义“水漫出”,古字“益”除了表示本义之外,还表示由此引申出的“利益”、“好处”、“增加”等义,表义范围大,而今字“溢”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个意义,所以范围小。前举的“文纹”、“责债”也可说明这种关系。所以,古字和今字在意义上是有联系的。
而通假字的本字与借字之间在意义上没有联系,只看本字和借字的读音是否相同或相近。如前面举例中的“畔通叛”、“信通伸”等,本字和借字的意义都是毫无关系的。
3.从形体结构上看,大多数古字与今字形体中有相同成分。
古今字中的今字大多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是以古字为声符,另加一个表意的形符形成今字,少数的是更换古字的形符构成今字,古字和今字在形体上有相承的关系。如前面所列举的古今字大部分都属于增加形符构成今字。改换形符的如《左传·烛之武退秦师》:“秦伯说,与郑人盟” 中,“说”的意思是“高兴”,后来写作“悦”,因为“高兴”与心理有关,所以就把古字的义符“言”换成了“心”,用“悦”来表示“高兴”、“喜悦”的意思。又如:“没殁”、“赴讣”、“距拒”等皆属这种情况。
而通假字的本字和借字在形体上一般没有联系,它们的联系主要是看读音是否相同或相近,形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如“罢—疲”、“倍—背”、“归—馈”、“要—邀”等。但也不排除有少数通假字的借字借用了相同声符的字,如“详、洋通佯”,“辨通辩”、“辩通辨”,这些通假字的本字和借字的形体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现象需要注意。
4.从古书注释使用的术语来看。古人对通假的注释一般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即“某通某”、“某读若某”、“某读曰某”或“某读与某同”等。因此,凡阅读古书见到这样的注释一般就是通假字(除了有时会用来注音外)。现在的古汉语教材或古书中对这两种字的注释,比较规范的注释为:注释通假字时用“某通某”,而注释古今字一般用“某,某也。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某”。例如“反,返也。这个意义后来写作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今字和通假字是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辨别它们的不同点,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而且在辨别的时候,要综合各种不同点进行,以提高辨别的准确度。
二、通假字和假借字
(一)假借字概说
这里所谓的假借指的是造字假借,即“六书”中的假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定义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是一种用已有的文字作为表音符号来记录无字的新词或新词义的方法。也即说,语言中已有某一个词,但在文字中没有记录它的字,于是就在已有的文字中找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兼记它,这就是假借。例如,“莫”的本义是“日暮”,《论语·侍坐章》:“莫春者,春服既成”中,用的就是本义。因为它与表示“没有什么”、“没有谁”的无定代词的“莫”的读音相同,而作为无定代词的“莫”,表义抽象,无形可象,故当时无法为其造字,就借用了表“日暮”的“莫”来记录,于是“莫”除了本义“日暮”外,又兼表了“没有谁”等假借义。例如《韩非子·五蠹》:“身死而莫之养也”及成语“莫名其妙”中的“莫”就是六书假借字,表示的是“没有谁”或“没有哪一个”之义。
假借字的产生也是由于古代汉字的发展跟不上语言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用字现象。汉字的数量有限,而语言中的词汇无穷,很多字又造不出相应的字来记录,就只能借用一些现成的字来表示,因此,就出现了很多假借字。古汉语中的虚词,大部分都是借一些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的。例如“之”、“与”、“呜”“而”、“然”、“且”、“则”、“何”、“夫”、 “其”、“于”、“或”、“为”、“也”、“邪”、“焉”等,都是假借字。
假借是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一种比较实用的用字方法,它缓冲了用有限的文字记录无穷词汇的矛盾,使语言中没有文字记录的词,只需在现成的文字中借一个同音字代替就可以了,因此,假借字的出现,扩大了文字的使用范围,节制了汉字的无限增长。同时,它是创造新字的桥梁,因为,一个字被假借以后,就形成了一字多义,后人为区别词义,又为这个字的本义或假借义造了新字。例如:
“辟”,本义是“刑法、法度”,《说文》:“辟,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罪也。”它曾被借去表示“躱辟”、“偏辟”,“开辟”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曰:“辟,法也。或借爲僻。或借爲避。或借爲譬。或借爲闢。或借爲壁。或借爲襞。”后人为区别词义,分别为这些意义都另造了避、僻、闢等新字。
因此,六书“假借”最初虽没有增加新字,只是借用音同的现成的字来记录新词,属于“用字之法”,但是,由于假借,又引起了造字的结果,形成了很多新字。所以,人们说它是创造新字的桥梁。
三、通假字和假借字的联系与区别
通假字和假借字的关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假和假借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都要借别的字使用,而且所借的字必须和本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第二,原有字和借字的意义都无联系。例如,例(1)、例(2)中借“畔”记录“叛”、借“信”表示“伸”,例(5)、例(6)中借“队落”的“坠”记录“队列”之“队”、借“采”表示“彩”等,所借字和本字的意义不同,但在语音上都是相同或相近的的,这也是通假和假借的前提。除此,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是否有本字记录词义方面看。通假字是本来有字记录而不用,却找一个同音或音近字代替,即“本有其字,依声托事”。而六书假借是无字记录新词义,而借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使用,即“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近代学者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曾经用“制字之假借”和“用字之假借”来区别它们,他说:“制字之假借一字两用,用字之假借是两字一用;一字两用之假借由于字少,两字一用之假借由于用字之宽。”其中的“制字之假借”就是六书造字假借,“用字之假借”则是古音通假。例如,新,本义是“砍柴”,《说文》:“取木也。从斤,亲声”。其读音和“新旧”的“新”读音相同,而本来就没有给“新旧”的“新”造字,所以,就借与之读音相同的“砍柴”的“新”来记录,从而形成一字两用。一个“新”,既记录“伐新”,又记录“新旧”,所以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古音通假的本字和借字是同时存在的,但书写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用本字,却借用了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记录。例如,例(2)的“信通伸”,本来当时有表“伸展”的“伸”字,《易·系辞上》:“引而伸之”,表示的就是“伸展”,它和“信”同时存在,却借用“信”来表示,就形成了两字一用。也就是说凡是通假字,一般都能找到本字,这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
2.从表义是否固定来看。通假字的通假义是临时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一旦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它的通假义也就不存在了。而假借字的假借义一般是永久使用,一旦借用来记录某个意义后,就长期使用,有的甚至原义消失,而假借义独占原有字形。例如,“焉”本义是“焉鸟”,后被借去作虚词用,本义消失;“离”本义是“黄仓庚也”,借为动词“离开”“距离”等,本义消失。
3.从字形是否有联系看。通假字的本字和借字在形体上一般没有联系,字形没有相承关系,如“蚤早”、“罢疲”、“畔叛”、“倍背”、“要邀”等。而假借字是没有本字的,一开始是一字两用,字形完全相同,同一个字既记录本义,又记录假借义,但后人一般都为其中的本义或假借义另造了新字,而且新造字和本字之间在字形上有相承关系。如前举的“砍新”的“新”被借去表示“新旧”之“新”后,人们在原有字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表意符号,另造了“薪”来记录它的本义。此时,新造字和原有字形成古今字关系,所以,古今字和假借字有时有交叉关系。如
前述的“队”和“坠”,一方面,“队”是“坠”的古字,另一方面,又用“队”表“队列”义,这个意义既非“队”的本义,也不是它的引伸义,从这个角度说,“队”又是一个假借字,是本无其字的假借。这类字,在今字没产生以前应该都是假借字的关系。
因此,从是否产生新字来说,假借是一种造字手段,假借的结果,一般都产生了新字,形成了很多古今字。而通假字只是借用一种现成字的用字方法,没有产生新字。
综上所述,通假字、假借字和古今字是几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特别是假借字和古今字,有时会交错在一起,给我们阅读古书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在运用过程中,要注意弄清楚各自的概念,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抓住不同点,才能准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3〕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江灝.古汉语之假借与通假[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9(3).
〔6〕姚小林.通假字、假借字、古今字的联系与区别[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