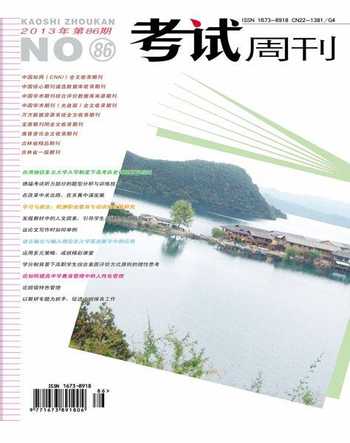菲 茨 杰 拉 德 “美 国 梦” 的 《圣 经》 之 源
2013-04-29胡渝镛
胡渝镛
弗朗西斯·司各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被西方文学评论界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优秀的“编年史家”。他一生虽然短暂,创作生涯充其量也不过20年,但他留下了4部经典式的长篇小说(第五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位君子》还没完成,便与世长辞)和160多篇才情横溢的短篇小说。菲氏的一生及其作品都充分说明,他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是20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既有成功与辉煌的一面,又有苦涩和失意的一面。他的生命交织着雄心和现实、成功和失败、得意和潦倒、纵情和颓废、爱情和痛苦、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矛盾、东部和西部的冲突、梦想和幻灭……这一切都在他的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梦”这一贯穿于美国两百多年文学史的文学主题,虽然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均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其内涵也在不断地积淀、发展,然而探究“美国梦”的历史文化渊源,却不得不提到它与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正是从宗教这一视角,解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探究其创作主题“美国梦”的宗教思想渊源。从《圣经》中的人类重返伊甸园之梦到清教徒开拓天国之梦,这些深邃的思想文化渊源使得菲茨杰拉德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他的“美国梦”的濃厚的宗教色彩。同时,为了渲染他的“美国梦”,他又从集文学与宗教特色于一体的《圣经》中借用大量的人物原型与意象原型,更增强了其作品的深刻性与厚重感。
1.《圣经》与西方文学
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与宗教,无处不在并共同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和文学,在人类历史上,又曾高踞上层建筑之端,左右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文学与宗教之间不仅存在积极与消极的相互影响、联系,而且存在互补与对立的共生关系,以及跨文化体系间的转型复合关系,等等。“文学与宗教的联系,在本文化体系中它们是相互影响彼此共生的关系。首先,它们总是在一定的时期以一定的方式,既在事实上与其历史有联系,又在理论上与其概念相融通,从而形成其文化、文学传统。其次,文学与宗教都同样由意义这一文化资源构成,并以各自的方式组成同一文化中的意义范畴。文学启发式地运用含义,以显示他们的意义所指及其关系的产生;而宗教则寓言式地运用含义,阐明它们的意义和相互关系的次序,以暗示它们的来源和出典。因此就意义而言,它们起同样的经验作用:通过象征帮助人们去理解和对待人同精神的与物质的环境之关系。再次,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无论是看作下意识的信奉,还是看作有意识或无意识构成的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它都会给文学作品提出同一文化体系中的程度不一的神学或信仰等思想问题”。
在研究文学与宗教问题的学者中,曾有人出语,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宗教的历史。这一命题虽然有失偏颇,但对于宗教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其艺术性不仅仅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原型意义上,更重要的是由圣言之“经”而引发的千年之久的人言之“释”所形成的基本教义和基督教文化积淀,与文学之间结成了根深蒂固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圣经》是西方文化之根的话,那么万紫千红的西方文学之花就是从这条根上发芽、成长、开放出来的。“《圣经》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柯勒律治这样说过:读了《伊塞亚书》或者《保罗书》之后,荷马和维吉尔令人生厌,弥尔顿也只能勉强一读了。许多西方的作家都从《圣经》文学里汲取题材进行过创造性的再创作。“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圣经》文学,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学”。西方著名文学评论家诺思罗普·费莱把《圣经》称作“文学象征渊源之一”。南京大学朱维之教授说:“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的《圣经》是世界最幽遂神奇而富于魅力的书。从中世纪以来,它成了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文字、艺术、历史、哲学,随将处遇到《圣经》的内容。”“《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泉或传统之一,不读《圣经》便不能很好地理解西方文学。”《圣经》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各种文体,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永恒的母题。
2.人类重返伊甸园之梦
《圣经》中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违犯了上帝的禁律,被逐出了伊甸园:这是人类犯罪的开始;该隐嫉妒并杀害了弟弟亚伯,被上帝判决并游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人类犯罪的继续。自此以后,人一直生活在罪孽中并渴望着天主的救赎。“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因罪而远离天主,而又因天主的仁爱和圣崇回归天主的历史”。人类始祖在偷吃“禁果”后就开始承受神的惩罚,神曾许诺人类,如果能在尘世中找到从伊甸园中失落的“神圣之果”,就可以宽恕他们所犯下的罪过,重新进入伊甸园。人类寻找时,心里充满希望和梦想,只为了寻找“神圣之果”,踏遍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梦想着找到那“神圣之果”请求神的宽恕,梦想着自己能够重返伊甸园。
纵观《旧约全书》及《新约全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圣经》总体上讲述了上帝造物、惩罚罪恶、引导和拯救人类的历史。无论是从上帝造人、人类始祖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大洪水、上帝与挪亚立约并以彩虹为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出埃及、上帝与摩西立约、上帝与大卫立约、巴比伦囚徒及荣耀冠冕等故事和典故来看,还是由犹太人的伦理规范、民事律例及饱含哲理与对上帝的赞美的文学作品和其他组成部分展开研究,《旧约全书》中贯穿着上帝对人施行创造、惩戒、引导和拯救,同时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梦想着能够重返伊甸园。《旧约全书》还提到因为犹太人一再违约犯罪,上帝决定结束旧约,派圣子耶稣以肉身降临人间,与人类另立“新约”,实施救赎。《新约全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以生动形象和极富想象力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末日审判图景及经过了末日审判以后出现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城中的美好景象。这更加突出了耶稣对人的引领。《圣经》认为,人因偷食“禁果”而犯下原罪就是自身偏离上帝的开始。但上帝从未停止过给人类提供各种悔过和消罪的机会,上帝以艰难困苦警醒和考验人,以圣子耶稣引领人回归乐园。虽然人类心灵距上帝的神性时近时远,然而人类却从未离开过上帝的慈爱和拯救。在上帝的安排下,圣子耶稣在人间布道传教、匡世救人,最终使人的灵魂重归乐园。从“失乐园”到重获“新天新地”是人苦苦追寻的梦想,也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人类蒙上帝之神恩圣助、受上帝之惩戒训导、生诸多卑小与罪愆、历种种磨难和考验,最终在圣子的教导与引领之下,人才会重返伊甸园。这就是人憧憬未来、追逐梦想的雏形。
人类对前景的期盼、对未来的展望,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对各种不同梦想的追逐。这尤其体现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当美国人刚从欧洲大陆迁来不久时,在他们眼中,新大陆就恰如生机勃勃的伊甸园,他们自己就是伊甸园中的亚当。美国独立文化的倡导者爱默生说过,这里站着古朴率真的亚当,以单纯的自我面对整个世界。美国许多作者在作品中描绘了新的乐园和新的亚当。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中塑造了一个亚当式的人物纳蒂·班波,他远离文明的城镇,只身来到美洲的原始森林,看到的完全是一幅亚当在伊甸园中如鱼逢水、悠然自得的图景。惠特曼的名著《草叶集》富于浪漫气息,充满讴歌创造与进取精神的激情。他描绘的虽是美国蒸蒸日上景象,却很像一个新时代的乐园神话。书中有一组名为“亚当的子孙”的诗歌,直接表现了伊甸园的神话意象。
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和波及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人们痛感“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彻底破灭,取而代之的是悲观苦闷,这恰与人类始祖被逐出乐园后的境况暗合。艾略特的《荒原》本身就暗示人类已丧失万物竞生的乐园。后期象征派诗人叶芝也认为世界上到处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要免于沉沦,只有等基督再次降临。他的《基督重现》一诗正表现了诗人的这一世界观。
当代大量西方文学也开始了世俗化,文学主题大多是表现孤独情绪和失落感。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失落感正表明了上帝的失落。因此,这些文学反映的仍属于深层次的“宗教精神”,仍可以从基督教神学中找到根源。在西方世界,不论作家信仰基督教,还是反对基督教,不论他们所选的题材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他们的文字绝不可能与《圣经》不发生关系。《圣经》中的谚语典故及精神早已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什么都不可能把它们分开。所以,“假如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化史要重新撰写”。
正因为如此,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便毫无例外地沿袭思想渊源,在20世纪初美国特定的历史时空和语境下,抒写出了具有自己独特气质的“美国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马焯荣.中西宗教与文学.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1:406.
[2][美]勒兰德·莱肯著.徐钟译.圣经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P13.
[3]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
[4][德]卡尔·白舍客著.静也、常宏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322.
[5]段琦.圣经知识宝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