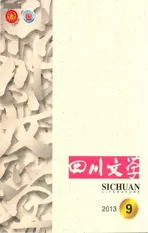春暖花开
2013-04-29第代着冬
第代着冬
春天,绒毛般飘落的雨幕里,满是琐碎而嘈杂的声响。远处,收荒匠“旧书旧报旧电器”的喊声悠扬而突兀。爱玲的目光离开小区吐芽的莹莹树梢,落到晒架的深蓝色床单上。床单是保姆周五洗好后晾晒在那里的。保姆刚离开,一场春雨就飘落下来,空中有了湿滑叶芽绽放的味道。
爱玲把手叉在腰间,缓慢地从客厅沙发上起身。六个月的身孕使她不复轻盈,身材臃肿,背影糟糕,就连她最满意的漂亮的唇线也被多余的脂肪撑得失去了原有轮廓,变成敷衍了事的一抹。她迈着滞重的脚步来到露台上,取下床单,看着天空自言自语说,鬼天气,还在哭。
声音惊动了书房里的麦田。
他刚把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拿到手里,那里面夹有一封旧信。麦田原本没有准备看旧信的。周日的午后无所事事,他像一只觅食的蚂蚁。先在房间里乱窜了一阵,然后来到书房,坐了一小会儿,忽然想读那封旧信。刚把辞典拿到手里,听到爱玲在露台上大声说话,他放下词典,来到露台上说,你喊我?爱玲说,没有,你看这混账天气,下了三天,也不停一下。
麦田抬头看天空。
云朵压得很低,光线凄迷而苍茫,灰暗的色彩像一大块鸟粪,满是黄昏时才有的落寞和忧郁。麦田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落到爱玲身上。她把深蓝色的床单团在怀里,像端着一盆湖水往卧室走去,脸上的表情像个掉钱的失主。麦田知道她在跟雨天斗气,心里暗笑一下,跟上了她的步伐。
麦田觉得,怀孕就像一剂神药,有效放大了女人的脾气。爱玲以前可不是这样。特别是谈恋爱那几年,春天飘落的淫雨,枝头蹿动的画眉,树木绽放的新绿,都能令她诗兴勃发,热情澎湃。那时她可真是一只依人的小鸟,额头饱满的脑后扎着一条马尾,像匹青春靓丽的小母马在大学校园里窜动,吸引着大片男生赤裸骚动的目光。
大四那年,麦田忙着报考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当时,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份工作并不难,他的选择令决定在省城扎根的同学大惑不解。麦田不这样看,他出生在边远山区,小时候见过的头面人物全是乡镇领导,从进入大学开始,他一门心思想当官。他心里想,当官又不是当嫖客,说出来没啥好丢人的。当同学们遥望辽远的星空,畅谈出国,当科学家,或者成为比尔·盖茨二世等远大理想时,麦田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准备当官。
没多久,麦田在校园的名气就跟校花并驾齐驱。同学们很高兴他们中间有一个立志当官的家伙,说明大学校园确实是个百花齐放的地方。到了大四下半学期,麦田毫不犹豫,报考了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他准备充分,态度决绝,轻易在笔试环节斩落一片人马,杀人面试。接到省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电话通知他进入面试那天,金黄的阳光跳出阴霾的云层,照亮了春天的校园。暖洋洋的光芒下,校园的草地渐渐松弛,环护草地的樱花和玉兰绽放出大片花朵,像梦境一样姹紫嫣红。麦田还沉浸在电话中那个金属般冷漠的威严声音里,爱玲从一片刚刚抽叶的夹竹桃后转出来。她穿了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高腰茄克,一米五八的玲珑身躯被年轻而饱满的欲望鼓胀得曲线荡漾,像一匹轻盈的灵猫。爱玲看见麦田若有所思地站在草地边,她说,麦田,你发啥呆,不准备当官啦?麦田说,谁说的?你正在跟一个候补官员讲话,小心点。
爱玲撒娇地呸了一下。
第一次说话之后,春天还没过去,麦田和爱玲就迅速进入热恋。那场铺天盖地的恋情一开始就短兵相接,瞬间进入刺刀见红的白热化状态。除了做噩梦和呕吐,麦田没发现还有什么东西比跟爱玲谈恋爱更加惊心动魄。在他眼里,爱玲真是一只小魔兽。她不断给他平静的生活带来朦胧的月光、生长的植物和寻偶的鸟鸣,除了当官,恋爱中的麦田有了毁坏的激情。
随着毕业临近,麦田不得不面对现实,怀着一颗垂死的心脏来到爱玲家,接受准岳父母的挑选。麦田知道,爱玲家境不错,不仅有洋房,小车,还有一间生产摩托车配件的私人工厂。临近要去见未来岳父母那段时间,麦田天天做怪梦,他一醒来,就按照电视里有钱人的习惯,准备了一系列问答题。从爱因斯坦到老子,从贝多芬到柴可夫斯基,麦田想用足够的高雅来博取准岳父母的欢心。他哪里知道,情况比想象的更严峻,当麦田迈进家门,爱玲的妈妈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几天没洗澡了?
麦田一下子就被这个问题逼到了死角,像一条狗被一根木棍逼到墙角。狗逼急了会咬人,麦田也豁出去了,从洗澡谈到选调生必须下基层,又从基层洗澡不方便谈到他当官的理想。
爱玲的妈妈看着表情慌张的麦田。没有再说什么,礼貌地宴请了这个未来官员,不置可否地把他打发出了家门。第二天晚上。爱玲回学校带来了她父母同意她嫁给麦田的消息。他一把把爱玲搂进怀里,靠到一棵枇杷树上。初夏,枇杷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空中有一股枇杷果化浆的,像蜂蜜一样甘甜的味道。
他们有了接吻。过了几天,他们又有了做爱。仿佛父母的批准使他们获得了参观对方身体的门票,一旦逮到机会,他们就手忙脚乱地跑到对方的身体里走马观花一番。全新的体验差点瓦解了麦田的意志,就在他准备放弃当官这个伟大梦想时,通知来了。他不得不打点起行装,告别爱玲和省城,像一只迷途的斑鸠飞到了乡下。
在乡下工作的三年真是匪夷所思,连麦田自己都不知道那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面对一叠枯燥的报表,一列空荡荡的远山,麦田眼里一天到晚晃动着爱玲的身体,她的鼻息和呻吟。除了拼命工作,麦田一有机会就往省城跑。他像条淫棍,跑到省城就想解裤带。妈的,做一次爱怎么这么难啊?
为了跟爱玲团聚,麦田拼命表现,见到上级首长就点头哈腰,加上准岳母的助推,只用了三年时间,麦田就从洗澡不方便的乡下调回到省城的地名办公室,成了天天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地名打交道的官员。
用麦田老家的俗话说,一个人有好运气。喜事会接二连三,一点不假。麦田调回省城不久,跟爱玲的婚礼如期举行。他岳母在离她居住地不远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花园洋房作为他们的新房。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区,绿树成荫,花木婆娑,弄得前来参加婚礼的同学大呼小叫,艳羡不已。麦田心里也感叹,结婚真好。
五年后,随着爱玲按照预期怀上孩子,他们暂时离开激情如钢花四溅的新婚生活,日子马上显得委琐不堪。麦田看到,他埋进爱玲身上的种子使她产生了能量裂变,过去依人的小鸟成为一只愤怒的小鸟。爱玲开口都带有金属的锵锵声,不时把麦田搞得焦头烂额,没办法,他只好反复哼唱王洛宾那句歌词——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现在,麦田跟着爱玲来到卧室,在她指挥下用那床深蓝色床单换下床上已经用旧的床单。今天是周日,保姆要休双休,宽大的家里只剩他们两个孤独的人影,潮润的雨丝放大了寂寞的味道。麦田细致地把床单的折皱抹平,放上蓝色靠枕,扶爱玲躺上去,看她从床头拿起一件巴掌大的小孩衣裳。放到手里轻柔地比划。亮开的床头灯驱散了雨天的阴暗,勾勒出爱玲安静孕育的轮廓。
麦田看了看,离开卧室回到书房,从《现代汉语词典》里取出旧信。那封信已经微黄,易碎,拿在手里有一种春天抚摸落叶的感觉。信是大二那年小禾写给麦田的,也是她从老家写来的最后一封信。小禾和麦田是高中同学,长得漂亮,安静,喜欢低着眼帘害羞地笑,仿佛笑开了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直到麦田考上大学,两人的爱情才在离别了的两颗心里猛烈燃烧起来,所以他们成为了一对靠信件抚摸对方的恋人。激情四射的恋情只持续了一年,麦田大二时,小禾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以后,就像麦田手中的一捧水似的,无论他如何努力终还是消失了。小禾的离开给麦田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直到两年后爱玲撞进了他的生活。
生活像云朵,说过去就过去了。自从有了爱玲,麦田不再刻意保留小禾的信件。只有这最后一封信竟然被他放到哪本书中给保留了下来。此时无意发现了,看着信纸上娟秀的字迹,一些过去的青涩岁月跟随记忆来到眼前,麦田有了一种别样的心情。尽管麦田没有给爱玲说过他和小禾的事情。但他并没觉得自己有啥秘密。但当他发现这封信,并藏进《现代汉语词典》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小秘密。
周日的午后,空气潮润,窗外的雨丝敲打着新绽的嫩叶,发出蚕子吃食时的轻微声响。麦田坐在椅子上打开信纸。信不长,有一页半的样子。麦田从麦田哥的称呼开始,到小禾的落款,迅速浏览了一遍。小禾从言情小说里摘了大量模糊而温软的句子,像只胆小的昆虫在上面试探性地卿卿我我。看到这里,麦田笑了。这时,咬合不紧的地板上响起爱玲往书房踱过来的脚步声。她的脚步明显吃重,米灰色的实木地板响起弹性极好的“吱吱”声。
麦田不想节外生枝,他把信纸装进信封。看了看周围,词典离他有点远,只好顺手把信塞进了一叠《南方周末》里。那里堆放着两个月来的旧报纸,有《南方周末》,《参考消息》,还有几张从单位带回来的本省日报。
爱玲右手叉着腰,左手提着一只环保菜篮子,像一只肥胖的泥獾,摇摇摆摆地来到门边。她站在门外朝里面看了看,似乎一眼就看到了麦田的慌乱。她皱了皱鼻子,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说,你鬼鬼祟祟的样子干啥?麦田说,大白天的,我能干啥?爱玲把手里的菜篮递过来,又从孕装前面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零钱说,家里没有鸡蛋了,你去门口的超市里买一点。
麦田胡乱答应着,带着一把黑伞走出家门。春雨似乎停了一会儿,路边灌木上新发的嫩叶凝聚起大量水珠。在午后微明的光线中像钻石一般闪亮。空荡荡的小区没有人影,麦田很快来到超市,熟门熟路地找到鸡蛋货架,等他结账出来,发现天空又飘起很密集的雨点。大门外有一口种有睡莲的池塘,麦田看见雨点砸在上面,溅起大片亮白的雨脚。
拎着鸡蛋回到楼下,麦田碰到了二回。二回是个走街串巷的收荒匠,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疏通了小区的保安,麦田常常看见这个跟他年龄相仿的收荒匠手提一杆老秤,熟练地在小区楼栋之间出没。麦田虽然叫不上二回的名字,但脸熟,每次碰见互相都点点头。今天二回穿了一身不太合身的迷彩服,偏大。看上去像个不得志的退伍军人。二回提前停下脚步露出笑脸。看样子他今天收获不错,手里提了一捆用塑料纸裹好的书报,背篼里还有一只旧电饭锅。
二回目送麦田进入单元门,才回身往小区外走去。他到省城当收荒匠快十年了,很摸到了一些门道。花了好长时间,疏通了保安,这个小区几乎就是他的地盘了。这里的业主不缺小钱,价钱好讲,有时运气好,还可以免费得到一些他们丢弃的破烂。今天收获就不错,不仅收到几样旧家电,37幢那个怀孕的女人还送给他大捆旧书报,如果把它们分类出售,应该能卖到二十多元钱。
下午又走了几条街道,黄昏时二回背着到手的破烂,转了两次车,回到他在河边租住的房屋。在省城十多年,二回搬过很多次家,只有现在租住的房屋他很满意。租赁房紧邻河边,看似偏僻,实际交通便利。由于这块地不当道,政府不急于改造,留下大片乱搭乱建的工棚。工棚虽然旧,但宽敞。二回租住的工棚不仅有三间房,还带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院坝。院坝上堆满了他从城里收来的破烂,有纸箱,塑料瓶,旧玻璃,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器。除了电器。破烂已分类码好。电器不行,它们得开膛剖肚,把里面的铜、锡、铝等金属分拣出来,才能卖到废旧物资回收站。二回打开院门时,院坝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他往里走,一路“叮叮哐哐”地响个不停。
放好东西,老婆小禾还没回来。雨天黑得快,刚进屋时,天边还有一抹明丽的亮色,等二回打开手上的报纸,屋外的光线迅速暗下去,像一张不高兴的老人的脸。二回搬出一把木椅坐在屋檐下,准备看看报纸。二回每次把旧书报收回来,归类之前喜欢翻翻,有时会遇到有趣的文章。有一次,他收到一本谈宇宙知识的科普书籍,他看入了迷。按照书上的说法。地球只是银河系中的一个球体,昼夜不停地翻滚。二回想,他一天到晚在球体上滚动,总有一天他会慢慢落下去,一直落到月亮上面。
二回觉得生活蛮有意思。
二回跟小禾的老家在同一个县,以前并不认识。五年前,二回收旧货时在一个小区的垃圾桶里捡到一封请柬。觉得印得很漂亮,顺手就捡了。回到家打开请柬,发现正是他们老家的县政府为了招商,要在省城搞一个同乡会发放的请柬。凡籍贯为本县的处以上官员,教授以上学者,资产过百万的企业家,概在邀请之列。请柬上还印有县长的话,说凡应邀出席同乡会的,都是老家人民最骄傲的儿子。二回显然是个很一般的儿子,他没有收到请柬,但他捡到了一封请柬。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换下迷彩服,穿上一套皱巴巴的西装,揣上请柬按期赴会去了。他知道同乡会吃得不错,老天爷既然给了他这个机会,不去吃几口太可惜了。
同乡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二回来这种高档地方的机会不多,但在城里混了几年,进出酒店并不发怵。他顺利地找到开会的地方,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上百来宾陆续落座。等二回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县长及老家来的一行官员登上主席台。从挺括的西服内里摸出稿子,对着麦克风慷慨陈词了一通。这个过程很短,还没等二回听明白什么。接着就是酒会了。来宾们涌到大厅的一侧,从侍者手里取过红酒,像蝌蚪在水田里摇头摆尾地游动,笑容可掬地亲切交谈。二回学着客人们的样子,端着红酒杯四处走动,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谁也不认识,自己没法像只蝌蚪摇头摆尾地到处游动。骄傲的儿子们要么在谈美国次贷危机,要么在谈普京和梅杰韦德夫的再次洗牌,要么在谈朝鲜半岛核危机,二回没法插嘴。
二回转了一圈,除了酒量比别人大,他没啥东西可拿出来跟人分享,知趣地离开人群,端着酒杯来到边上的一盆棕竹后面。那里人少,清静,可以专心喝酒吃东西。二回走过去时,发现小禾穿了一身小西装站在那里。小禾是陪她的老板来的,她在酒会上站了一会儿。见老板正忙着用不上她了,于是站在了棕竹后面,在这里独享清静,同时透过棕竹的缝隙可以观看那些走来走去的成功人士。
小禾很快就注意到了二回。小禾在餐馆干了几年,别的本事没有,但吃饭不掏钱的客人她一眼就能认出来。她很快看出他是来骗吃骗喝的,此时见他走来,就好笑地招呼说,领导,你在哪个单位高就啊?二回呷了一口酒说,环保部门。小禾觉得逗下去也没多大意思,她说,你少跟我装,我还看不出来你是干啥的?奇怪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听小禾这么一说,二回不用装了,反而轻松下来。他从西装里摸出请柬说,我收旧货时捡到一封请柬。
小禾看了二回手里的请柬,两人就算认识了。以这种方式相识他们很是快乐,仿佛他们专心等候的就是对方。二回和小禾喝起了红酒,喝完后二回就去拿,一杯接一杯,很快他就把自己喝醉了,没能吃上晚上的大餐。还好,纪念品他领到了,一张购物卡和一只苏泊尔高压锅。
同乡会后一个月,初夏,城市有一股稠重的槐花味道。小禾来到二回的租住处。那时二回还没住到河边,在一栋坡地上的老旧砖楼里。砖楼不隔音,有一股很重的生石灰气味。二回喝醉了,小禾是送他回来的。之后小禾再没来过。但他们不时通电话,开始他们说同乡会的事情,接着说到自己的生活,话题越来越多。大半个月后,小禾被老板扣了钱,或者感冒了,就在电话里哭鼻子,她喊一声哥,叫得二回的肠子都揪紧了。恨不得马上把小禾搂到怀里。冷静下来一想,二回又觉得自己配不上小禾。小禾好歹是服务员,他只是一个收荒匠,二回有点自卑。
又等了一个月,小禾见二回没有主动约,就主动上门来了。约着一周见两面,像城里人那样看看电影。吃吃肯德基。事情发展迅速,很快他们就上床了。两个身在他乡的年轻人,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互相的安慰,接下来顺理成章地,二回把小禾娶到了手。
夜色袭过高楼。已经看不清河道上的莹莹树梢。小禾还没回来。二回打开灯,收拾起今天收获的废书旧报,这一摞报纸是37幢那个怀孕的女人送给他的。一封信像一片被风吹动的落叶,掉到了地上。二回伸手去捡起想归于报纸中。一眼却看到信封上熟悉的地址,手一时僵在那里,像一条风中的茄子。信封上的地址跟小禾老家的地址一模一样,连门牌号码也没区别。二回犹豫了片刻,好奇地打开信纸。只浏览了几句,他的目光便定格在信纸上,仿佛纸上有一团火苗,令他眼睛越睁越大,瞳孔越来越小。随着瞳孔像打架的狗眼睛逐渐收缩下去。二回脸上的表情慢慢变成一块生锈的毛铁。满脸都是乌青的铁锈。狗日的,原来,老婆以前也风花雪月过。他想了想37幢男主人麦田的模样,暗自比较了一下,自己真的拿不出手。
这封信像一记打在狗身上的闷棒,给二回带来空前的打击。他呆坐很久,也没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如果小禾知道那个叫麦田的男人住在五公里外的小区。会不会去找他?二回首先想到要把信藏起来。这样想着,他进屋找了一圈,找到一只旧皮鞋盒子。他把信放到鞋盒子里,再把鞋盒子藏到沙发下面,刚舒一口气,小禾回来了。
今天是小饭馆发薪水的日子,小禾按期领到了工资,一高兴就忘了注意别人的表情,她没发现二回丢三落四,一脸不自然。吃过晚饭,看了一会儿没头没尾的电视,关灯上床,小禾像条泥鳅蠕动过来,主动把手伸到二回身上。二回不想让小禾看出他有心事,期望自己表现好一点,但毕竟心里装着事,很影响情绪,二回两腿间那个以前野心蓬勃的家伙像一条弯曲蚯蚓。小禾折腾了半天,说,二回,怎么回事,你搞野鸡了?二回急了,赌咒发誓地说,绝对没有,谁搞野鸡谁是乌龟变的。钱都在你那里。我用啥子去搞野鸡?又不是同乡会,可以混到吃一顿。小禾说,那你说,怎么回事?二回说,阳痿了。小禾说,我知道你阳痿了,我问你,怎么就阳痿了?二回说,中午盒饭吃多了。小禾说。放屁,关盒饭啥事?
小禾不再理二回,她侧过身去,一会儿吹送出入睡的鼾息。二回这才放松下来。他睁着眼睛想,决定明天去会一会那个叫麦田的男人,把事情做个了断。现在小禾是自己的老婆,放着别人老婆的旧信是啥意思?如果麦田要动手,二回准备只打三下。三个耳光,第一下,告诉他,进城丢掉农村恋人,龟儿子,现代陈世美;第二下,让他明白,老婆怀孕了,是个男人都得学会夹紧两腿;第三下,正式宣告,老子的地自己种,不用别人操心。
此时,在同一片夜幕之下,离二回五公里远的地方,麦田同样睁着眼睛,望着空洞的,无边无际的黑暗出神。在他身边,身子日益粗笨的爱玲恣意摊开她的四肢,像一只发福的蜻蜓。当麦田回家听说爱玲把夹有旧信的报纸送给了收荒匠,忽然发现心里空空荡荡的。睡在夜色深处,他想,收荒匠可能一时半会不会把报纸卖掉,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他能够找回小禾的旧信。
早上,连绵的春雨没有停住的迹象,麦田起床洗漱完毕,保姆过来了。夜里没有休息好,头有些沉,像脑子里装了一片模糊的云影。吃过早饭,他把一杯热牛奶送到卧室。自从怀孕后,爱玲喜欢赖床,她曲在床上的样子像只幸福的抱鸡母,张狂的姿态中流露出小小的得意。麦田把牛奶放到床头柜上,摸了摸爱玲的头发说,我上班去了,如果你再见到收荒匠,给我打个电话,让他等一会儿,我们单位有旧东西要处理。爱玲说,知道了。
麦田出门跑了几步,到树阴下开出别克轿车,离开小区汇人大路。路上不是太堵,他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到达单位。地名办公室在政府大院边上,是一栋七十年代的老旧建筑。麦田进屋泡好茶,一时想不起干啥事,只好坐在办公桌前发呆。麦田发现,官并不容易当上。他在这间办公室坐了几年,看着奇形怪状的地名在自己眼前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尽管它们爬了很久,他还是连个副调研员也没混上。想起过去野心蓬勃,麦田觉得有些好笑。
上午没啥正事,下午开了一个小会,快下班时,电话响了。电话是爱玲打来的,她说收荒匠又在楼下喊“旧书旧报旧电器”,让她喊住了。她问了,收荒匠叫二回。麦田没等爱玲说完,撂下电话,下楼开出小车,离开了单位。
麦田回到家,看见二回依然穿着那身迷彩服,站在他们家敞开的门口,没有进去。他的表情不很自然,像条挨人揍过的狗——既想寻人报仇,满脸的不高兴;又怕再挨一次揍,眼里闪烁着胆小而游离的光芒。麦田走到门边,看见爱玲站在门后,他没有进屋,隔着门框把公文包递给她说。我带他去取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爱玲接过包说,用得着这么急,明天不行吗?麦田说,明天别人就买走了。不等自己把话说完,麦田用手抓住二回的胳膊往楼下引,到了一棵桂花树下。树叶上粗大的雨粒砸落到他们脸上,使他们看上去像两个悲痛欲绝的男人,满脸泪痕。麦田松开二回的手臂说,你昨天从我们家带回去的报纸卖没卖?你放心,报纸还是归你。二回说,我不放心,我知道你想要那封信,我专门来告诉你,信你别想拿回去。麦田说,懂不懂,偷看别人的信犯法!二回说,犯个铲铲,那是我老婆写的,你看才犯法。麦田说,打胡乱说,小禾是我过去的女朋友。二回说,她现在是我老婆。听着二回坚定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麦田惊讶地张大嘴巴,像看外星人那样看着二回。
两个男人站在树下又争执了几句,情节一点点浮现,搞得麦田脑子很乱,理不出个头绪。争执到最后,麦田让二回坐上车,到他租住的地方一看究竟。在二回的指引下,小车沿主干道走了两公里,拐进一条支路,接着下到河边,又沿河滨公路上行了几分钟,到了一个工棚连片的地方。麦田泊好车,将信将疑地跟在二回身后,钻进了一条布满泥淖的小路。
推开院门,麦田闻到一股混着垃圾气息的浓重泥腥味。他看见,院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废旧物品,有用的整齐地码在一边。没用的则被胡乱丢在地上,连绵的雨水正一点点地把它们沤烂。麦田像只兔子,一蹦一蹦地往前跳。他走过的地方,连续的水淖上露出暗淡的倒影,天色正急剧地度过黄昏,慢慢沉入黑暗。
小禾已经回家,她刚在厨房切开一只老南瓜,就听见院门传出响声,知道二回回来了。她把菜刀停在空中等了等,没有听到二回的声音。过去,只要她先回家,二回进门就会快乐地高喊,接着听见重物落地。小禾担心小偷进屋,她把菜刀放下,关掉灶上的液化气,肩上搭着一块毛巾走出厨房。走到门口。看见二回阴着一张脸站在檐下,一个衣着干净的男人像一只没有吃饱的跳蚤,拖拖拉拉地跳过院坝。
小禾认出了麦田。
小禾认出麦田的瞬间,麦田抬起头,吃惊地看见小禾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站在门边,像一张表现农村女民兵的宣传画挂在那里,朴素,粗糙,又有几分笨拙。麦田走到跟前,有些不敢确认,他试探着说,小穗,是你?小禾说,麦田哥,是我。说完,她想让二回让座,回过头,看见二回从屋里抱出一只旧皮鞋盒子,大概他听到了麦田喊小禾叫小穗,吃惊地愣在门边,像一棵被雷击的老树。小禾说,二回,你不去端板凳,抱一只旧鞋盒干啥?这是麦田哥。又对麦田说,麦田哥,你怎么碰到二回了?麦田说,他到我们小区收旧货,把你姐姐给我的一封信收走了。小禾说。要是姐姐在就好了。
小禾把麦田引进屋坐下,二回抱着旧鞋盒站在旁边。通过他们的交谈,二回弄清楚了。原来,小禾不叫小禾,叫小穗。麦田大二那年,小穗的姐姐小禾在老家小水电站工地上出事故死了,她爸爸妈妈天天哭着喊小禾,小穗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小禾,让她爸爸妈妈再喊姐姐的名字时,有人答应。听小禾说起亲情时,麦田僵硬的脸抽了抽。咬肌明显地突起来,像两条泥鳅挂在腮边。二回见麦田回头看着自己,把旧信从鞋盒里取出来说,信给你,但你不能走,我要请你喝酒。
二回跑到门外买酒。
晚上喝了不少。喝掉一斤白酒,二回还想开啤酒,让小禾挡住了。在喝酒的过程中,麦田决定回家把过去的事情告诉爱玲,如果她愿意,也可以看看这封失而复得的旧信。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请二回和小禾到家里来喝顿酒。这个念头让麦田变得轻松快乐,他突然发现,除了爱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切都显得不重要。连当官的梦想也无足轻重。
麦田从二回家出来,发现连续下了三天的春雨突然停住,空中动荡起一缕阴凉与清新。他因为喝了酒,没敢开车,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在小区大门外下车往里走,麦田发现。雨过天晴的夜空清爽甘甜,沁人心脾,轻拂的晚风中有一股春天厚重的暖气。他深深吸了一口,看见路边粉红色的樱花在杏黄色的路灯光下一片片绽放。多么美好的季节啊,春暖花开,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呢?
音任编辑:张即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