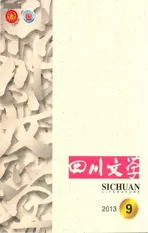张心阳杂文精选小辑
2013-04-29
作者简介:张心阳。安徽桐城人。高级编辑。1979年2月参加南疆作战。三次立功。1988年从事专业媒体工作并开始杂文随笔写作。现为北京杂文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出版《带毒的亲吻》《中国杂文·张心阳集》等多部文集。十余篇文章选入中学生课外读物。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并撰写的系列杂文曾在文坛引起波澜。
我相信这样的“阵痛逻辑”
管辖湖南凤凰古城的县政府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连同沈从文、吊脚楼、苗寨风情、苗家美食等一起,将古城以51%的股份卖给了开发商,继而以每位游客148元的价格收取门票。因为限制了游客进城,古城里酒店、客栈、船主等商户顿时生意惨淡,于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在美丽的古城持续爆发。抗议者拥向街道、拥向城门。拥向河边。
面对群体性事件,我们的政府已然学得相当成熟。气舒神定,他们只动用警察,没有慌张。没有退缩,也不必对商户妥协。县主管官员带着领袖般的口吻对媒体说:“这是新政带来的一个现实”,“新政阵痛是必然的。”
我非常佩服这位官员的水平,他的话深得中国目前社会管理之精髓,人们的一切心结都可以从中释然,没有丝毫的理由不相信这样的“阵痛逻辑”。当代中国人就是这样从一个个阵痛中走过来的,随着人们适应和习惯一个个阵痛。让阵痛变成长痛,长痛变得麻木,之后就不再有痛感了。这次凤凰城商户的阵痛,无非是生意萧条的阵痛,须知,中国人有多少阵痛要比这高出N“分贝”。
人们印象里最早的是物价之痛,那年头一说盐要涨价、米要涨价、煤球要涨价,人们那个抢购,用排山倒海来形容也不过分。后来是什么东西都涨价。想涨价就涨价。不该涨价的也涨价,就再罕见有多少人排队抢购什么东西了,听到涨价的声音就像秋天听说树要落片叶一样。这就是阵痛变成了长痛而不觉得痛的感觉。
近几年的住房也是百姓心中一个痛,当初房价涨一涨,百姓痛一痛,政府管一管。而将实际情况连成一条线来看,政府越管,房价越涨,管了十年,疯涨十年。人们怀疑。这政府是不是房产商的托儿,或是房地产商后台老板?现在百姓再也没有心情焦虑和疼痛了,因为敏感的神经早已碎成N段,不再指望政策,也不质疑政策,能做的。就是看政策里有什么漏洞,比如婚姻与住房的关系,通过离婚再复婚、复婚再离婚的折腾,钻点房政空子。
如果人们不会忘记,某年的社会动荡与腐败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那时人们神经还敏感,充分感受到腐败之伤痛,对查出个贪污几十万的贪官就恨不能碎尸万段。现在早已不这样了。出现贪污几千万乃至上亿的官员,也当成笑话调侃,谁要是钱贪少了、情妇养少了,被举报出来还觉得挺冤,深表同情。因由也自不必说,过去人们痛恨腐败是没有适应腐败,逐渐地腐败人物多起来,腐败质量提高,成为常态,大家就习惯了。不信试试,中国人三个月不闻腐败事件。反而觉得身上像沾了跳蚤似的,很不习惯。
这期间自然还有下岗阵痛、教育阵痛、医改阵痛、钞票贬值阵痛、有毒食品阵痛、禁言禁语阵痛、被代表被增长被幸福被死亡阵痛……中国百姓似乎命里注定要经历人生全方位、全过程的阵痛,从经济利益到民主权利,从自然生态到人身自由。从维护私有财产到维护人格尊严……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待遇不公的阵痛,从走上社会就开始面对机遇不公的阵痛,从一行使个人权利开始就遭遇权利不公的阵痛。从走出产道的阵痛,一直到焚尸炉的阵痛。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们的一些社会管理者深谙此理。天天侵占你的利益,久而不知利益被侵占;天天剥夺你的权利,久而不知权利被褫夺;天天麻醉你的神经。久而不知神经已被麻醉。我不相信,凤凰古城被政府和开发商强行夺走垄断经营权后,普通商户仅仅是个阵痛,十天半个月又能恢复经营生机。门票的意义就是要把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挡在门外,这是傻子都晓得的道理。我相信的是,县长大人所说的“阵痛逻辑”是真理,商户们强忍着惨淡的生意,持续地强忍着惨淡的生意,最后不得不使一部分人撤离市场,关门大吉,沦落为民工或盲流,中产变成无产。对新政造成的“阵痛”成为一生刻骨铭心的回忆。因为他们正在精制地制造着又一个“阵痛逻辑”的标本。
“阵痛逻辑”衍生出难以数计的新概念和现实,比如,多少人以为当下热门词汇“屏丝”是个庸俗不堪之词,然而我就不这样认为。这是人们经历了一次次阵痛的结果,是长痛、久痛之后神经麻痹的哀叹。有识之士呼吁,不要让有志青年都成为屌丝。可屌丝的感觉就是国人经历了一次次阵痛的感觉,它是时代留下的一个深刻的符号。
气场乎 气虚乎
有一个说法:大人物是有气场的。说这个气场散发一种人难见、神莫测的能量,可以形成一种冲击波,让人自我矮化。不击自溃。许多人都在这么说,但好像都没怎么经历过。不过,我倒是看到有人经历过。
那是在某单位成立×周年的时候,某大人物要来视察。大家早早就剃好胡子理好发,还有女同胞专门买了鲜艳的衣服,如同过年。视察那天,大家站好准备与大人物合影的队形。静静地等待大人物的出现。可是,大人物就是迟迟不出现,于是大家就耐心地等待,半小时、一小时地等待。许多人越是等待,就越有一种期待感,越有期待感,就越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地失重。终于,突然有人宣布,大人物已到,请大家热烈鼓掌。于是,我明显地看到有人就像受到一种无形能量的冲击,重心顿时不稳。身体开始晃动。行止有些失常,头脑像是出现了空白……我想。这大概就是大人物气场所产生的作用吧。
可能是我天生木讷,神经不够敏感,与许多人不太一样。没有感受到大人物有那么大的气场,就那么呆呆地站着,也没有太多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不过过后我还是似信非信地认为,大人物是有气场的,不然,一见大人物怎么那么多人反应强烈。
然而,有一件事把我将信将疑那点想法颠覆了。那是在H国发生的一件事,一位出租车司机像往常一样拉客赚钱。傍晚时分他拉到一位顾客,与平常一样看也没看拉着就走。走着走着彼此就不由自主地攀谈起来,谈社会、谈人生、谈生活不顺心的事,有时还不免夹带一些脏话。后来遇到堵车,司机瞅了顾客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原来这顾客不是别人,正是他早有耳闻的大人物。这时突然就慌了神。脑子有点蒙,心跳也加快,汗不住地往下淌,想接着再说点什么,可就是说不出来。一句话,当初与顾客闲聊时的那种自然,那种心平气舒,顿时荡然无存。
为什么说我得知这件事后,当初以为大人物是有气场的观点就被彻底颠覆了呢?你看那出租司机,在不知身边坐着的是大人物时,他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一如往常,十分平静;而当他得知他是大人物时,一下子就像遭遇了冲击波,心理支撑顿时坍塌,汗水出,话语塞,头脑蒙。你想,如果大人物真有气场的话,那他一上车司机就会感觉到非同寻常,伟光四射,车壁生辉,心情亢奋,犹如被如来佛光照耀。可他没这感觉,一点也没有。
我曾一直想建议气功大师将大人物是否有气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工程来研究。倘能研究个成果出来,通过测定气场来断定何人将来能成大人物,写出“气场决定论”论文,就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或诺贝尔奖什么的。气场属于物理现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人获物理诺奖还是空白,如果我们得上了,那又可以像莫言得文学奖一样,让咱们傲视世界一回。只可惜,这个试验让一个出租司机在不经意间做了,让人很失望地感到,大人物一点气场也没有。
断言大人物没气场,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不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到医院考察工作。结果被医生认为挡了给病人治疗的通道,叫卡梅伦等一干人统统滚出去。开始卡梅伦以为自己有气场,不可能让人撼动,只叫随行人员出去。可医生就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大人物气场的存在,口中嚷嚷着“我不吃这一套”什么的,让人觉得倒是这个医生气场极强,最后卡梅伦想发功也不成,只好悻悻离开。
我在想,为什么大人物和普通人一样就是没气场呢?后来在掉到地上的一张纸片上看到也是一个大人物说的话:“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终于大释所然。中国人真的跪得太久了,都世界GDP老二了,都把人送上太空了,精神上还在跪着。还说本文开头所说的接见,且不说制度体制、宣传机器早已把大人物营造得神秘莫测、神通广大。就是那现场环境和气氛的营造,也让大人物如同神从天降。大人物要在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出来,要人们等到心理几近崩溃才出来,要在前呼后拥中出来。这绝对是一个心理战,这种战法本身就在构成了一种冲击波,从心理上先把常人打垮。
貌似被大人物打垮,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垮。我们自己一直在跪着。崇拜权力,极度崇拜极端的权力;敬畏权力,极度敬畏极端的权力。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多少人根本也不知道,大人物权力原来不过普通人授给他们的,大人物之以所以能活着,是因为普通人用粮食喂养的。你哪一天断了他的粮食试试,看他还有大人物样子没有?人们哪一天不在他的周围唱赞歌试试,他还有大人物的谱儿没有?
说大人物有气场是唬人的,而普通人自造神仙,见了神仙就晕场,才是事实。
哪有气场,只有气虚。
丑行不在于脚跷多高
一位左派人士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把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一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不同工作场合跷脚、以至引来其身边工作人员不屑的照片转发到网上。该左士对此情绪颇为激动,弦外有音地感叹道:“哇塞,这只是习惯吗?”
跷脚或者说跷二郎腿,对很多人来说就不过是个习惯。有医生说,这是个不坏的习惯,适当的时候把脚抬高,有利于增进血液循环。这里,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不是习惯,如果不是本能地增进血液循环,那该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某些爱用“左”眼观事者的思维,或许应当从政治层面来解读。比如,一个可以在总统府里把脚跷到办公桌上的人。那他也一定能把脚跷到人民的头上:一个在生活上都不注重小节的总统。政治上也一定会为所欲为。这样的演绎,一点也没越出他们的惯用逻辑。
其实,这种“生活小节决定论”早已被二战时期的著名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打破了。罗斯福的相信巫术、搞婚外情。丘吉尔的嗜酒如命、吸食鸦片等恶习,不知要比爱国信仰坚定、保持素食主义、做事极有条理、无任何不良嗜好的希特勒的“良好品行”要恶劣多少倍。但他们给国家和人类留下的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重要人物从来都被作为社会道德楷模来看待,其一言一行既代表一国之形象,也对国人具有示范效应,不谓不重要。比如最近,俄国总统普京在日本首相安倍来访发言时玩手中的铅笔,就很受国际社会诟病。比尔·盖茨在接受韩国总统朴槿惠接见时,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被韩国媒体视为不知礼节而被骂得狗血喷头。不过,往根子上说,人们看待政要,觉得顺其自然、不刻意掩饰普通人的一面,还是要比把内心的肮脏伪装起来,成天作正人君子状。要可爱得多。
在历史的大人物中,不只是希特勒以其完美无缺的外在形象示人。前苏联的某个领袖也曾经多少年被人当作无比崇高、无比伟大的“上帝”供奉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专门以虐杀善良的动物为快乐,专门以听取同僚被契卡施以肉体折磨而发出的嚎叫声为快乐,他不仅斩杀了当年和自己一起起家的大部分战友,而且致使数百万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人头落地。而我们去察看一下他的从政史,却是从来没有过跷二郎腿之类恶习记录的。不仅如此,而且没有一个夜晚不是“办公室里的灯亮到天明”,没有一个时候不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操碎了心”。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体制,就是运用各种宣传机器甚至暴力来遮蔽那里的大人物的丑行。他们贪得无厌,富可敌国,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副清心寡欲、天下为公的形象;他们残酷无情、剪除异己、灭掉政敌,却被作为纯洁本党、为我人民来大加渲染:他们权力嫡传、基因决定、用人唯亲。却被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历史的选择;他们喜新厌旧、玩弄女性,却以志趣相投、理想远大而加以赞美;他们各立山头、拉帮结派、相互倾扎,却被表现成一派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很难列数这个世界上这种组织有多少,但已垮台的前苏联和罗马尼亚等东欧政权无疑是典型代表。人们确实不曾见过关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齐奥塞斯库等跷二郎腿的有损其光辉形象的报道,但上述所有行为无一不是他们政治生涯中的家常便饭。对此,不知道我们某些富有发现眼光的人。为何一点也不惊讶、不感叹。
大人物真正的丑行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不适当的场合跷了多少次二郎腿,也不是半夜起床还要贪喝几夸特威士忌,甚至不是意淫过谁和感情移位。而是政治上的丑行、人格上的丑行。反人类、反人权、出卖国家利益的丑行,并且还要将其掩盖起来。大加粉饰,渺小被歌颂为伟大,拙政被吹捧为盛世,造孽被美化为造福。这种人才真正的祸国殃民,才是最大的丑恶。
在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下,大人物再有能耐最多也只能把脚跷到桌子上。在一个不好的政治制度下,大人物的脚也许不跷在桌子上,但往往跷到人民的头上。跷起看不见的脚比跷起看得见的脚更可怕。
此兰彼兰
汉文化里因为一个人而诞生一个新汉字——(“√”下面一个“三”字)。这个字这样释义:上面“√”表示同意。下面不是“三”。而是一十二,舍起来就是一十二次都同意。此人岗位神圣,手举神器,代人入庙堂议政,历时六十载,代表十二回,人谓之为共和政权之活化石。这个字由“兰”字变异而来,缘于此人尊姓大名中有个“兰”字,姑且音也读“兰”。
这恐怕是世界政坛上极其罕见的活化石,也是现政体的活标本。典型意义必定永载史册。当年克林顿调侃与米国相邻的某国元首:当初我上幼儿园时,他就是总统:我上小学时,他是总统;我上中学时,他是总统;我上大学时,他是总统;我工作后,他还是总统;我结婚后,他还是总统;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总统任期满了,他居然还是总统。克林顿如果遇见活化石,完全可以将这番话语套之一用:我上幼儿园时,她手举神器;我上小学时,她手举神器;我上中学时,她手举神器……我总统任期满了,她居然还手举神器。
一个人高居庙堂,能把神器举这么久,最大的秘诀就是“三”上面那个“√”。她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忠诚二字可形容我一生”。章伯钧不懂得这个道理,握神器仅四年即旁落。马寅初不懂得这个道理,握神器仅十年即丧失。彭德怀也不懂得这道理,握神器也不过十来年,最后连性命都搭进去了。
庙堂之上的事情我不大懂。由此联想到的是我娘姓名中也讳一个“兰”字——淑兰。她是不识多少字的家庭主妇,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四方邻居只知她叫“张老太太”,欲知其真名实名得上公安局查户口簿。她与她年龄相仿,但此“兰”永远也不比彼“兰”幸运。
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或代表自己或代表别人,或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我娘也常面临如此选择,她很多时候也选择“同意”——尽管不知表决器为何物。
那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树皮树叶被人吃光,观音土也都被挖空,许多人饿成浮肿,许多人头天还在食堂照过面,第二天就草席裹走了。大食堂成了地地道道的食人堂。这天一样也在食堂等着捞不着米粒的饭食,公社书记走过来,我娘不知哪来的胆子,靠上去说:“书记,你敢不敢把食堂解散了?你要是怕担责,征求意见,我今天说的话算是第一个同意。”那年代,说这档子话是犯天条的事,好在书记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母亲的同意注定不会被同意,但也就算什么也没有说。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喊“万岁”喊得惊天动地、灿烂辉煌,俺娘一听就不耐烦:“古时候哪个皇帝不被喊万岁,见谁万岁了?我看都万睡了。如果喊万岁,实活百十岁,那等于打到一折,还是个短命的哩。要是喊个‘身体健康什么的,我倒同意。”
我父亲是个两肋插刀、疾恶如仇的人。一辈子除了税务工作就是替人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对仗势欺人、以权压人、横行乡里的人。能豁出命来和他们干。这其实是要给自身和家庭添麻烦的,可我娘居然从来没反对过。有一年大年除夕,我娘一开门,便见门口摆着一担稠稠的人粪,她很快知道是什么意思,遭人“行为艺术了”,很想哭,但她没哭,一抖擞精神,把那担粪挑进了田里浇了小麦。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开年遏吉兆啊,有人给我们送肥料,那是祝咱家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我娘对我爸的行为从未说同意,但同意在心里。
她同意人要明是非、知丑恶、持公道、讲正义。反右你同意、反左你也同意,吃大食堂你同意、包产到户你也同意。闭关锁国你同意、改革开放你也同意,斗私批修你同意、不论姓资姓社你也同意。对这样的人,用我娘的话说:“那叫思想婊子。”
我娘很喜欢她名字里那个“兰”字。繁体是“一”下面一个“门”,门里有个“柬”。她说,即使是一棵小草,那也要长在门头上。那该说的真话还要是说。我说,兰与兰不一样,您是那高贵典雅的惠兰,可还有头朝下的吊兰。娘说:“你以为头朝下吊着不造孽啊。”
“兰不生当卢,别是闲庭草。夙被霜露欺,红荣已先老。”李白这首咏兰草诗的前两句,俺娘是用得上的。她没进过庙堂,她没举过神器,她就是一棵普通的草。确实不及有的草那么幸运。但她有无数无名草的高贵品格,不是风吹两边倒的草。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虚伪的草。吃自己的饭。做自己的草,无愧于自己,无愧于自然,无愧于草朋草友。
李白这首诗还有后两句。诗云:“谬接瑶华枝,结根君王池。顾无馨香美,叨沐清风吹。”这大概就是原本是棵无名草,摇身一变成为“√”字头的草了。接在瑶池边。伴在君王侧,看上去风光无限。但说到底也就做了个花盆而已,等到那点可怜的馨香没了,就风吹雨打去了。
责任编辑: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