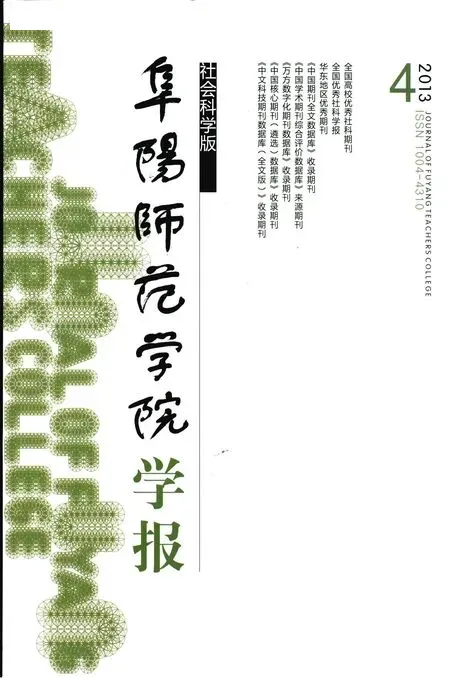汉代春秋决狱之价值评析
2013-04-18窦晓玲
窦晓玲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通读整个中国法制史的教材,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法制史实际上记录了整个中华法系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春秋决狱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大规模的礼法结合的法律传统,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融合的有益尝试,对于中国封建法律传统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决狱概述
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中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的依据指导司法实践。其出现在汉代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秦朝的法律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而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下,秦朝的法律体系表现出“严而少恩”的特色。在秦朝,法律被推崇为规范一切社会行为的唯一准则,加上秦朝秉承法家“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立法原则,使得其法律被后世评价为“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盐铁论·刑德》)。秦朝仅存二世而亡,应该说与其严刑峻法不无关系。陆贾也在《新语·无为篇》中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了轻徭薄赋等与民生息的做法。在法律的制定方面亦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态度,约法省刑。有历史资料显示,汉高祖入关时,仅与乡亲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实际上后来汉高祖刘邦亦认为三章之法太简略,难以适应统治的需要。于是命相国萧何作律九章,史称《汉九章》又称《九章律》,自此汉朝律令才基本成型。从内容上来看,《九章律》是在秦朝《法经》的基础上又加入户、兴、厮三律而成的。尽管其以约法省禁为原则,对一些定罪和刑罚亦有所减缓,但是实际上秦律的指导思想乃至秦律中定罪科刑的标准并未加以改动,且一些酷法和苛法也都保留了下来[1]。可见,一方面汉朝统治者忌讳秦朝的严刑峻法,而另一方面在法律的制定上却又不得不沿袭秦朝律令。这就造成了立法原则与实际立法中的矛盾。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加入礼的思想和精神便成了较为适宜的选择。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当然,实际上当时的儒术已经不仅仅是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从孔子到董仲舒,其间经过了孟子、荀子等人对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当时的儒学在经过改造后已经形成了兼具各家学派之长的儒学,其中也包括法家理论中的有益部分。这一学说体系的中心思想就是建立一套长幼有序、尊卑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秩序。而这样的儒学恰好能够满足当时汉武帝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需要,故为汉武帝所大力推崇。汉武帝对于儒术的推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儒之风,自然而然官吏中的儒生也渐渐增加,且古代官吏身兼行政和司法之职,加上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时常引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进行司法审判,这样司法领域内儒家思想的推进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原心定罪及其价值评析
原心定罪可以说是春秋决狱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对相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主要是刑法评价)时要充分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动机,甚至行为人之客观行为及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都是次要的。对此董仲舒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着其论轻。”[2]解释起来就是说,按照《春秋》进行断案,首先要查清案件事实,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还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如果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恶的,那么不需要等到犯罪完成时就可对其进行处罚,为首的人即主谋的人罪行最大,处罚也最重,而对于主观动机是善的人,则可以从轻处罚甚至不处罚。以当时董仲舒审判的案件来说则更加清楚明白:
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执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3]
该例中甲作为儿子伤其父乙,按照当时的法律,甲应被判死刑。然董仲舒对此援引《春秋》中的经典事例,解释道:甲虽然误伤其父,但分析其主观方面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想救他父亲的。即其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的经义,所以“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客观地说,原心定罪有其积极的一面,其强调在对行为人进行刑法评价时应该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这一点应该说在当时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因为在此之前的秦朝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审判的。即只要行为人之行为从客观上来讲符合刑法的某一个条文,则不管其主观方面如何,直接按照法律来定罪处罚。如在著名的大泽乡起义中,被大雨所阻导致赶去戍守的陈胜、吴广等一批军人失期,而按照秦朝法律,军人失期就是死罪,而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考虑主观方面,这才导致一干人等揭竿而起。总的来说,秦朝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归罪,而从上述史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客观归罪往往有失偏颇,应予以纠正。而原心定罪要求在考虑行为人客观行为的基础上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纳入法律评价的体系中,就这一点来说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原心定罪消极的一面,即当原心定罪被运用到极致后,就会导致“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亦即只要主观动机合乎儒家的精神,就算客观上违法也可以被免责,而主观动机不合儒家精神的就算行为在客观上合法也不可被免于追究责任。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思想罪”,是彻彻底底的主观归罪。且其中作为评定志善或者志恶的标准的儒家的道义和精神又具有不确定性,极易导致司法的混乱。
然而尽管以当代的法律思维来看,原心定罪是荒有其荒唐甚至可笑的地方,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些,即当时的原心定罪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将人们的犯罪行为扼杀在尚未萌发的状态中。在没有民主而又强调等级观念的封建社会,这一做法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治国需要的。
三、亲亲得相首匿及其价值评析
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刑罚适用原则之一,大概的意思就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包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其来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法家是反对相隐的,而且商鞅还为此制定了连坐之法,鼓励吿奸。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秦律是区分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其中非公室告包括子女盗窃自己父母的财产,以及父母对子女、主人对奴妾肆意加诸的各种刑罚等案件是不允许告诉的,即使相关人员进行告诉,官府也是不予受理的,甚至还要追究告诉者的责任。可见在对家长父权和尊卑等级的维护方面儒法两家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影响下,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下诏明确规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4]据此,卑幼隐匿有罪尊长,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尊长隐匿有罪卑幼,犯死罪的可上请廷尉决定是否追究罪责,死罪以下也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举例来说:
例: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罪?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3]。可见,在当时对于一定范围内亲属间的隐匿法律上是允许的。不过,一方面其范围仅限于几种直系亲属关系,另一方面其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如其对“谋反”、“不道”等重罪就是不适用的。对于这几种特殊的重罪案件,则另以春秋“大义灭亲”为据,其亲属非但不得首匿,相反还要告发;否则,法律将严厉制裁[5]。
在笔者看来,亲属相隐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应当予以准许。如果强迫犯罪嫌疑人亲属承担告发亲属犯罪的义务,一方面在现实中无法很好地落实,容易导致相关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强行要求当事人背弃亲情伦理,将会导致亲情淡化,人格扭曲,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目前,很多国家在诉讼中都不要求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承担提供不利证据的义务。而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的例外,笔者认为这虽然不是亲属间相隐的直接立法规定,但其也算得上是亲属间相隐的精神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的一个体现。
除上述内容外春秋决狱中还有很多原则值得具体分析。像“恶恶止其身”原则,又称“罪止其身”,是指在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惩罚,而不株连无辜。这一原则与当今世界刑法理论中的责任主义原则不谋而合。不过遗憾的是这一原则一不适用于相关的重罪,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加以贯彻。还有号称是古代中国疑罪从无的名言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亦是春秋决狱所倡导的准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偏宽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这一原则即使在当代也被认为是具有相当积极意义的。此外,春秋决狱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则或准则,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综合来评价春秋决狱这一历史现象,其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方面兼顾了个案的正义,在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或者按照相关规定会导致结果的实质不公正的情形下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法律原则,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妥善解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首先春秋决狱对司法官要求很高,即其要精通儒家经典,否则将无从断案,而这又是不现实的。其次儒家经典是一套十分庞杂和琐碎的体系,且其语句简短,而内容丰富,从而极易导致不同的儒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而将其作为评判案件的依据则未免太过随意,给司法者留下了太多自由裁量的余地,也为官吏的枉法裁判提供了借口。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无论哪一时代的法律条文都只能针对社会的一般状况做出规定,法律的确定性会导致法律的僵化,而司法实践中的个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又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因此原心定罪体现了法律的实质理性,这远比形式上的理性要重要得多[6]。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诚然法律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法律的确定性容易导致其僵化,而法律的不确定性则会破坏其作用的发挥,走向“人治”,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求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那个平衡点,使法律在对行为人之行为进行评价时既能够作为准则得出相对确定和唯一的结论,而又不失其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春秋决狱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作为对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的春秋经义所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从而极易导致不同司法者依据春秋经义进行司法审判时的结论的多样性,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有走向法律虚无主义的嫌疑。
当然,对待历史,我们还应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开启了以经义审判案件的司法传统,在过去一味强调客观归罪的大背景下主张对行为进行法律评价时应该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这一点应该说是春秋决狱对于司法审判实践最大的价值所在了。且在春秋决狱的影响下,礼法进一步的结合,乃至在后世出现了引经入律的立法实践,如“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的相继入律都或多或少受到春秋决狱的影响。乃至唐朝作为封建法制的巅峰,在致人死亡中区分“谋杀”和“过失杀”也与其不无关系。而在立法中加入礼的观念和道德因素,从而使“恶法”向“良法”转变又可谓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所以说,春秋决狱对于整个中华法系的形成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百度百科.九章律[EB/OL].http: //baike.baidu.com/view/37374.htm.
[2]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218.
[3]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 中华书局,2003.161-162.
[4]钱大群.中国法制史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78.177.
[5]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EB/OL].http: //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kongzi3/201001/0118 _ 9295 _1515466.shtml.
[6]孙家洲.秦汉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