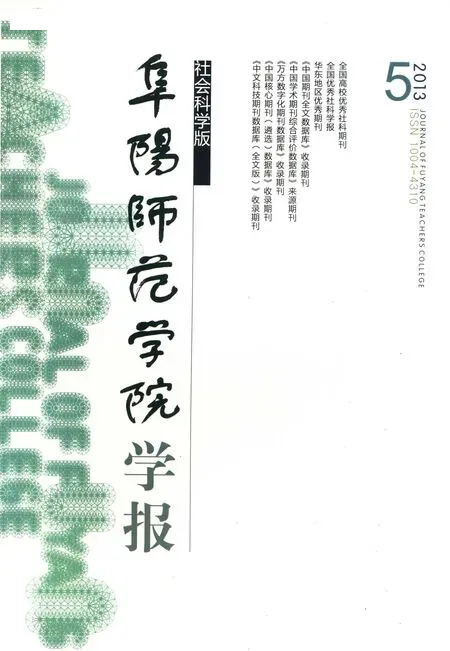张謇未参与红十字会运动原因探析
2013-04-18蒋国宏
蒋国宏
(1.南通大学地方公共政策研究所;2.南通红十字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张謇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称之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1]3毛泽东在20 世纪50年代接见黄炎培时也曾表示,“谈到近代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孝若是张謇之子,也是民国时期南通(县)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张孝若热心慈善受到了乃父的影响,其在红十字会的骨干也多为张謇的门生、子侄和大生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那么张謇本人为什么没有参加红十字会运动呢?本文试作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
1894年,张謇为慰亲之望,进京参加会试,不意蟾宫折桂,高中状元,但他目睹国势危殆、朝廷腐败,毅然于1895年弃官从商,开始筹办大生纱厂,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张謇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匮乏。为了筹资,他四方求援,却到处碰壁。纱厂动工建厂后“用款日繁月紧,而各路许入之股不至”,他向原先允诺筹资25 万两的盛宣怀求救,“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但盛“百方腾闪,迄不应”[2]83。手有余资的盛宣怀的言而无信使恪守传统伦理的张謇无法认同,且处境更加困难。他想将大生纱厂出租,浙江候补道朱畴和盐务督销严信厚乘人之危,一再压价,使谈判毫无结果。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与好友何嗣焜、郑孝胥徘徊在上海大马路泥石桥的路灯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后来还是采用了沈敬夫“尽花纺纱,卖花买纱”的建议才使纱厂避免了胎死腹中的厄运。张謇一直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特地请画师单竹荪绘成“厂儆图”四幅,由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悬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以警诫全体员工和后人不忘大生纱厂创建过程中所经受的来自各方的毁约、侵吞、刁难和欺骗。第一幅《鹤芝变相》中“鹤”指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字茂芝),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变卦,退股发难。第二幅《桂杏空心》指的是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和买办盛宣怀(杏荪)食言自肥,拒付股金。第三幅《水草藏毒》指的是南通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汪字有“水”旁,黄字含“草”头)煽动乡绅秀才起来向张謇发难。第四幅《幼子垂涎》指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信厚企图乘人之危,以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显然,其中第二幅和第四幅即涉及盛宣怀和严信厚。事实上,除有大生纱厂开办之初的不愉快,后来1906年12 月23 日,张謇在旅泰设宴邀客为淮河水灾劝募,推举吕都统(蒙古都统吕海寰)、盛侍郎(盛宣怀)为首,盛未至,“是日请客九十九人,到者不及三十人,写捐十一万两有奇”[3]582。这种对慈善不太积极的行为也令张謇不满。另外,在铁路国有、汉冶萍公司管理等问题上盛、张意见对立。张謇对盛宣怀的人品颇不以为然,不愿与其为伍。
1901年12 月,张謇的好友罗振玉(叔韫)奉张之洞、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和财政。罗振玉回国后,与张謇一起到南京诣见刘坤一,商讨教育改革之事,并主张先立师范、中小学,起初刘坤一颇为赞同,但第二天却反悔了,原因就在于“衙参司道同词以阻”。其中反对最烈的当数胡延和吴重熹。盐道胡延说“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张謇)过信罗叔韫,叔韬过信东人之过也。”[3]466藩司吴重熹亦加以反对。此议遂罢。张謇和罗振玉受此刺激,愤而自立师范,这就是后来的全国第一所民立中等师范:通州师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不同不相为谋。现代社会学也认为,社会组织领导人的素质和形象对其发展影响巨大。盛宣怀是政府任命的红十字会会长,吴重熹是创始人之一,严信厚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作为红十字会的重要领导人,盛宣怀、吴重熹和严信厚的人品和政见显然不利于红十字会对张謇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红十字的本质、宗旨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其早期容易被误解,而在清朝末年,一些人利用其公信力和能自由进入战争区域的便利假红十字会之名进行诈骗和政治活动,这也使红十字带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这也可能是张謇对其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如当时的《申报》和南通地方报纸《通海新报》就有不少此类报道。《通海新报》1913年8 月6 日“本地新闻”有“冒充红十字会长被拏”:“沙淦②系本邑某区人,社会党小党魁,鼓吹无政府均贫富主义,以破坏现状为目的。去年由政府缉拿未获。宁沪战事起,沙乘此大好机会组织红十字会,各处招摇,广募捐款,……目前沙……来通收捐。咋夜二时由军队查夜,于文明旅馆缉获。”[4]南通地方认定其并非真正的红会人士,而是假借红会名义行骗,因此该报还发表了署名“健”的时评:“穿凿探珠者吾知其为窃,持械越货者,吾知其为盗,诈欺得财者吾知其为骗子,是皆受国法之制裁者也。若乘人之颠沛之秋,假借慈善之业而实行不义以供挥霍之资,其结果适阻人之为善心,陷被难者于死地,而莫肯顾国法,既无此明条,而居心之险实较盗贼百倍,非寻常骗子之罪足科也。沪上战起,闻以红十字会名义抢劫者有之,作奸细者有之,招摇募捐者有之,今之沙淦已被捕矣。不知上海红十字会有□□□……”[5]
南通县知事储南强③很快将捕获沙淦的消息上报苏省当局。江苏省民政长(省长)应桂馨发去致红十字会公函,询问:“是项救护团是否贵会所组织,有无派沙淦赴通募捐情事,即祈示复,以便电饬知照。”[6]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回复说所谓上海红十字会救护团并不属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无沙淦其人,并在《申报》发布启事,说该会“向无在外挨户募捐”之事,沙淦和闸北诸某的募捐均系假冒红十字名义,说其冒用红十字会救护团名义在通募捐,殊损红十字名誉,希设法严惩,除函请行政官缉拿惩儆外,还予以悬赏,“如能查获实据,鸣捕扭送警局捕房通知本会外,证明实在,赠洋一百元”[7]。应桂馨即指示储南强,“……查沪上战事,乱党多假红十字会名义为叛军奸细,沙淦亦系组织非常国会之人,为乱党无疑,应即按照军律就地正法,其余均按律办理。除咨镇守使外,仰即遵照等因。……除行知军队,按照军律执行,具报以便呈复外,合亟明白布告,俾众周知”[8]。储得电后即于农历十一日(公历8 月12 日,引者)下午三时许,饬军警于北城上真殿后将沙淦杀害,由家属收尸回殓[9]。
张謇一直渴望社会稳定,希望南通自治事业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愿过多卷入政治,更不想参与反政府活动。沙淦的行为支持了革命,但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对红十字运动产生了畏惧,削弱了其对社会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二次革命”前后,张謇对革命充满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因此也不可能参与红十字运动。
三
张謇热心慈善公益事业,被誉为“全中国最慷慨,最热心公益”的人[10]4。为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他“用开放的思想接纳和利用一切有助于他同胞的力量”。1912年基督医院在南通成立,这是南通最早的现代医院之一。据说在1918年就接诊了5000 名病人,处理了近12000 例病例[10]8,为南通市民的卫生和健康作出了贡献。基督教会的救死扶伤、热心社会慈善公益赢得了张謇的好感。据说,张謇不仅邀请基督教徒进驻他的城市以及周边的地区,还承诺将全市最好的土地提供给他们用来建造基督学校。另外,“出于对基督徒的美德的信任”,张謇任命一名女基督徒做孤儿院、济良所的负责人,在监狱的监管队伍中也有一位基督徒。五位基督徒(其中四位是留学生)在农校担任教师,他还让一个传教士与一批中国人共同掌管慈善资金[11]28。
高诚身起初供职于金陵神学院,后来到南通,在1916-1932年间在南通从事教育和传教工作。据高诚身说,他曾收到张謇兄弟的邀请,参加了南通几所学校的联合毕业典礼,还作了主题为“进步、谦逊以及团结”的简短发言[12]17。在1918年11 月3 日第一所教堂落成典礼上,张謇在布道进入尾声时走上布道坛,当着全市权贵的面“表达了他对教会事业发展的欣喜,以及对将来大批文人及名门望族加入教会并为之效力的愿望”[10]7-8。在传教士的笔下,张謇对基督教十分友善,他“为现代传教士敞开了南通的大门。即使是《使徒行传》中所记录的任何一位对早期基督使徒友好相待的非基督徒,都无法与他的热忱相媲美。现代传教史上很难找到另一则如此伟大的事迹”[10]7。其实,说张謇对基督教相当友善,特别亲睐,如果不是传教士基于一厢情愿的误读,那也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之嫌。由于西方传教士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因此,张謇基于不拘一格吸纳人才的思想,采取了广泛接纳和比较宽容的态度,期望其能为南通地方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至于其是否是基督徒并不特别在意。当基督传教团在南通准备创办学校(即后来的英化职业学校,校长高诚身)时,张謇即要求学校以英语和化学为特色,学生的毕业设计也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因为“张謇迫切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他在南通推广的诸如肥皂制造、墨水制造等实业的需求”[11]28。对高诚身所说的此次活动,张謇在日记中并无记载。在《张謇日记》中仅记载“(农历九月)三十日,(公历)十一月三日。退翁六十八岁生日”[3]740。即便真有其事也不能说明张謇就真有意信仰基督教。事实上,在1918年中,仅其日记记载,他就曾多次礼佛或参加佛教活动,如农历正月三十日,“再至狼山观音院礼佛”[3]735;三月二十四日,“徐夫人十周年忌之前,延僧施食于文峰塔院”[3]736;九月八日,“成观音院礼佛歌”;九月十七日,“作十九日礼大悲忏疏”;九月十九日“清晨礼佛,有诗”[3]740;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太夫人百岁冥寿,文峰塔礼忏”[3]742等等。笔者以为,张謇对南通基督教堂的发言可能更多是出于礼节的一种应付和应景说辞,并不表明张謇对基督教真正信仰和青睐。张謇对宗教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迷信的一面予以否定,对其乐善好施、有助于道德教化的作用予以肯定和推扬,即使对传统的佛教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不会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为了地方慈善公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张謇与基督教会保持了一定的联系甚至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即使基督教会也承认,张謇虽然有些欣赏基督徒在培养美德方面的价值,甚至曾在一次宴会上说,“中国最急需的是那些有崇高品质和领导力的人,他进一步阐述说,需要乞求神的帮助来获得这样的人。中国需要神与他的儿子的知识,没有这些,中国是无法到达发展顶峰的”,但“张謇这些言论不代表张謇是个基督徒”[11]28。
但是基督教会的目的并不是慈善公益活动本身,而是借机在中国发展宗教势力,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慈善公益活动更多是一种手段,“我们要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开展各类传教活动,将我们的基督组织与中国人自己已经开办的项目关联起来,并且充分地将福音的真理与教谕传授给中国人民”,“把这片宽广的非基督徒的土地耕耘成为上帝的圣土”[10]7-9。这与张謇渴望民族独立,坚持慈善自办,担心会因此受制于外人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红十字运动源自西方,与基督教会的活动如关爱弱势群体、救援贫穷之人等有相同之处。在南通,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堂均是红十字活动的重要参加者和重要阵地。尽管红十字会是以人道、博爱、奉献为宗旨,具有政治中立的取向,但在事实上,要真正超脱于现实社会和政治之外是难而又难的,特别是在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中国要被人们认定与政治无涉尤为困难。在国人看来,红十字运动与西方的宗教联系起来,这与西方的政治、军事侵略相伴随,与其文化侵略相纠集。红十字会的西方背景与宗教色彩,使时人望而生畏,心存芥蒂和警惕。这可能也是张謇不与红十字发生联系的重要原因。
四
191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提供了40 万美元的赈款,这一人道行为赢得了张謇对红十字会的好感,尤其是其建筑适当的工程以防止淮河水灾的建议更是与张謇的主张一拍即合。众所周知,张謇对导淮十分重视。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22 岁的张謇随原通州知府孙云锦查勘淮安渔滨积讼案,“目击淮祸”,认识到,“我江北人民之隐患大害无过于是”[13]513,“淮不治,江北无宁日”[13]560,因此萌生导淮之志,并付诸实践,从此开始了40年的艰辛导淮历程。但由于治淮工程周期长,风险大,所需资金多,尽管张謇四处游说,但一直收效甚微。所以美国表示愿意提供借款导淮使张謇感到高兴。张謇曾主持了北京政府与美国红十字会的接触。1911年夏,美国红十字会全国委员会在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下,派工程师詹姆士来华考察淮河区域。同年,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ames Calhoun),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美国红十字会的这一意图,受到清廷的欢迎。中美双方并就此进行商谈,达成意向,规定中方为美国测量技术人员在淮河流域的工作提供一切便利和在华宿费、旅费,美国红十字会负担美国测量技术人员的薪俸。1913年,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出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积极活动,要求北京政府将导淮工作交给美国承担。1914年1 月31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作为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张謇作为北京政府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导淮借款草约》上分别签字。草约规定,美国红十字会或其代表,或其承续人向中国提供2000 万美金贷款,年利5 厘,用于疏导淮河流域内河道,美方应在合同签订1年内筹集这笔贷款;中国政府聘请美国工程师担任导淮总工程师,中方以开浚流域中所有政府土地收入及将来导淮工程竣工后增加的收入、开浚地区的运河使用税为担保,如这些收入仍然不敷,中国政府需从他项收入中拨款支付本息。不过,中国与美国红十字会一直未能签订导淮借款正式合同,借款未能兑现,其原因既与一战爆发有关,还因为安徽和江苏在治淮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借款条件没有得到沿淮地区政府的认可,得不到当地士绅及各界人士的支持,愿共同开发淮水流域的有识之士十分有限。而美国对于治淮工程的干预过深,引起中方的抵制,无疑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14]。美国希望参与、控制导淮工程,借此对淮河流域进行控制。张謇认为,外债可借,但必须以民族利益为重,保证得其利而避其害。他曾严肃地指出:“借外债,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在导淮借款中,张謇“对于磋商条件的立场,完全根据保障主权维系人民利益的范围,丝毫不能迁就”[1]202。
美国红十字会的借款与政府和财团相关联和纠缠,本就使人们对其独立性产生怀疑,美国试图借机控制中国的目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感,而借款的失败更降低了其威信和吸引力。
五
对于张謇为什么没有参加红十字会运动,张謇本人未曾言及,红会的各种资料也未有记载。笔者管窥蠡测,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红十字事业源于战场救护,在其各项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场救护可以说也是红十字会根本性的社会救助活动。众所周知,瑞士人亨利·杜南目睹索尔弗利诺战争伤兵遍地的惨状后,呼吁各国成立民间救援组织,用人道之光驱散战争阴霾,减轻战争的恐怖,是为红十字之起源。清末民初,地方绅士成立红十字会大多出于免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保障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带有明显的功利、救急和乱世求安的色彩。许多地方的红会即成立于战争临近之时。例如1923年底,全国有红会分会241 处,1924年初江、浙、闽三省,“因时局不靖,各地士绅,均请组织分会,俾便预防救护,综计现在已经筹备者,亦有三十一处之多”[15]。1924年江浙战争发生后,许多地方即出现了建立分会的热潮,“战区以内之各处红十字分会,纷纷筹备救护。其未经设立各区,亦在积极筹备……日来各地士绅,因惧当地军事之骚扰,纷纷加入红会,籍资保护……”[16]。南通僻居江海一隅,除太平天国时期受到一定的波及外,自明代以后一直少有战乱,被誉为世外桃源。这也使红十字会成立的重要性、必要性不易为张謇所认识。二是红十字会系“舶来品”,源自西方,表面上为民间组织,而背后有着西方政府的影子,同时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创始人笃信宗教,宗教信仰是其设立红会的精神动力,“十字”也带着明显的“西教”意味,尤其是在其发展初期宗教色彩更加浓厚。张謇饱受传统文化熏染,渴望民族独立,担心因此受制于外人,而一些人利用其开展政治活动也使他避而远之,免遭是非。三是张謇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于民生与社会稳定高度重视的思想,在南通建立了众多近代慈善和公益事业,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世界。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除救护外就是救助,既然社会救助等事业在南通已经落到实处,风生水起,自然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分散精力和财力。四是张謇在创业的过程中,曾与盛宣怀、吴重熹、严信厚有过交往乃至直接接触,对其印象不佳,评价不高,因此也就很难参加他们领导的红十字运动。
注释:
《通海新报》,1913年3 月18 日创刊,南通第一张对开铅印大报。1929年5 月26 日为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查封终刊。
②沙淦(1885~1913),字宝琛,号愤愤,江苏通州兴仁镇人。12 岁时考入通州第一高等小学(城北高等小学)就读,13 岁时就剪去辫发,以示对清廷的不满。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浙江吴兴陈其美等人东渡日本,留学东京成城学校,后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沙淦从日本回国,著书办报,宣传革命,曾于江宁策反清军,险遭捕杀。脱险后又去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任国民党上海分部秘书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于汉阳参加救护工作。不久返沪,与陈英士、李平书等人积极策应,在上海鹿鸣旅馆组织敢死队,组织围攻上海制造局,后任沪同盟会秘书及江北副招讨使,兼上海都督陈其美参谋。次年参加江亢虎组织的社会党,任总部庶务干事。江投袁叛变后,沙淦另组社会党。民国二年(1913),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独裁发动二次革命,沙淦力助陈其美讨袁。7月,因革命军军饷供给不继,乃以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名义返通,拟往江北各县筹募捐款,抵通后被捕,于8 月12 日在南通城北王家坝被杀害,年仅28 岁。其遗骸归葬家乡李观音堂东北。民国十七年(1928),邑人于狼山南山坡建“沙淦烈士纪念碑”,以彰功烈。
③储南强,字铸农,江苏宜兴人,民国初年为南通县知事,与张謇友善,支持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
[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
[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卷三[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卷六[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冒充红十字会长被拏[N].通海新报,1913-8-6.
[5]时评[N].通海新报,1913-8-6.
[6]红十字记事[N].申报,1913-8-4.
[7]中国红十字会悬赏缉拿冒收捐款[J].申报,1913-8-4.
[8]县令[N].通海新报,1913-8-13.
[9]无政府党员被戮[N].通海新报,1913-8-13.
[10]查尔斯·T·保罗.中国的召唤[A].南通市档案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11]华莱士·C.培根.聚光灯下的南通[A].南通市档案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12]高诚身.南通的进步与隐忧[A].南通市档案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1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卷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4]李琛,马陵合.民国时期的水利借款研究—以导淮工程为中心[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15]红会之分会统计[N].申报,1924-2-17.
[16]红十字会之昨讯[N].申报,192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