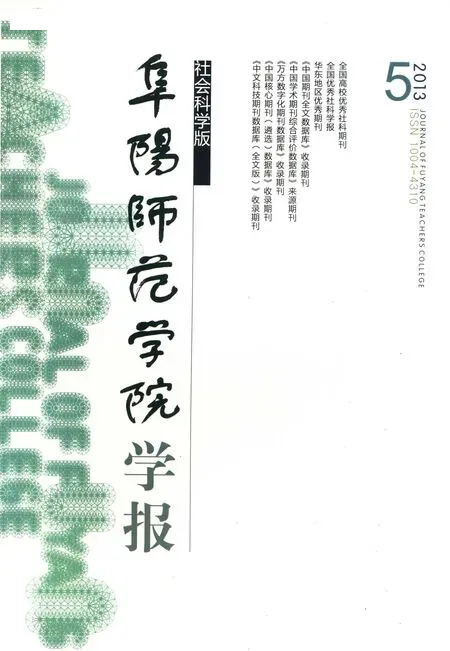《老子》哲学语境下的“无为”思想探析
2013-04-18汪锋华
汪锋华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老子》又名《道德经》,系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代表作。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的诞生,往往与其思想的超越和创新是息息相关的。《老子》尤为如此,它所营造的特有的哲学语境,与老子生活年代以前的任何一部文献都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仅以传统的语境去解读《老子》,这样很可能会引起读者望文生义的不良阅读而导致误解乃至附会。因此,对《老子》的和解读和研究首先要从它的语境入手,而语言考察则是进入老子哲学语境的第一步。
一、《老子》哲学对传统语义的颠覆
在《老子》这本书里,老子对传统语词意义的颠覆随处可见,而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运用自如,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柔弱向下的词汇来表达其合“道”的思想
这些柔弱向下的词,在传统语境意义上是贬义词,常用来表达和描述消极不可取的行为和思想,不具有积极向上的涵义;但在《老子》文本里,这些词往往作为褒义词使用,用以表达其对高尚、向上人格的追求。其用词非常丰富,有“闷闷”、“昏昏”、“愚”、“拙”、“虚”、“冲”、“雌”、“辱”、“敝”、“下”、“黑”、“少”、“柔”、“缺”、“不居”、“不为”、“后”、“寡”等等不胜枚举。如《老子》第二十章说:
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这是老子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或精神状态,这里的“傫傫”意思是指疲惫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广雅·释训》:“傫傫,疲也”。“昏昏”的意思是指“暗昧的样子”,昏昏沉沉得像被打败了似的。“闷闷”的意思是指愚钝不够精明的样子,仿佛随时会吃亏。与之相对的则是“昭昭(光耀明亮)”、“察察(精明能干)”、“熙熙(兴高采烈)”,但在这里却是用来描述“俗人”不合于“道”的非智慧性作为,而“傫傫”、“昏昏”、“闷闷”则表达其“道通为一”的人生境界。通过这样的阐述,老子将柔性向下的词语重新加以提炼而赋予其积极向上的含义。再如《老子》第二十八章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受其辱,为天下谷。
这章描述有道者如何在社会中居处作为。老子在这里给出的是,有道者应该要“守雌”、“守黑”、“受辱”,这大大打破了人们的惯有思维。“雌”指纤弱的意思,“黑”是愚昧不开窍的意思,“辱”指卑下,被人瞧不起的意思。老子将其作为褒义词使用,用以表述其合于“道”的智慧性作为,因而也具有了积极向上的语义,成功实现对传统语义的颠覆。这样的现象在《老子》八十一章中随处可见,这里不再赘述。
(二)用具有刚强向上性之词来表达其不合“道”的思想
与上述现象相反,此类词诸如“强”、“刚”、“敢”、“伐”、“盈”、“锐”、“仁义”、“智慧”、“利器”、“企”等比比皆是。如《老子》第七十六章中说:
故坚强者食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这里的“坚强”、“兵强”、“木强”等词在传统语境义下具有刚大向上的积极语义,但在这里却成了表消极语义的词,强大只能处在下面,终不能胜过柔弱,如此一来“强”也不具有了原先积极向上的意义,反而成了死亡的征兆。再如《老子》十九章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圣”、“智”、“仁”、“义”都是时人普遍所追求的东西,是儒家、墨家等所崇尚的大智慧,而老子在这里却要人们将其抛弃,回归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心境,认为这些是不合“道”的非智慧性行为,只会给人们带来不良后果。如此,“圣”、“智”、“仁”、“义”这些人们平时所崇尚的理念在瞬间失去了其积极向上的意义,在价值取向上来了个颠倒的体悟。关于“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争论,本文姑不作讨论,而是择从通行本。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老子所使用的这些词语符号虽与传统无异,但其所呈现的意义却与传统背景下的语义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即在传统语境看来是贬义的、不可取的、不具有积极向上的,到了《老子》中却用以描述合于“道”的智慧性行为,具有高尚、刚大、向上的积极语义,完全转化为褒义词;在传统语境下看来是褒义词的、可取的、具有积极向上性的,到了《老子》中却是用以表达其不合于“道”的非智慧性作为,具有贬义性。
如果将《老子》这一语言特征与儒家典籍里面的用词特点进行比较的话便更为明显。如“恭近于礼,远耻辱”(《论语·学而》)中的“耻辱”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在《老子》中却被当作褒义词使用,“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二十八章)。“好学不好仁,其弊也愚”(《论语·阳货》)里的“愚”字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不够聪慧的意思,这也是当时“愚”字所具包含的普遍性词义,但在《老子》中却变成了褒义词,成为人生境界的一种追求,“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二十章),这里的“愚”表达的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第一》),道德仁义礼,是儒家追求,也是当时普通人的追求,但在《老子》里却成为应该被摒弃的累赘,“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慈孝;国家混乱有忠臣”(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寥寥数言就将儒家所求、时人所趋的表示高尚的词义统统被老子纳入其不合“道”的非智慧性作为的范畴。
老子对传统语词意义的颠覆,在语言的运用上进行了一次大胆革新,大大拓展了人们阅读的思维空间。
二、老子哲学语境的构建和表达
老子是怎样实现对传统语词意义的颠覆的?这是基于老子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语境而言的,正是在这一特殊语境下,老子哲学才得已成立,传统词语的意义才被颠覆。具体来说,《老子》的哲学语境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构建和完成的:
(一)在业已功成或刚大盛有的条件下加上刚性向上之词来表达其不合“道”的思想
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于刚性向上之词(刚性之词表示业已功成或刚大盛有的条件)上再加上刚性向上之词。如《老子》九章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认为一事物在达到其完满的时候,不以柔弱的方式去作为是非智慧性的作为,必然会走向毁灭的道路。“持”指持有或拥有的意思,“揣”是指锻打的意思、“金玉”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富贵”是人们的向往,这些刚性向上之词表明事物已处于刚大盛有的条件,处在事物发展完满的状态之上,在此之上,老子复用“盈”、“锐”、“满堂”、“骄”等刚性向上之词来表达其不合“道”的思想,分别诫之以“不如其已”、“不可长保”、“莫之能守”和“自遗其咎”,随之这些词也带上了贬义性。再如《老子》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勇敢于坚强就会死,勇敢于柔弱就可以生存。这里“勇”是刚性之词,表达刚盛的状态,“敢”也是刚性之词,合起来表达其不合“道”的非智慧性作为,随之这些刚性之词也带有了贬义性,不再具有积极向上的义涵。
二是直接用刚性向上之词,而有意无意隐去其功成刚大盛有的条件。如《老子》四十四章说:
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太爱某一东西必然会带来很大耗费,藏有丰富的财物必然带来严重损失。“甚爱”必以爱有某物为前提,“多藏”必以藏某物为前提,从而才会发展到“甚爱”和“多藏”的程度,文中隐去了这一前提条件,直接用之以“甚爱”、“多藏”这些刚性向上之词来表达其不合“道”的非智慧性作为。再如《老子》十二章说:
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能够享有“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和“驰骋田猎”的人,一般皆为士大夫阶层,其拥有的社会地位是普通百姓所无法企及的,说明其已处在刚大盛有的条件之上。老子隐去了这一条件,直接用“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和“驰骋田猎”等词,这些指的都是时人需要花大力气去追求的东西,在普通人心中是荣华富贵的象征,但在老子看来这是不合“道”的非智慧性追求,是应该被摒弃和超越的,而超越此的出路就在于返归于自然,因此这些词在这里也不再具有先前的积极向上之义。
上述两种表达方式在书中出现的几率并不多,但阅读时需要细心体会,确切把握。
(二)在业已功成或刚大盛有的条件下加上柔性向下之词来表达其合“道”的思想
这一表达方式同样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于刚性之上之词加上柔性向下之词,如《老子》二章说: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章老子论述的是圣人该如何作为,仔细分析会发现他是通过刚性向上之词加柔性向下之词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的。万物因他兴作而不做其主宰,衣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促成万物蓬勃发展而不自恃其能,功业成就了而悄然离去,正因为如此圣人的功业才能得以亘古长存。这里老子用“万物作”、“生”、“为”和“功成”等词表示刚大盛有的或功成的条件,在此之上,老子分别在加上“弗始”、“弗有”和“弗居”等这些柔性向下之词来表达其合“道”的智慧性行为,随之使这些柔性向下之词具有了刚性向上性的意义。再如《老子》八章说:
大成若缺,其用不蔽;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这章的主旨是说合于“道”的智慧性作为是不会让事物的完好性完全表露出来的。因此,从“道”的角度来说,最完美的往往看似是有缺的,这样它才能继续发展,不会被穷尽;最盈满的往往看似空无一样,这样它才能继续盈满,而不会枯竭。老子的这一思想通过“大成”、“大盈”等刚性向上之词和“若缺”、“若冲”等柔性向下之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句话来表达其合“道”的智慧性作为,从而使“缺”、“冲”具有了刚性向上之义,其他章节如第六十八章、六十六章、三十四章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可以说这种表达方式在《老子》中最具有普遍性,几乎在每一章节都可以找到一两句,这里不再一一举例分析。
二是直接继之以柔性向下之词,隐去其功成或刚大盛有的条件。如《老子》六十九章说: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打仗的时候“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和“不敢进寸而退尺”,说明其有“为主”和“进寸”的条件,即业已处于刚大或盛有的状态之上,老子隐去这一条件,直接用之以“不敢为主而为客”和“不敢进寸而退尺”这些刚性向上之词来表达其合“道”的智慧性作为,从而颠覆了其原有的词义。再如《老子》七十八章说: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此句表明,能以自己一人之能去受“一国之垢”和“一国之不祥”者,绝非一般之人,他必是已经处于功成或刚大盛有之态。老子隐去了这一条件,直接继之以“受国之垢”和“爱国之不祥”这些柔性向下之词来表达其合“道”的智慧性作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天下之王,而“受国之垢”和“受国之不祥”由原先柔弱向下性转变为具有刚大向上性的意义。
老子哲学的独特语境正是通过以上几种独特的思想表达方式来构建、呈现的。也正是在这些独特的思想表达方式之下,传统话语的意义被颠覆了过来,我们才能从中获得崭新的阅读体验和思想感悟。
三、老子哲学语境下的“无为”思想内涵
(一)“有”和“无”之假设
由上所述,我们知晓在业已功成或盛大的条件下,刚性向上之词表达的是不合“道”的思想,而柔性向下之词表达的则是合“道”的思想。以之为基础,如果借用某个文字符号指代刚性向上之词,而用另一个文字符号代称柔性向下之词,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老子思想的表达方式更加抽象化和理论化。
假使借用《老子》一章中“无,名地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中的“无”指代柔性向下之词,而用“有”来替代刚性向上之词,那么在功成或刚大盛有的前提下,以柔性向下之词所表达的“合道”的思想便可称之为“无为”,同样的道理,以刚性向上之词所表达的思想行为便可称之为“有为”。
(二)“有”和“无”的哲学内涵
以上所设之“无为”并不是《老子》一书中的“无为”思想,而是为解释“无为”思想而作的方便假设,本文以下对《老子》“无为”思想作进一步的解读,具体如下:
1.什么是“无”和“有”
王中江先生认为“正是老子实现了‘有’和‘无’从普通语言符号向形而上学语言符号的转变”,“老子第一次使‘有’、‘无’超出了它的普通意义,把它们一起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1]确实如此,那么什么是老子哲学中的“无”和“有”呢?《老子》一章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句话是说“无是形成天地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2]77。“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文解字注》:“始,母之初也”[3]617;“母,牧也。引申之,凡能生之以启后者皆曰母”[3]614。从常识义理看,“女之初”具有弱、柔、朴、微、隐、虚、静……等一系列柔性向下的特性;“能生之以启后者”具有刚、强、盛、大、显……等一系列刚大向上性的特征。联系这些,这句话便蕴含着这样一个信息:用以表达微、弱、柔、朴、隐、虚、静……等具有柔弱向下性的“无”是创生宇宙的初始力量;具有大、强、刚、盛、显……等刚性向上性的“有”是创生万物的母体力量。
换句话说,“无”代表的是一切具有柔性向下性力量的语言符号,“有”是代表一切具有刚性向上性力量的语言符号。前者为始之力,后者为母之力。因“始”之力具有柔性向下性的特性,“母”之义含有刚性向上性的特性,因此老子以“无”对“始”来表述柔性向下之力,以“有”对“母”来表述刚性向上之力。正是在始之力与母之力的相互作用下,天地万物才得以实现,所以书中说“此两者’”是“众妙之门”,就是说“无”和“有”(即始之力和母之力)是一切生成和变化的总门径。这里老子将普通语言符号上升为形而上学语言符号,而它的语义也超出了其普通的意义,具有了形而上学的高度:它不再是普通语言符号意义上的事物的存在和不存在,或事物的存有和没有的意思。
2.“无”与“有”的关系
“无”和“有”的关系如何?“无”和“有”孰为先?两者之间又是如何运动的呢?这些问题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老子》四十章说: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生”就是出生、诞生之意。诞生某一物,就是此物从彼物而来。因此,此物内藏了彼物的特性,其能也因此转入彼物之中,并在彼物中继续生发作用,这就如同禾之生稻,禾之能转入稻之中,促生谷的生成。同样道理,“天下万物生育有,有生于无”,就是“无”生“有”,“有”生“万物”,而“无”之力和“有”之力(即始之力和母之力)于此皆消藏于“万物”之中。《老子》十六章又说:
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意思是“万物纷纷芸芸,各自返回到它的本根”[2]139,《老子》称之为“复命”。陈鼓应说“复命”是“复归本原”之意,也即回到“万物的生生本原”[2]136-137,根据“无”生“有”,“有”生“万物”,而“道”以“有”、“无”而存在,并以“无”为体,因此万物的生生本原是“无”,又因万物消藏“有”之能,所以当万物复归于“无”时,“有”之能亦复归于“无”。“无”就成了万物复归的终极之所。
于是,我们可以描绘出老子关于宇宙万物的运动图:“无”生“有”,“有”生“万物”,“万物”藏“有”之能,又复归于“无”,“无”又生“有”,如此循环不息。
“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反”,《康熙字典》引《说文》曰:“覆也,从又厂”[4]许慎《说文解字注》:“覆与复义同。复者,往来也。”[3]357高亨说:“反,旋也,循环之义。”[5]王弼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6]概而言之,“反者,道之动”包含两层意思,即“有”复归于“无”,后者是“往来”之义,即循环相生之义,也即“无”又生“有”的意思。在自然界之中,“有”复归于“无”,便是万物趋向微弱、消亡的方向运动;而“无”诞生“有”,便是万物向刚大盛有的方向运动发展,而这两者的运动,便是“道”的运动。
由此可见,《老子》表述了这样的理念:万物在“道”的作用下,最初由弱(代表“无”的诸性能)至强(代表“有”的诸性能),这是万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万物由强至弱,亦即“有”复归于“无”,这是万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万物消亡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万物重生阶段,即“无”生有,此时万物又重新向繁荣的方向运动。而这样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道”的永恒性由此得以体现。本文将“道”的运动——“无”生“有”和“有”复归于“无”,概括为“无生有而归于无”。
综上所述,《老子》一章的“无”和“有”是一对形而上学的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前面所设之“无”只是形而上学之“无”的形而下之存在,即“无”以形而下的柔性向下的诸性能为存在,如微、弱、朴、隐、柔等特性。因此,所设之“无”就是对这些形而下的诸性能的一个概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形而上之“无”。
3.提出“无为”思想的形上依旧
老子认为,每一事物中都消藏着“无”和“有”两个因子以及“无生有而归于无”的自然律令,这两个因子在自然律令的作用下相互运动,促生着万物的运动和发展。这相当于说,一物之中有两极,一级是“有”,它代表强大发展的一面,一极是“无”,它代表柔弱消亡的一面。当“有”在一物中居主导地位时,事物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当“无”占主导地位时,事物呈现衰微和消亡的状态。
在万物中,“无”的因子的运动促生事物趋向微、弱、朴、虚、静等,向消亡的方向发展,但却也蕴含了这一事物再发展的可能。这就是说“无”能生“有”,“无”既是“有”,又是“无”。换言之,“无”的因子具有两种力量:它既具有使万物趋向微、弱、朴、虚、静等衰微、消亡方向发展的力量,同时又具有无限的生生力量——“无”能生“有”。在传统的语境下,时人通常只是看到“无”的衰微消亡的一面,因此认为柔性向下性的东西是灭亡的表征,进而认为柔性向下性的行为也是懦弱、无能、走向消亡的体现,由此表达柔性向下性的词语也就成了人们所不崇尚的贬义词。老子正是在看到了“无”的消亡一面的同时,更加强调其催生的一面,进而将原先不具有积极向上的语词转变为具有积极向上之义,颠覆传统以来的语词意义,并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将其呈现出来,从而给人们的思维以震撼性的启示。
同样道理,“有”的因子的运动促生事物趋向强、大、盛、明等兴盛繁荣方向发展的同时,又酝酿了不可抗拒的归终之能,即不得不遵循“有”复归于“无”的自然律令。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有”的刚大盛有的一面,只一味地去追求“有”,殊不知“有”出于“无”,复归于“无”,反“无”才能更好地“全有”,正是在这基础上老子提出“无为”思想以“全有”。
4.“无为”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其终极指向
由上可见,事物在到达它的刚大盛有时,就会不可避免地趋向衰微和消亡,使事物返回原初,这是“有”的不可抗拒性的归终之能所决定的。那么如何才能保存已有的强盛之能而使其生生不息呢?(王弼在解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先反于无也。”王弼的这一见解可谓是深谙“无为”之道。可惜他没有进一步深入解读。)面对这一问题,老子提出了于“有”的因子上济之以“无”的思想,即于刚大盛有的条件下,济之以柔性向下之能,达到以“无”济“有”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老子“无为”思想的全部内容。
于“有”的因子上,济之以“无”,一方面是主动应“有”返“无”的自然律令;另一方面,由于是主动顺应返无,因而保存了已有的强盛之能于衰微、覆灭、柔弱等“无”的性能之下。同时“无”能生“有”,“无”之性能会发展为“有”之性能,因此在“有”之上济之以“无”不仅是保存了已有的强盛之能,同时又使事物朝向生生不息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了使事物整体性地走向消亡和复归。于是,在看似柔弱、愚钝、微茫的状态之中,包藏着强大的生生之能;于看似衰弱、覆亡的归终之态中,蕴含着无限的生生之力;它如鹰之睡立,虎之慢行,冬之叶落,日之西去,其力绵绵不绝。这是老子“无为”学说的深刻内涵。笔者将其概括为“处有居无为之事”,意思是说,处“有”之上,以“无”而为,即以微、弱、朴、隐等“无”之性去作为,那么“有为”便是处“有”之上,以“有”去“为”,即以强、大、刚、盛等“有”之性去作为。如《老子》二章说: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圣人处无为之事”,陈鼓应作“是以圣人居亡(无)为之事”[2]433,圣人是处“有”之人,故居“无”而为,“居无为之事”就是说,主动顺应返“无”,抛开已有的成就而以“无”来作为,从而全“有”于“无”。所以文章接下来说,“不为始”、“不有”、“不恃”、“弗居”,进而“是以不去”(不会消亡,生生向上,即“全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主张以下为美,以愚为美,以复归于朴为美,以无知为美,以虚静为美,以不争为美,以守柔为美等,其最终指向是通过一系列“无为”实践,将“有”消解于“无”,返璞归真,达到大圣大愚、大智大拙、大勇大缺、大昌大昧、大明大微,与天地万物合一,亦“有”亦“无”,而全其“大有”,即拯救了“有”的覆亡之路。这其中又出世的逍遥,有心性的空灵,又入世的智慧,有宏大的人的担当,正因为如此,后世之学者始能在《老子》这本书中读出他的逍遥空灵,读出他的智慧和谋略,读出他的担当和告诫,同时也读出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脉络,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体悟和启迪。
[1]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38-139.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清)张玉,等.康熙字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74.
[5]高亨.老子正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67.
[6]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