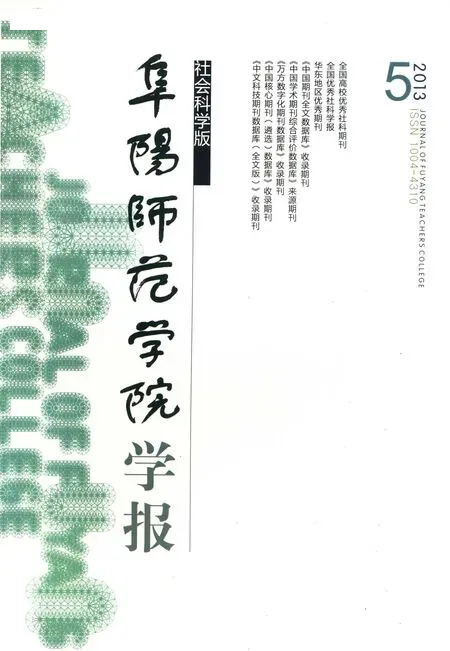试论《管子》的财产思想
2013-04-18葛宇宁
葛宇宁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管子》是一部治国理财的“奇书”,含有许多深刻的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就是在当代也放射着它的理论光辉。财产思想就是这些重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管子》一书的始终。
《管子》在治国理财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富民”理论,具有民富国强的思想取向。认为只有藏富于民,国民富有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才会“水涨船高”,国家也才会真正地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只有“民富”了,社会才能长治久安。《管子》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①
《管子》提出的治国先富民,民贫则国危的理论,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秦朝,拥有甲兵百万,夺六国财富为己有,富有四海,财倾天下,不可谓不强大,不可谓不富有,可以修长城,建阿房宫,甚至建造无比豪华的陵寝。然而,秦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历经二世便灭亡了,存在仅十余年的时间,打碎了秦始皇当初设想其子孙后代万世拥有天下的美梦。秦朝短命的根源就在于长期的征战,再加上长期的大修工程,导致“民贫”“民苦”,因此一旦有人“揭竿而起”,便会天下响应。国强民弱,则国家犹如一座矗立在流沙之上的庞大建筑,虚有其表,地基不牢,稍有震动,便有崩塌的危险。
民富国强虽然是个理想的目标和雄伟的战略,然而要“化作”现实,变成真实的存在,却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思想和理论,其中财产思想和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只有具备合理的财产理论,才能保证民众去踊跃地创造财产,也才能真正实现民富国家的目标。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筹划的社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要“富民”,“藏富于民”,让利于民,增加居民收入,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改善人民生活和增进社会和谐。这与《管子》的“富民”理念不谋而合,足见《管子》财产思想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以及对我们时代的借鉴意义。
一、财产的主要形式
对财产主要形式的认识是财产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只有知道财产表现为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以视为财产,才能对财产有所认识和研究。
春秋时期,我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自然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囿于时代背景,《管子》提出的主要财产形式都是实物财产,表现为各种实物。对实物的把握具有简易直观的特点,因此各种实物才会首先成为人类的财产形式。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比,《管子》的财产形式相对比较少,没有对无形财产和权利性财产的认识,还没有抽象出财产的复杂形式,这是其不足之处。具体而言,《管子》的财产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土地
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土地一直是人类的最主要财产形式。在农业经济中,土地提供着各种生产和社会资料,是财富的来源。《管子》也十分重视土地财产,认为土地是万物的来源,提出“地者,万物之本原”(《水地》),“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形势解》),并认为“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所取焉”(《形势解》)。即土地自古以来只知给与,不会索取,是人类的“恩人”。
土地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提供了人类所需的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只要人们愿意在土地上付出,土地就会有回报,就可以获得各种财富。在西方,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之说。土地的分配和管理一直是《管子》非常关注的事情,指出:“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乘马》)由此可见,对土地的管理是攸关一个国家政治兴衰的大事。
为了有效地拓展土地的范围,增加土地财产的数量,《管子》提出了两条扩张土地的方式。其一是开荒。通过开荒,把荒芜的、没有价值的土地变成财富的源泉,增加土地的供给。土地荒芜,不加以开垦就等于无,在本质上就还不是财产,“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权修》)。因为荒芜的土地,不能生产,不能提供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地之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七法》)。其二是战争。战争是迅速扩张土地的直接手段。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其目的多是为“掠夺”别国的土地,从而扩展自己的地盘。管子也看到了战争的这一功能,提出“战胜者地广”(《治国》)的说法。
众所周知,洛克的财产理论是以土地是无限的自然资源为前提的,提出一个人的开垦利用,不影响他人的权利。而《管子》则比较务实,认为土地非常有限,通过开荒和战争而增加的土地都是有限的。因此若想增加土地的财产价值,就应该向现有的土地本身“索取”。通过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来增加定量土地的产出才是“硬道理”,于是《管子》提出“尽地利”的理论,亦即“尽地之利”(《小匡》)。并认为“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君臣下》),只要把握好天时,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用,就一定能获得足够的财富。
对于充分发挥土地财产价值的这一思想,《管子》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其一是“度地之宜”,亦即根据土地的不同,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具体而言就是“相高下,视肥跷,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立政》),如此以来,就会做到“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立政》),从而可以获得大丰收,使财富大量增加。其二,也就是深耕细作,提高利用效率。《管子》提出“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八观》),也就是通过其耕翻土地的状况,就可以知道其收成如何,从而也就知道了这个国家将会处于温饱富足还是饥馑贫寒状态了。
(二)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除了土地以外,还有各种生产资料,同时人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各种生活资料,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也是财富的重要形式。
首先是各种农畜产品。当时因为处于农耕文明的初期,人们的生产生活还比较简单,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在农业文明的时代,一个国家农畜产品的拥有量是其财力的标志。各种农畜产品不仅是人们的劳动成果,同时也是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它们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国家实力的保证,各种农畜产品便是人们的重要财产形式。因此,《管子》提出“五谷桑麻,民之司命也”(《国蓄》),和“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牧民》)的主张。甚至《管子》认为五谷桑麻及六畜比金玉更能代表财富,是更根本的财产,拥有五谷桑麻才是真正的富有。即“时货不多,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
在各种农畜产品中,《管子》认为谷物最重要。它不但是“民之司命”,是人们的生存下来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谷物还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但可以利用充足的谷物控制国家内政,使政治社会稳定,各项事业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利用谷物控制和制约其他国家。《管子·山至数》中就提出“彼守国者,守谷而已”。
其次是各种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虽然不是人们的劳动产品,乃是天然形成的,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但是这些自然资源也有价值,是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财产的形式。《管子》对自然资源的财产形式也给与了重视,提出:“为人君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轻重甲》)。也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和利用是一个君王能够掌控天下的条件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管子》不但提出各种自然资源是人们的财产形式,是宝贵的财富。还提出对各种自然资源要合理使用、注意节约、加强保护的先进理念。《管子》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八观》)。因此,虽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如果取用无度,必将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从而使人类失去自己的生活家园。
最后是各种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手工业者的劳动产品,也是财富的一部分,是重要的财产形式。马克思曾把生产工具的变革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管子也对生产工具这种财产形式给与了重视,认为没有生产工具,人们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
(三)货币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货币一直是人类的重要财产形式,起着财富象征的作用。作为理财治国经典的《管子》,对货币这种财产形式也是十分重视,提出“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国蓄》)。认为货币是流通的关键,为政者只要能控制好货币,就能控制经济财富的命脉。货币的主要功能是流通,促进交易流通,使财富流动起来,活起来,即“刀布者,沟渎也”(《揆度》)。由于管子比较重视商业的价值,而货币又是商业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条件之一,所以《管子》就把货币看作是财富中的财富。
《管子》依据各种货币的不同价值对货币进行了分类,具体是:“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三种货币价值不同,在财产上有贵贱之分。其中,珠玉最贵,主要用于礼品往来,很少用于交易流通;黄金为中币,则是主要的货币;刀币处于辅助货币的地位,价值较低。
二、财产的主要来源
财产的来源在人类社会中是个有较多争议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财产来源本质的复杂性,而在于对财产来源的界定往往关系着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对于社会财产的分配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常理,谁创造了财产,谁就应该拥有财产,财产应该属于创造它的人所有。而在人类社会中,事实并非如此,往往创造财产的人一无所有,得不到财产,而那些没有创造财产的人却“坐拥”大量财产。
在西方的财产理论中,对财产来源的界定学说以洛克的比较著名,那就是劳动掺入理论。个人通过将自己的劳动付出掺入到原来的共有物上,便取得了这个事物的所有权。具体而言,“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自己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成为他的财产。”[1]18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经济的长期研究,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认为财产应该归劳动者所有。
《管子》也对社会财产的来源给与了自己的解释,比较接近劳动创造财产的理论。《管子》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因此,天下的一切财物都来源于力气,而力气来源于“劳身”,即从事劳动。在两千多年前阶级严重对立的时代,《管子》能够提出劳动是创造财产的来源这一学说,实属难能可贵。因为这种理论的提出,既需要一种深刻的理论把握能力,也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具体上,《管子》认为人类的财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劳动”。
(一)生产劳动
如前所述,当时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农牧业生产和一些手工业的生产,这些生产供应着社会所需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没有这些生产劳动的顺利进行,人们的生存就没有保证。“一农不耕,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或为之寒。”(《轻重甲》)
财产的本质在于不断地创造新的财富,而不是拥有“死物”。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前,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殖民侵略,尤其是对美洲的压榨,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一时财富无国可比。然而不注重生产创造,很快就为英国等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所超过。
当然,《管子》把生产主要看作农业生产,认为“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八观》)。因此认为农业生产是根本,它创造了大部分的财产财富,为了农业生产,甚至可以牺牲其它行业。在《管子·五辅》中便有此论,提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一直是我国为政的根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大事。
为了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管子》还重视人才的培养,以提高人的创造能力,许多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可见,培养人才比直接种植五谷桑麻更有价值,收益更多。另外,《管子》还主张奖励各种“能工巧匠”和“生产能手”。具体的奖励措施非常详细,具体有:“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山权数》)但《管子》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重农不抑商”,把商业也作为财产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力提倡和鼓励。
(二)商业贸易
《管子》认为市场是物品的集散地,大家互通有无,凡进入市场交易者皆可获利。因此提出“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这就是暗示了商业经营是社会财富增加的途径之一,也创造财产和财富。通过商业贸易,各取所需,充分实现产品的价值,实现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源的合理配置。《管子》充分看到了市场对资源供应和配置的作用,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乘马》)。
管子对商业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其对商人地位的界定上,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石民”,即是国家的柱石之民,是一个国家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士”的地位一直很高,受人尊重,是个特殊的阶层。而《管子》把商人和“士”并列,统称为国家的“石民”,商人的地位可见一斑。
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创造财富,《管子》主张减轻赋税,甚至有时候实行免税的政策,对各种税赋的征收有着严格的限制。在关税方面,实行“驰关税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并且规定“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问》)。也就是不但关税较低,而且关税和市税不重复征收,可以折抵,同时对于空车和徒步者不征税。另外,齐国靠近大海,渔盐产业丰富,是重要的国家物资,为了把这些资源变成价值,变成财富。对来齐国贩卖渔盐的商人实行免税,即“通齐国之渔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小匡》)。
在传统社会里,商业对财富增殖的功能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直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充分认识到商业的价值,商业也能创造财富。
三、社会财产的分配
社会产生的各种财产,只有经过分配环节,才能被人们真实地拥有,也才能进入交易和消费的环节,充分发挥财产的生产生活功能。《管子》非常重视社会财产的分配环节,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
《管子》首先提出对社会财产的渴求和占有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产,财产拥有的多寡是个人财富和实力的象征,也是个人自我确证的方式。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主要持有“人性善”的理论,因此提倡“重义轻利”。而《管子》则不同,它充分肯定人们对“利”的追求,它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禁藏》)商人为了营利,不惜千里奔波,夜以继日,甘冒各种风险;渔人为了获得渔利,不惜深入大海,乘风破浪,其目的都是为了“逐利”,为了获得财产。获得财产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没有财产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管子》主张为政者要对其百姓“牵之以利”(《禁藏》),如果能在社会财产分配上处理好利益关系,便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
因此,社会财产的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故《管子》指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就是说天下不怕没有财产,就怕有了财产,没有人能进行合理的分配。在当时的春秋时期,社会的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社会财富并不充裕,远达不到富足的程度。不合理的社会财产分配制度很可能导致社会上一部分人出现生存危机,由此会引发社会和政权的动荡,甚至崩溃。因此,社会财产的合理分配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一定尽量做到公正合理。
(一)土地的分配
如前所述,土地是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财产形式。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农耕社会里,土地是维系人们生存的根本条件,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土地的产出。因此,对土地的分配就成为社会财产分配的第一要务。对土地的分配公正合理与否,是一个社会能否公正的开端和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公正的源头。如果土地分配得公平合理,就会政治清明,各行各业就能顺利进行,社会财富也会增长起来。
《管子》对土地分配的主要思路是“均地到户”,即“均地,分力”(《乘马》)。首先,就是公平合理的均分土地,使每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保证生存的基本需要,大致数量是“方一里,九夫之田也”(《乘马》),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其次,要分田到户,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平均分配土地,并且分田到户,就可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使国家和生产者都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
《管子》在平均分配土地时,还特别提到根据各种土地的肥力和实际产出情况进行折算,以保证公平合理。具体折算方法非常详细,也很合理,具体如下:“地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乘马》)另外,土地分配之后,还要根据一定时间的变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就是“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乘马》)
《管子》对土地分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年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土地政策,其先进性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农村实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就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把土地合理地分给农民,实现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生产,结果取得了成功,农村经济活跃起来,整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
(二)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已经衰微,天下秩序遭到破坏,各种“强权”势力借助自己的势力明抢豪夺,欺压百姓。社会劳动产品大多被各种豪强势力占去,分配严重不公,严重挫伤了各行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管子》看到了这种分配状况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的弊端,指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不行,万民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国蓄》”社会不稳定,难以治理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公平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影响了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最能体现出《管子》的“富民”和“藏富于民”的思想。《管子》主张:“薄征敛,轻征赋”(《五辅》)。国家和当政者取的少了,留给生产者的就多,人们就会逐渐富有起来,拥有更多的私有财产。
《管子》在农业税赋的征收上提出两大措施,其一是,年景不同,则征收不同,灾荒之年免税。具体是“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征,岁饥驰而税。”(《大匡》)其二是,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则征收不同,也即“相壤定籍”。“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乘马数》)。也就是征收赋税的官吏,要核对土地的肥沃程度,登记在册,按照上中下三种等级进行税赋征收。
对商业贸易的“收成”,《管子》也主张宽松政策,把收入主要留给商人,国家尽量少取,让利于民。如前所述,对商业贸易的关税征收比例仅是“五十取一”,并且还不能与市税重复征收,对于来齐国贩卖渔盐的商人还免征关税。这些政策都有利地促进了齐国的商业贸易。
四、财产的伦理向度
在《管子》的财产思想里,财产不仅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具有“物”的向度,它还和人的伦理密切相关,具有伦理向度。
(一)财产是礼仪道德的物质基础
《管子》认为财产是道德的基础,没有物质作支撑的道德,只能是虚伪的道德,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具有相通之处,都认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管子·牧民》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管子》还把“德”和人们的财富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德有六兴”,其中第一“兴”就是大力发展生产,从而多创造社会财产,丰富人们的生活资源。即“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五辅》)
(二)对不“义”之财的限制和夺取
如前所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还非常有限。其中,有一部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而是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出身进行巧取豪夺或者一些不法“商人”通过囤积居奇获得了大量的财产。在《管子》看来这些财产的取得具有一定的不道德性,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可以进行“夺取”。在《管子·轻重甲》中,桓公为优待齐国阵亡将士的家属而发愁,当时齐国因为长期征战,国库亏空,国家没有财物来支付优待费用。桓公就来问管仲怎么办,管子的建议就是让“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来进行“贡献”。
(三)对那些非因个人原因而致贫的人给予人道主义援助
《管子》看到有些人生活贫困,导致生存危机,从而也带来人道危机。这些人生存困境的形成不是出于个人的“懒惰”,而是出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具体有两类人属于这一情况,其一是,鳏、寡、孤、独、疾、废者;其二,是天灾人祸导致贫困的人。对于这些人,国家有义务给予帮助,给其财产,让他们生存下来,这是财产伦理的需要。财产本身是“人”的财产,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的。《管子》把“救济贫困”看作是“德”之所需,因而指出“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五辅》)
注释:
①本文所引《管子》的内容均来自谢浩范和朱迎平译注的《管子全译》(上、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下文引此书只注篇名。
[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