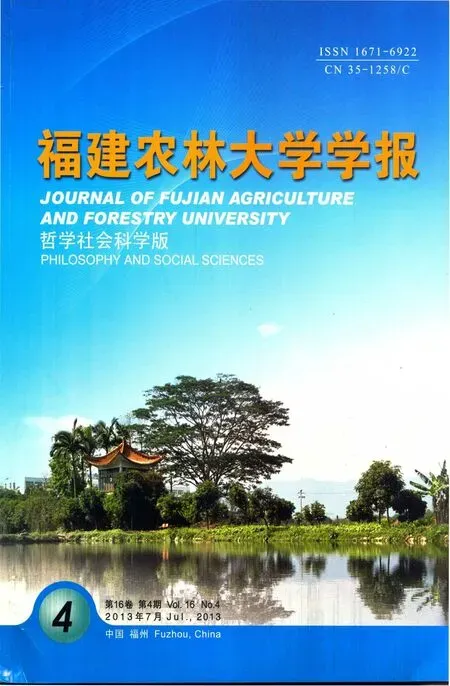历史话语与虚构的后现代结合——从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视角解读《女勇士》
2013-04-18黄玉虹
黄玉虹
(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美国女作家汤亭亭是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二代华裔,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美国女性华裔文学的代表人之一,其多部作品颇受欢迎,在美国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同时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作家。其中,汤亭亭出版于1976年的处女作《女勇士——生活在群鬼中的少女回忆》(以下简称《女勇士》)更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所在。当年该书以“自传”、“非小说”的名义出版,并一举拿下了包括当年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非小说类的最佳作品奖在内的多个奖项。由于汤亭亭的性别和华裔移民后代的身份,中外学术界向来将其当作女性主义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的典型代表,对她的作品主要从女性主义、文化、族裔及后殖民理论这几个角度加以讨论。此外,该书的文类划分,即应该归为自传或是小说,也曾是一部分学者热衷探讨的议题。然而,此书从书名上看像是自传或者回忆录,内容却并非完全忠实于作者的真实生活,而是夹杂着许多明显的不属于作者真实生活经历的、虚构的情节。事实上,汤亭亭读大学和写作此书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国发展并达到顶峰的时候。从有关她生平经历的资料中可以知道她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女勇士》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勇士》融合了小说和非小说而造成在文类划分上的不确定,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该书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已经为不少学者所认识,多数人主要从汤亭亭在写作中采取的戏仿、拼贴、虚构与事实相结合等后现代的艺术手法进行研究。本文则将借助加拿大文论家琳达·哈琴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概念,对《女勇士》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话语与虚构的后现代结合进行探讨。
一、从元小说到历史编纂元小说
“Metafiction”,即“元小说”,由美国文论家William Gass 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意为“关于小说的小说”。换言之,元小说就是一种“含有对自身叙事和(或)语言特色的评论”的小说[1]。以下形容词常被用来描述元小说:self-informing,self-reflective,auto-referential 以及self-reflexive 等,也就是说,元小说的主要特征是self-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和auto-representation(自我代表)。元小说中通常包含作者(或叙述者)对小说本身和故事进程的评论。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评论,小说的虚构性被有意地暴露给读者,以便让读者参与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来。在元小说的作者看来,让读者了解小说的创作过程就如同让他们了解小说的情节一样重要。在元小说这种写作模式下,小说的内在连贯性被消解,叙述和情节变得支离破碎,传统小说与批评文本之间的界线越来越难以辨别。
元小说并非到20世纪才产生。事实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堂·吉诃德》一直被当作元小说的始祖。除此之外,18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和法国作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也是此类小说的先驱。在这几部作品中,小说的叙述者时不时进入到小说的叙事当中打断读者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元小说才真正作为一个文类活跃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异军突起。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能够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综合多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在“二战”之后产生并于五六十年代逐步发展且达到顶峰的一股新兴的文艺思潮。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得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与之对抗的后现代主义便应运而生了。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颠覆性使后现代主义小说在主题和写作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小说相背离,转而具有了一系列新型特征,如去中心化、不确定性、互文性和元小说等特征。在哈琴看来,“后现代主义”一词最初就是用以称呼当时那些具有自我意识特征的文本[1]。哈琴认为,“今日的元小说在形式和主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就是利奥塔德所谓‘后现代’世界的大多数文化形式的范例”[1],因此,“否认元小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极其愚蠢的”[1]。
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作品对现存形象的映射和反讽性挪用使得它们丧失了影射政治的能力[2]。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认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形式与历史无关[3]。与此相反,哈琴注意到了后现代小说自我指涉的特征与其历史性的矛盾之处。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指称小说时,‘后现代主义’一词就是用来描述那些因与过去的文本和语境相互呼应而同时具备元小说性和历史性的小说”[4]。为了将这种新型的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区分开来,哈琴创造了“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即“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专有术语,并用其来归类“那些广为人知且受到欢迎的,具有强烈的自我映射性却又与此矛盾地宣称拥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小说”[1]。这一类小说具有元小说自我反映和自我指涉的特征,同时在其叙事中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又绝不是单纯的元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的变体,可以被看作“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学)和“metafiction”(元小说)的结合体。用哈琴的话来说,历史编纂元小说“致力于使自身在历史和话语中立足,同时又坚守自身固有的小说性和语言学风格”[1]。在哈琴的笔下,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Cien anos de soledad)、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The Public Burning)、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等早已享誉文学界的经典名著一起都被归入了“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新型的小说体裁。
二、《女勇士》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特征
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真正公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而且“历史的写作总是带有为自己立传的性质”[5]。换言之,历史也是一种类似于小说的文本,历史编纂元小说正是“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真实与否尚待考证(这一漏洞)”[6]。尽管历史通常被定义为“非文学性的话语”,历史却与文学作品有着一个共性,即“倾向于夸张地叙述过去(的事实)”[6]。这种“被叙述的历史”既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非小说,因为它“如同小说一样将任何材料(此处即过去的事实)依据今天的眼光重新加以塑造”,而“这个(对过去事实)重新阐释的过程恰恰就是历史编纂元小说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6]。
在《女勇士》中,作者故意篡改了若干个为众人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如汤亭亭对花木兰、岳飞和蔡琰的传说或历史记录作了大量的改写和拼贴。她将各种来源的历史片段与道听途说、口耳相传的故事情节结合起来。此外,她的创作素材还包括从第一代华裔移民那儿听来的有关他们对故国的回忆、亲戚寄去的信件内容,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出版的英语出版物中对中国的描写等。从这些素材当中她获知了有关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及后来的文革等历史事件。与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在《女勇士》这样一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这些真实的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碎片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证明小说所写之事属实,而是要通过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构来挑战历史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历史编纂元小说将历史与虚构相结合,旨在找到历史所代表的“过去”与作家写作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使创作者得以发出与历史主流不相同乃至与之相对抗的声音。
历史编纂元小说把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2个文类,即历史和小说,并置在一个文本里面,目的是为了揭示标榜真实的历史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及历史话语内在的虚构性[7]。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后现代语言特色并非仅仅通过历史(或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报纸文献等)与虚构文本的互文来体现。独特的叙事方式,即多重视角或控制一切的叙事者,造成了一个自信能确定了解过去事实的叙事主体的缺失,“这不是对历史的超越,而是带着疑问把主体间性刻进历史……稳定的叙事声音(和主体)依靠记忆来理解过去,但后现代主义构建、区分而后又消解了这种稳定的叙事声音”[6]。《女勇士》的叙事方式打破传统自传的一般形式,整本书由5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每个小故事中往往不止一个叙事者。这样,多个叙事声音在故事情节的流动中交叉出现,让读者难以分辨哪个声音才是事实真相的代言人。这种多重的叙事视角有意强调人类记忆和家族历史的不可靠性,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鼓励读者对看似权威的历史性叙事发出质疑,同时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不确定性”特征的典型体现。
在小说的第一章《无名女子》中,汤亭亭首先复述了母亲所讲的无名姑妈之死的故事。母亲讲故事本是为了警示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但显然女儿对待故事的态度偏离了母亲的预期。女儿不仅没有被姑妈的悲惨下场吓住,反而放开想象力,大胆猜测起了姑妈的性格生平、为何与人通奸等细节问题并就此给出了多个假想版本。在这一章中,叙述者“我”在叙事时混合使用虚拟语气与陈述语气,将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润色、补充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认为“我的姑姑不可能是独身的浪漫主义者,放弃一切去追求性生活”,因为“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通奸是一种奢侈”[8]。“我”还猜想姑姑遇见那个男子的地点、那个男子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姑姑如何在猪圈里生下私生子以及如何投井自杀。随着“could have”,“may have”,“must have”和“perhaps”等词语的交替使用,叙述的语气在肯定与推测之间来回转换,这等于是在告诉读者,“我”也不确定姑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猜想去找出姑姑犯下通奸罪的动机,即“借助‘可能’去解释‘不可能’”[9]。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创作的过程与故事的虚构性就暴露在读者面前。母亲试图以无名姑妈的故事来告诫女儿不要使家族蒙羞,然而女儿违背了母亲要其保持沉默的命令:“我”不但将家族的丑闻公诸于众,在转述时还添加了自己的看法,对母亲这一家族权威所讲的家族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章《白虎山》的开头,叙述者先告诉读者,尽管中国女孩子向来被瞧不起,她们却听到很多关于女英雄和女剑客的故事,花木兰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对叙述者“我”而言,给女孩子们讲这种故事是与她们“被教导成为妻子和奴隶”的实际生活经历相互矛盾的[8]。受到这些故事的启发,“我”决定“必须成为一名女武士”[8]。在接下来的3个段落里,“我”大量使用情态动词“would”来描绘“我”是如何变成女武士的:“The call would come from…The bird would cross the sun…I would be a little girl of seven the day I followed the bird away into the mountains…I would keep climbing…I would drink from the river...I would break clearly into a yellow,warm world…”[8]。由情态动词“would”构成的虚拟语态在这里描绘了一幅虚拟的画面:故事的主人公“我”童年时深受木兰传说的影响,决心长大后不当平庸的家庭主妇,而是要成为花木兰那样的女英雄,因此才在想象中让自己脱离平凡的生活,在一只神鸟的召唤下离开家乡,进入深山有了一番奇遇。然而,让读者吃惊的是,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竟然在第25 页至第54 页这么长的篇幅里,全部使用一般过去时的陈述语气,即把“我”进入深山之后的遭遇当作客观事实来描写。在这些篇幅里,“我”变成了花木兰,女扮男装征战沙场,为受恶霸欺凌的父老乡亲报仇雪恨。这2个角色之间的切换没有任何过渡性的暗示或提醒,读者一时之间如坠迷雾之中,辨不清这个跟随老神仙学习武艺的“我”与之前同母亲一起吟唱《木兰辞》的“我”是否同为一人;而且,很显然,“我”与花木兰合为一体之后的故事掺杂了不少超自然的因素,绝不可能是客观世界中真正发生的,作者怎么能把其当作真实经历来叙述呢?读者这样的疑惑一直持续到“我”凯旋归来,与父母公婆团聚,从此孝敬老人、生儿育女,过上了美满安定的生活。这时,那个生活在美国的“我”再次出现,慨叹“我的美国生活是如此的令人失望”[8]。这句话让读者恍然大悟,此前读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不过是作为少数族裔、边缘人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我”不切实际的童年幻想。在这一章中,作者故意模糊了虚构与事实的分界线,一个真实的“我”与一个想象中的“我”并置在一起叙事造成的强烈反差,突出地体现了一个华裔女孩想在宣称“人人平等”的美国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与她在实际生活中遭遇到的族裔歧视、性别歧视相互冲突的现实困境。
第三章《巫医》的主角是作者的母亲,讲述了母亲来美国之前与之后的生活变化。在写作这个故事时,汤亭亭延续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并非原原本本、按部就班地向读者复述她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而是一边转述,一边对母亲的话提出质疑、发出评论。在描写母亲学生时代在宿舍捉鬼这一情节时,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来引述母亲的原话,即让母亲成为叙述者来讲述其亲身经历。按照惯例,这种由当事人出面讲述的叙事方式是为了证明所讲之事的真实性;但在本章中,母亲讲完捉鬼故事之后,作者插了一句:“当烟雾散尽,我想我母亲是说她和同学们在床脚下找到了一块滴血的木头”[8]。“我想”这个短语一下子将叙事的视角从母亲转到了女儿,并对母亲所讲之事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
第四章《西宫门外》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讲述了母亲英兰的妹妹月兰在姐姐的鼓动下,从香港来到美国,向丈夫在美国娶的“小老婆”(即邪恶的西宫娘娘)主张自己作为“正室”(即善良的东宫娘娘)的权力。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使得叙述者看上去像无所不知的造物主,全然洞悉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前因后果和故事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动机等等。这样的叙述者本身就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只能存在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在《羌笛野曲》的开头就向读者证实了这一点。全书的最后一个故事又回到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在一段作者向弟弟询问姨妈洛杉矶之旅的对话之后,作者补充说道,“事实上,弟弟并没有对我讲过去洛杉矶的事情;……这个故事他一定讲得比我好,因为他的版本比较直白,不像我的(版本)绕来绕去……”[8]。“事实上”一词表明,前一章所讲之事,尤其洛杉矶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真相,而更像是作者推断,甚至是想象出来的。但这一切究竟是事实抑或虚构,作者并不直接言明,而是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最后一章的故事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交流相关。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历史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故事的叙述者一家是外来移民,要想与美国人打交道甚至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学会美国人的语言。但她从小生活在华人聚居的社区,一直使用家乡四邑的方言,鲜与白人接触,因此,当她去美国的学校读书时,一开始就曾因语言不通而显得沉默寡言、行为怪异。然而,与固执保守、时刻想着落叶归根的父母不同,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非常渴望被美国的社会接纳,可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时刻让她意识到自己身为少数族裔所处的边缘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她将蔡琰的故事用作全书的完结篇是别具深意的。蔡琰(又称蔡文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生活于东汉末年,战乱时被掳至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育有二子,12年后被曹操重金赎回。得归故土自然是蔡琰所期盼的,但代价却是从此骨肉分离,母子永无相见之日。《胡笳十八拍》就是她根据自身经历所创造的琴曲。同花木兰的故事一样,汤亭亭借用了蔡琰这一历史形象并对其进行再创造。在汤亭亭的笔下,蔡琰不再是一个被掳掠的任命运宰割的弱女子,相反,她与匈奴丈夫恩爱地同骑一匹马,双臂环抱着他的腰;打仗时亦与丈夫并肩杀敌,砍掉任何挡路的人的脑袋[8]。她唯一的苦恼是语言文化的差异,如2个儿子不会讲汉语,匈奴人似乎也没有真正的音乐。有天晚上,她第一次听到匈奴人围坐在一起吹奏羌笛,她深受触动,数日后终于和着羌笛的曲调歌唱出心中对故国和亲人的思念,“她唱的似乎是汉语,但匈奴人听得出歌词中的悲伤和愤怒”[8]。汤亭亭侧重表达的是蔡琰从沉默到歌唱的转变,以及她与匈奴人最终所达成的相互理解。这也是汤亭亭为身处中美两种文化的夹击之下的自己和同胞所寻求到的摆脱困境的出路,即不能因为身处社会的边缘而变得沉默不语,而应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寻求自身身份的确立。
三、结语
美国先锋派作家罗纳德·苏肯尼曾说,“一切有关我们经验的描述、一切关于‘现实’的说法,都具有虚构的本质”[10]。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看来,历史并非文学的对立;与此相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虚构,“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10]。元小说的本质就是要把文本的虚构性揭露出来,使读者意识到,小说所描写的绝不是现实世界的映像,而是作家所杜撰出来的人工制品。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后现代元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元小说的自我意识、自我指涉与历史的叙事语境结合起来,对历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出了质疑。汤亭亭的《女勇士》把中国传统的“讲故事”与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后现代创作手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了大胆地挪用、改编,试图说明一个民族的“现在”离不开其“过去”,但过去的历史对现在的人不应该是一种羁绊。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创造性改写,汤亭亭指出,华裔美国人应该在传承前人文化的基础上,顺应新的时代潮流,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方能在美国社会确立起自己的族裔政治身份。
[1]HUTCHEON L.Narcissistic Narrative: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M].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0:xii-xiv,1-2.
[2]HUTCHEON L.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3.
[3]BENESOVANA J.Whosestory is it?——Postmodernism,History and“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J].Oriental Archive,2010(3):303-320.
[4]HUTCHEON L.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Parody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of History[C]//O'DONNELL P,DAVIS R.Intertextualit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3-32.
[5]GEARY D.Labour History,the“Linguistic Turn”and Postmodernism[J].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00(3):445-462.
[6]HUTCHEON L.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114,117-118,132,137.
[7]GRICE H.Maxine Hong Kingston [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6:51.
[8]KINGSTON M.The Woman Warrior [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7,24,54,88,189,243.
[9]MYERS V.The Significant Fictivity of Maxine Hong Kingston' s The Woman Warrior[J].Biography,1986(2):112-125.
[10]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9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