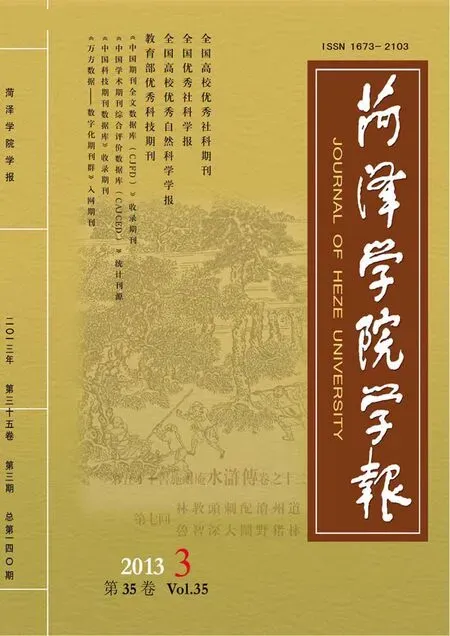论萧红作品女性意识中的孤独情怀与抗争精神*
2013-04-12李宗超
李宗超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萧红,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东北女作家,因为创作抗日名著《生死场》一举成为文坛耀眼的新星,她的自传意味浓厚的小说《呼兰河传》更是成为现代文坛的文学经典。萧红虽英年早逝,但创作成果丰硕,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体裁均有涉猎。她的作品中有浓郁的女性意识,擅长采用复调的叙事手法。此外,女性特有的细腻婉转被她发挥到极致,但又不做作矫情,而是融入了东北女性特有的凛冽情怀。这使她成功跻身于人才济济的三十年代文坛,并为鲁迅赞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1]。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意识是人类精神意志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并且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女性意识愈发被关注。萧红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贯穿于她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她擅长将内心的孤独情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融入到字里行间,女性意识中的孤独情怀和批判精神成为她艺术创作的重要特色。
萧红一生多苦难,常颠沛流离。儿时的萧红缺乏家庭关怀,尽管在幼年时有外祖父相伴,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尽冷落与斥责。成年之后即逃离家庭躲避包办婚姻,将自己寄托于伴侣,期望获得家庭的温暖,最后却事与愿违,几经坎坷,甚至遭遇始乱终弃;期间还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最后在而立之年客死他乡。一生苦难与孤独相伴,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敏感与脆弱的感触以及对于男性话语、国民愚昧的失望与批判,以至于发出“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要一个人走路似的”[2](P68)之感慨。
一、孤独情怀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生命最后几年于香港写就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意味。小说为我们再现了她的童年时代东北东村的生活景象,笔调朴素又凄婉细腻。1911年6月2日,萧红出生于东北呼兰县城的一个封建小地主家庭。其父亲是传统的封建家长,对于女孩子冷漠无情,生母在萧红年幼时病故,继母的到来亦没有给予她幼时最渴望的温暖与爱。祖母对萧红关爱甚少,甚至会用针尖来惩罚她孩提时的小顽皮,这给她留下很深的阴影,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写得那样清晰可见,读者无不因此而对幼小的萧红感到同情。唯一能暂时让年幼的萧红内心世界摆脱独孤的人,恐怕只有她那年迈的祖父了。萧红不止一次在文中提到家里是荒凉的,但是后花园却是她和祖父的充满温馨的乐园。“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3](P259),她和祖父在后园里,“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3](P259)在《呼兰河传》中这种用简单的散文化语言为读者勾勒出的温馨场景有很多。
萧红在小说中用了一整章节的内容来写幼时的她和祖父在后花园玩乐的场景,或者是因为那段生活实在是没有别的温情寄托,仅有的一点温暖,让萧红记忆深刻,多年之后依然很怀念。
但是,萧红刚出生的时候,她的祖父已经六十了,她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过世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3](P380),祖父的离去让萧红在父亲的家庭里唯一的一点感情维系都没有了,荒凉的院子里真的没有一点寄托了。萧红短暂的快乐童年就这么结束了,而童年所遭受的冷漠和压抑,在她的人生中已经埋下了叛逆的种子。正如冰心所说,“提起童年,总是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最深刻的一段”[4](P355),“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她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4](P355)。
萧红离开家乡,开始了在哈尔滨的学生时代。这是她第一次从家庭的逃离。逃离不能给予自己温暖的家庭,逃离没有共同言语,让自己无限寂寞的家庭。学生时代的萧红,深受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曾经把妇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对于人性的钳制。在接下来的五四运动中,女青年们亦举起“男女平等”的大旗来身体力行追求解放。成长于五四运动后的萧红,在哈尔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了这种进步思想以及外来文学的影响,女性意识觉醒并逐渐走向成熟。
中学毕业之后的萧红,因为家人的阻挠无法继续自己的学业,且婚姻被父亲包办。此时的萧红,果断逃离了父亲的家庭,拒绝了包办婚姻,毅然和自己自由相恋的人生活在一起,尽管她的选择终究没有给予她长久的幸福和温暖,但是,这终究是一次勇敢的抉择。
逃离父亲家庭之后的萧红,似乎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独立又强大的女子,因为她始终没有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她在父亲的家庭中很少享受到亲人的照顾与疼爱,使得萧红从小就抱有缺憾,以致于逃出父亲的家庭后,她不是学会先独自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把握自己的人生轨道,而是急忙要走进另一个男人世界,以获得这种期待的温暖。这也是为什么她轻易相信了李姓青年的诱骗,满怀期待的结果是无尽的伤害。
然而,这只是苦难的开始,她的婚恋生活充满各种坎坷波折。从与大男子主义情绪浓厚的萧军的分分合合,再到与优柔寡断没有担当的端木蕻良的仓促婚姻,最后与没有责任心的骆宾基保持的暧昧关系,她拥有敏感孤独的女性意识,却始终没有成熟到自立,在现实生后中一再放下自己的自尊,屈服于父权话语社会对她的控制,坎坷的婚姻生活是萧红青年时代最主要的痛苦根源之一。因为她始终处于矛盾的选择之中,婚姻家庭给她带来暂时的温暖的同时,却又不能给予她所需要的女性的尊严和自由。
自幼体弱多病的萧红,生性又敏感脆弱,再加上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童年时代开始的孤独情绪一直徘徊在她的左右,从未离开过,一直到她在战火中的香港病痛中逝去。她不免自怨自艾的情绪,但是更多的是对于这种悲剧命运的抗争与批判。
骆宾基曾在为她写的传记中记述她的话:“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80岁吗?生活的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得了什么呢?我很坦然的。”[5](P99)
二、命运的抗争与批判
萧红曾感慨:“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 我会掉下来……”[6](P265)生命短暂,却一路坎坷,童年孤独寂寞,青年狼狈潦倒,在相依为命的恋人那里又找不到长久的安慰和体谅,但是她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悲剧时代和悲剧命运的抗争和批判。
青年学生时的萧红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她逃离家庭,开始通过世界之镜来观照自身命运,再加上人生经历丰富且充满辛酸历程,在萧军的引导之下走向文学之路,开始寻找人生的突破口,与多灾多难的人生做斗争。具有天然禀赋的萧红很快成为继五四女作家群之后又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作家。
萧红擅长自传体性质的记叙文,而且常常选择女性视角来观照长期在男权社会受到压抑迫害的女性,以及那些备受统治阶层奴役的农民。
萧红的文学作品擅长通过深刻的个人体验,关注社会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对男权中心的社会现状予以犀利的讽刺和鞭挞。从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红玻璃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妇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核心题材。萧红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批判意识,不停地冲击着给她带来痛苦的男权社会,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特色。
在作品中,萧红有时候会以一种很直接的吼叫来表达对于男性的不满和批判。这和她女性特有的感性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不过,她更习惯于大量书写受迫害的女性哀怜的形象,让读者自己体味整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悲剧生活。例如,在她的小说《桥》中乳娘“黄良子”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丈夫的名字“黄良”后面加个“子”便是人们对她的称呼了。面对地主家对自己和孩子的欺侮她只能忍气吞声。小说《手》中印染匠家的女儿王亚明在求学过程中,勤奋踏实,却因为家境贫寒,且手上因为常年印染而留下的青的紫的颜色饱受老师同学甚至校役的欺侮,最后竟被迫辍学。小说中的“我”对于王亚明的不幸遭遇饱含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在小说《商市街》中,作者虽处于穷苦潦倒的状态,却仍不忘关注那些比自己更加穷苦的求医的母亲。“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7](P33-34),通过细腻的观察,犀利讽刺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歧视的心态。
在她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对于下层女性遭受迫害的场景描写更多。《呼兰河传》第五章就详细描写了邻居小团圆媳妇被婆家人活活折磨死的过程。萧红为了加深读者对于女性意识的认识,甚至在作品中采用了复调的叙事手法。一边以小女孩的视角来描写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表示好奇惊讶,不停跑来跑去跟祖父交流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一边又时而跳出故事来,以成人的视角来深刻描写小团圆媳妇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和周围看客的冷漠无情。
萧红特别擅长从日常生活入手来细致刻画女性所经历的不幸和苦难,揭示作为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民族灾难的牺牲品,以及男人的奴隶和私有财产的女性的悲剧命运。她所描绘的都是普通的下层女性,平凡,却深入人心。萧红应该也已经把自己规划到这类人里面去,但是,和她所描绘的这些女子不相同的是,她对于自己的命运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努力去抗争,去改变,尽管每次都是更深的伤害。
除了普通女性之外,在萧红小说角色中农人的故事亦占了很大比例。她既悲悯于农民的简单质朴,又痛恶他们的愚昧麻木。
她同情那些备受贪婪的地主们、军阀部队,以及日本侵略者残酷迫害,又要忍受变幻无常的大自然折磨的农民。萧红欣赏他们受尽苦难却依然极端乐观。在她自传性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回忆了家乡的生活场景,其中对于农民形象的描写颇多。在最后一个章节中出现的冯歪嘴子就是其中一个。冯歪嘴子是村里品性忠厚、做事踏实,与邻里相处融洽的磨倌,但是因为和老王家的大姑娘成家,同居在磨坊遭到东家的呵斥,周围邻里也一下子转变了对王姑娘的一贯好评,制造各种传言对这对夫妇进行冷嘲热讽,他淡然地找了新地方安顿好了妻子,即使在他的妻子早早地去世,留给他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时候,他也“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绝望”[3](P378);“好像他活着还是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3](P378);“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地,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3](P378),“于是他照常地生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3](P378)。
在刻画冯歪嘴子的悲苦人生过程中,萧红同时讽刺了村里看客们的愚昧和粗暴。这些看客是他乡里的邻居,平时会拿冯歪嘴子开玩笑,还曾一致评价王大姑娘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可是在二者结合以后,周围的乡邻相约结伴跑去冯歪嘴子寒冷的小棚子外听取只言片语,然后以制造二者谣言为乐。本应该善良淳朴的乡邻成了麻木愚昧拥有变态好奇心的冷酷看客,面对别人自由的婚姻结合,不是抱以祝福,而是拿了传统的礼节去衡量别人的过失,同时期待二人因为旁人的指责而感到懊恼或绝望。
萧红的作品以自己的孤独敏感为主调,以女性角色为主角,带着批判的眼光,表现自己的倔强地抗争和批判的意识。
她的语言感情浓烈,她的批判少哲理式的长篇大论,多用感情用事,“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是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8]。到了80年代,读者们评价萧红和鲁迅一样,“从来不以旁观、冷漠的态度进行创作,总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于描写对象之中;在塑造民族魂的同时,他们真诚地显示着自己的灵魂”[9]。萧红因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影响了自己的人生,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是,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竟是最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一面。
此外,萧红的语言简洁有力,不雕琢,尤其在描写她那短暂的幸福时光时,行文自然得如诗歌一样美。熏风曾经评价萧红作品“不以诗名,别具诗心”[10]。
《呼兰河传》中对故园的描写便很能体现她的这一语言特色:“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3](P380),“小黄瓜,小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3](P380),“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子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就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儿功夫变出一匹狗来,那么变着……”[3](P380)简单清新的文字却有着极其动人的力量。
萧红具有天然的语言禀赋,擅长重述个人人生体验之酸甜苦辣,既能以充满感情、理解以及清澈的笔触叙述家乡人民的纯朴和山川的秀丽,又能用冷静犀利的笔触描写家乡农民的愚昧;既能用温暖的诗化语言描写美好的童年,又能描绘穷苦潦倒的婚姻家庭生活;虽体弱多病,心境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向着“温暖”追求;虽然一次次地在婚恋生活中收获更大的痛苦,却没有放弃对于生活的希望。
萧红生活在被敌寇占领的国土上,她在失望的爱情中流浪,在病痛的折磨中挣扎,最终寂寞地死在香港。寂寞的童年和坎坷的成年经历,以及自己的女性身份让萧红始终不能释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11](P95),短暂的生命里承受了太多时代的苦难,她在寂寞中试图倔强地抗争。虽然她的努力终究没有让她获得所期待的胜利,但是她在文学上所创造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意识,影响了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她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作品也将作为经典不断被后来者解读。所以,萧红似乎又不再是孤独的了。
[1]斯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J].新文学史料,1987,(3).
[2]梅林.忆萧红[G]//王观泉.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萧红.萧红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4]冰心.我的童年[M]//冰心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
[5]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6]聂绀弩.在西安[G]//萧军.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7]萧红.商市街[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8]景宋.追忆萧红[J].文艺复兴,1946,(6).
[9]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J].十月,1982,(1).
[10]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作为诗人的萧红[J].学习与探索,1981,(5).
[11]石怀池.论萧红[M].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