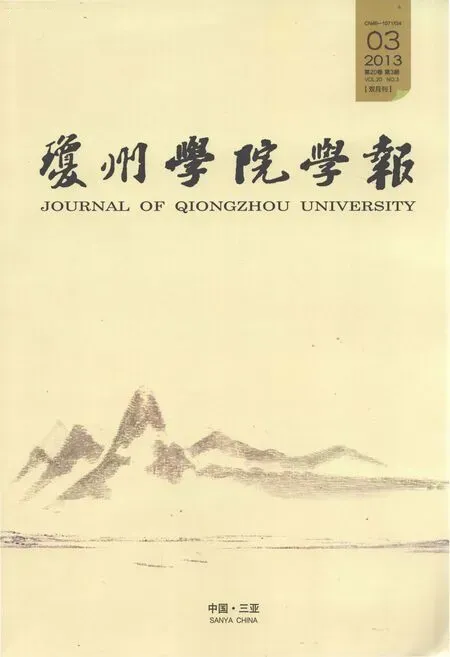意境与梦境的纯美年代——简析徐志摩小说的意象与梦幻追求
2013-04-12吴荣芳
吴荣芳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徐志摩1922年初春开始写诗歌,1923年春尝试小说创作,十年的创作生涯,他留下来的诗歌集有4部,而小说集却只有《轮盘》一个薄薄的集子。尽管徐志摩创作的小说作品不多,但因着“独特的华丽”[1]而别具特色。徐志摩将自己的理想和浪漫心绪赋予了他作品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意象选取上因了满腹诗绪和诗化语言而诗情画意。在诗意意境中追求爱、美与自由的梦境,由梦境的生成到幻灭,隐喻着徐志摩人生的起伏与跌宕。本文从一些意象,如镜子、季节、花、窗口等富有女性形象的意象入手,深刻体会徐氏小说在意境与梦境变幻中的形而上的追求之美。
一、镜子与梦境
拉康曾指出,镜子作为一个意象在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形象确立和培养的过程中始终存在。拉康的“镜像理论”虽以婴儿作为解说对象,但“镜像阶段”形成的过程是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存在的,对于意识的确立,不仅婴儿,甚至成人时常也会出现“非我”状态。这时他的意识就会出现短暂的游离情态,伴随这种游离而生虚幻,进而产生一种“忘我”的梦境阶段。这种梦境的出现在无镜的情形下也可产生,但“非我”意识与“自我”意识形成的对比性就决定了媒介的存在,而镜子是最好的媒介。人在镜子中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形象,也会是幻象。“自我”与“非我”两种意识的较量,决定着是真象还是幻象。也正是这种既共谋又互斥的关系使两者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
镜文化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女娲正是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才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了人;西方有“水仙花情结”的主人公纳西萨斯(Nar-cissism)在水中看到自己英俊面容的倒影而顾影自怜,最后想拥抱而溺水身亡。这两则神话虽以水为镜,但道理相通,即“人通过自己在镜中的反射得到自己的印象,并凭借这种印象,确立了自我形象,从而把人类与自然界和动物区别开来。而个人,也正是通过自身在外界的映像,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2]因此,镜中的影像极易使人将思维投向个人的内心深处,寻找真实的自我。而作为女性妆扮不可或缺的物品,镜子又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人物与照镜子的关系通过镜像描写的幻觉呈现,揭示了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
徐志摩小说,从首篇《春痕》(原名为《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开始,镜子意象伴随梦境就已出现,如开篇,“逸清早起来,已经洗过澡,站在白漆的镜台前,整理他的领结”;“他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益发激动了他Narcissus 自怜的习惯,痴痴地尽向着镜里端详”[3]3逸本是男性,但作者却将逸美好的面容呈现于镜子之上,更多的是透视人物忧郁凝滞的内心情态,将其性格女性化,从而明确逸的性格里缺乏刚强与自信,“俯看下界的烦恼尘俗,微笑地生怜,怜悯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数未经生命严酷教训的少年的幻想”[3]4,在镜子反射中影射逸的青年梦想与追求。透过镜子寻找自我,正是逸在镜前端详的原因。逸如他的名字般清逸,却如女子般多情,他在自设的梦境里陷落。
小说第三节是逸悲观情绪的迸发高潮阶段,他在现实与梦境中进行着“自我”与“非我”的较量,即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较量。这一节主要叙述了逸如何因春痕的病而自扰。逸得知春痕因病入院的信,这时的他独自在房间便是尽想“人生老病死的痛苦,青年之短促”;艳丽鲜花因风催雨虐而落地成泥;春痕也会变老变丑。自发的悲观情绪顿时涌上逸的心头,然而他所迷恋的梦境却是美好自由的,因为他觉得“圣母玛利亚不会老,观世音大士不会老,理想的林黛玉不会老,青年理想中的爱人又怎么会老呢”?正是这一疑问使得他相信“将来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创造的”,他的“自我”战胜了“非我”。但转想,逸又被“非我”所打败,因为“理想的将来不过只是烟淡云稀,渺茫明灭”。几经转折,逸仿若明白了恋爱老死的意义——“精神的事实,是永久不可毁灭的”。[3]8带着释怀的心情去看望春痕,回到家中,逸最终还是陷落进了自设的梦境中:“他想见一个奇大的坟窟,沿边齐齐列着黑衣送葬的宾客……里面却埋着世上的种种幸福,种种青年的梦想……又埋着春痕,和在病房一样的神情,和他自己——春痕和他自己。”[3]10逸和他的理想主义随着他的两颗热泪瞬间崩塌,十年后重遇已是年老色衰的春痕的事实彻底幻灭了他的美好理想,他那“葆涵着春痕当年可爱的影像”的梦碎了。
作者在小说一开篇就将忧郁多情的逸呈于镜面之上,起到了先声夺人之用。在诗情画意的田园间尽显逸的梦,这也是受过康桥文化洗礼的徐志摩的梦,尽管作者说逸的原型是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在日本时的青年时代形象,但处在动荡时代的有志青年,他们的理想其实都是相通的。
人通过照镜子会看见自己的神情甚至内心,这时镜子与梦境的功能相似。现实的反差大小与否会与人物的思想紧紧相连,“镜前之我”与“镜中之我”通常会相融或相斥。在《两姊妹》和《轮盘》中,作者同样预设了一个镜台:
“她(玛各,笔者注)站在镜台前,怔怔的,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的是什么,在愁的是什么……她无意的伸上手去,在身旁的镜台上,拖下另一把手镜来。她放下了那只手里的照片,一双手恶狠狠的擒住那面手镜像擒住了一个敌人,向着她自己的脸上照去。”[3]16-17
“(倪秋雁,笔者注)站定在衣柜的玻镜前对着自己的映影呆住了。这算个什么相儿?这还能是我吗?……像是有一个恶鬼躲在里面似的。……觉得头脑里一阵昏,眼前一黑,差一点不曾叫脑壳子正对着镜里的那个碰一个脆。……使她记起不少早已遗忘了的片段的梦境……手指摸着了玻璃极细微的一点凉感从指尖上直透到心口,这使她形影相对的那两双眼内顿时剥去了一翳梦意。”[3]57
玛各和倪秋雁在镜前认清了自己又迷失了自己。玛各因看到了自己七岁和十七岁时的照片,联想到这二十几年被姐姐掌控在黑屋子里并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青春流逝,留下的却只是空洞无趣。她只能对着镜中那年老无用的“我”歇斯底里地大声喝斥,甚至将“镜中之我”的映影认作敌人般恶狠狠地擒住。倪秋雁面对镜中的自己:脸红如火,颧骨亮如琥珀,鼻腻如油,唇被烟卷烧得如煨白薯般焦紫。这是从轮盘上输尽家产及心爱的珍珠项圈后的倪三小姐。镜子是真实的,“镜中之我”也是真实的,唯独虚幻的是那些过去美好的、魂牵梦萦的回忆与梦境。镜子本身的质地会使人产生易碎感和冰凉感,就如梦。玛各的梦境里住着一个可爱又妩媚的年轻貌美的自由的自己,倪秋雁的梦境里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她像蝴蝶般轻盈飞舞,永远靠着坐在湘妃竹椅上做针线的母亲,听着爹爹送的小黄鸟歌唱,心爱的珍珠项圈依旧在匣子里……深处梦中是美好空灵的,但梦醒了,“自我”与“非我”、现实与梦境因距离而美好。
二、窗与梦境
窗意象与镜意象一样,在文学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说文》说:“在墙曰牅,在屋曰囱。窗,或从穴。”在建筑学上是指墙或屋顶上建造的洞口,用以使光线或空气进入室内。在古代窗是当镜之用的,如“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诗》),“小轩窗,正梳妆”(苏轼《江城子》)等。陈敬容诗《窗》寄托了抒情主人公的梦与憧憬。澳大利亚女作家泰格特的《窗》通过写靠窗的病人和不靠窗的病人来说明境由心生的意义。美好的梦幻是心造设的。晓窗当镜,窗具有了镜的功能,与镜一样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而窗与门一样都与外界发生联系,受到空间的限制,人站于窗前或眺望或凝望时便会产生无限暇想。思绪与外界一旦发生碰撞,就会陷入自设的梦境中。
徐志摩运用窗意象来带领小说主人公进入梦境,这在《船上》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船上》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二十岁的女主人公腴玉跟随母亲搭船第一次到乡下替祖母看坟地,从未体味过大自然的腴玉从中寻到了无限乐趣,仿佛成就了她的第一次寻梦。与青草对话,亲吻青草,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具有完美童真的少女形象,“她恨不得自己也是个乡下孩子,整天去弄水弄泥没有人管”。腴玉搭乘的船“是一个大箱子似的船舱,上面盖着芦席,两边两块顶中间嵌小方玻璃的小木窗,左边一块破了一角,右边一块长着几块疙疤儿像是水泡疮”,“她倒不怕晕,她在热褥上盘腿坐着,臂膀靠着窗,看一路的景致,什么都是不曾见过似的,什么都好玩”[3]29,芦苇、老鸦、水牛、浣衣的乡下女孩子、水车,一切的一切对于一个生活在城里的女孩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并道出了“谁说做乡下人苦”的心态。说腴玉不懂世间沧桑也好,不食人间烟火也罢,这一次的寻梦对于她而言是有意义的。
腴玉在船上度过了猎奇的一天,晚上躺在船上,她仿佛自己如做梦般,因为“这天以前的腴玉,她的思想,她的生活,她的烦恼,她的忧愁,全躲起来了……不再是她原来的自己……她的梦思风车似的转着”,腴玉的生活不曾接触过这些,她的生活里满是妈妈的逼迫声和念书声,烦恼和忧愁充斥着她的思想,但“那块长疙疤的小玻璃窗外天光望见了她。咦,她果然是在一只小航船里躺着,并不是做梦。窗外是什么光呀,她一仰头正对着岸上那株老榆树顶上爬着的几条月光,本来是满月,现在让榆树叶子揉碎了”[3]30。白天,腴玉通过小玻璃窗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好景致,晚上腴玉被小玻璃窗外的天光所看,在这窗与外界相连的“看”与“被看”中,完成了腴玉的寻梦之旅,满月被榆树叶子所揉碎,洒下清冷的月光,腴玉的梦醒了,“她还是她,她的忧愁,她的烦恼,压根就没有离开过她——妈妈也转了一个身,她的迟重的呼吸就在她的身旁。”[3]31清冷月色刺激了她,她最终还是会离开大自然回到城里继续书写她的忧愁与烦恼。
《船上》仅一千多字,多情的徐志摩赋予了腴玉多彩的梦却又亲手揉碎了它。他更多的是想说梦仅仅是生活的调剂品,人不应沉溺于自设的梦境中,如玛各般生活在自己的牢笼中。在《两姊妹》中,妹妹玛各相对于姐姐安粟来说,对生活更多一些怀疑和憧憬。她尽管二十几年都被自己的痹症和姐姐捆绑在这屋子中,但是她可以通过屋里的窗口去释放不安的情绪,就算她只是通过窗口看到女佣玛丽拿着手镜在拍粉、擦胭脂,看到对门那家瑞士人如期在跳舞。透过窗口,玛各从女佣那里看到愤怒,从瑞士人那里看到羡慕和嫉妒。随着音乐和穿着银丝镶边的枣红色礼服的小姐和高高美男子的舞姿,玛各也陷入了梦境中:“安粟侧着一只眼望进来,只见妹妹的身子有点儿摇动,一双手紧紧的拧住窗幔,口里在吁吁的响应对面跳舞家的乐音……”[3]14-15,而梦醒是在姐姐的一声“扼衡”中,忘情的玛各只能“赶快低着头回转身”。四十几岁的玛各甚至比不上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她的情最终被压抑着,她的梦在时间的冲击中扭曲,梦醒对于她而言也许是解救她。
三、花与梦境
花与镜子、窗同是传统意象,它们在徐志摩小说中与主人公一起交叉被诠释。花意象,比起镜子和窗,更富有多变性、动态性和多情性,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万种风情无地着”。中国古代传统诗词人也格外钟情于花,如李清照、苏轼等。小说中提到的花意象,包括瑞香花、藤花、梅花、红玫瑰、茶花、初菊、迟桂、茉莉、红锦(在日本是形容遍地枫叶的样子)、桃花、李花、红心蕉等,其中瑞香花、藤花、红玫瑰、茉莉、红心蕉是与主人翁心绪相通的,其余的花种仅是作为陪衬(在这里不作详述)。花与特定的时令、季节相关,与人物心境也是相通的。人物将各种心绪移入花中,寄情于物,这一过程便能产生很微妙的梦境,虽短暂却能传达人物的心灵状态。
季节和花意象在《春痕》中有明显的叙述,小说分为四节,每节题目分别与季节和花相关,如瑞香花——春(第一节)、红玫瑰——夏(第二节)、茉莉花——秋(第三节)、桃花梨花处处开——十年后春(第四节)。作者采取这样的结构是为了从逸和春痕的相处中选取四个生活片段来推进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且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作者选用自己擅长的诗人语言将这样的结构、意象和情感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小说更富有诗意,也正如他所说的,他愿他的小说“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灵异的闪光”。[3]457瑞香原产中国和日本,为中国传统名花。小说中的主人公逸在日本的住处看见朝晨满园的瑞香花,“受到了清露的涵濡,春阳的温慰”,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思。一段极富诗意的描写将人物与花融合在一起。浓劲的花香从窗外飘散进来,一种“不见其花便闻其香”之感将逸一整天的心绪也如“小蜂迷醉地环舞”,[3]4逸年轻时的梦也随这春天的满园瑞香含蓄地怒放。第二节中的红玫瑰是春痕亲手所画,“真是一枝浓艳露凝香……情词哀曲,凝化此中”[3]6,玫瑰赠郎君,情愫如浓烈夏日盛开的红玫瑰,散发着暧昧的缱绻。第三节中的茉莉正值“秋风秋雨愁煞人”时节,逸在初菊、迟桂和茉莉中选中茉莉,香幽色淡的茉莉一如春痕素净淡雅的容颜,不着胭脂,不矫情。十年后的逸再次回到日本寻芳踪,而这时的春痕却是年老色衰、臃肿绻曲,曾经几番神魂迷荡也挽不回今日梦的破碎。逸有风的飘逸与轻盈,却无风的洒脱与泰然。时令不会随着流年的过往而消逝,春天花的盛会也不会随记忆的模糊和事物的变迁而流离,心中再缭绕的梦境也会如花般脆弱,逸总是将自己蜷缩在自己飘渺的梦境里,得到的却是哀怨一曲,灵犀飘然杳逝。
《春痕》作于1923年初春,徐志摩借他人故事来诉说自己的梦,其实与花的移情作用一样。《“死城”(北京的一晚)》中作者借用廉枫之口与坟边三朵萎谢的红玫瑰,道出了“光彩常在星月间”和“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的心声。[3]《“浓得化不开”(星家坡)》中的红心蕉则是从梦境深入到人的潜意识,“这叫做孤单的况味。这叫做闷”,这“闷”表现何处,“‘红心蕉’,多美的字面。红得浓得好。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紧紧的卷着,我的红浓的芭蕉的心’”[3]43,正是“现实与梦境交替,心灵与自然契合,联想与幻觉融汇,表现出主人公变幻莫测的紊乱的‘潜意识的内心世界’”。[4]
结语
徐志摩在小说集《轮盘》自序中说:“至于怎样写才能合适宜,才能博得读者的欢心的一类念头,我从不曾想到过。这也许是我的限度一宗,在这一点上,我期望我自己能永远倔强:‘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3]458这篇序作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这时作者梦的国度已被现实冲击,开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也正如他在致友人凌叔华的信中所说:“我的想象总脱不了两样货色,一是梦,一是坟墓,似乎不大健康,更不是吉利,我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其实是太晦涩了……”[5]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求梦,他的梦如绅士般款款风情。作为新月派的一名元老,他的诗情梦意就像天边的新月飘渺,正如学者们强调的,“徐志摩后期的诗文,格调消沉得可怕。很明显,徐志摩由‘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顽废’,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个人主义理想的破灭”。[6]1928年初春发表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这首诗,“与其说诗人是在描写如梦境中的情绪,不如说诗人是把现实与梦境迭加在一起。他的梦境即是他的现实,他始终生活在如梦的世界里。”[4]44他的小说与诗歌构建了他的梦,而他的梦最终因个人理想的破灭如风般迷失方向。可以说,徐志摩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小说家。他是站在诗人的立场上写小说的,他的小说有诗的味道。意象化追求可谓是徐氏小说的重要成分,意象可以渲染环境气氛,构筑小说的意境美。意境与梦境的混沌使得他的小说在意象选取上更接近女性之美,且这些意象也更符合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情感发展。
[1]方仁念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毛凌莹.《红字》中的镜子意象及其叙事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2011(3):81-88.
[3]顾永棣,顾倩编.徐志摩小说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4]任国权.论徐志摩小说的诗化性[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23(2):39-44.
[5]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日记书信集[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149.
[6]赵稀方.徐志摩思想新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1):2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