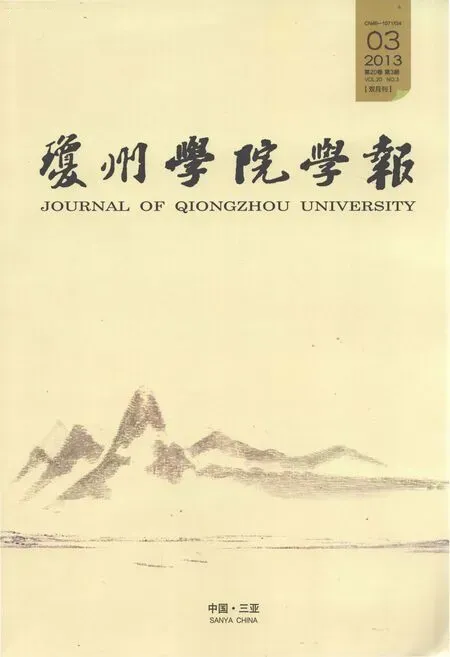滇东北苗族丧葬礼仪及其符号功能探析
2013-04-12任继敏王琼杨焰
任继敏 王琼 杨焰
(昭通学院 教育科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丧葬习俗,是重要的民俗事象之一,是人生礼俗的最后一项告别仪式。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复杂宽广的心理世界,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它是考查、观照民族文化积淀的一个独特而真切的窗口。”[1]
云南(滇)东北部的昭通市是一个地域特别、民族多样(15 种民族)、文化多元的地方,受民族风俗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各族人民有着不同的丧葬习俗和礼仪,它们记载着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对它们进行研究,可以考察昭通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人生态度、生活哲学和价值取向等。限于篇幅,本文只对苗族的丧葬仪式及其隐含的符号功能进行探析。
一、滇东北苗族的丧葬仪式程序
昭通市有苗族17 万余人,占昭通总人口的3.31%,是人口总量仅次于汉族和回族而居第三的民族。根据方言不同,其内部又分为花苗和白苗。“白苗”以川、黔、滇方言为交流语言,多聚居于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四县与贵州毕节和川南接壤地区;“花苗”以滇东北次方言为交流语言,一部分聚居于彝良、大关两县境内沿洛泽河两面的二半山或高山地区,一部分散居于昭通、鲁甸、巧家、盐津、水富、永善等区县的高寒冷凉地区。因为支系不同,丧葬礼仪也各有细微差别。甚至同一支系、同一地域的苗族,不同家族都有较为固定的、区别于其他家族的丧葬程序。这些不同程式也就成为各姓氏内部区别是否同宗的标志。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明显趋同习俗特点的民族,昭通苗族丧葬仪式中主要的程式和内容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现以昭通市威信县“白苗”中较为固定的丧葬仪式为例对滇东北苗族的丧葬仪式进行叙述。
(一)临终 小敛
昭通苗族历来实行木棺土葬。凡是苗族已婚之人病重时,都要遣人奔告至亲好友前来探望,家人要轮流日夜看护。老人临终时子女要守候在侧并让其在怀中落气,并且要把当时处于熟睡状态的人唤醒,以免亡人把睡梦者的魂魄带走。老人落气后迅速将其头脚调换方向,抹合眼皮和嘴唇,在门外吹牛角号或者鸣炮三响向乡邻报丧,然后把死者生前铺床的稻草取一把拿到路口焚烧,烟飘向哪里则指示死者的灵魂飘向那里了。乡邻闻讯后一般都会马上放下手中活计赶来丧家帮助料理后事。
之后,孝子们披麻戴孝为死者沐浴更衣,死者的衣裤奉行穿单不穿双,也有的姓氏奉行男单女双的习俗。苗族较为特别的是:死者穿的衣裳与生前正好相反,是小衣襟在面上盖住大衣襟。穿戴完毕后用麻线将死者双手捆缚贴于身旁保持直立形式,然后“头东脚西”停尸于火房上方(有的姓氏停在火房下方)。明末清初时苗族曾经盛行过头朝东方,脚朝西方的横式葬法,后来受汉族习俗影响,逐渐改为南北方向的顺葬。但是,停灵时依然采用头东脚西横停于中堂的方法,这是表达对东方故土的怀念之情。据说昭通的苗族祖先是从东方迁徙来的,头东脚西可以让亡魂回到东方故土与祖先的灵魂会聚一堂。这种横式停尸法是苗族丧葬仪式中较为外显的区别特征。这个过程俗称小敛。
(二)指路 入殓
“指路”是苗族丧葬礼仪的中心环节。苗族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要到天庭与祖先一起笙歌娱乐过逍遥自在的生活,而去天庭的道路遥远而崎岖、陌生而险阻,需要指路师的指引。如果不指路,亡魂将沦为孤魂野鬼到处飘荡,还会找后人的麻烦。所以,苗族老人死后,不论家庭条件好与坏,丧葬仪式完整与否,过程简朴还是隆重,指路环节必不可少。只要会端碗拿筷的、会说话的人死亡后都要给其指路。指路仪式在死者停尸于火房时即可进行。
苗族的指路仪式有一套特定的程序:之前要由外姓人反手搓绳编织一双草鞋,家人准备一只大公鸡和酒饭,指路师自备一副竹卦、弓弩和一团麻线。指路时,孝子跪于亡人一侧,儿媳举火把照明,指路师端坐于亡人一侧,用极其悲戚的声音吟唱古老的《指路词》。
《指路词》的第一部分讲述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人的死亡是因为十种药有九种都医不好以后无可奈何的结果,以此来安慰死者,让其对死亡想得开;第二部分是指路词的重点所在,细致地指引亡灵归祖的路线,告诉亡灵途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求生、解难、辨识苗寨和祖先以及新家(坟墓)等;最后一部分讲述人在生前如何受苦,死后如何解脱以及家人的悲伤难舍之情,并且嘱咐亡人忘掉世间的一切“过去”安心上路去同祖先会合欢聚。苗族认为,只有经过指路之后,亡人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
指路完毕即举行大殓仪式——“装棺入材”。先用布料或者绸缎铺垫于棺材底上,将亡人抬着顺鼓架转三圈(有的姓氏转九圈)装入棺材,按头左脚右(古时的东西方向)横停于中堂上方。每个儿媳要拿出一丈二尺白布挂于灵柩上方的墙壁上或者拉直覆盖在棺材上,出殡时拴在灵柩之前,俗称“马缰绳”。停柩期间,棺材盖不完全封闭,留一条缝供亲友瞻仰遗容。
(三)祭奠 出巡
苗族的丧葬传统不讲究黄道吉日,成年人死后停尸三天即可安葬。停丧期间,丧家在堂屋中间安放鼓架,上挂一个牛皮鼓,堂屋暂时设做灵堂供亲友祭奠。牛皮鼓的安放方法各个家族和姓氏各有不同。停丧期间,大家聚在亡人身旁昼夜吹笙击鼓。苗族认为这样可以解除亡人赴阴间路途上的寂寞与愁闷。“鼓架”是苗族丧葬仪式中极具象征意味的、必备的道具。
祭奠分为正祭和客祭。正祭主要由指路师、寨主、叔父、舅父和笙鼓乐师祭祀,正祭每天天明和天黑各祭一次;客祭是出殡前夜由亲朋好友举行的吊唁活动,热闹而隆重。正祭和客祭时,笙鼓齐鸣,祭悼者和孝子一起跪拜于堂下,死者儿媳或者侄儿媳妇两人执火把于灵柩两侧照明,掌祭师用酒食敬献亡人,告知亡人这是某人做的道场。
威信苗族有一部分姓氏在每次上祭前还要先举行出巡仪式——由叔父带领举行武装巡游活动。巡游时,领头的叔父要在队伍前面披毡舞矛,紧随其后的是一个芦笙师,一个执火把者,一个号角手和众多手舞竹竿的青壮年汉子。现在这样的仪式已经程序化和符号化,多由儿童担任,带有表演性质。出巡时先在堂屋绕鼓架一周冲出大门,然后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不同方向绕房屋三周后进入堂屋左右分别转三圈后结束。据说这种仪式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是古时候,怕野兽啃噬人的遗体,因此组织身强力壮者护卫尸体;二是古时战争期间举行葬礼,怕敌人偷盗阵亡者尸体,不得不组织巡逻队伍武装保卫;其三是驱赶妖魔鬼怪,出巡也就只针对凶死者。
苗族丧葬祭奠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宰牲”仪式。苗族老人去世后,家人一定要宰杀牛、猪、羊等牲畜献给亡人。家境困难的,一只鸡也行,不能没有祭牲。宰牲一般在正祭之后进行。牲畜宰杀后除去头、内脏和四肢,一起煮熟交由掌祭师放于堂上摆设的各种器皿中念祭。
苗族老人的丧事也叫“白喜事”,除了每天早晚的正式祭奠之外,其他时间大家就聚在鼓架下吹笙击鼓、跳芦笙舞自由娱乐。最隆重的吊唁活动在出殡前夜。其时村寨乡邻、亲戚朋友都要前来参加吊唁活动,所带物品大多为白酒一斤,火纸一刀,送钱与否视与丧家的交往而定。至亲如姑母、舅父、女婿、叔父和儿女亲家等要备专门的祭礼:一丈二尺白布(用来裹盖尸体),还要牵猪拉羊抱鸡背粮食,请上唢呐乐队热热闹闹地前往奔丧。这些礼品一般陈于鼓架下,如果宾客带有交礼师,主客双方交礼师还要在交礼时唱歌互相谦虚礼让,展示才学。女儿女婿及其他至亲带来的牲畜在午夜时交牲,杀后不上祭,由掌祭师告知亡人即可。
(四)谢孝
苗族丧葬吊唁活动的高潮是安葬前夜举行的“谢孝仪式”。当主要宾客到齐后,午夜时分,鼓乐全停,鼓架下摆放酒菜(用两条高凳或方桌摆在鼓架下,用矮凳子团围四周),邀请寨老、祭师、笙师、舅父、姑父、叔父、亲家等重要人物就坐,众孝子在堂下长跪举行“谢孝仪式”——也叫“团桌论事”,实际上是集体悼念仪式。
这个仪式由“管事”主持并陈述《谢孝词》。“谢孝词”从天地日月、洪荒蛮古开始一直讲到人烟、五谷、草木、金属的产生,然后向宾客陈述亡者在病危期间子女如何护理、如何安排善后事宜等详情。洋洋洒洒上万言。然后寨老、祭师、笙师、舅父、姑父、叔父等依次对亡人进行追忆,对孝子表示安慰,叔父还要告诫孝子以后如何守孝、铭记亡人恩德,如何继承先人遗志,发愤图强以慰亡人等等。谢孝时间一般长达一至二个小时。
谢孝之后,笙鼓乐师起坛烧袱子。众亲友与孝子一同跪拜于灵前将带来的火纸一一烧给亡人。笙鼓乐师演奏《分道场曲》表达对死者的难舍之情。
黎明时分,笙鼓师演奏《黎明曲》,最后一次为亡灵祭祀。接着吹奏《辞灵曲》,整个祭奠结束,解除鼓架,由女婿念咒后将鼓架掷出门外。然后出殡。
(五)出殡 安葬
出殡时,灵柩移到大门外,用粗大绳索捆牢四根抬棒,准备八个人抬棺材上山。棺材上放一个盛有火炭的器皿。准备就绪之后,祭司手持斧头致完发丧词,击碎火炭器皿,众人大呼“起”,即刻拉的拉,抬的抬直奔墓地。指路师背着竹弓、抱着公鸡在前引路,孝男孝女一路叩谢,鞭炮、锣鼓和唢呐齐鸣,热热闹闹地送亡人到墓地。“花苗”出殡则少有鞭炮,以笙鼓奏送。
苗族的安葬情形与汉族差不多,掘墓、入圹、清棺、盖棺、封土、垒坟。之前死者的儿子媳妇和侄儿媳妇各自敬献的一丈二尺白布——“马缰绳”这时则分给孝女、媳妇们留做纪念。
从安葬之日起,连续三日孝子都要早送饭,晚送火。送火在晚上夜深人静时进行,放火的地点不像汉族固定在坟前,它是在墓地到家之间的路线上,一次比一次往后退,离家近,并且交代“请某某于此取火”,第三晚上最后一次送完还要嘱咐道:“火就送到这里为止了。”有的还用几根竹片搭成房屋形象将其烧毁,意思是亡灵回来取火看见房子已经烧毁,就不再回来了。
安葬后第三天举行“复山”仪式。丧葬仪式至此结束。
(六)烧契 除灵
烧契又叫“周祭”。从安葬之日起到第12 天进行(有少数宗支为第七天),目的是接亡灵回家来游玩、看望家园。接灵仪式各姓氏各有不同。有的姓氏早上接灵时要抱一件衣物(男的用上衣,女的用裙子)随去,作为亡灵的依附之物。接灵的方法:有的拄一根竹竿到坟墓上杵三下,呼请亡灵回家,有的持一火把到坟前接灵;有的用指路师的弓箭去接灵;有的只在半路上呼喊。亡灵接回屋檐下,祭上洗脸水,然后请上灵位。有的人家灵位设于火房下方西面,有的设于火房上方,有的在死者烟气的床上,有的设于中堂上方。周祭一般不杀大牲畜,仅以一只鸡念祭。灵桌上放一升米谷插香,点燃菜油灯,摆上祭食。亲友也会带上纸钱和酒水前来祭吊。祭师会将亲友好意一一祭告亡灵。夜深人静,纸钱烧化给亡灵后,儿媳执火把照明,孝子跪拜,祭师掷灵卦辞灵。
除灵,威信苗族叫“uat wangb”,即“解除簸灵”——超度亡灵。这也是苗族极具民族特征的丧葬仪式。它的来历与一个传说有关:相传远古之时,人鬼杂居,鬼强人弱。一次人鬼又打斗起来,鬼追至人的家门口,人眼看已逃不掉,急中生智将一个大簸箕掷向鬼,簸箕竟然神奇地附在鬼背上,背着大簸箕的鬼就被阻挡在门口,人得救了,从此鬼就背负着大簸箕。威信苗族认为,人新死变成鬼,亡灵会背着个大簸箕行动,极不方便和自由,做孝子的为此牵挂劳心,必须为其举行仪式解除掉,是谓除灵。人死未除灵之前,一直是鬼,除灵以后才能变成祖宗家神,归入列祖列宗之位。而只要未除灵,孝子之孝长在,就不能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一般亡故120 天之后即可为其除灵,有的规定三年。凡是亡故时经过指路的,都要除灵。家族人丁兴旺者,“除灵”仪式尤其隆重。
除灵时,于中堂上方设一灵床(家用方桌或者冲糍粑的粑槽),放一个小簸箕,用竹篾弯曲两头插于簸箕边缘,围上衣服,装饰上帕子,像一个人坐在簸箕内,即为灵位。簸箕内放一个糍粑(有的姓氏放动物肝脏)作为亡灵的座位。上点菜油灯。然后祭司端着另一只装有五谷和桃枝的簸箕到各房间驱邪念咒,开始接灵。笙鼓师也要吹奏相应的曲子。亡灵就位后开始隆重的祭献。除灵的活动要延续两个昼夜,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可以三昼夜或者更长。无子嗣或者困难人家,烧契结束后即可除灵。
除灵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辞灵。待笙鼓乐师吹奏完辞灵曲,祭司即刻进行辞灵——亡灵背上的簸箕已经除去,让它回去了。(各个姓氏举行的仪式不一样)仪式之后,将祭祀时用过的灵粑(糯米做成的糍粑)分给大家带回去给孩子吃。据说孩子吃了特别聪明。因此,最后分灵粑时,大家你争我夺,热闹非常。
一个亡人的丧葬仪式就在圆满热闹的氛围中结束。
二、滇东北苗族丧葬仪式的符号功能
丧葬仪式除了“处置亡人的遗体;安慰亡人的家属;肯定亡人的业绩;(在信仰宗教的民族中)通过宗教仪式祈祷亡人的灵魂平安离去等显性功能外”[2],还存在一种特有的隐形功能——符号功能。
符号:symbol,源于希腊词,该词的基本意思是“象征”。符号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具有超越本身的功能性价值:人运用符号系统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这个符号系统也影响着人们所看见、听见和想到的一切东西。丧葬仪式很显然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既是物质符号,也是行为符号。丧葬仪式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便是“尸体”,“尸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象征着今生与来世、此岸与彼岸、人与鬼之间的跨越,于是处理尸体不再是一种简单行为,被赋予了更多符号化的象征意义。
丧葬仪式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祭祀包括祭祀亡人,祭祀祖先,祭祀神灵。仪式上,一般都要敬献牲畜等祭品,那些被祭献的牲畜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动物,也不是食物,而是代替人类向神灵表达崇敬和服从的祭品。如苗族丧葬仪式中的宰牲、彝族丧葬仪式中的捶牛、宰羊,以致最后吃牛羊肉的时候,实际上都不是在世的人独自在吃,而是与亡灵和祖先神灵在一起享用。神灵们既然享用了祭品就代表着他接受了人对他们的崇敬以及与他“和解”的请求,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保佑人们。“仪式经常固定地和重复地在某个时间或某一特定情况下举行,并且承载着某种象征意义和功能。”[3]于是,在丧葬仪式中,普通的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意,人们在自己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丧葬符号中活动,以便保证以后在人世的生活更“和谐”顺达。
丧葬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文化教育功能
符号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该符号系统中的人进行“教育”上。因为,人不是生下来便能够运用和创造符号,首先应当学习已经存在的这个符号系统,而社会中那些先进入和学习了该符号系统的成员有义务帮助后来者学习此符号系统。这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将符号系统继续传承下去的需要,也是每个社会成员成为“真正的人”的需要。
人们学习符号系统即为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人们参与丧葬仪式便可学习并使用这种符号。正如杜威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有生有死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与“种族”的社会生活则是要继续下去的。于是,成人对青少年就必须传授知识与经验,包括风俗、制度、信仰、语言、文化、思想等,这种传授与继承,就是广义的教育。丧葬仪式的教育功能表现在:
1.耳濡目染的隐性教育
丧葬仪式通过器物、祭词、禁忌、音乐、行为、互动活动等显性和隐性的方式进行传承,并在传承中对人的发展并产生影响。苗族丧葬仪式主要是通过祭师的专场“说唱”和“表演”来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不管成人还是孩子)进行隐性教育的。所谓隐性教育是指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手段,把教育贯穿于其中,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丧葬仪式作为人生重要的最后仪式,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其相对固定的祭祀的形式和祭词内容会在反复进行的仪式表演中慢慢地被记住、被内化。这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使教育过程具有无意识性和愉悦性,教育目的因此具有潜隐性和持久性,能达到教育的最优化效果。尤其苗族葬礼上喜欢吹芦笙、跳芦笙舞的习俗使丧葬仪式肃穆中有几分欢娱,其“载歌载舞”的表达形式,对于苗族传统文化的演习和传承也是一种寓教于“艺术”的学习方式。更是苗族丧葬仪式实现其符号教育功能最独特的方式。
2.内容丰富的知识教育
丧葬仪式有一套程序性的“祭祀语言”,其中包含了日常生产、宗教信仰、历史、规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知识,它可以使参与者学习本民族的历史,了解规章制度,确立本民族的社会价值观,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苗族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七千年来仅凭口头传承,其丧葬祭词的演说是苗族历史的主要转播方式和途径。指路师的指路词记载:苗族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先民的田园和沃土而四处漂泊,但他们认为在死后,灵魂也要回到祖先的居住地。苗族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唱词:“天是那样的阴沉,地是那么的黑暗,老天不帮我们,我们要走了,美丽的田园沃土沼泽湖泊,我们舍不得啊!……”这样丧葬祭词不仅是生者对逝者的告慰,同时也为逝者指明回归祖先故土指路,更重要的是它对后人的启迪意义。
这些内容对于研究苗族先民的迁徙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也是研究苗族社会形态的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指路歌》,是苗族先民为后人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关于种族迁徙路线的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先民所经历的苦难史以及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顽强抗争。
除此之外,苗族的丧葬仪式还具有民族艺术、思想道德和劳动等教育内容。艺术教育体现在歌舞、芦笙的吹奏和表演上;思想道德和劳动教育则集中体现在“谢孝”过程中,通过追忆逝者的功德、铭记亡人恩德,教育后辈继承先人遗志、发愤图强热爱劳动,热爱现在的生活。
(二)情感抚慰功能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代表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即便是很原始的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情绪也是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对于死者的爱恋和挽留与对“死亡”的反感和恐惧。
丧葬礼仪的本质就是处置“尸体”。面对着因为病痛和死亡折磨而面容变形的冷冰冰的尸体,活着的人会有愧疚、悔恨、惧怕等诸多情感奔涌而至,这时,“乃有宗教插进脚来,解救情感在生死关头的难关”[4]33。于是生者带着复杂心理将死者的灵魂打发到“另一个世界”,为了表达对逝去亲人的热爱和留念,就用“酒肉祭奠、家属哭丧、明器陪葬”等形式来讨好死者或者报恩于死者,或者求得死者的谅解,并以此抒发自己内心的各种复杂感情,同时给自己的尘世生活带来好处。同时,将死讯告知亲友,可以得到慰藉和帮助,从一定程度上解除精神和物质上的压力。因为葬礼上相聚的人们一般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和人生理解的特定群体,其中传递的相同的社会价值信念、道德理解、生命感悟等就会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信仰救赎和灵魂治疗,让生者坦然面对死亡。这种聚在一起的社会性礼仪活动,有助于克服人们因死亡而产生的削弱、瓦解、恐惧、失望等离心力,使受了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重新统协,以此加强个人与群体的连接和力量,从而保持文化传统的持续和整个社会的再接再厉。
据调查,90%的苗族认为可以不举行婚礼,但必须要有一个像样的葬礼,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和完满的。因为苗族认为人死后,如果没有指路师指路,此人就回不了祖先居住的“东方”,就只能做孤魂野鬼。所以,丧礼不仅是为了死者,更多的是为了生者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信仰。人们用隆重的方式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也建立起勇敢面对死亡的决心和勇气。“任何人在他亲历过许多别人丧葬的仪式之后,对于他自己的死,便也有所准备,永生的信仰,经他屡次在亲友们的死亡仪式中练习之后,会使他愈清晰的觉得:他自己的来生是更可预期的了”。[5]
(三)加强民族认同
苗族习俗,有亲人病逝,不管多远亲属都会按照礼仪赶来参加丧葬仪式,这时本家族的人们更会团结在一起。苗族村寨里一旦听说某人去世了,大家会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计赶来丧家安慰亲属,并竭尽所能帮助丧家处理丧事。苗族老人病重期间,家门族内、团转四邻的亲友会白天派人轮流到场,晚上除留人看家外,大多要参与守候,如同平时的其他重大事项必须帮忙一样,体现出族人的亲情和友情的力量,维系着一种团结、互助的凝聚力。因为人人有父母,个个有六亲,故参加守护、送终别人家的老人,又可为自己家将来有事情时“换工”。这样每个人活在世上心里才底气,一旦自己家有事需要帮忙时,亲友也才会全力以赴。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丧俗不但使个人精神得到完整,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得到完整,从而“死这专私的行为,任何人唯一最专私的行为,乃变成一项公共的事故,一项部落的事故。”[4]30于是,丧葬仪式成为一个充满了民族性符号的“场”,它从各个方面强化了族群之内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为这时具有民族性的符号就会集体出现,像服饰、饮食、方言和音乐、舞蹈等,这些显性符号的同时出现,无形中加强的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首先,从物质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饮食和服饰最具民族特征。以服饰为例,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都与他民族有巨大的区别,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服饰的样式和花纹与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服饰的民族性与仪式的民族性总是互相辉映的,所以人们喜欢在仪式过程中穿上民族服饰。
其次,从历史、伦理、道德观和禁忌等精神文化符号来看,葬礼强化了本民族的各种思想和规范,从而强化民族的认同感,尤其是仪式中的禁忌特别能反映该民族的特点。如苗族没有为死去的亡人“除灵”就不能参加社会活动等禁忌,反映了苗族特有的“孝道”和“人伦”观念,表达了苗族人民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是与苗族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特征。
第三,仪式的反复操练,也使族群认同感得到加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丧葬仪式也会经常在相对固定的集体里面上演。于是,因为仪式的反复操练,“不仅让操演者回忆起该群体认为最重要的分类系统”[6],也使群体共同记忆的东西具有了持久性。比方苗族指路师指示亡灵顺着“祖先迁徙”的来路回归时,强调沿途有很多符号性的障碍,哪些地方能过,哪些地方不能去等等,这一仪式的内容与汉族的“开路”、彝族的“送魂”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都在强化着“苗族”族群界限,加之,苗族“横式”停放灵柩、“除灵”等的特别仪式,也划清了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边界,将“自己人”和“他人”区别开来,强化了族群意识。
总之,丧葬仪式的符号功能体现在仪式的每个活动中。人们在隆重、庄严的气氛中,在每个亲身参与的丧葬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教育,并将其转化为外显的行动,从而也教育了别人。所以,丧葬礼仪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人 的“遗体”的过程,它承载了许多的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并使之更好地为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作用。研究它存在形式以及符号功能,找出其中的利与弊,对于引导当前沸沸扬扬的殡葬改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曹毅.土家族的丧葬习俗及其文化内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1):36-38-46.
[2]李彬.金岭镇回族的丧葬习俗及其社会功能[J].回族研究.1994(2):52-56.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31.
[4][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5][美]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4.
[6][美]保罗·康纳顿著.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