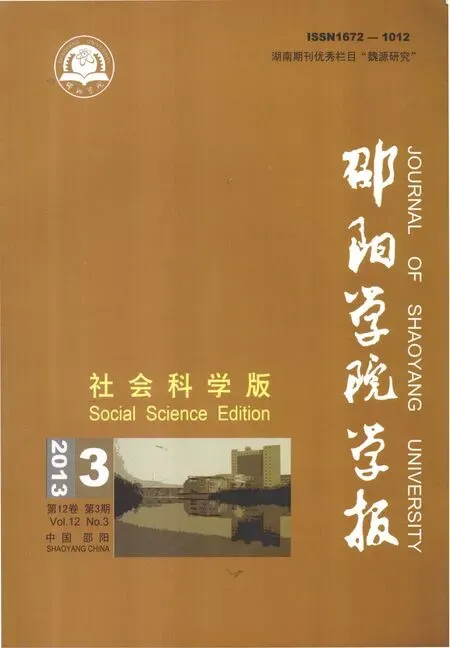哈姆莱特性格悲剧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2013-04-11廖金罗
廖金罗
(广东科技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000)
一、引言
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不仅认为“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而且认为“莎士比亚所要描写的,在我看来很明显,即把一件伟大的行动放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一个察性优美、纯洁、高尚而最有道德的人物,却没有作为英雄所必具的魄力,垮倒在既不能担当叉不能抛弃的重负之下”。
歌德的观点很符合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认为“不是邪恶,而是行为错误,或者,性格弱点导致主人公的厄运”。不过,亚里斯多德的“性格弱点”(frailty)指主人公的性格特质,诸如:脆弱、多疑、犹豫和本性邪恶等。“行为错误”(error)不是指主人公的道德错误,而是指主人公的认知偏差。在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性格弱点”和“行为错误”是高度吻合的。自歌德以来,《哈姆莱特》一直被认为是“性格悲剧”的典型代表。主人公在认知上的“犹豫”和“过多思考”不仅被认为是“性格弱点”,而且被认为是在“复仇”过程“行为错误”(“行动延宕”)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歌德的“性格说”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是因为他忽视了性格既不是一个“天生的”、也不是一个“被给予的”、更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根本属性,而是一个“后天的”,“流动的”和“可以被建构的”个体属性,忽视了在哈姆莱特表层言语行为等性格表层结构后面隐藏着价值取向的矛盾以及忽视了价值取向的矛盾影响主体在“复仇”行动中的价值判断。显然,哈姆莱特的性格弱点不是使凡人不能成为英雄的原因,而是使人成其为人,而不是使人成为电脑的根本所在。没有经历这种性格弱点的英雄只能使现实世界增添“喧哗和骚动”。
二、个体性格矛盾性
性格是指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被给予的”和“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近年来,性格被认为是一种人的“后天的”、“被建构的”和“流动的”个体属性。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从哪儿带来什么,也没有被先天给予什么,更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东西。人从来就不是自己,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物,是生活方式的媒质,是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工具,是在物质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内在规律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性格建构。性格表层结构,如言语行为,和深层结构,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是在物质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内在需要的反映。生活方式的长期稳定以及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内在需求的长期一致性使得主体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得以固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要求性格同样发生变化以便性格和活方式的客观需求相适应。然而,新兴生活方式的内在需要以及在新兴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新兴经济、新兴政治和新兴文化的内在需要不会立刻影响个体言语行为等表层结构,更不会立刻影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深层结构。影响性格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变化的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点滴的和局部的变化,而是生活方式彻底的、深刻的和全面的变化,是伴随经济转变和政治变革的文化革命。没有一场巨大的经济革新、彻底的政治变革和深刻的思想革命,诸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性格深层结构很难改变。有时,在生活方式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点滴的和局部的变化可能导致特定个体言语行为的变化。然而,隐藏在言语行为等表层结构之后的诸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性格深层结构不会改变。在表面看来崭新的言语行为之后隐藏同样旧的价值取向、旧的思维方式、旧的认知方式和旧的行为模式。哈姆莱特就是这样的人。仔细研究哈姆莱特的言语行为表明在其表层言语行为之后隐藏旧的深层结构。
在中世纪,农奴制、王权制和基督教构成英国的宗教封建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在宗教封建自然经济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决定经济贵族、政治权贵和精神贵族的相互结合。广大封建农奴被排除在分享经济成果、政治权力和文化话语制定权之外。基督教认为“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创造了人类。“上帝”之所以创造人类,是因为“上帝”希望人类实现其意志。人是“上帝”的工具,人的一切是天生的,被给予的,永恒不变的。“上帝”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和价值选择的终极指向。因此,人们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信奉“上帝”、“否定世俗欲望”和“否定今生,相信来世”等。基督教的二极指向和世俗两极化趋向建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基督教文化对主体心理的影响和“二元化”思维方式影响认知方式的僵化。十四世纪时,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些近代自然科学萌芽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精英迅速成长,在政治上不断壮大,在文化上开始建构一种价值体系。此时,人们开始抛弃“上帝”,肯定人自身的基本欲望和实现自身潜能,追求今生今世的欲望实现。在英国,宗教封建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世俗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生活方式发生矛盾,不断斗争。然而,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不仅没有导致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在政治上的完全掌权和在文化上的彻底革命,而是不断地与封建世俗势力和精神贵族势力结合,产生一种带有浓厚封建宗教色彩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生活方式。在威廉·莎士比亚时代,英国正在经历两种生活方式不断矛盾和不断融合以及植根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的两种政治、两种经济和两种文化的融合。这种社会客观存在不仅决定封建宗教思想和科学精神,法律意识和决斗习俗并存,而且决定个体性格深层结构的不可能变化,而且决定个体性格中表层言语行为和深层结构的深刻矛盾性。四百多年以来,哈姆莱特因为“高雅的学问”、“潇洒的外表”和“高强的能力”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然而,对哈姆莱特性格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仔细研究表明哈姆莱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底的封建基督教徒。当然,彻底的基督教徒并不排斥言语行为的某些科学性和内心经历的价值取向的矛盾。
哈姆莱特是一个“个体怀疑主义者”。在过渡时代,哈姆莱特既怀疑建立在旧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宏大叙述”,又不相信建立在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话语体系”。他既质疑“上帝”和“鬼魂”的存在,又不认同“现实的欲望”和“今生的幸福”。哈姆莱特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学习过一些近代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但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科学论者,家庭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环境决定了哈姆莱特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也许,当时新的思想和留学经历会影响哈姆莱特的某些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但是,丝毫动摇不了他在灵魂深处的对”上帝“的信仰。他不仅承认“鬼神”、“上帝”和“魔鬼”的存在,而且拥有浓厚的基督教价值取向。“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二幕二场)虽然,“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不一是天堂,但是,忘记“上帝”,追求实现世俗欲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一幕二场)以及“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一幕二场)显然,哈姆莱特矛盾的话语体系表明他经历着价值取向的矛盾。价值取向的矛盾是整个时代旧的价值取向崩溃和新的价值取向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反映。普通市民可以在价值矛盾中度过一生。然而,哈姆莱特不是一个踌躇度日的市井小人,而是国家命运的拯救者和价值体系建构者。“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一幕第五场)在被告知老国王被谋杀的阴谋后,哈姆莱特在为父亲复仇和重整乾坤的道路上开始“孤独的思考”、“单独的探索”和“个体的建构”。
三、个体思考、个体探索和个体建构
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异化物。这种异化物是个体对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需要的认知。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需要的变化要求“自我”和“自我意识”也发生变化。因此,哈姆莱特需要了解在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真实需要以便建立被认同的社会秩序。早年,哈姆莱特王子跟随父亲料理国事,父亲和当时的国家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他也认同父王以及当时的祖国。然而,哈姆莱特离开祖国多年,一直在外求学。因父王的突然死亡才被召回国内。回国之后,父王死亡的神秘、母亲再婚的仓促、社会现实的突变、王权的被窃取、群臣的背叛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在这些重大事件之后隐藏的深层社会原因给哈姆莱特带来认知挑战。
哈姆莱特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徒,而是一个具有科学思想的基督教徒。他不像传统教徒一样对无知感到满足,而是具有思考世界、探索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天使保佑我们!不管你是一个善良的灵魂或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了天上的和风或是地狱中的歪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因为你的形状是这样的可疑,我要对你说话,我要叫你哈姆莱特。君王,父亲!尊严的丹麦先王。啊,回答我!不要让我在无知的愚昧里抱恨终天。”(一幕四场)“我的命运在高声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像怒狮的筋骨一样坚强。它仍旧在招我去。放开我,朋友们:凭着上天起誓,谁要是拉住我,我要叫他变成一个鬼!走开!去吧,我跟着你。”(一幕四场)
“孤独的思考”、“单独的探索”和“个体的建构”受到传统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个体是生活方式的媒质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构个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一旦主体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被建构,除非大规模的政治变革、经济革新和文化革命,心灵就很难从这种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旧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影响“个体思考”、“个体探索”和“个体建构”的方式。例如:当父王“鬼魂”出现时,哈姆莱特就怀疑故事的真实性。“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样一种本领的,由于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崇,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凭着这一出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二幕二场)为了验证鬼魂话语的真实性,哈姆莱特精心设计了“戏中戏”情节。应当承认,戏中戏的安排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哈姆莱特既试图通过鬼魂揭示谋杀案的真相,又试图通过科学验证鬼魂的存在。这种认知手段的荒谬性是主体价值取向矛盾的反映。在一个叔父弑父夺母,情人和同学被敌人利用成为刺探自己信息工具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充满“无形的”蕃篱。事物的表面总是具有欺骗性。在宗法关系后面隐藏着个人阴谋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忏悔后面隐藏着犯罪的肆无忌惮;在同学友谊后面隐藏被人利用和潜在杀机。为了了解真实世界,哈姆莱特必须摧毁人和人之间存在的这道“看不见”的“防线”,因此,他需要制定特别的认知策略和使用特别的认知手段。为了避免了解真相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哈姆莱特不得不假装“疯狂”。“你们必须再一次宣誓,我今后也许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颠颠的样子,你们要是在那时候看见了我的古怪的举动,却不可像这样交叉着手臂,或者这样摇头摆事实脑的,或者,嘴里说一些吞吞吐吐的言词,例如“呃,呃,我们知道”,或者“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就可以”,或是“要是我们愿意说出来的话”,或是“有人要是怎么怎么”。诸如此类含糊其辞的话语,表示你们知道我有些什么秘密;你们必须答应我避免这一类言词”。(一幕五场)显然,“装疯”被哈姆莱特在不太正常的社会中当成一种有效的获得真实现实的认知手段和认知方式。哈姆莱特两极化的认知是“二元”思维方式的直接结果。
价值判断是“思考”、“探索”和“建构”中最关键的环节。也就是说,价值判断受到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深层结构影响。长期以来,哈姆莱特的“独白”被认为是和前文脱节的。显然,这种认知忽视哈姆莱特内心世界的思想矛盾斗争。独白安排在“戏中戏”的前面,“戏中戏”的安排是哈姆莱特为父亲复仇的第一个行动。这种启动“复仇”程序的事件必然导致主体对事件及其后的思考。这种事件必须需要合理化的借口以及价值判断。在独白中,哈姆莱特的怀疑反映他对两种价值取向的失望。在确认叔父的弑父罪行后,哈姆莱特决定为父亲复仇。在去母亲寝宫的路上,哈姆莱特发现叔父在做祷告,没有动手。“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薜正重的时候乗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跟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罪薜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醉酒之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簸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二幕三场)此时,如果哈姆莱特是奥塞罗,或者雷欧提斯,那么行动推延不会发生。然而,奥塞罗的鲁莽行动和雷欧提斯的意气用事给世界带来什么?除了给尸横遍野的世界增加一些“喧哗和骚动”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不管叔父罪恶多深,亲自手刃叔父,眼睛一眨都不眨的人是否是真的英雄?这种英雄在生活方式的重建过程中是否有道德感召力?
哈姆莱特不仅需要从肉体上消灭克劳狄斯,把他的灵魂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叔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叔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之中相互消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叔父的灵魂在其肉体被消灭后进入天堂,他代表的旧生活方式得以继续维持。因此,当历史为剌杀克劳狄斯提供最简单和最便捷的机会时,传统价值取向影响哈姆莱特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哈姆莱特没有像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一样把复仇看作是纯粹的“私人”恩怨,目标虽然明确,意志坚定,无所顾忌,但是复仇的成功与否并不能改变什么。像雷欧提斯一样,个人之间的厮杀使得世界再一次充满“喧哗和骚动“。显然,哈姆莱特需要将宗法责任与重整乾坤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建构一种价值意义。在克劳狄斯做祷告时,哈姆莱特没有杀死他。当叔父利用误杀事件试图“借刀杀人”以及在雷欧提斯临死前揭穿克劳狄斯的阴谋之后,受了重伤的哈姆莱特才完全剌杀克劳狄斯。虽然,哈姆莱特没有完全复仇,没有建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通过霍拉旭,他的死亡和他的故事不仅被讲述给了后人,而且给后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四、结论
几百年来,因为过多地注重外部世界和事物外表,歌德的“性格说”没有能够找到解释哈姆莱特内心世界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复仇过程中的影响倍受批评。显然,在哈姆莱特的性格中存在基督教价值取向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矛盾。然而,在关键时刻,基督教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影响他的价值判断,使他把事物表面和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僵化了。哈姆莱特的价值判断表明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存在。
[1]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廖金罗.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悲剧成因后现代主义阐释[J].外语学刊,2009,(6):183-187
[3]Plato. The Republic[M].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
[4]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王逢振.文化研究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6]姚乃强.西方经典文论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