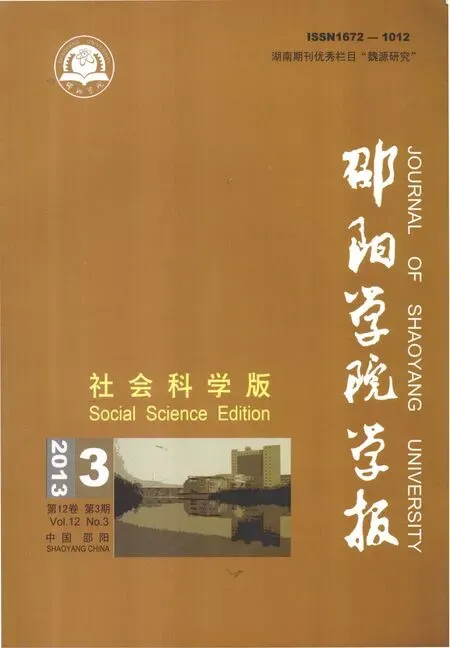试析奈保尔作品中的景物意象
2013-04-11何善秀李宗
何善秀,李宗
(华东交通大学 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V.S.奈保尔祖籍印度,成长于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处于东西文化强烈冲突和夹缝中的奈保尔面临处处似家,处处不是家的尴尬境地,无奈选择自我流放和漂泊,成为一个一直在路上的寻根者。双重移民的身份虽然注定奈保尔漂泊的命运,也赋予他复杂而独特的文化视角。V.S.奈保尔曾言,景物只有经艺术家阐释才具真实感。在奈保尔作品中大量特定景物的描写正是作家主观停顿的印记。世界之旅是奈保尔的文学创作之旅,也是作家的精神之旅,旅途风景明媚或衰败,取决于旅行者的眼睛。世界依旧,转变的是体验世界的敏感心灵。
一、黑暗中的风信子
意象就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是融入作者思想感情的对象,是赋予特定意义和特殊感情的具体形象。相对于视觉而言,意象更倾向于其他感观的体现。超越简单的明喻﹑暗喻范畴,具备更为深远意义及引申含义的意象被称为象征。[1]
〈河湾〉的主人公萨勒姆是一个来自非洲东海岸年轻的穆斯林,出生在已经在非洲生活了几百年的印度家庭,成长背景颇为复杂。小说讲述了萨勒姆不满家乡的生活和命运的安排,流浪到刚果河拐弯处的河湾镇的经历。风信子意象在奈保尔《河湾》中,重复的频率高达近十次之多,是其他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现象。“自南而北,河湾之外,满眼都是丛生的风信子,漂浮在黑暗河流上的黑暗岛屿,飘摇在急流之中。急雨和惊浪撕扯着最黑暗处的荒草,仿佛要将它们投入到遥远的海中,只是海太远。唯独风信子是河流的孩子,那高大的、淡紫色的花出现仅仅几年而已,当地的语言中甚而没有名字。人们只是叫它‘新东西’或者‘河里的新东西’,认为它是另一种敌人而已。因为它们稠密的枝蔓纠缠密集,附着在河岸,阻塞船道。风信子生长极快,快得超出有工具的人类的扼杀。因此,河道不得不时常清理。就这样日以继夜,风信子不停自南向北漂浮,一路播撒种子。”[2](P45)这是作家对风信子意象的首次描述,不难看出作家寓情于景,赋予风信子丰富的内涵:它是生长极快的新东西,是敌人,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在殖民主义制度崩溃,殖民者离去后,非洲大陆残留的殖民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对这一景物反复描述反映了本地非洲人面临西方文明和本地化的艰难抉择,也凸显了作家作为“夹缝人”矛盾和两难的心态。[3]河湾镇是殖民时代结束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缩影。《河湾》中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赶走了殖民者,一夜之间把从国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统统更改,摧毁殖民者的住宅,把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拿来泡木薯;同时又盲目地模仿西方模式:不分贵贱,给人人都冠上“公民”的称呼;在河湾镇的旁边建立一个新领地,并宣称将是一个现代化的非洲。新领地陷入了比殖民者统治下的河湾镇更迅速地衰败中:垃圾随意丢弃,腐败横行,现代化的大学成了养鸡场。主人公萨勒姆和奈保尔一样,身处异乡,作家通过萨勒姆以局外人的角度,指出极端保守主义导致历史的倒退,盲目模仿也会导致混乱。正因为奈保尔穿行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才能冷静地指出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现实,盲目复制西方模式无异于“自我殖民”。
二、疯长的常青藤和白嘴鸦
《抵达之谜》是奈保尔的半自传体小说,文中并无故事的情节。作家只是展开细致的描写,犹如中国的水墨画,将一幕幕瞬间流淌的画面凝固,用极其清淡的笔触,轻描淡写朦胧记忆中跳跃的光点、模糊的身体和记忆的碎片,极具“不在场”的距离美感。“常青藤”和“白嘴鸦”实际上是《抵达之谜》的最后两章的题目。常青藤往往让人联想起青春、活力和美好,然而《抵达之谜》中,奈保尔对常青藤的描写所引发读者的联想绝非如此。相反,它是人性脆弱的一面;它是生活表面的温柔蕴涵着的残酷;它是使得人类历史延续的不完美却极富生命力的神秘力量。“常青藤密织,扼杀了不少树,我对树知之甚少,还不能辨认是什么树。有一年倒地的一棵,后来才知道是樱桃树。我只是在之前见到过它在长青藤致密的缠绕中持持续续的花期。”[4](P216-217)常青藤如此美丽,被允许沿树攀延而上,而树最终死于这种致命缠绕,直至倒地。”[5](P321)一个生命的生是以另一个生命的死为代价,最终取代了其在这个世界的地位。白嘴鸦同样是以惊人的速度繁衍,而且,非常善于伪装。“我们给白嘴鸦的噪耻声搞的心烦意乱。噪声是在人头顶盘旋的白嘴鸦群发出的,长长的黑色的缘,大大的黑色的翅膀。以前怎么就没见过。我习惯了尖叫中突然而至的八哥鸟群,象黑色的树叶一样落到树上。这么多的白嘴鸦,倒是没见过。他们徐徐飞起,卿卿喳喳的,好像在议论我们一样。”“老菲力普先生关于白嘴鸦预示钱财或死亡的话增加了这种鸟的神秘色彩。大群盘旋窥视的黑鸟使得多株榆树死于无形之中”。[6](P296-297)
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精心挑选并极为细致的描写了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常青藤和白嘴鸦。这两个意象都包含了某种威胁生命的不明力量,透露出悲伤和死亡的气息。文章缀满忧伤和落寞,这种弥漫的忧伤被许多评论解读为无根人的痛苦,无家可归的困惑。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种忧伤是对帝国衰败的隐痛,是眼见帝国繁华不再的惆怅。文中死亡的气息是帝国逝去的隐喻,或是“想象中的帝国”不在的象征。奈保尔在文中说到,“我来得太晚了,无法找到原先的英国,她已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帝国的中心模样”。诞生于殖民地的奈保尔用想象中的一切或者书本上的一切取代了对于宗主国世界的真实认知,他为帝国繁华逝去感到痛苦。孩提时代在特立尼达他从英国进口的炼乳听商标上看到了有蓝天白云作衬托的黑白花奶牛。这幅图画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凝聚着这个“异乡的印度人”对大英帝国无限的美好遐想,吸引着这个男孩渡过千山万水,来到这个“幻想的最中心”[7],人到中年的奈保尔却无奈发现想象中的帝国只存在于想象中。
三、抵达“中心”
奈保尔从早期的英国求学之路,60 年代特立尼达回乡之旅,印度次大陆的寻根之旅,70 年代的东中非之旅直至定居英国的乡间,一直在旅途中。从风信子到长青藤和白嘴鸦,作者表征的自我和他者,经历了巨大转变。《河湾》中的风信子是黑暗河流中的新东西,体现了当地人对西方文明既依赖又害怕的矛盾心态,也展示了身处双重文化背景下,奈保尔两难的文化处境: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三访印度,结束了长达一年的印度之行后总结说:“直到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地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同时,他又发现,一旦回到自己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间,“印度精神悄悄地从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以捕捉不回来的真理。”[8]在母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他始终面临既亲近又疏离的两难抉择。《抵达之谜》中,奈保尔记录了他在英国威尔特郡乡间十年生活经历,作品中处处是极致的细节景物描写,对琐碎生活繁复的讲述。与《河湾》中人们不知所措的困境和排斥的心态相比,《抵达之谜》讲述的是理解之后的认同,体现了更加从容的心态。多年几乎遍布全球的旅行是无奈的自我放逐,是奈保尔无尽创作的源泉,流放之旅也是创作之旅。奈保尔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审视和反思,借助文学文本想象和建构自己的家园,在想象和现实中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河湾》中,奈保尔站在文化的外部审视,从一个“异乡人”的角度,刻画了在文化的内部,人物对“新东西”渴望又害怕的心态。《抵达之谜》中,奈保尔站在威尔郡的山坡上,看到了炼乳听的商标上“那有蓝天白云作衬托的黑白花奶牛”,当时只能在课本上看到高高的山毛榉树和高耸入云的教堂塔已经真实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年文化苦旅的中年奈保尔已经成为英语世界颇负盛名的作家,他虽然难掩悲伤,却在英国的乡间获得了平静。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临近尾声时,奈保尔感叹他已经心满意足,“每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走过这里,特别是在山坡的顶端有几头乳牛在蓝天的陪衬下悠然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感觉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一种微弱、遥远的渴望——像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那样遥远,几乎已经遗忘的记忆——已经得到满足,我已经置身于那副炼乳商标图案的原始美景之中。”从最初的挣扎和逃避,到最后的水乳交融,文学的创作旅途呈现了奈保尔从一个漂泊的旅行者成为一个英国经典作家的过程。1990 年奈保尔在一次为纽约曼哈顿学院作题为《我们的普世文明》的演讲中指出“只有英国才能使他实现当作家的梦想,连美国都做不到这一点。”、“它是既给予我从事写作生涯动力和想法,又给予实现那一动力方法的文明;它使我能够实现从边缘到中心。”[9]
四、结语
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V.S.奈保尔踏上寻根的旅程,有着异常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文化来源。他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超于寻常的观察和探究。成功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在西方文学界享有盛誉的移民作家,从帝国的边缘,前殖民地印度和特立尼达来到了帝国的中心伦敦,“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单向旅行”[10],在帝国的怀抱中得到平静,得到西方文明世界的认可。
[1]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ture Term[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0.
[2]奈保尔著. 方柏林译. 河湾[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汪家海.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反思—〈河湾〉的后殖民文化解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129-132.
[4][5][6]奈保尔著. 邹海伦,蔡曙光,张杰译. 抵达之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7][法]德洪迪著. 邹海仑译. 奈保尔访谈录[J]. 世界文学,2002,(1):120.
[8]奈保尔著.李永平译.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北京:三联书店,2003.
[9]Naipaul ,V. S,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The Writer and the World:Essays[M].New York:Knopf,2002:506.
[10]雷燕妮.英国20 世纪的殖民和后殖民小说—宗主国的视角[J].外国文学研究,2003,(4):153-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