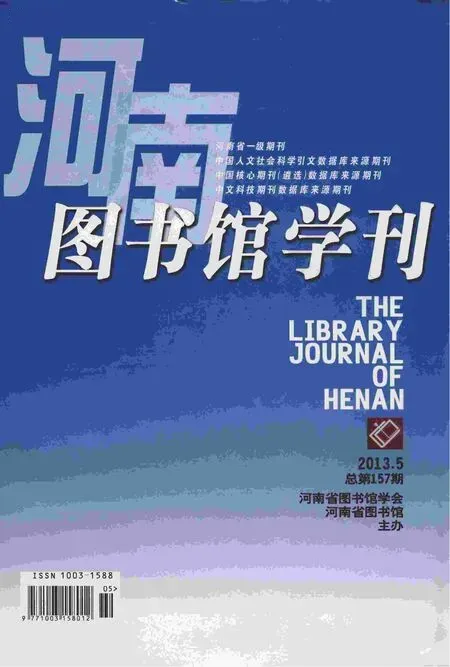《读书与传媒》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比较
2013-04-11陈业奎
张 瑜,陈业奎
(1.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信阳师范学院文献研究所,河南 信阳 464000)
《新华文摘》与《图书馆学情报学》都是转载、选录或摘编高质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论文的文摘期刊。两者绝非平庸思想地来回搬运和信息模块的复制拼接,必然加入了编辑团队的追求、信念、理想,是整体期刊编撰思想的绽放,是让人敬重的精神瑰宝。前者是刊物《新华文摘》的重要专栏,后者是系列刊物《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的一种。“读书”是两者关注的“关键词”。两者皆以关注读书问题研究学术成果为本命,但学术定位的标杆不同,形成了有趣味与有意义的差异。
1 相同的问题源
有的学者做过其他刊物与《新华文摘》的比较研究,如《读者》与《新华文摘》的比较研究[1],也有学者单独对《新华文摘》进行研究,比如对“《新华文摘》(1979年~2009年)全文转载的图书馆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2],但没有学者做一个专栏与另一种期刊的比较研究。为什么笔者拿一个刊物中的专栏与另一种刊物来做比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提问,也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有共同的问题源”是两者可做比较的根本原因:①读书问题研究贯穿于人类文明史,是人类学术研究永恒的主题。人生无法回避读书活动,比如如何写好读后感和日记是我们的入门课。读书问题的研究“进入门槛”较低,其参与度较大,人人皆有感知。“书”既是图书馆人又是传媒人的“衣食”。两者不可能回避读书问题的研究。“书是图书馆学永远的DNA。图书馆学刊物思想的主角与场景永远是读书。”[3]传媒行业也非常关注人类读书活动,如备受知识分子关注的CCTV栏目《读书时间》、《读书》等就是如此。②读书问题研究具有可持续性、动态性、丰富性,是人类永远要探索下去的“慢问题”,如名著产生的学理问题、基本阅读书目问题、读后感、书史研究等。它们没有标准答案与定论,人类可以找到更美、更有诗情画意、更有道德情操的人文答案。这些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是机器思维成果无法取代的。③读书问题是古典问题、现实问题,又是后现代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矛盾和问题也不少。时代在发展,新的读书问题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困惑、苦思、求索,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有些问题绝非纯粹书斋式的问题,而是有现实针对性与理论生机的问题,举例如下:如何看待SCI问题、“SCI核心期刊”政策推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等问题;如何看待读书活动出现的后现代问题,如郭英剑在文章《<虎妈战歌>:中西教育的正面冲突》所提到的问题;网络阅读存在诸如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功利性阅读、文化不确定性等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与探讨等问题。这些问题既为前者关注也为后者关注;诺奖作品的出版与阅读热等新问题。
2 不同的发展路径
两者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留下不同的痕迹,同样的问题源,但有不同的境遇、命运和经历,有不同的内在资源建设,不同的实践意义。
问题源是客观的,但问题意识是主观的。两者的编撰思想具有主观性。这是两者有区别的主观原因。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人有研究的强烈冲动,有人成为疲弱无力的失语者。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阅读状况调查研究就有不同的调查方法与结论。两者围绕读书问题研究而表现的旨趣、观点、思想、路径不同,两者转载或转摘的文章很不相同,这样就形成了许多有趣的,有意义的差异。差异是两者同时存在的意义。正因如此,持诸如“希望《文摘》聘请一些图书馆学界的权威来选择与审定应该摘引哪些图书馆学论文”[4]此类观点就没有学理支持了。
两者的比较有理论意义。两者在理论资源内在建设等方面发展的状况不同,从而表现在方法论的突破、研究对象的确立、学科范围的划定、书写内容的取舍、脉络系统、观念框架、问题意识、价值取向、话语系统、书写规范等几个方面不同。两者一起丰富、发展与传播了读书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两者可以相互借鉴。正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见解不一。”这是比较两者的积极意义。
两者的比较有实践意义。正所谓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树。两者对当代读书活动的实践批判性与实践指导意义不同。读书问题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文章,重要的是为了改造读书活动的现状,指出人类读书活动的正确方向。尤其网络时代,人类读书活动的研究需要各种理论指导。我们既需要像《中国图书馆学报》中读书问题的研究文章,又需要《中华读书报》中的读书问题研究文章。这是比较两者的最重要目的。后者对图书馆事业的业务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作为一名图书采购人员我们可以经常看看前者中的好文章,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可以经常看看后者中的好文章。
3 精神格调不同
前者是大众的,后者是精英的;前者重实际,后者重引进。读懂前者并不难,文中谈的问题大多为人文知识分子切身体会,读后,清新朴实文风扑面而来。一些高深的理论并非言之无物,并非空洞乏味,也不味同嚼蜡,比如《传世之书的十大特点》(《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11年18期)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朴实无华。学术性极强的文章《译者的本分》,艺术性极强的话语“译事同样通于造化,而造化万千,通者活,不通者死”(《新华文摘》全文转摘2003年12期),读者读后定有收获。前者的精神格调与《新华文摘》一致,目的是弘扬人文精神,着重提升人们读书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怀与精神理想等思想境界。比如,我们阅读何明显《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新华文摘》全文转摘2011年18期)后,既可普及知识又得到精神享受。同样的读书问题,前者多用感悟与思想的关怀来表达,文章多为优美的散文,后者多用统计、理论来表达,多为学术论文形式。比如同样是书评,前者多谈读后的思想喜悦、悲情,后者多谈该书如何发展理论与如何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前者重思想,后者重技术。人类读书活动既是科学事业又是人文事业。但每种期刊都有侧重点。就读书问题研究而言,前者走的是大众化发展之路。“我们全部的尊严在于思想”[5],这句话用来概括它的贡献很恰当。从选题重点可以看出,前者有“读书方法与感悟研究”、“阅读状况的实证与调查”、“解读书史”、“名著与经典的编撰过程及其流变史”、“名著与经典的学理研究”、“名著与经典的传播研究”、“图书、报纸与期刊发展研究”、“编撰技术与对策研究资料”、“图书馆概论”、“图书馆技术”[6]。它的主旨在于发展文化事业,表现出从容与淡定的学术风格,起着“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学术作用。学界以科学化为荣的今天,它仍然坚持转摘读书感悟、书史研究、古籍整理、目录学、经典问题研究、书史类文章。这些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修课,也是一生关心的平凡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者都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感应、顿悟是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途径。亚里士多德的“惊讶”,马克斯韦伯的名言“热情是‘灵魂’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的“热情”,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库恩的“猜想”等,实质上就是哲人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意识离不开经典的阅读。后者走的是精英化发展道路,主旨在发展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其中论文是非要引经据典不可的,有些甚至全靠各路引文支撑着,从中可以见学问。比如,全文充斥着数字图书馆、引文分析、数字挖掘、云计算、web2.0等专业概念。再比如,2012年11期的专栏《科技情报工作》、《文献计量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公共图书馆》、《信息网路》、《数字化》、《信息资源管理》,两者的差异实质上是人文与科学的差异。
前者重内容,后者重形式。前者的读者群是文化人,后者的读者群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士。文化人历来具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对形式要求不强,看重文章内容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4 学理产生机制不同
两者学理产生的机制不同,两者的研究立场不同,其一,领域研究立场,其二,学科研究立场。
前者兼收并取,综合性,是研究读书问题的“思想库”、“信息库”、“小百科全书”。笔者的切身体会,通过30多年的阅读,学到了许多诸如版本、SCI、善本、题录、数字版权、基础阅读书目等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也了解了诸如“经典的重版与名著的重译”、“《水浒传》的三个版本”、“畅销小说”、“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情况”、“传世之书的十大特点”等问题。读者不仅能在专栏中找到所需要的专业信息,还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动态和发展方向。后者强调专业性,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前者有强烈的领域研究立场,具有强烈的学派意识,只要是读书问题研究皆可选取。学派意识主要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通过研究者个体的创造性活动,影响、改造、构筑学科群体或整体。[7]正因如此,双方的取材不同。前者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力,它还在不断地汲取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华。《新华文摘》编辑部每月订阅大约1500种报纸杂志,此外还有一些编辑部邮寄赠送的近500种报纸杂志。它没有学科立场的限制,有相对自由。它可以从大量的优秀的人文报纸杂志选取文章,比如从《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学习时报》、《秘书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制日报》、《读书》等报纸杂志中选取。也正因为《山东图书馆学刊》有读书问题研究的专栏《东方阅读书院》,它受到《读书与传媒》的青睐,如陈亮先生发表在《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4期上的文章《“浏览式阅读法”与“精读式的阅读法”》被《读书与传媒》全文转摘(《新华文摘》2011年第23期)。后者主要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刊物中选材。
后者有强烈的学科意识。正因如此,它的文章主要转载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在学科日益细化、项目中心主义的学术环境的今天,后者不可避免有强烈的知识规划的诉求。学科意识主要是一种群体或整体意识,它倾向于研究者个体遵从学科群体规范,学科整体引导、支配着研究者个体。学科研究立场者的一般模式为,学科问题提出、文献综述、做出假设、数据来源与处理、模型与方法、计量、发现和结论、政策含义,这八个部分一个都不能少(因此有人称之为“新八股”)。不可否认,学术研究遵循某种范式有助于构建共同的学术平台和统一的话语体系,便于研究者在同一个“屋檐”下探讨问题,比如图书馆学人可以就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学科意识的立足点是建设基本的、公共的学科知识体系,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前者所关注的问题难免跌宕起伏,没有连续性,有时的确难以把握,而后者变现出连续性和集中性,比如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版权、分类法等。
5 社会评价不同
毫无疑问,两者都有学术评价及文献检索功能,学术交流的功能,给人不同的精神享受。
前者的学术影响力远强于后者。它的政治责任感、文风、立意等编撰思想看似无形,却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其可读性、完整性、学术性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巨大的。它激励钱学森、钱三强等社会精英与普通人的故事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它的肯定与奖励的故事很多。学术界对被前者全文转摘文章的作者给予的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远大于被后者全文转载文章作者所获得的奖励。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与期刊界皆以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为荣。专栏的社会反响也是巨大的,后者主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内部的反响,对推动学科化建设起着一定的作用。
通过比较,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们疏远的往往是那些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读书问题研究的“理论”,也就是无用的、无帮助的“理论”,而不在意是转摘在前者上还是转载在后者上。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启迪人,引导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读书问题研究理论成果,不仅不会受到冷淡和疏远,相反受到追捧和崇尚。所谓的范式、技术、方法、工具都是“仆人”,都是为了读书问题研究的需要,不能反客为主。前者与后者将长期存在,并一起为我国读书事业做出贡献。
[1] 许丽.文摘期刊的两个杰出代表[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1(9).
[2][4]王萃.对《新闻文摘》(1979年-2009年)全文转载的图书馆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5).
[3] 陈业奎.书:图书馆学永远的DNA[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2).
[5] (法)帊斯卡尔.思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张瑜.2011年度《新华文摘》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点及启示[J].新世纪图书馆,2012(3).
[7] 陈业奎.学科研究立场与领域研究立场[J].新世纪图书馆,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