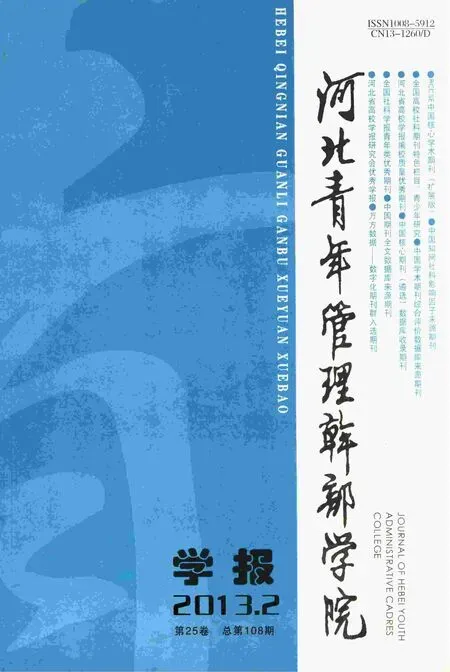试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论探索
2013-04-11王琴
王 琴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重庆400712)
“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一直是近现代哲学家探索与追寻的话题。黑格尔从“绝对自我”,“绝对观念”之中推演出人及整个世界,无中生有推演出来的人无疑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人。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学,把人当作基本核心和立足点,使人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却又把爱贯穿于整个人本主义学说,不得不把人又抛向了天堂。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过程中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伟大观点,指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最初萌芽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哲学从中世纪神学光环中挣脱出来,打破了“哲学沦为神学婢女”的神话。近代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这面大旗,讴歌、弘扬人的主体精神,重新开启了沉寂几个世纪对人的重新审视和评判的大门。不管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还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精神都在理性指导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人是理性的动物”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哲学家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拖着庸人的辫子,在私底下高声呼喊着革命,软弱性导致他们仅在思想中发生着激烈的革命。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接受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曾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拥护者的他,直接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笔者认为,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绝对精神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形式,在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下,理性的人随处可见。在他的学说中,他把人的本质精神化了,使自我意识成了人的本质,通过自我意识进而发展到最高阶段“绝对精神”,回复到自身。对他来说,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更不是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而倒是另一种社会抽象,即主体已不是人,而是神,是思辨式的绝对精神的神。虽然黑格尔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他注重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黑格尔笔下的人是理性的人,是没有血肉的空灵人。
马克思在黑格尔保守体系影响下,逐渐确立起他对人的本质的初步认识。他曾以“精神自由”为武器,撰文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道“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1]90,人是作为精神存在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即无视人的精神自由的本质,反而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这里,马克思是站在肯定精神的自由本质来论证的,将精神自由看作人的现实本性,“以头朝地”的方法去理解人的主体性,将其归纳为理性,这与黑格尔从自我意识的角度理解人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发展了。”[1]16这种抽象发展的结果,只能将革命的热情深深地暗藏在内心深处,在现实中只能是“南柯一梦”。理性是世界的本源,是人活动的根据,这是青年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思想依据。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初步探索
在莱茵报当主编期间,马克思对现实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即使行政当局具有最善良的意图,它还是不可能摧毁这些本质的关系的势力。”[1]229这促使马克思回到现实物质利益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首先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开始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以客观唯心主义方式把自然和人变成抽象精神,使人脱离了现实世界,将抽象精神变成人的最终归指。“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了人的异化,——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一切要素。”[2]119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纯精神、纯思维运动中蕴涵着人的普遍本质和运动的普遍规律性,但黑格尔把这些对象(国家、财富)视为精神异化产物,于是绝对精神作为主体,就有资格和能力通过自己的继续活动,扬弃这些异化了的对象,占有和改造他们,使之复归于绝对精神主体本身。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将主体地位的人消解在绝对精神之中,又抓住了黑格尔的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辩证法。它是人把自己的力量和本质对象化、外化,即人创造出自己的外部对象世界。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人的异化学说,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4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自觉的能动性的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如果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被迫的劳动,异化劳动就是违反人性的。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必须批判以前的唯物主义才能达到自己学说的形成,这主要是批判费尔巴哈来实现的。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绝对观念和上帝造人的宗教观,他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关于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将人从天堂拉回了人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他是为证明“事物和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和某人的本质”[1]47。这就表明他们承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论述,终结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中推演出的空灵人。“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3]226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经过了从康德直到黑格尔的长足发展之后再回到唯物主义的,他的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人本主义,认为不能再把精神自我意识当作主体,而必须回到现实的人、感性的人,而人作为主体是不能脱离自然基础来谈论的。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有这样的特点,以人为中心而非单纯强调自然,并企图抓住现实的人研究他如何从自我异化(虽然他看到的还只是宗教意义上的异化)中得到解放,才受到马克思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在对人的本质逐步深入理解过程中,马克思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大门的道路。他同时指出,费尔巴哈要求回到感性的主体和对象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除了唯心论的消极方面,也有深刻意义,他没有注意到人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践)才是使人成为真实的存在,使自然界也发生了变化。费尔巴哈对人和自然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感性直观的水平上,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吃喝、情欲和人的理性、意志、感情等。这就决定了他的人本学也就只能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范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就成为只是那些关于爱的空谈而失去批判意义了。
笔者认为,不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都极力消解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体意识,一个是在绝对精神统摄下的没有血肉的人,一个是标榜“人同时既是我,又是你——以他的类、他的本质为对象”[4]468,并试图用爱来消除个体差异性。所以恩格斯认为,在宗教领域里费尔巴哈眼中还有男、女之分,但一旦涉及道德伦理领域,个体差异性就完全消失了。他们对人的理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现实一切作出的解释,并企图淡化阶级意识和扑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用纯粹抽象的精神或爱使人安于现状。“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3]237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发展了辩证法,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议论的批判。针对黑格尔只讲“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不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针对以往哲学家如费尔巴哈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马克思强调要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他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9这表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他的人学使命和作用是改变世界。
人具有内在的自我创造,自我否定发展的特性,这种特性不单纯的是在思维活动中产生,也非孤立、静止地自我完善,发展。而是与外界、社会不断交换信息,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而显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和桥梁,它注重的是人如何使世界发生改变而达到自我的实现与发展。这种实践本质上就是一种建构活动[5]。这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57所以人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7。
从理性的人到异化的人、从将人立足于自身最后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本质认识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着马克思从关心人应是什么出发批判现存的一切,把未来社会建立在对现有旧的政治制度和现实人的本质异化剖析基础之上。马克思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把人静止在某个点或某个层面上,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深化对人的理解,把他所秉持的凡是现实的都必将灭亡的宗旨贯彻到底,将对人的本质理解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认为,它并没有将人的本质的理解划上句号,反而提醒我们时刻反思现有经济、政治制度对人的本质及价值的体现程度。马克思提出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原则,达到如此境地只有在批判现有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完成。立足于我国现实情况,是否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全面消除了异化,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社会主义从物质和制度上保证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和才干的发挥,但这一过程又导致了异化问题的再现。比如政治官僚者由于缺乏民主监督将政治视为攫取权力的手段,保证自己享有特殊的物质特权,人自己创造了政治机构,却失去了对机构的监督权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话,政治参与不再是积极的活动,有人大声疾呼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一形式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还处在虚拟之中。另一方面,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逐步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反思过去,在计划经济中,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的中央计划决定了剩余价值和利润与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计划经济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了。随着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和发展,国家职能逐步退出了市场,甚至将指挥棒交给了市场,让“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人正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前进。人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在市场经济规则之下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真正实现了自我的发展与飞跃,当然这只是人的本质体现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韩庆翔.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J].江海学刊,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