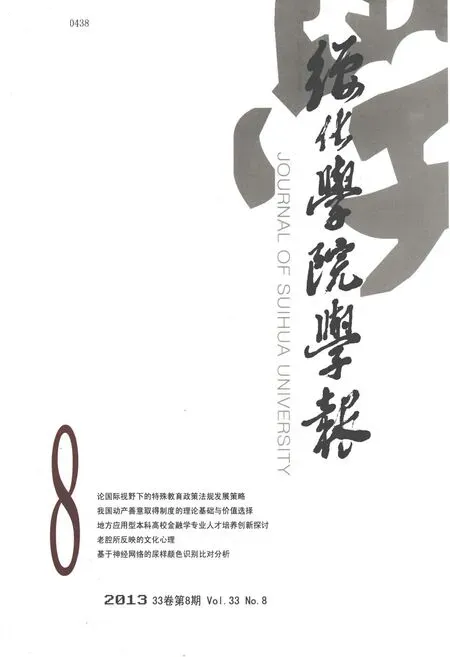中西口译研究历史特征之比较
2013-04-11杨毅隆
杨毅隆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口译在21世纪的经济、文化发展中作为一种重要沟通途径,扮演着连接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作用,并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互促共进。口译员也因此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之而来的口译研究和教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口译的多学科性质显现,且同语用学、心理学、翻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广泛结合。
在翻译研究历史上口译研究所占比例较小,其中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口译工作言语的媒介是转瞬即逝的语音声波,于是可供参考的资料甚少,乃至连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也都要依照史料记述获悉。尽管口译的研究并不丰富,但它却拥有悠久的历史。
口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初期。原始部落群体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较为孤立的区域之内,各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活动互不往来。由于时间的演进,此种不开放的生活方式很大层度上阻隔了人们的文化和经济活动,这些民族因此有了超越边界进行外部发展的愿望,并与不同语言民族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障碍显然成为最大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口译作为一种不同语言间沟通的媒体,得以让不同部落与其他民族展开文化与经济交流。故而,不同语言间的口译由此诞生,并成为了不同文化和民族间的交流途径。
数千年来西方各国都有专门从事口译工作的人员,但译员大多都以其他职业为生,口译仅是他们的临时工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口译才开始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职业登上国际舞台。于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第一次瓦解了在国际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法语,和会的口译工作由法、英双语共同完成。从此,口译的职业性得到了认可,口译基本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开始受到重视,职业口译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1](P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几乎同步的口译方法首次出现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同声传译”作为一种全新的口译形式从此诞生,让人们对这种高级口译方式刮目看待。伴随联合国成立、诸多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的兴起,国际交流日益频繁。20世纪50年代,各类国际组织纷纷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对口头翻译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强烈,由此催生了许多口、笔译培训课程在欧洲涌现,对口译的研究亦达到空前高度。业内对译者越来越器重,联合国还增加了翻译部门,日内瓦组建了“国际会议译员协会”。在同一时期,口译成为一门学科,高等院校也开展了对其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各种跨文化的机构和组织都重视高级口译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级国际会议译员的培养,并给予较高的声望和地位。
一、西方口译研究
历经50多年发展的西方口译研究,理论体系已趋于成熟,表现出以会议口译研究为主、发展阶段特征分明的两大特点。
会议口译研究是西方最早开展的口译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深度最大、最为系统,其研究成果相对于其他类别的口译也是最多的。显而易见,会议口译指的是在多语言环境的国际会议中利用译员作为媒介,使与会方能成功地顺利交流从而避开不同语言之间障碍的一种沟通手段。会议口译涵盖各类国际会议、技术讨论、官方互访等。当前同声传译已成为国际会议的普遍口译形式,因此部分作者将会议口译误认为同声传译。虽然基于时效性的考量,国际会议都以同声传译为主,但交替传译在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口译研究的初始阶段。此一阶段以译者论述其翻译经验及对翻译活动和工作环境的分析和心得,所讨论的题目囊盖译者的知识、语言、困难、和客户关系等因子对目的语输出的影响等。此时的口译研究还处在经验描述阶段,然而Herbert和Rozen所著的两本手册被译界奉为经典,许多人至今仍传扬书中部分交传笔记的原则及方法。
20世纪60-70年代初为口译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心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运用心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探究口译的认知问题,对口译过程提出了一些假想,并分析了源语、噪音、发言速度、EVS等变量对口译的影响及译员常采用的对策等。[2]然而有些学者却并不认可该阶段的研究,认为对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口译过程并无效用。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口译从业人员研究阶段。主要研究对象为口译从业人员(其中多数为兼职的教师),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创立的释意派理论是此阶段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它强调口译不是字词和语言结构的对译,其活动中心应围绕意义来展开。口译界的主导性理论曾一度被释意论所占据,至今在口译培训中仍有强大效用。但是此一时期各学派交往甚少,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几乎无人注意到实证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以1986年在意大利的Trieste大学举办的一次重要的口译会议为转折点,口译研究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3]自此各学派之间开始广泛深入地交流,大大强调实证研究地位,口译界结束了多年的封闭孤立状态,这就带来了口译的科学和跨学科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口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之上愈来愈活跃,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体育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优秀口译人才的缺乏更加突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际地位随之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起飞,在此背景下,其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强。20世纪90年代,许多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陷于衰退,而中国经济仍犹如一列动力十足的列车,以更加快速的步伐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在众多海外投资者和游客的目的地中,中国格外抢眼,其对外开放的广度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各行各业正需要大量各类专兼职口译人员,高级口译员尤其成了紧缺人才。中国对外交往的这座大桥今日急需一大批译员来构筑,今天的译界也迫切需要对口译理论、方法进行探索。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与其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就带来了对口译市场的巨大需求,口译从业人数不断攀升,对译员素质的要求亦今非昔比。在此形势下,口译研究与教学中的机遇和挑战随之而来。然而由于口译行业具有其自身特殊性及国内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相对落后,在口译的培训、教学方面还难以跟进时代的步伐,合格的口译员(特别是高级译员)的短缺冲突日显激烈。除此而外,跟西方的口译研究相比,中国的研究历史较短且尚未形成体系。
在翻译研究当中,中国的口译研究长期以来都未被重视。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主要翻译和外语刊物有零星几篇关于口译的文章发表,中国学者对口译研究的初步认识和探索基本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口译的特点及技巧进行论述,属于谈论经验和问题陈诉阶段。[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口译研究发展迅速,开始呈现开放型跨学科研究的态势,但是其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5]当今中国译界较之以往更急需对口译中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深层次探讨,具有中国特殊的口译理论亟待跟进创新以满足新时期的需要。
参照翻译理论体系研究的框架,结合口译理论研究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口译研究一般划分为“一般口译研究”、“特殊口译研究”和“应用口译研究”三大分支。一般口译研究指对翻译的性质、标准、过程等基本概念的研究;特殊口译研究是对两个特定语言的比对和翻译、对二者文化的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得到指导性的口译理论;应用口译研究则是对口译技巧、教学与培训的研究。
中国的口译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全方位、跨学科、引进吸收、多视角等特点。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改变了对口译过程的研究
口译过程的研究由之前的描述渐渐转变为深入译者思维层面的研究。然而对口译工作的完整过程作出科学的探讨由于其瞬时性会难以实现。早期的口译过程研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李越然的“听懂—记住—构思—表达”、齐宗华的“听清—理解—表达”、周丕炎的“解码—换码—编码”等。[6](P20)由于口译研究的深化,研究人员慢慢意识到口译并非仅是语言的转变,更是对源语言意义的理解。鲍刚借助神经学新突破,对口译者在工作中的脑活动作出了描述性解释。同一时期,口译过程研究也引进了其他的新视角。刘勒的研究重视口译的认知过程,纪康丽的研究侧重口译过程信息处理模式,蔡小红的研究强调口译员思维规律,另有语用学角度的诸多研究,如王滔归纳的语用失误因素、陈湘蓉的交际因素、廖开洪谈到的“合作原则”因素、芮敏提及的关联因素、周红民的语用能力因素等。
(二)口译评估标准的变化
由不确切的经验总结和同类比较上升为理论性的定量分析,此种口译评估更加科学、实际。从李越然的“准、快、顺”标准以后,口译标准体系不断变迁、推层出新,如李芳琴的“信、达、切”,梅德明的“准确、流利”,王学文的“信、达、速”,张平的“顺、达、信”等。但是,这些评估体系都来自理论,并无实验支持,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可操作性。通过借鉴Bachman的测评体系,陈菁作出了一个详细的量化测试表,从而使口译质量评估的标准更具科学性且更易于操作。此外,方凡泉和蔡小红重新定义了口译性质与口译评估,并根据构成口译任务的众多因素的差异,提出口译评估与口译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假定。刘和平从科技口译与一般会议口译的不同中探讨了科技口译质量评估问题。[7](P206)除此而外,冯之林还认为口译质量的核心参数是语义准确性。
(三)逐渐重视口译能力研究
国内的口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重点是译员的经验谈,因而口译工作被大部分人误作一种技巧。近年来,口译界逐渐意识到,口译“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要求译员掌握专门的技能”。[8](P211)陈菁认为,口译的能力包含译者的技巧、知识与心理能力。梅德明提出,口译工作包括二语转换、交际心理和跨文化沟通,翻译能力为言语解码、信息重组、记忆力、语言能力以和背景知识等。
(四)口译教学、培训发展迅速
培训材料的撰写呈现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新特点。仲伟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研发出完整的培训体系,将口译技能区别为“连续传译技能”和“同声传译技能”,并分别对二者原理、特点、操作过程进行了研究。吴冰编写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口译教材《汉译英口译教程》以及厦门大学外语系撰写的《新编英语口译教程》、梅德明的《中级口译教程》和《高级口译教程》、冯建忠主编的《实用英语口译教程》、王文学的《新编经贸口译教程》等都是经典教程。
(五)中国口译理论性研究基本继承了西方口译理论成果,其中塞莱丝科维奇创立的释意理论与吉尔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是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理论。中国口译研究者在借鉴这二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引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其进行了实证与扩充。
三、结论
今天,口译研究呈现出广泛融合、多视角、多手段齐头并进的崭新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口译学科的复杂性和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一方面口译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口译本身,它还涉及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其他学科知识;另一方面,历次口译新成果都建立在其他学科取得的新成果基础之上,因此口译研究的新进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新突破。
虽中西口译研究在侧重点、研究深度、科研水平上仍有较大差距,然科学无国界,亦无种族、性别之差。中国的译学研究,尤其口译研究,应首先大量借鉴西方理论成果、紧跟时代步伐,同时结合本土实际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应坚持走“引进来,走出去”、“齐头并进”的路子,方能在世界译学研究舞台上大展风采。
[1]张维为.英汉同声传译[M].上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Gerver,David.Empirical Studies of SimultaneousInterpretation:A Review and Model [A].Brislin R.Translation: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C].New York:Gardner Press,1976:165-207.
[3]Gran,L.Dodds.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Aspects of Teaching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C].Udine:Campanotto Editore,1989:112.
[4]胡庚申.从发表文章的状况谈加强我国的口译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1989:43-45.
[5]刘和平.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现状及展望[J].中国翻译,2001(2):17-18.
[6]龚龙生.顺应论与口译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7]蔡小红.口译研究新探[M].香港:开益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