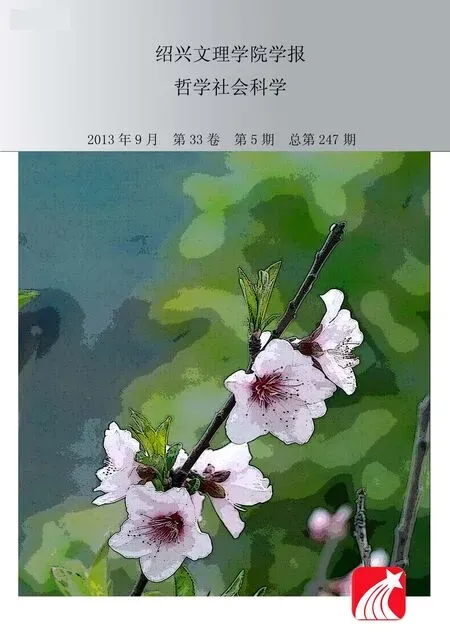残酷的战争与凄美的情爱
——桑子《德克萨斯》创作访谈
2013-04-11吕晓英
吕晓英 桑 子
(1.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2.绍兴市港航管理局,浙江 绍兴312000)
受访者:桑子,越战题材长篇小说《德克萨斯》作者,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绍兴市作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交通作协常务理事。曾出版长篇小说《爱来成就》,长诗《鬣狗公主娜比》和长诗集《永和九年——诗说魏晋》等。
采访者:吕晓英,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吕晓英(以下简称吕):我的审美观念,或者说欣赏趣味,可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我以为,小说、电影的中心应该是故事,音乐、歌曲的中心是旋律,我喜欢有故事性和旋律性的作品。而当今的许多作品却似乎背离了这种传统特征,小说、电影越来越不会讲述一个故事,音乐、歌曲也越来越不会演绎一段旋律。可能就因此,我和许多小说的潜在读者一样,逐渐放弃小说,喜欢看电视剧胜过看电影,因为在电视剧这种文化形态中,故事性被表现得最为充分。
但是,在读完你的《德克萨斯》后,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你在以美国越战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德克萨斯》中,在演绎金融博弈、越战之殇、政治阴谋的同时,对缜密的经济、军事、政治元素进行了深刻地解构,有着极生动的故事情节。我特别欣赏的是,你对爱情在战争中如何饱受摧残,而战争又给予了爱情怎样的纯粹高尚的叙述,细腻委婉,亦真亦幻,将强烈的情感融汇于迷离的幻象中,有令人着迷震撼的艺术享受。
桑子(以下简称桑):创作《德克萨斯》,我内心是胆怯的,出于对题材得何等的尊重,唯恐自己力不从心。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感兴趣于一个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文化河床——向蛮荒宣战的筚路蓝缕的历程。美国认为这是“上帝的选民”的一项使命,而如此的“美国式自我”则成为一个先知预言的普世蓝图的化身。
我在小说中加入了卡莱尔在德克萨斯州考古并挑战了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关于人类大陆迁移是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大陆桥到达北美洲的学说,这是有寓意的。他们对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不感兴趣,既乐观又自信的他们只想每一代、每一日都重新起步向前走。以这样的思想背景去观照美国的传统,必须脱开中国人“慎终追远”“毋数典忘祖”的历史之思想习惯,才能把握美国式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一切偶然与必然。
吕:你一定读过许多与美国越南战争相关的书籍,可以说它们是你创作《德克萨斯》的源泉,那段历史给了你不竭的思考,在你文学性和史学性皆备卓尔不群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这段历史的“当代性”的思考。
桑:1964年1月威斯特摩兰将军初到越南,乘坐的民航机还未降落,他就对这个热带国家的美丽景色着了迷,当他驱车进入西贡,南越首都混合着法国人留下的那种巴黎气氛更使他陶醉。威斯特摩兰,这位生性好斗的四星上将,30岁就荣升上校,成为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前途不可限量,他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关键时刻不手软。
然而,越南战争却成了他一生的分水岭。当他看到“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着陆、起飞,像山一般的巨大运输机卸下房子大小的重型武器”。他自信地想:这场战争怎么可能打不赢呢?后来才顿悟:“这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疾病,是一场瘟疫。”美国在越战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应验了越南的一句老话:“铁砧的寿命比锤子长。”美国著名作家桑塔格在越南访问轰炸密集的乡村时,农民们有一个很普遍的做法是,每天去稻田时都扛上棺材,如果有人死去,他们就马上把他掩埋,其他人继续劳作,这样的国家,美国人要使之屈服,可能吗?[1]这是东西方历史文化差异的渊薮。
我总在思考,如何觅得一柄穿地长锤凿它个万丈深渊,才能将12年血战,58000名战死美军,100万越军忠骨以及所有失去至爱亲朋的悲恸埋进深谷。即使如此,也不等于就能埋掉那些长期萦绕几代人心灵的越战幽灵。
吕:细读《德克萨斯》,在享受你百转千回的故事情节和汪洋恣肆的文风之余,在深陷你无边思想的原野之中,在经历你对历史的杰出演绎和雄辩的哲理洗礼之后,我相信,一切答案都会尽在其中的。
桑:战争一直是文明史的非常态,除了战争本身外,还穿插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人性关系,让我着迷的永远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产生结果的原因,也就是战争背后美国人的“忧隐”。
忧隐之一:越南人很顽强,他们从来矢志不渝。
拉塞尔议员在约翰逊总统上台两周后便去劝说“撤出越南”。并且搬出曾经他们俩在1954年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要向在越南作战的法军提供军事援助,他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们进入那儿的话,50年之内别想出来。”[2]
战争伊始,武元甲将军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敌人不得不旷日持久地熬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敌人并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政治手段”,而被充分激起的意气风发的约翰逊总统是这样看待这场战争的——“现在这场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了,而美国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只是在朝鲜和中国打了个平手。”[2]
随着战争的深入持久,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北越敌人很了不起,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从来矢志不移,他们跟法国人打了几十年的仗,不在乎再跟我们干上几十年。”
不久后的美国军事报告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对手的:“他们师从中国军人,纪律严明,英勇无比,视死如归,顽强得几近疯狂,进攻时,北越军士兵像潮水一样涌来,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军没有见过这种情景……”[2]
忧隐之二:美军空中突击师炸出了满目疮痍,也炸毁了自己的信仰。
老式B-29、B-59型轰炸机夜以继日地将多达百万吨的炸弹扔在北越的公路上,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发现越南人又在上面通过了……尽管美国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实际上从未有效切断过越南的全部交通线,航空兵皮特·希拉里把轰炸效果描述为“将垃圾从路北边挪到了路南边。第二天,我们再把这点垃圾从路南边挪到路北边”。
美国兵通常用一两个小时,就把一座城市炸回到“石器时代”,到处都是房屋的地基,甚至没有一根竖立的柱子。
这些才华出众的空军,有时候也会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忧隐之三:眼前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
肯尼迪总统在战争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宣誓:“我们会不计任何代价,不怕任何负担,也不畏任何艰难地为捍卫自由而战。”大批的新兵,搭乘着二战的老旧运输舰,驶到这个遥远的国度来,他们年轻、自信、热爱祖国,他们大多是两年期的义务役士兵,能够这样为祖国效劳,他们内心十分骄傲,只要上头一声令下,他们就像父辈在二战中、兄长们在朝鲜战场上一样英勇。而不久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有可能静静地躺在家乡的墓地里。而那些脱下军装回到魂牵梦萦故乡的将士们,则又成为一群茫然无依、备受指责的陌生人,因为当他们在敌人的交叉火力网下匍匐前进,在酷热的丛林里奋战拼命时,国内激烈的反战人士已经带领民众像憎恨战争般开始憎恨起他们来了,国内的同胞还会怀疑他们是否还有健全人的心智,以适应正常人的生活。这些从战场上活着回去的幸运者,除了因疾病、伤痛而失眠失神外,只留下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大箱装着绶带和勋章的可资追忆与感伤的东西——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死者看到过战争的终结。是的,活着的人看到的只是被岁月遗忘的创伤,以及被轻描淡写的历史。痛苦将退回到一垛矮墙和一块小尖碑的后面,还有一小部分至亲的灵魂与生命里。
至此,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决策已不是一种过于自信的武断行为,而是为了挽回错误的越南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而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豪赌中的孤注一掷。
越南正像一个巨大的沼泽地,给予了世界一流军事强国深陷其中、欲拔不能的痛楚。
所有眼前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受苦,不是牺牲,而是白白受苦,白白牺牲。
吕:这三点忧隐,其实就是战争残酷性的集中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作品就是哲学意义的形象化,你将对战争刻骨铭心的独特感受艺术地描述了出来。
从你对战争的哲学思考里,我感觉到你作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心中有一项更严肃的使命——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有自己独到的艺术和审美发现,并凭借自己深刻的思考让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复活。的确,一个民族延亘了数十个世纪的道德感和价值观,不应该成为过时的、几近枯萎的陈旧纸页。遗憾的是,在对历史喧嚣的批判和歪曲颠倒的孟浪解析和刻意误读中,年轻一代应有的正确的历史观,被胡乱地抛撒到虚拟的网络和低俗的荧屏之中。唯其如此,更显《德克萨斯》的价值。
桑:对于这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来说,所有文字都是轻薄的。《德克萨斯》人物众多,事件众多,我进行了全视角的表述,力求赋予它们更深的含义,我希望人人都按自己的理解去欣赏它,只有心中所思,才是心之永恒。《德克萨斯》不是一个框框,让读者囿于其中的,它只是一双翅膀,可以带您进入一个全视角的19世纪60年代,让您看到您想看到的一切。
如果仅仅是着力描写越战的惨烈和残酷,那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累牍的越战题材小说中徒增一本可有可无的作品罢了。是的,在倾颓的焦土之上,世界现出了它的创伤与皱纹,它一下子老了,并且关心起道德,追问着为什么不能在时间之河中逆行,把我爱过的、非常想过的一种生活还给这个世界。
吕:当然,你的《德克萨斯》的价值除了展现战争跳动的旋律和令人窒息的危险,在表述战争的惯性恐怖感受和作战的超现实主义方面成功外,启示人们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世界的,给读者更大阐释空间的是你对处在战争这一非常态下的情爱的描写,对非常态的情爱的这种人文关怀同样令我痴迷。特别想听听你自己是如何诠释小说中苏珊与克洛特·盖博之间的情爱的。
桑:这世上,热爱与忠诚就是朗其诺斯插入胸膛的矛伤。
最初,不知道该如何去承认苏珊娜与克洛特·盖博之间的情爱,小说中人物内心道德伦理的拷量,直接折磨着我,在写完他们激情爱欲之后,折磨一度达到了顶峰,几欲有删节复始的冲动。
只得慰藉于苏珊娜与浮西努相同的身世,神似的气质,假借战争的苦难造成人物情感的偏执走向,并且借弗希里的口:“人在最无助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是,这像嗜酒一样。”
苏珊娜这颗在非常态下活过来的灵魂,在战场上表现了卓然的气概和非凡的英勇,这样一路走来,直到她为克洛特·盖博殉情。爱是真实之发生,而非伦理之规则。
爱如此深刻地伴着主人公挨过战火洗礼的岁月,给生命贯注了神性的高贵,让理想主义脱胎换骨。并且相信,人毕竟是人,既非不死,也非神灵。羞涩与虔诚交织的又怕又爱就这样高于伦理的绝对命令,迎候了受难牺牲者灵魂的复活。
到后来,我坚定地认为,应该无悔让苏珊娜与克洛特·盖博如此深刻地爱一场。
克洛特·盖博牺牲以后,苏珊娜把手术刀深深地切入了自己手腕的肌肤。有风经过,有风作证,也许是树叶的簌簌?也许是泉水轻柔的淙淙?夜的一角已经渗透了树林和天空,任何恳求般的忠告,再也约束不住她对盖博汹涌澎湃的爱恋与渴慕:
“你终于是我全部的世界了。”[3]
克洛特·盖博死后的时光是多么虚妄,只给苏珊娜留下了一个深切的渴望,渴望那神圣的夜,那永恒、真实、融合一切的夜。于是,她选择为盖博殉情。她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再也不允许尘世的干扰来触犯她。现在,死亡的二重奏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说不出的期待中,甜蜜而永恒的黑夜,无所不包的极乐之土!这是一个动人和宁静的终场,沉浸在没落的黄昏霖雨的回光中,一片离解和熄灭的气息。
但是,苏珊娜并没有死,她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在爱的面前,死丧失了骇人的力量。我认为这样戏剧化的处理可以让悲剧更深入人心。
吕:是的,小说中,你有太多这样的对传统伦理的完美颠覆,那灵魂与意愿协调一致的永恒细语,令人久久沉湎而无法自拔。残酷的战争中,情爱故事仍不可思议地产生了,而且还改变着人的灵魂和命运。
如果说盖博和苏珊娜的爱是爱在神性的死中战胜了自然性的死,那么,浮西努对盖博的爱,便是努力地将一眨眼的幸福变成永恒的情爱,浮西努因为战争,可以让自己对一个男人的爱意轻而易举地无限地扩张,由此产生的艺术魅力使整部作品充满诗意。
桑:在盖博牺牲之后,浮西努曾用很长时间来思考感情的问题。在她这个年纪,正是见解成熟,思力旺盛的时期,并且能够很好地处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准确些说,可以更合理地把自己从种种困惑中解脱出来。只能说即使是若干世纪之后,时间还是这样不紧不慢,天气仍是诡谲神秘,一定仍会有人像自己,像是轮回转世一样,仿佛自己又复生了一般。对于为盖博殉情的苏珊娜,浮西努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把她的遗物与盖博合葬在德克萨斯。
小说中,有一段浮西对克洛特·盖博说的话:
在很长时间里,我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您不会把自己既给了我,又给了别人。您是我的一切,而别人只是从您生命边上轻轻擦过去的路人,在多年漫长的岁月中,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可后来,我认识到这想法出了点差错。
第一次在库·汉斯的信中看到了苏珊娜的名字,您永远不会完全知道,我亲爱的,这不经意的一句话从我的生活里带走了什么。
我不埋怨您,我爱的就是这个您,我这样告诫我自己,从前我不了解您,直到我在德浪河谷的运输机上亲见了她,我理解这一切,是因为这场战争。
这世上一定有一种凌驾于爱情之上更真挚、更崇高的爱,在战场上,身处绝望如炼狱般的境况,随时随地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某种感情自发而生,为袍泽而战,为兄弟而死,为彼此哭泣,这个世界一定缩小到只剩下身边的战友和围绕四周的敌人,生命仰赖彼此间的互相扶持而延续,你们分享所有的恐惧、希望、梦想,分享仅有的美好事物。是的,我得承认,当时我看了她一眼,她像我,坚韧而诚实,不懂掩饰。而我,穿着华贵的衣服,在一大堆战需品中,在她偶然的眼神中,我感觉自己倒像个突然闯入你们情感生活的人。您永远不会相信,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3]。
写到这里,当时我忍不住流泪了。
人心有许多情感足以战胜死亡——战场上的仇忾压倒死亡,相爱者的忠诚战胜死亡,自由的荣耀蔑视死亡。一个流放的时代,曾经冲动而不自如,后来有罪而不自觉,现在纵观统筹、高谈阔论。我说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人们在危急时刻的表现。
吕:当年,你出版长篇小说《爱来成就》后,有评论家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保留语言炼金术的魔法,又能够超越这种“情感写作”的成就,更多地破译和直面当代人置身其中的巨大虚无感和存在的困局;在叙述策略上,尽可能地将各种悄然来袭的程式化故事摈弃净尽,让有限的作品对称无限的现实复杂性,并在个体生命的界面之上展示出一种更为悲悯、宽广而高迈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精神[4]。欣慰的是,今天,从你的《德克萨斯》中,读者一定会看到你的这种自我超越。
看你的创作轨迹,万行长诗《鬣狗公主娜比》与50万字的长篇小说《德克萨斯》,两者几乎是并行交叉完成。你曾说,写历史长篇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你很享受不断改变自己的过程,因为这除了考验人的意志力,更时刻检验作者对历史文化艺术的独特视角与卓越见解。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是一个全新的超越,会倍有成就感。
桑:写作是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进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这当中,我拒绝一切陈规俗律的束缚,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写作,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狂热地爱着《德克萨斯》,《德克萨斯》是我在最美的岁月中用灵魂创作的一部作品,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与思想。它将是我一生的珍藏,我只将它献给我最爱的人。我希望我的痴心倾注,能赋予作品一种内在激情及真实性。
吕:王小波曾说:
我觉所有的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在解释自己,另一类在另外开拓世界。前一类作家写的一切,其实是广义的个人经历,如海明威;而后一类作家主要是凭借想象力来营造一些什么,比如卡尔维诺、尤瑟娜尔等人。……我总觉得一个人想要把写作当作终生事业的话,总要走后一条路。当然,一个人在一生里总要写到自己,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只做这一件事是不行的[5]。
你这部50万字《德克萨斯》的出现,令人无限欣喜与惊讶。你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你属于“在另外开拓世界”的作家。你应该又开始“预谋”写更多风格迥异的作品,继续你的颠覆式写作了吧?
桑:目前,以德国普通士兵的视角反映二战的长篇小说《占领区》(暂名)和《诗说吴越春秋 魏晋治乱》的创作正同时铺开。春秋战国、东晋、南宋是绍兴历史上三个最辉煌鼎盛的时期,我们应该为绍兴文化的再次闪耀而去努力。为此,我还计划在明年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马踏惊弦广陵散》,来展现绍兴的历史文化。
吕:看来,你这次是要“穿越”魏晋时代了,期待早日读到你的新作。
参考文献:
[1]姚君伟,姚望.丹尼斯·约翰逊及其越战重写——走近《烟树》[J].译林,2011(3).
[2]丹尼斯·约翰逊.烟树[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桑子.德克萨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4]胡志军.时代的怕与爱——评桑子长篇小说《爱来成就》[EB/OL].2011-06-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2a3ad01018rfp.html.
[5]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