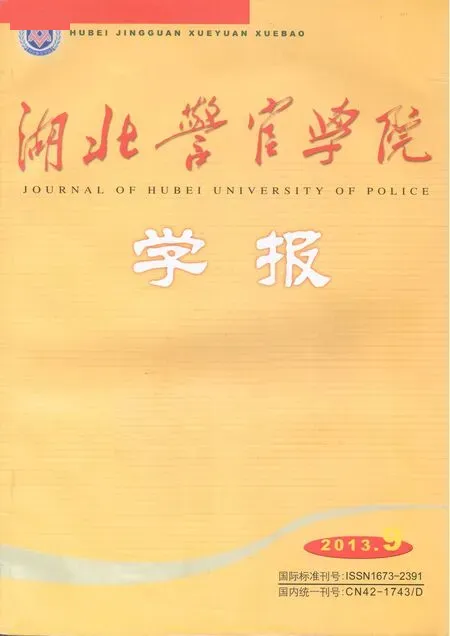墨子“杀盗非杀人”法律观之吾见
2013-04-11梁翠
梁翠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 保定071000)
墨子“杀盗非杀人”法律观之吾见
梁翠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 保定071000)
自古至今对墨子“杀盗,非杀人也”观点的评述非常之多。从法律观的角度审视,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墨家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的驱使源于“贼盗”对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基本主张的严重背离。这一观点与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点并行而不悖,影响了历代“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刑事方针的确立和实施,也是墨家侠义观念的表征。
法制史;墨子;杀盗非杀人;古代法律文化
一、“杀盗,非杀人也”命题研究现状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出自《墨子·小取》篇,其文如下:“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1]大意是说:车是木头做的;但乘车不是乘木。船是木头做的;但入船不是入木。盗贼是人;盗贼多,但不是人多,没有盗贼,并不是没有人。怎么明确这一点儿呢?厌恶盗贼多,并不是厌恶人多;希望没有盗贼,并不是希望没有人。世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虽然盗贼是人,但爱盗贼却不是爱人;不爱盗贼,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并不是杀人。
理解起来,除了最后一句“杀盗,非杀人也”外,其他语句并无歧义,然而仅此命题引发了古今一系列探讨和争辩。首个发难的是战国后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他在《荀子·正名》中批判此命题是“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即批评墨子混淆了名词的使用,模糊了“盗”与“人”的概念。近代,多位学者运用逻辑学和推理学对此命题进行论证,梁启超和胡适力挺此为真命题,郭沫若和方授楚则驳斥其为假命题。20世纪80年代,一批学者继续从逻辑学的不同角度深入细化探讨,大多持认可和维护态度。罗契、郑伟宏认为:“墨家为什么说‘杀盗非杀人’呢?这是因为,墨家把‘杀人’中的‘人’,与‘盗,人也’中的人作了区别。前一个‘人’指盗以外的人,杀盗不犯杀人罪,杀盗以外的人则犯杀人罪。词语是同一个,表达的概念却不相同”。[2]曲海滨也总结道:“我们说墨家的‘盗,人也;杀盗非杀人也’的命题,根本不是诡辩,而是深刻地反映了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是完全符合同一律的”。[3]袁锡福认为:“‘杀盗,非杀人’也叫做‘是而不然’。对于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论式这正是‘名实合’的表现,并非诡辩,也不是片面性错误命题”。[4]陈卓祥也认为墨家“杀盗非杀人”是一个朴素的辩证的命题。[5]
进入新世纪,探讨仍在进行。程恺从“杀盗非杀人”看正名思想。[6]程仲棠从“杀盗非杀人”看逻辑与价值的混淆,认为此命题反映了“逻辑屈从价值,价值牺牲逻辑”的问题。[7]至此,学术界对此命题的关注不再拘囿于逻辑学领域来辩证命题的真伪,而开始从社会学、政治学的领域来探究其价值取向和成因。桑东辉写《“杀盗非杀人”命题的法文化诠释》,聂长建等写《墨子“杀盗非杀人”的法律价值分析》,开始从法学的角度解读,谈及逻辑上的涵摄和法律上涵摄的区别,也涉及到了法律伦理视野下人学的内涵、古今中外语境下的犯罪人概念、民间法视阈下杀盗价值判断等论题的论述,[8]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多有浅尝辄止、意犹未尽之憾。笔者有意借东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古代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墨子“杀盗,非杀人也”法律观的成因和历史影响。探求其成因,即应在墨学的整个体系中来分析和探究墨家对盗贼的看法和认识,当然也离不开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审视。
二、墨子“杀盗非杀人”法律观之成因
墨子提出其命题后,其本人和争辩的各方都认可“盗,人也”,即盗也是人,可既然盗是人,那么为何“杀盗,非杀人也”?从逻辑学角度的探讨已经很多也很深入,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应认识到前者的“人”和后者的“人”在含义上是有所不同的,支持者为不同的含义解释证明其合理性,反对者则反驳支持者的观点,揭示其矛盾和不合理性。对此,笔者是逻辑学的门外汉,孰是孰非,不可置喙。笔者仅欲从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挖掘其对于盗的界定和态度,阐明在墨家的观念中,“盗”和“人”(非盗的普通人)有明显的地位悬殊。
(一)墨家对“盗”的界定
“盗”从词性上来讲,有动词和名词,即行为和行为人。在古代,其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偷,偷窃。《荀子·修身》:“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讲到“诸窃盗”时,疏云:“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第二,敌人,敌寇。即外来的侵略者。如杜甫《登楼》诗:“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第三,对起义人民的诬称。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七:“(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诗书,屡举进士不第,遂位盗。”总而言之,古时,“盗”与“贼”、“匪”和“寇”字常意相通且词相连,指代侵犯他人或他国利益的行为和人。
《墨子》一书中,论述“盗”的语句还是比较多的。《墨子·兼爱上》:“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墨子·非攻上》:“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墨子·节用上》:“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困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墨子·明鬼下》:“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投,天下失义,诸候力正。……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从前两句引文可看到“盗”的最原始含义,即窃取他人财物之意。从后两句引文可以看到“寇乱盗贼”,及盗的引申之义,囊括了大小范围的非正义侵犯行为。
笔者认为,墨子的“盗”的含义应从广义上理解,小偷小摸是“盗”,攻城略地的国家征伐行为也是“盗”。《墨子·鲁问》就明确表明此观点:“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墨子·非攻上》道:“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9]在此,墨子视“窃人桃李”、“取人马牛”、“攻人之国”为罪恶层层加重的行为。
(二)“盗”背离“兼相爱”
研究墨学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思想。所谓“兼爱”就是提倡芸芸众生要平等互爱,即“爱人若爱其身”。这一看法为后来墨家研究者所认可。[10]笔者持相同观点。对于天下大乱,盗贼四起,攻伐不断的时局,墨子在《墨子·兼爱上》分析道:“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11]
墨子指出盗贼只爱自己的家室,不爱别人的家室,所以就盗窃别人家室的财物来维护自己家室的利益。盗贼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仅为自己的利益,都是因为不相爱。可见,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乖忤、篡夺、盗窃、战争等各种行为的最根本原因都是“不相爱”造成的。在此,墨子穿透物质层面而直接进入精神层面,显示了其超凡的洞见能力。《墨子·兼爱上》有云:“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12]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对于盗贼来讲,如果将他人之家视为自己家,谁还偷窃呢?视他人之身如自己的身体,谁还戕害人呢?这样盗贼就不存在了。
(三)“盗”违背“交相利”
那么怎么来扭转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而造成的种种乱象呢?这就不能不谈到“交相利”。如果说“兼爱”反映了墨家的安危治乱的理想和目标,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的话,“交相利”则反映了墨家贴实、务实的精神,二者互为一体。正如《墨子·经说下》所说:“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若左目出右目入”。[13]“交相利”即倡导人们应互帮互助,共谋福利,反对“亏人自利”。“兼相爱,交相利”表达了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互相平等、互相爱护与尊重以及共谋福利的主张。《墨子·非乐上》说:人不同于鸟兽,人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14]即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靠自己劳动的人得以生存下来,不靠自己劳动的人就难以生存。墨子认为人不同于鸟兽之处就在于人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而不劳而获、亏人自利的盗的行为背离了人的本性,也违背了“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和处事规则,是应该抨击和抑制的。
《墨子·兼爱下》说:“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15]《墨子·非乐上》描述当时之世:“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墨子·尚同中》则表达了墨子要“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要“摩顶放踵利天下”。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正义感,使得墨家嫉恶如仇,亮出了“杀盗,非杀人也”的利剑。
三、“杀盗非杀人”法律观之影响
“杀盗非杀人”鲜明地表达了墨子关于“盗”的法律观。这一观点与后世的诸多法律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杀盗非杀人”与“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其总结和分析了墨家关于处置杀伤人行为的主张,即禁止杀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同为墨家的主张,怎么来理解这两句话表达的看似矛盾的观点呢?关键还在于对“盗”和“人”的不同界定。在这两句话中,“人”指的是大多数安分守己“非盗”之人,实施杀伤行为的人是“贼盗”。“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兼爱”思想下一般性的规范,表现其戒杀伤、戒盗的主张。“杀盗非杀人”是对背离“兼爱”而实施杀伤等盗的行为的特殊主张,二者并行不悖,表达了墨家欲“兴天下之利”,而不得已“用天下之罚”,以“除天下大害”[16]的救世情怀。
《墨子·尙同中》中也表达了墨家“不杀不辜,不失有罪”的主张。[17]其实,早在《周礼·秋官》就有“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的明确规定。汉高祖刘邦开国前曾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其中就融入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点,也亮明了国家对“盗”予以追究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此处的“盗”是与杀伤人“贼”的行为相对应的,是狭义的侵犯财产的行为,外延小于墨家语境中囊括“贼”和“盗”之意的“盗”。
(二)“杀盗非杀人”与“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墨子提出“杀盗非杀人”观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代表当时小私有财产者(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强烈谴责盗窃行为”。[18]对此,笔者认为对于盗贼的态度,并不适用阶层分析的手法,因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士不痛恨盗贼,不能仅仅说小私有财产者珍惜自己的财物。家财万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官僚不更渴求无盗贼的清平时代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古往今来人们的理想生活状态。
正因为如此,早在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变法执政时就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方针,[19]《法经》的前两篇就是贼律和盗律。此后,盗贼成为所有朝代打击镇压的重点。汉武帝为加强对盗贼的镇压,颁行《沈命法》和《见知故纵法》。唐律中对侵犯财产的行为进行归纳,总称为“六赃”,“强盗”和“窃盗”是前两赃,对其处罚也极为严重。比如,对于强盗罪,未得财物,处徒二年;赃物满一尺者,徒三年;赃物满十匹者处绞刑。如果手持武器实施强盗,即使不得财,亦处流三千里,赃满五匹者,处绞刑。而且,强盗罪不分首从,一律不予减等处理。《唐律疏议》中还记有:“夜无故入家”条文,即“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无论”。宋朝则重点惩治盗贼,颁行《盗贼重法》和《窝藏重法》,对盗贼的处罚明显重于唐律。明沿袭此精神,对盗贼的处罚比唐律的处罚要重。可见,墨家“杀盗非杀人”所表现出的对盗贼的痛恨和严惩决心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认可和实行,也可以说墨家的盗贼观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观。
(三)“杀盗非杀人”与侠义精神
近代许多国学大师认为,墨家学派与古代的“侠义”精神有着源流的关系。冯友兰在《原儒墨》一文中认为墨家源自武士,即最初的侠。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写道:“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20]的确,墨家很重视和推崇“任侠”,《墨子·经上》讲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上》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侠之精神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慷慨悲壮,急他人之所急,必要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也就是“侠义”精神的内核。《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可“用天下之大罚”以“除天下之大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21]这与侠客的重义气,轻生死的气节完全一致。
然而,侠,一方面体现了匡扶正义、舍己为人的人或者情操,另一方面则是无视法纪,凭一己喜恶任意妄为的人或观念。在统治者看来,可谓亦正亦邪。韩非子在《五蠹》中就讲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杀盗”的行为对被盗者来说带有自卫的性质,而对于别人来讲则就具有了铲奸除恶“侠”的作风,墨家主张“杀盗非杀人”,实则倡导“杀盗”侠的作风,也可以说“杀盗非杀人”观念正是墨家“任侠”精神的表征,它影响了后世的侠义精神。
提出并竭力实现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弱济困,匡扶正义,以安天下之民这样的理念,在战乱不断,贼盗四起,朝不保夕的社会中,无疑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及抗争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侠义精神自古至今绵延发展、经久不衰的原因。
[1][9][11][12][13][14][15][16][17][21]周才珠.墨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529,158,502,298,138,206.
[2]向容宪.附性推理规范化尝试——兼评墨家“杀盗非杀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4).
[3]曲海滨.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J].殷都学刊,1984(4).
[4]袁锡福.“杀盗非杀人”是片面性错误命题吗[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4(3).
[5]陈卓祥.墨家“杀盗非杀人”是一个朴素的辩证的命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6]程恺.从“杀盗非杀人”看正名思想[J].学说论坛理论月刊,2004 (5).
[7]程仲棠.从“杀盗非杀人”看逻辑与价值的混淆[J].中国哲学史, 2005(1).
[8]桑东辉.“杀盗非杀人”命题的法文化诠释[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2);聂长建.墨子“杀盗非杀人”的法律价值分析[J].兰州学刊,2009(10).
[10][18]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8-511.
[19]朱勇.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55.
[20]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92:164.
D929
A
1673―2391(2013)09―0077―03
2013-05-22 责任编校:谭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