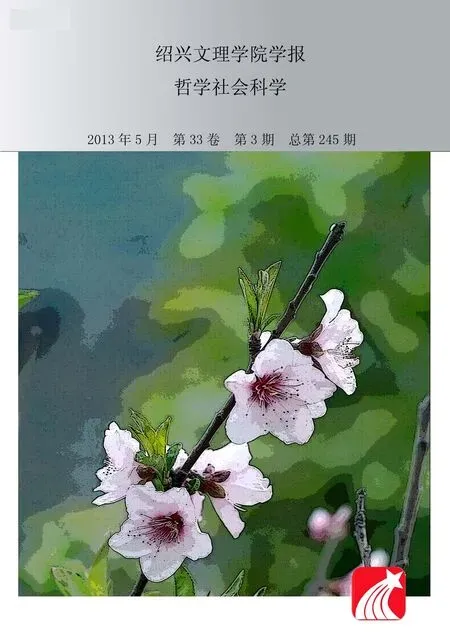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
2013-04-11戴鞍钢
戴鞍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其中,乡村教育的困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困苦和无奈。近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专著和论文颇多,但相对而言,对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际状况的探讨仍显薄弱,本文拟作补充。①
一
近代以前,中国城乡的教育都与科举制度相联系,属传统文化的范畴。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的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庶民文化;可以说几乎没有明显独特的都市文化或都市性格。城、乡之间几乎没有界线。乡村常是学术文化中心,书院、藏书楼常在乡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坚人物的士绅阶级,其活动地点常在乡村”。认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据点是乡村,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乡村文化(农业文化)为特质”。[1]这种局面,在近代随着开埠通商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新式教育的展开发生变化。
笔者曾对清末民初东西部的新式教育做过比较研究,发现鸦片战争前后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授首先是从东南沿海起步的。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为了推进其传教事业,设立了一些教会学校,[2]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后,教会学校又在这些城市相继设立。[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最初的五口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到1875年,各地的教会学校总计有800所。[4]
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一批洋务学堂也应时而生。1862年清政府官办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5]继而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京、沪、粤三地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以后,则渐有数理化和医学等课程的开设。1872年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描述京师同文馆:“学生们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数学、自然生理学和化学。”[6]随着洋务企业的开办,广州、福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设立,开启了近代教育的风气。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兴起,各式外语学馆在沿海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性教育改革开始之前半个世纪内,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已经设立66所新式学堂。[5]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光绪帝连颁谕旨予以推动。新近刊布的“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有清晰记载:8月19日,“奉旨前于五月廿二日降旨,谕令各省开办学堂,限两个月覆奏,现在限期将届,各省筹办情形若何,著各督抚迅即电奏”[7]85。8月21日,“翻译西书,为方今要务,罗丰禄、庆常、伍廷芳熟于英法文字,就近购译尤为便捷,著即选择善本陆续编译成书,咨送总理衙门呈览”。8月22日,“奉旨昨于初三日降旨催办各省学堂,计已电达。直隶为畿辅重地,亟应赶紧筹办,以为倡导,著荣禄迅饬各属,将中学堂、小学堂一律开办,毋稍延缓,并将筹办情形即行电奏”。8月28日,“奉旨前有旨,饬令各省开办学堂,复经降旨电催,已据各省陆续奏报开办,而广东迄无只字覆奏,岂藉口于部文未到耶。著谭钟麟、许振立即妥筹开报,并将办理情形即日电奏,毋再任意迟延干咎”。8月30日,“学堂造就人才,实为急务,著陶模切实劝导,以开风气,章程已由总署咨行,务即勉筹经费,迅速开办”。8月30日,“奉旨前经降旨催办各省学堂,据谭钟麟、德寿电覆,均尚无切实办法。著该督抚振刷精神,确筹开办事宜,认真举办,总期多设小学堂,以广作育,不准敷衍延宕,仍将筹办情形即行电奏”[7]85-89。但9月21日“百日维新”失败,改革举措停顿。新式教育在通商口岸以外地区较普遍的开展,是在清末新政期间。[5]
1901年后推行“新政”需要相应的新式人才,张之洞、刘坤一呼吁变革:“今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8]1901年9月,清廷颁旨:
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9]
12月颁布学堂选举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1902年(旧历壬寅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学校分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大学堂、大学院七级,修业年限共计20年。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但该学制并未具体实施,直到1904年(旧历癸卯年)1月,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才正式颁布实施。修订后的“癸卯学制”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主管全国学政,初步形成中央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癸卯学制”的实施和次年宣布的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二
自清政府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和废除科举后,各地新式教育发展迅速。1908年6月,刘大鹏与友人同游山西汾阳写道:
城隍庙东,有初等女学堂,在堂肄业之女学生三四十人。堂之规模不甚宏壮,其门联云:许多别径旁门休轻着走,不到升堂入室莫漫回头。初等小学堂设文庙之侧,中等学堂在府署之东,黄公祠内设西河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实业有限公司设立东大街,面目宏丽,维新气象咄咄逼人。府城风气之开,较之县城为早。[10]
就全国而言,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新式教育在清末新政期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城市新式教育的推进明显,特别是工商实业各门类的技能教育及高等院校的设立,“清末十年间,上海至少就培养了13万多名新学学生”。[11]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12]各地的新式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1912年沈钧儒在出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期间,对省内学校进行整顿,制订教育规章制度,强调:
国家之强弱,视教育发达与否为标准。东西各国规定义务教育,凡学龄儿童已达就学之期,非有不得已事故不得废学,否则罪其父母,此教育之所以溥及而国乃以强盛。方今民国初定,百端待理,顾尤以普及教育为根本之要图。而谋普及教育,须从调查学龄儿童入手,某地应添设学校几所,某地应需经费若干,种种设施,皆恃是以为准则。而以学龄儿童之人数比较就学差数之多少,尤足觇各地文化之迟速。[13]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展,显然得助于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近代文化和工商业的发展。无此依托的广大农村,则明显衰弱,因此对新式学堂的推广不能估计过高。1911年,黄炎培在其邻近上海的家乡川沙县调查所见,“全境私塾百七十一所,内男教员百五十六人,女教员十五人,学生共二千五百八十五人”[14],而当时该县只有小学17所,学生674人,只占当地适龄儿童的6.3%,私塾的学生则占适龄儿童的24.1%。据黄炎培的调查,“学堂有学生父兄所不喜者三焉,一体操,二读经钟点太少,三习字不用描红簿,以是私塾多学生而学堂较少也”。[14]此外,还有新式学堂的开办经费及学生缴费过多。其影响,如黄炎培的调查所显示的,城乡间教育的不平衡极为突出,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而农村的新式学堂相对较少,同时新式教育相对于科举时代的旧式教育来说,是非常昂贵的教育,其后果是乡村儿童的入学率非常低,乡村初等教育仍然是以旧式的私塾为主。[14]时至民国,“在法制上,书院制与私塾制不能存在,然而在实际则私塾遍布全国,据安徽、广东两省之统计,私塾数远过于小学数,私塾生远过于小学生”[15]。即使在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无锡,1916年前后亦有私塾2000余所。[14]
清末在新式教育起步时,浙江钱塘县私塾俞氏就敏感地意识到时势的变化,劝导自己的学生骆憬甫:“现在的时代,光光做策论是不够的。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体操、图画等,家塾哪里学得到?而且也请不到这样多才多艺的名师。……我刚从杭州回来,知道安定学堂、杭州府中学堂都在招考,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奉劝你俩赶快去报名投考,勿再过家塾生活以埋没一世!”[16]经历了两次乡试失败的骆憬甫在老师劝导下,在1905年秋考入了杭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他的人生转折。
一旦有机会走出乡村求学乃至出洋留学者,很少有人学成后再回到农村。据1915年的调查,清华留美归国学生无一人住在乡镇。另据1925年对584名归国留学生的调查,其中34%住在上海。一些农科毕业生,也远离农村,1926年有一位外国人指出:“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在美国大学农科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后真正地回到农村服务。”[17]原因之一,在城市任职的收入丰厚。有人估算,在1927年的上海,一个非熟练工人抚养五口之家每月需费21.34元,其中伙食费11.1元;而一个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五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四倍以上。[18]据一项范围较广的综合考察,“三四十年代时回国留学生任职于教育界的约8500人,若减去兼职者40%则为5100人;政界约1558人,军界近1000人,工商界约1500人,共计近1万人”[19]。
即使那些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也不愿呆在农村。有学者指出: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20]
1927年的农村调查,也折射了读书人在村民眼中的尴尬处境:“读书成本太大,出来非但没有官做,即教员位置亦粥少僧多,而况学些空架子,文不象秀才,武不象丁,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不事生产,要吃要用。”[21]
农村知识人的流失,如当时人所描述的,“农村中比较有实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22],令很多有识之士十分焦虑。1919年2月李大钊以《青年与农村》为题,撰文指出:“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一方面,“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认为“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23]但情况依旧,1921年陶行之疾呼:“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就是有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然而乡村的学校只有百分之十。”[24]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新式教育有所推进,但成效甚微。就在南京城郊的江宁县淳化镇,1931年乔启明实地调查所见:
教育在淳化镇乡村社会中,是不很发达的,大半学校多系私塾,俗名叫做“蒙馆”,就是在一个乡村中的农人,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大家摊派几个钱,请一位能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来教学生读古书。在淳化镇乡村社会里56村中,共有34村有了这种私塾,占全体村数中51.8%,什么新式小学倒反很少。近年江宁县政府及私人方面极力提倡,到了现在,总算共有5个村庄已经设立,但亦仅占全体 7.1% 。[25]
1931年,河北省有学龄儿童3236313人,其中就学儿童只有1147469人,就学率只有35.46%。1932年,山东省学龄儿童有4260708人,其中就学者有157770人,占总数的27.17%。1934年,河南省广武、灵宝等35县的调查,共有学龄儿童1344629人,其中就学者323673人,仅占总数的24.07%。女童失学者更多,1932年山东省的小学生有1233789人,其中女生只占7.3%;据1934年的调查,在河南省镇平、巩县等15县的学龄女童中,失学者高达90%。[26]
远离口岸城市的边远地区,情况更糟。1932年甘肃省会兰州,“所设学校计有甘肃学院一所,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各一所,省立第一中学及农业学校共二所,省立工艺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各一所,公私立小学校共三十余所。此外复有回民自办之清真学校二所。除小学生外,仅千余名而已。程度均甚低,不能与口岸地区相比。女子师范生不及百名,以兰州人口十余万之众,妇女居其半数,入学受教育者乃如此寥寥,可知甘省女子教育更属落伍中之落伍者。此省会区域,其教育情况尚不逮内省之县城,则其外县乡村更无论矣”。[27]
据新近刊布的《甘肃天水县风土调查录(1927年4月)》记载:
县属学龄儿童向无详确之调查,推原其故,良由地方辽阔,山川绵亘,村庄繁多,居户零星,加以近年来供应繁重,人民之迁徒靡常,金融恐慌,夫马之薪费无出,旧有户籍无从依据,新近勘查难期彻底。兹经前劝学所暨教育局制印表格,赓续调查始得概数,计全县五学区约共有学龄儿童男三万七千二百余名,女二万七千四百余名,内除就傅学校男二千六百七十九名,女一百零四名,又就学私塾男三千零六十二名外,计已达学龄之失学儿童,男约三万一千五百余名,女约二万七千二百余名。[28]
据此统计,该县失学男女学龄儿童分别约占其总人数的85%和99%。如调查者所言,出现这种状况“实因人民苦于征徭,不但无教,而且无养故耳”。此言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乡村地区新式教育衰微的症结所在。
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使在近代城市里,新式教育也与众多贫困者无缘。1936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九十元以下者占百分之六十六,浙江尚恐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29]况且当时的高等院校又多设在少数大城市,据1934-1935年的统计,全国110所高校中,有41所设在上海和北平,内地的四川为4所,湖南、广西各2所,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各1所,贵州、西康则空白。[30]费孝通曾不无感慨地指出:“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但大学是如此,就是中等教育也是如此。”[31]
显然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虽在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少数城市有较明显的推进,但在广袤的农村仍很隔膜,城乡间近代文化教育的联系微弱,甚至呈现出明显的断层,远不足以能触动乡村经济凋敝、文化闭塞、教育落后的普遍状况。政府却依旧冷漠和无所作为,穆藕初曾尖锐地指出:“农村经济之破碎零落,已至不堪收拾之程度,此其故何在,盖徒托空言,而不务实际是也。”[32]
有鉴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城市知识分子,人称乡村建设派,曾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尝试乡村改造,推行诸如识字扫盲等社会改良举措,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收效甚微。1936年,吴景超就直言:
中国今日的普遍农村破产,于是有一些志士仁人出来提倡农村运动。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风起云涌,数得出来的总在数十以上。他们的目标,自然不专为改进农民经济状况,但无论如何,救穷总是他们主要目标之一。经这许多人在各地的努力,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不能说是全无影响。在现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33]
显然,枝节的改革无补于大局。诚如有学者肯定其良好的愿望和一定的实际成效后指出:“它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出发点、依赖地方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力量资助的经费来源,及其所推行地区和所取得实际成效的局限性,相对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背景和普遍贫穷的广大农村,显然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更不能成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34]
注释:
①中国近代教育史专著,较有代表性的有多卷本“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和多卷本“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阅许庆如撰写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9期。综观上述论著,大多侧重教育史本身的考察,结合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研究有待加强。
[1]刘石吉.传统城市与通商口岸:特征、转型及比较[M]//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22.
[2]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9-20;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42-48.
[3]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39.
[4]吴宣德.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
[5]戴鞍钢.清末民初东西部新式教育推进的比较[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6][英]魏尔特著.戴一峰等译校.赫德与中国海关[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468.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二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2)[M].第11页。
[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4719,4787.
[10]刘大鹏.游绵山记(手稿)[M]//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399.
[11]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
[12]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M]//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
[13]郭之莎整理.沈钧儒民初教育轶文[M]//近代史资料(总10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5.
[14]赵利栋.从黄炎培的调查看清末江苏兴办学堂的一些情况[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5]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存稿[M].北京:中华书局,1936:6.
[16]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7.
[17]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M].台北: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241,166.
[18]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J].近代史研究,1994(3).
[19]虞和平.民国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C]//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庆祝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中国近代史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5.
[20]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M]//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43.
[21]巫宝三.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句容[J].东方杂志,1927,24(16).
[22]潘光旦.说乡土教育[M]//潘光旦文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371—372.
[23]李大钊.青年与农村[N].晨报,1919-02-20至23;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992.
[24]陶行知.师范教育之新趋势(1921年的演讲记录)[M]//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93.
[25]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J].金陵大学农林丛刊,1934第23号;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105.
[26]郑起东.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M]//王先明等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2-23.
[27]林鹏侠.西北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60-61.
[28]张显菊整理.甘肃天水县风土调查录(1927年4月)[M]//近代史资料(总10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0.
[29]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N].申报,1936-05-09(15).
[30]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01-302.
[3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0.
[32]穆藕初.李馥荪氏重农说之再进一解[M]//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79.
[33]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6.
[34]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C]//杜恂诚等.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