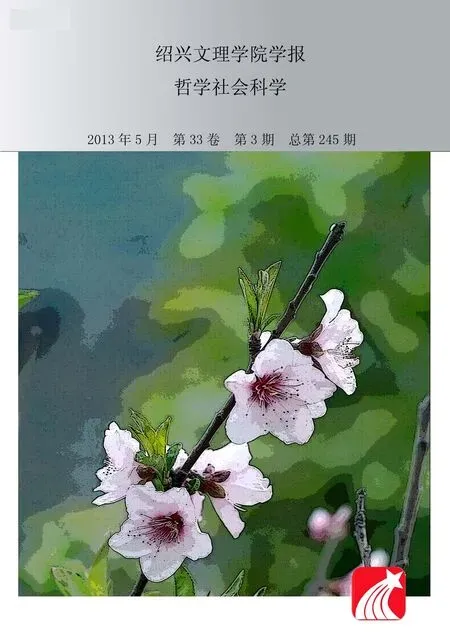感恩与怜才: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考
2013-04-11汪永祥
汪永祥
(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 文物保护处,浙江 绍兴312030)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等,明晚期杰出文学艺术家。张岱(1597-1679),字宗子,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400多年前的绍兴城中,张岱家族中的张天复、张元忭、张汝霖祖孙三代,以及张岱本人,与徐渭一起,构成了一段以“怜才与感恩”为主题的风雅往事。
一、相知
徐渭从小居住在大云坊观桥弄大乘庵东边的榴花书屋(今青藤书屋),距张岱高祖张天复和曾祖张元忭居住的车水坊状元府,大约只有10分钟的步程。徐渭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比生于明正德八年(1513)的张天复小8岁,又较生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的张天复的大儿子张元忭大17岁。因此,徐渭与张氏父子可能从小就熟,但由于年龄的原因又不可能有太深的交往。
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徐渭与张氏父子交往的第一次记录是在嘉靖庚戌年(1550)。那年,徐渭写了首《送张伯子往嘉兴沈氏读书》:“我闻石联丈人如大海,无宝不有藏真大,手书万卷付乃郎,何止珊瑚八尺长。伯父今日为我别,上堂手触山人箧,一撒铁网莫教空,会有金谷园中七尺红。”[1]142-143文中的张伯子即张元忭,石联即沈爚(字士明),嘉靖四年举人,伯父即张岱的高祖张天复。查徐渭《张大仆(天复)墓志铭》中有“庚戌服除,谒选,授礼部祠祭司主事”[1]1033。这一年天复丁母亲忧服除,去北京就任礼部祠祭司主事,顺道送13岁的儿子元忭赴嘉兴沈爚处读书,徐渭送行,故有此诗。但徐渭与天复的交往时间似应更早。天复补邑诸生在嘉靖甲午年(1534),嘉靖癸卯年(1543)领乡荐,嘉靖丁未年(1547)中进士。徐渭则是嘉靖庚子年(1540)进山阴学诸生,嘉靖癸卯年(1543)第二次参与乡试。[2]因此,徐渭与天复很可能是在嘉靖庚子年(1540)共同乡试后开始熟识、相知而交往起来的。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天复左迁云南按察司副使,徐渭有《送张大夫之滇》诗:“锵锵剑珮鸣,万里赴王程,楚泽鱼龙侯,沅州杜若生。碧鸡来入赋,白马去提兵,想见南夷定,相如拥汉旌。”[1]181诗中叙述了天复从湖广提学副使到云南副史的经历,时云南为沐氏所统治,土酋拥兵自重,因此,徐渭表达了“想见南夷定,相如拥汉旌”美好祝愿。然而,天复云南平乱不但无功,反受到祸害牵连,子元忭奔走申冤终得脱。元忭赴云南迎父,徐渭作《灯夕送张君之滇,迓其尊人》相送:“今岁风光倍觉饶,无人不去踏虹桥。独辞午夜千门月,去迓高堂倍里遥。飞盖梅花梁苑雪,归帆杨柳楚妃腰。此行不为营名利,要度衡阳雁影高。”[1]797元忭接父亲恰逢正月十五,故有“今岁风光倍觉饶,无人不去踏虹桥”。相传北方大雁因惧凛冽寒风而成群往南迁徙,飞至气候温和的衡阳,便歇翅停回。因此,“此行不为营名利,要度衡阳雁影高”有元忭远去云南,是迎父而不是为了享受的意思,表达了徐渭对元忭孝父之情的赞赏。
元忭嘉靖戊午年(1558)举于乡后,“连上春官不第”,徐渭也是连举连北,共同的科举经历,让徐渭和元忭熟识起来。某年,元忭又去会试,徐渭前去送行,并赋诗二首。其一《送张子荩春北上》:“离筵驿路正芳梅,骑马听莺是此回。旧日繻生关吏识,新年罗袖内家裁。泽兰把赠携春色,苑杏留花待异才。却说涸鳞县尾在,欲从天上借风雷。”其二《赋得紫骝马送子荩春北上次前韵》:“紫骝嘶断驿亭梅,紫色翩翩燕共回。不用连钱千个剪,秪借葡萄几点裁。桃杏满堤冲雪片,烟云一道本风才。要知他日飞腾处,试听蛟潭夜半雷。”[1]774-775驿亭、梅花,嘶骝、翩燕,徐渭与子荩相别。“泽兰把赠携春色,苑杏留花待异才”表达了徐渭对元忭会试成功的信心,但现下却如涸辙之鲋,尚处困境之中,因此,“欲从天上借风雷”,等到会试中殿飞腾处,便能“试听蛟潭夜半雷”。这诗何尝又不是八试不售徐渭的夫子自道?
二、救难
徐渭与张氏父子的关系,因其嘉靖四十五年(1566)因杀妻下狱而变得紧密起来。
狱中的徐渭,引来了众多的同情和营救者,张氏父子便是其中之一。
张天复来探望狱中的徐渭,徐渭有《张云南遣马金囊(时余尚羁而张亦被议)》记之:“百颗缄题秋暑清,遥闻摘向最西营,张骞本带葡萄入,马援难抛薏苡行。万里锦苞辞晓露,一泓寒舌搅春饧,年来不为临邛病,无奈羁愁渴易生。”[1]774-775马金囊为药名,缄题原指信函的封题,此处应指装马金囊的包裹。“时余尚羁而张亦被议”指徐渭尚在羁押之中,而天复在云南事件中虽得释,但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尽管天复尚处谤议之中,他还是给狱中的徐渭捎来了马金囊,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隆庆五年(1571),元忭再次赴京参与会试前看望了徐渭,徐渭作《送张子荩会试正月十七日》:“……身伴棘墙鼠,心摇芳草途。不得双握手,惟听只呼卢,看君将笔赌,一掷万青蚨。”[1]827“身伴棘墙鼠,心摇芳草途”,尽管身陷囹圄,徐渭仍倾心相送。“看君将笔赌,一掷万青蚨。”《淮南子》中把“青蚨”称为“神钱”,有“青蚨飞去复飞来”之说。因此,这两句诗表达了对元忭为会试所付出的勤劳必有回报的良好祝愿。
这年春天,元忭会试中了状元,徐渭“侧闻胜事,便拟随俗称庆,念无可致羔雁者。得报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制词者二,敬书以充。”兴奋之余,徐渭没有忘记去向天复道贺,作有《闻张子荩廷捷之作,奉内山尊公》诗。
徐渭对元忭中状元的激动,固然是为朋友高兴,另一方面也从中看到了他出狱的希望。
早在隆庆四年(1570),徐渭在给好友、礼部右侍郎诸大绶(1523-1573,字端甫,号南明,绍兴山阴人)的《书启》中就说过:“……每及诸公,相与举手加额曰:‘亏却礼部工部’。或添寸烛,不觉屈指再陈云:‘莫忘老张新张。’……盖明公之拨不肖,如圣众取经于西极,历百艰而务了一心;不肖之答明公,如贫僧拜忏于荒庵,有赞叹而无供养。兹念罔极,何以为情!”[1]1295文中的礼部即礼部侍郎诸大绶,工部即时任工部营缮司主事的陶幼学(1521-1611,字子行,明绍兴会稽人),老张即张天复、新张即张元忭。“不肖之答明公,如贫僧拜忏于荒庵,有赞叹而无供养”,徐渭在文中表达对这四位同乡官员救援自己的感激之情。
大约在1570年左右,由于张氏父子等人的救援,徐渭终于解下戴了4年的枷栲。张元忭的儿子、张岱的祖父张汝霖(1557-1625,字肃之,号雨若)去狱中看望徐渭:“余髫时颇为所喜,尝入视圜中,见囊所著械悬壁,戏曰:‘岂先生无弦琴耶?’文长笑:‘此子齿牙何利!’其《阙篇》成,自序用‘怯里赤马’,余偶语人:‘徐先生那得误怯里马赤作怯里赤马耶?’其人往告,文长曰:‘几为后生窥破。’”[3]徐渭虽解除了枷栲,但尚未正式豁免,因此将枷栲挂在壁上,故有张汝霖的戏言—“岂先生无弦琴耶?”。“怯里马赤”为蒙古语,意译为翻译者,引申为代言人。徐渭将“怯里马赤”误为“怯里赤马”,或是由于其发音的诘屈聱牙。然这一错误竟被一个小孩发现,所以徐渭要有“几为后生窥破”的感叹了。
隆庆六年(1572)天复60大寿,生日的那天,徐渭作《张大夫生朝》祝贺:“解组归来白发新,每因萸菊赏年辰,沅州芳草行吟后,镜水荷花荡桨春。百粵既凭传檄定,五湖宜着浣纱颦。南冠未必长留系,来问桃源第几津。”[1]272-273天复自云南削职归来,在镜湖之滨构筑许多别业,以养鱼灌花、诗酒自娱。凭着天复对镜湖别业景色的描写,加之徐渭旧日游憩时的记忆和想象,在《张大夫生朝》基础上,徐渭为天复的别业赋有《镜波馆》《流霞阁》《垂纶亭》七律三首。徐渭诗中有“南冠未必长留系,来问桃源第几津”,“南冠”有“囚犯”之意,因此,这二句诗意味着,徐渭已经感到出狱有望,开始向往起陶渊明式的生活。
徐渭《畸谱》称:“五十三岁。除,释某归,饮于吴。明日元旦,拜张座。”[1]1329万历元年(1573),徐渭在张氏父子等人的努力下,加上适逢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在除夕终于保释出狱。徐渭没有忘记张氏父子的情谊,元旦即去拜访了张氏父子。这年冬天,元忭因父病归越,开始编纂会稽县志,“今之文学士优于史无如徐生渭者”[4],同时推荐徐渭来参加编写工作。万历《会稽县志》中的序文总论,均出自徐渭手笔。
万历二年(1574),张天复去世,徐渭悲痛欲绝,作《祭张太仆文》:“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务合群喙而为之鸣,……其同心戮力而不贰,……夫以公德于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处,而公今殁矣,将何以为酬也!嗟乎!此某虽不言,而寸心之恒,终千古以悠悠也。”[1]664徐渭回忆起纯厚好施天复,待己如兄长一般的点点滴滴,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感到了一丝的迷惘,发出了“夫以公德于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处,而公今殁矣,将何以为酬也”的感叹。
万历三年(1575),经元忭疏通,徐渭正式释放,心情大好,准备去游天目山,留有《十四日饮张子荩太史宅,留别(久系初出,明日游天目诸山)》诗。
由此,由杀妻入狱,到保释、正式释放,经过张氏父子的一路呵护,徐渭得以重获自由。
三、生隙
万历八年(1580)徐渭来到北京,以授经为生。“狱事之解,张宫谕元忭力为多,渭心德之,馆其舍旁,甚马雚好。”[1]1295徐渭将家安置在长安街张元忭宅的旁边。
这一段时间,徐渭经常为元忭代书,交往比较频繁。徐渭有《答张翰撰(阳和)》,与元忭讨论了书画用纸问题。北京一夜大雪后清晨,元忭给徐渭送来了短袖羔羊皮袄和老酒,徐渭留下了《答张太史当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症药也。酒无破肚脏,罄当归瓮;羔羊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一笑。”[1]1017老酒喝光得还瓮,短袖皮袄不是我这种平民百姓所能穿,寒潮过后晒晒也当奉还。信末所引的一句民谚最有意思。明朝时萧山西兴是绍兴前往杭州、北京等地的码头,那里的挑夫不避寒暑常年辛劳,他们说:“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诙谐中不乏自嘲。徐渭这一短笺似受不受,似谢非谢,充分显示了徐落拓不羁的个性,说明当时其与张元忭的关系很是不错。
然而,就在元忭送徐渭皮袄和菽酒的那个冬天,一缕阴影出现在徐渭和元忭之间。
徐渭在《梧阴洗砚图》诗中道:“夏景冬题欲雪辰,翻思炎暑渴生尘,梧桐世上知多少,解得乘凉只此人。”[1]872《梧阴洗砚图》描绘的是夏景,索画者却在冬季求题,“解得乘凉只此人”,徐渭的题画诗含有世态炎凉的反讽意味。诗中徐渭注云:“某翰撰索题,时值(冬季)。”徐仑认为,某翰撰应是指朱赓,徐渭的题画诗引起了朱赓对徐渭的不满。[5]因为,徐渭在《答朱翰林》中说过:“日者于某人书见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于门墙,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颜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1]1022朱翰林即朱赓(1535-1608,绍兴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六年(1578)以侍读为日讲官,故徐渭称其为朱翰林。朱赓认为徐渭故作清高,称其“有意自外于门墙,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颜色”,徐渭因之作《答朱翰林》以抗辩之。元忭与朱赓曾一起读书龙山,既是儿女亲家,又同朝为官,故在朱徐矛盾上,更多站在朱赓一边,导致张与徐的关系逐渐冷淡起来。当时徐渭的心情颇感压抑,《九月朔,与诸友醉某于长安邸舍,得花字》表达了他的郁闷:“满庭山色半阑花,觞曲交飞古侠家,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会最天涯。不教酩酊归何事,望到茱萸节尚贝余,烛暗沟浑都莫虑,近来宫道铲堆沙。”[1]289诗题中徐渭有一注:“时一旧友稍贰,故及之,时又值大除沟道。”说明郁闷是因“旧友稍贰”而起。因精神郁结,徐渭旧病复发。张汝霖说过:“(徐渭)尝私言余:‘吾圜中大好,今出而散宕之,迺公悮我。’”[3]1349迺公即乃公,指张汝霖的父亲元忭。可见,徐渭将自己重新发病的原因归咎于了元忭。
万历十六年(1588)元忭去世,已绝户十年不出的徐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送别张元忭。张汝霖记道:“先文恭殁后,兄弟相葬地归,阍者言:‘有白衣人径入,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涂,第小垂手抚之,竟不出一语,遂行。捷户十年,裁此一出,呜呼,此岂世俗交所有哉!”[3]1349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其与张天复、张元忭父子的交往,由此落下帷幕。
四、辑佚
天复、元忭父子与徐渭已先后离世,然而徐渭与张岱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
元忭曾孙张岱对徐渭十分景仰。其《跋徐青藤小品画》中对徐渭的画作了如下高度评价:“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崛强,朕视之更觉妩媚耳。’崛强之与妩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余蓄疑颇久。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太宗之言为不妄矣。故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6]306
元忭父子雅与徐渭游好,笔札丰富。在徐渭门人商浚(字维濬)等合编《徐文长三集》29卷的基础上,张岱箕裘博雅,得逸稿分类为若干卷,从而校辑出徐渭集外佚文《徐文长逸稿》24卷,并于天启三年(1623)刊印。王思任对张岱的《徐文长逸稿》有如此评价:“予有搏虎之思,止录其神光威瀋,欲严文长以爱文长;而宗子有存羊羔之意,不遗其皮毛齿角,欲仍文长以还文长。”[7]认为他自己编徐渭集是在精上做文章,而张岱编徐渭佚稿则是在广博上下力气。张岱编徐渭逸稿的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广收徐渭文章,让人们不仅了解徐文长其才,还能了解徐文长其人,还原一个完整的徐渭。对于这一点,张岱祖父张汝霖在《徐文长逸稿》中说得十分明了:“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矣!……(袁宏道)方其挑灯夜读,亟呼周望,惊叫称奇,如将欲起文长地下,与之把臂恨相见晚也。顾中郎知文长,似人尽于文;而余素知文长者,谓其人政不尽于其文。文长怀祢正平之奇,负孔北海之高,人尽知之;而其侠烈如豫让,慷慨如渐离,人知之不尽也。……余孙维城,搜其佚书十数种刻之,而欲余一言弁其端。为文长搜佚书,故亦搜佚事与之,使知其人果不尽于其文耳。若以文,则当吾世一中郎足矣……”[3]1348-1350
纵观张岱家族,从张天复、张元忭经过张汝霖到张岱,都十分欣赏徐渭的才学。从送马金囊、短袖皮袄和菽酒,鼎力帮其出狱,到编写《会稽县志》,天复、元忭父子主要通过生活上、行动上体现了对徐渭的关爱,而张汝霖、张岱祖孙俩,则通过写文辑书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徐渭的敬意。
徐渭在自编《畸谱》的“纪恩”栏中只提到四人:“嫡母苗、张氏父子、绩溪少保胡司马。”[1]1333嫡母苗氏对徐渭有养育之恩,胡宗宪(1512-1565)为抗倭名将,徐渭作为幕僚参加了胡宗宪组织的抗倭活动,颇得胡宗宪信任,这对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的徐渭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徐渭自然也要纪恩。张氏父子能和苗氏、胡宗宪列在一起,被徐渭纪恩,说明张氏父子在生活上、行动上对他的关爱,徐渭已铭记于胸,永世不忘。
感恩和怜才构成了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的主线,尽管由于徐渭“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1]638,而张元忭则是一种介耿不苟的性格,因此,徐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仅仅是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主线中的一种变奏,反而丰富了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的内涵。400多年后,当我们回顾徐渭与张岱家族间的这一段风雅往事,无疑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道风景。
[1]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徐渭.畸谱[M]//徐渭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7.
[3]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M]//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1349.
[4]张元忭.会稽县志叙志[M]//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编7(《会稽县志》明万历三年(1575)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83.
[5]徐仑.徐文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77-178。
[6][明]张岱.张岱诗文集[M].夏咸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06.
[7]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M]//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