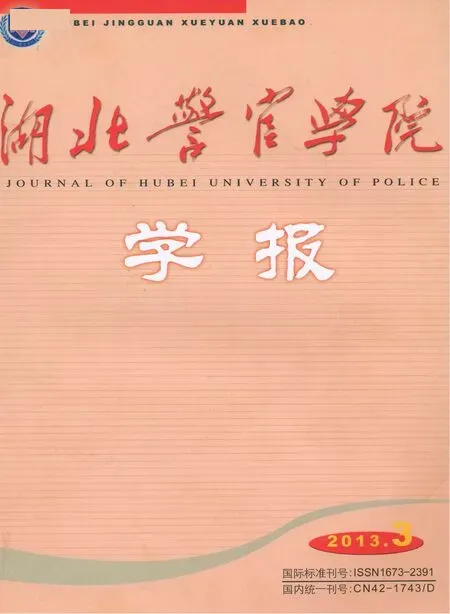论保险诈骗罪未遂形态的认定
2013-04-11刘文强
刘文强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 沈阳110854)
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关于保险诈骗罪犯罪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另外,根据司法解释,个人诈骗数额较大以1万元为限,若某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数额为2万元,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为8千元,那么,本罪诈骗数额以8千元认定还是以2万元认定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如何认定数额较大也应该进行深入探讨。
一、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通说认为,行为犯是以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一类犯罪,而结果犯的既遂还需要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保险诈骗罪应归入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学者主张,保险诈骗罪是结果犯,即本罪的既遂必须要求行为人骗取的保险金达到“数额较大”,如果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没有成功或者行为人仅骗到数额较少的财物,那么上述情况只能以保险诈骗罪未遂论处。还有学者主张,根据现行《刑法》第198条的规定,本罪是行为犯,因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并非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实际上取得的保险金额,而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通过实施保险诈骗活动所获取的保险金额,至于行为人是否达到了主观目的,在所不问。
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是妥当的,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理由:第一,保险诈骗罪从其罪质上考量属于诈骗犯罪的特殊形式,诈骗罪在刑法理论中被一致认为是结果犯,保险诈骗罪虽然发生在保险领域,但基本的行为构造和诈骗罪如出一辙,因此在结果犯这一点上应该具有诈骗型犯罪的共性。第二,把“数额较大”解释成行为人意图骗取的财物数额,不具有合理性。按照上述观点,将导致骗得了5万元保险金的行为人和意图骗取5万元尚未得逞的行为人承担同样的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难以做到罪责相适应。笔者认为,“数额较大”一直是作为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存在的,将其作为主观要件有主观定罪的嫌疑,因此本罪是结果犯,而犯罪数额既是犯罪对象也是犯罪结果的财物价值量。第三,从本罪的罪状上看,《刑法》不仅规定了保险诈骗罪法定的五种行为方式,还在每种行为之后规定了“骗取保险金”。行为犯只要求法定行为的完成即可构成既遂,那么为什么《刑法》还要不厌其烦地在每种行为之后都加上“骗取保险金”这一要素呢?采取这种表述方式说明,《刑法》不仅规定了危害行为,同时也规定了危害结果——“骗取保险金”,因此本罪符合结果犯的特征。
二、保险诈骗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对于本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意见相左的主张。支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诈骗犯罪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的,因为诈骗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是骗取一定的违法数额,不具备“数额较大”这一要件就不构成犯罪,也就不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支持“肯定说”的学者则认为,保险诈骗罪等诈骗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故意犯罪,是可以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的。
笔者赞成“肯定说”。第一,如前所述,保险诈骗罪是结果犯,因此可以通过结果犯的犯罪特征进一步分析,所有的结果犯都可能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因为区别结果犯的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法定的危害结果是否已经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出现即意味着犯罪既遂,否则便是犯罪未遂。就保险诈骗罪而言,若行为人已经着手进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但由于出现了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阻碍而没有得逞即是犯罪未遂。第二,否定说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数额犯存在未遂形态,这混淆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和罪与非罪的界限。因为行为人实施的保险诈骗犯罪是一系列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统一,对于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希望骗取数额较大的保险赔偿金,但实际上骗得保险金数额较小或者尚未取得赔偿便被揭穿而没有骗得保险金的,应当以保险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若行为人只是意图骗取较小数额的保险金而实施诈骗行为的,则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保险诈骗罪作为结果犯是存在未遂形态的,行为人已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金的或者骗取保险金未达“数额较大”的,应认定为犯罪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保险诈骗罪着手的认定
着手不仅标志着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表明行为人所实施的实行行为,而且是划定未遂犯处罚时期的概念。如何认定行为人着手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这是本罪未遂形态存在的又一疑难问题,需要进行探讨。
关于着手,国外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传统观点认为,所谓着手,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形式客观说”,“形式客观说”被德国刑法所采用,原因在于德国刑法和理论强调行为无价值,基于风险社会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的原则,增加了很多危险犯的规定,甚至于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犯罪,希望尽早将危险遏止在危险状态的阶段,以便更好地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我国的刑事政策一直秉承对犯罪行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比较重视对刑法处罚范围的限制,而新《刑法》注重结果无价值,因此采用形式的客观说认定着手并不十分妥当。犯罪的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因而对法益没有侵害的行为也就不会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对法益侵害具有紧迫危险的行为,当这种危险达到紧迫程度,或者说只有当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状态时,才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就保险诈骗罪而言,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的虚假原因、制造保险事故等行为,目的都是为骗保制造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制造保险事故后并未到保险公司索赔,保险秩序与保险人的财产即本罪的法益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性就低。只有当行为人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要求时,才能认为保险诈骗罪的法益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性已经达到了紧迫的程度。因此,本罪的实行行为是行为人到保险公司索取赔偿的行为或者要求支付保险金的行为,而本罪的着手,就是行为人开始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或者要求支付保险金的行为。
四、对“数额较大”的认定
保险诈骗罪是结果犯,即构成本罪不仅需要实施五种保险欺诈行为,而且还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即骗取“数额较大”的保险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个人实施保险诈骗活动,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较大。就本罪而言,判断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是认定本罪既遂或未遂的标志。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存在“脱离控制说”、“实际占有说”、“控制说”三种观点,其中以“控制说”为理论通说。“控制说”认为,区分保险诈骗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以行为人是否取得对保险金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为界限。具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形式控制说”和“实质控制说”。“实质控制说”指公私财物脱离了所有人的控制而行为人则确立了自己对该财物的控制;“形式控制说”则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取得该财物,已具有控制财物的可能性即可。采用“形式控制说”或“实质控制说”将会给保险诈骗罪“数额较大”的认定带来不同的结果。例如,张某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数额为2万元,但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为8千元,按照“形式控制说”的观点,张某已经具有了控制2万元保险金的可能性,所以构成保险诈骗罪既遂;按照“实质控制说”的观点,张某实际控制的保险公司损失的仅为8千元,因此应认定为保险诈骗罪未遂。
实质控制说是妥当的。通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意味着法益受到了实质上的侵害。保险诈骗罪的法益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控制说实际上并没有对法益造成实质的侵害,因为行为人并没有实际控制保险金,当保险金脱离了保险人的控制而行为人则确立了自己对保险金的控制时,如果数额较大,则应该认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既遂。
综上所述,对“数额较大”的认定应采“实质控制说”,即以行为人实际控制保险金的数额为准进行判断。
[1]刘宪权.刑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04.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刘宪权.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
[5]张永红,姜国强.保险诈骗罪停止形态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