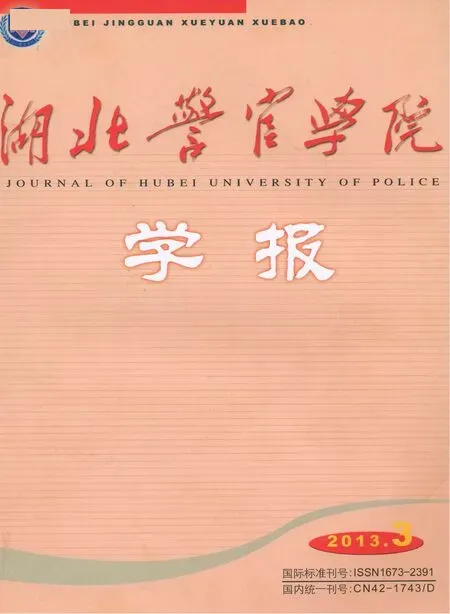对邓玉娇案的刑法学分析
2013-04-11黄思颖
黄思颖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08)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工作人员黄德智到当地雄风酒家梦幻城休闲中心消费。进门后,黄德智一人走入水疗区包房,见服务员邓玉娇在洗衣,便要求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表示自己是KTV服务员而非水疗区服务员,拒绝其要求,双方为此发生口角。后邓玉娇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尾随进入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加入。邓贵大认为自己来“消费”,理应得到服务,并拿出一叠钱朝邓玉娇的头和肩部搧击。争吵中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欲离开休息室,却被邓贵大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欲起身离开,随即又被推坐,邓玉娇遂拿起水果刀向邓贵大刺去,致其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见状上前阻挡,被刺伤右臂。后邓贵大因动脉割破、右肺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邓玉娇案情节并不复杂,但有几个影响定罪的关键情节的认定却饱受争议,这在巴东县当地公安部门侦查过程中先后发布的两个通告中就能发现。首先,邓贵大用钱搧击邓玉娇这一情节系二次通告时新增的,这一情节的加入似乎提供了另一种暗示:邓玉娇有可能是被邓贵大该行为所激怒,伺机举刀报复的;其次,原来“按倒”的说法改为“推坐”,这使得强奸的可能性大为减弱,防卫行为直接指向的内容是否为“强奸”有待研究。这些细节都是影响本案定罪的关键情节,涉及到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理论的要件,对于认定邓玉娇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邓玉娇的行为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正当行为,是指客观上造成一定损害结果,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实质上既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正当防卫是正当行为的一种,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不允许滥用,只有合法的防卫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致成立故意犯罪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邓玉娇虽然被免除刑罚处罚,但仍是“有罪之人”,这也是很多网友愤愤不平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邓玉娇是清白无罪的。
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可以分为防卫意图、防卫起因、防卫对象、防卫时间和防卫限度五个方面。从防卫意图看,邓玉娇对邓贵大和黄德智正在进行的“推坐”和羞辱有清晰的认识,该情形下很可能会继续对邓玉娇暴力伤害甚至是强奸,于是在危机关头拔出水果刀进行自卫企图制止不法侵害,以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及贞操,满足了防卫认识和目的两个要素,符合防卫意图的要求。从防卫起因看,邓、黄两人的不法侵害是实际发生并客观存在的,邓贵大多次的“推坐”已经威胁到邓玉娇的人身安全。从防卫对象看,邓贵大和黄德智是联合对邓玉娇进行侵害的,邓玉娇的防卫行为仅仅针对这两个当事人,完全符合对象要件。从防卫时间上看,邓贵大已经多次把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对邓玉娇的人身安全造成了现实的紧迫性的危害,邓玉娇遭到暴力和强奸的可能性仍在继续。综上所述,邓玉娇的行为完全符合防卫意图、起因、对象、时间这四个要件,判断邓玉娇到底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分歧明显地见于防卫限度这一法定条件。
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典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出于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可能带来潜在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的间接打击。法院判决邓玉娇故意伤害罪,认定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也即认定邓贵大等人的行为不属于“行凶”、“强奸”或者是“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刑法典关于“特别防卫”的规定本来就十分模糊,对“行凶”并没有确切的解释,至于“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到底包括什么、其判断标准是什么也没有详细叙述,这就为该法条的适用带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难。在本案中,公安部门提供的第二版侦查情况的通告中把“按倒”修正为“推坐”,且强调当时旁边仍有其他服务员在场,似乎客观上减弱了邓贵大企图施暴强奸邓玉娇的可能。至于邓贵大和黄德智的行为是否属于“行凶”,法院也持否定态度。从法院的角度,由于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邓玉娇防卫的是邓贵大企图强奸或者是严重暴力侵害人身安全的行为,也就无法认定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理论中“防卫限度”的要求。
本人对邓玉娇案的定性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邓玉娇的行为是基于邓贵大多次把她“推坐”在沙发上并企图侵害其人身安全而采取的,属于防卫行为。在主观上,只在于保护个人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而不是采取积极的行为报复邓贵大或者企图杀害他们,因此,可以排除成立故意杀人罪。
其次,在争吵中邓贵大确实有对邓玉娇实施暴力侵害身体健康甚至是强奸的可能和趋势,并且这种危害状态已经开始尚未结束,不能排除“强奸”这一“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可能,邓玉娇可以采取特别防卫,造成侵害人伤亡的,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邓玉娇在立案审查阶段就表示邓贵大是企图性侵犯,而公安机关使用“推坐”这一概念,也无法排除性侵犯的可能性。再说,在邓玉娇给警方提供的供词上,她说道:“我用刀刺他们前之所以没有警告他们,是因为如果我警告他们,他们肯定会将刀子夺过去,死的肯定就是我。”按照邓玉娇的认识和其他证人的口供,可以推知,当时场面紧张,二人已情绪失控,邓贵大和黄德智采取严重暴力手段报复、加害邓玉娇的危险已经生成。
那么,刑法典规定的“行凶”具体指何种行为呢?从新刑法颁布以来,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主要有四种观点:重伤死亡说、故意伤害说、杀伤说、暴力说。每种学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内在矛盾,但可以肯定,“行凶”必然具有以下几个内涵:第一,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罪名;第二,从字面来说,“行凶”必然有暴力、暴行的内涵;第三,“行凶”指代的暴力与其他规定中的暴力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凶”是无法判断为具体何种罪名的暴行;第四,“行凶”除了行为内容的暴力性,还有暴力程度的严重性、暴力手段的不限定性等性质。邓贵大、黄德智两人的情绪已经激发,对邓玉娇即将造成暴力伤害,并且伤害的手段可以说是严重的、难以预见的。邓玉娇主观上用水果刀进行自卫,系客观上由于两人身体争斗,从而造成了邓贵大的重伤死亡。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中,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一说,尽管这一原则不完全及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上,但在证据及事实上的适用是没有异议的。基于“疑罪从无”,美国刑事诉讼法在“安全”和“自由”两个价值的权衡之间,更倾向于选择自由。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同和法制发展阶段的差异,我们不能完全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但其司法理念有可以借鉴之处。本人仍处在法学学习的入门阶段,不确定邓玉娇案在中国是否也适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但无疑许多人所持的“正当防卫”的观点似乎具有较为充分的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邓玉娇刺伤黄德智的行为已超出防卫时间,黄此时已经停止侵害行为,因此邓玉娇对黄德智可以成立故意伤害罪。邓玉娇为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对邓贵大、黄德智两人采取防卫行为,符合防卫意图和起因;黄德智与邓贵大联合对邓玉娇进行侵害,也是不法侵害人之一,邓玉娇的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要件。但是,黄德智在上前阻挡邓玉娇时,实际上已经终止侵害行为,邓玉娇也就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因精神紧张,邓玉娇出于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对黄进行伤害,是情急之下的故意伤害行为,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
二、从犯罪构成理论看邓玉娇的罪责
法院认定邓玉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下面考察法院对罪名的裁定。
法院认为:从犯罪客体上说,邓玉娇侵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从客观方面来看,邓玉娇的防卫行为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非法损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一死一轻伤),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损害结果;在犯罪主体上,邓玉娇案发时为21周岁,在湖北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的医学鉴定中,被认定为心境障碍(双向),系部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邓玉娇的行为虽然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行为人对伤害结果处于故意,而对死亡结果则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属于故意伤害致死,鉴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另外,在影响量刑的裁量情节上,邓玉娇还具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综上,法院判决邓玉娇犯故意伤害罪,免于刑事处罚。
按照法院办案的逻辑和司法实践的惯例,邓玉娇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也没有太大不妥。作为邓玉娇来说,能够免于刑事处罚,意味着能够重获人身自由,从功利角度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现实中,像邓玉娇这一类的案件有很多,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有时候仅仅是毫厘之差。就本案来看,首先,如果邓玉娇的那几刀刺歪了,邓贵大捡回一命,似乎邓玉娇就很有可能无罪释放了。事实上,刀刺的部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由邓玉娇决定,在争斗过程中到底落在哪里纯属意外。所以,我对此持有很大的疑问:在判定一种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出必要的限度”时,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防卫人防卫的强度,而不是仅仅考察其防卫行为到底有无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其次,有必要强调邓玉娇采取该种防卫手段的现实必要性,至少不能期待邓玉娇可以采取其他相对温和的手段进行防卫。在德日刑法中,“期待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而存在,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对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罪过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本案,如果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就很难认定邓玉娇属于间接故意犯罪。
在外国,邓玉娇案很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争议处疑点过多而宣告无罪,而在我国,尽管邓玉娇难以作无罪认定,但应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法院判决的“故意伤害罪”。正当防卫理论强调,正当防卫本质上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故意行为。虽然刑法意义上的故意区别于日常生活上的故意,却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因为目的在于防卫犯罪就不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应当强调,故意行为不等于故意犯罪,故意行为是指有意识的一种行为形式。同理,防卫过当作为一种防卫行为,它对不法侵害的防卫必然是故意的,但不一定成立犯罪构成理论中主观方面的“故意”。防卫过当,是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所以,确定防卫过当的性质不应该根据防卫行为的性质(因为防卫行为一定是有意的,有针对性的),而应该根据是否把握必要限度的性质。假如防卫人忽略了防卫的必要限度,或者防卫人自以为能够把握防卫的必要限度而实际上未能把握,就有可能构成防卫上的过失,即防卫过当。由于防卫行为的有意性与犯罪故意有本质区别,所以防卫过当只能定性为过失,而不应该定性为故意犯罪。
在邓玉娇案中,如果法院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是正确的、合理的,那么根据防卫行为性质,防卫过当只能定性为过失犯罪,在此即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典对“过失致人死亡罪”明确规定:“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包括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这里的过失是对死亡结果而言,至于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影响认定。”对于邓玉娇来说,她并没有预见到邓贵大的死亡结果,她对这种结果持的是否定的心理态度,邓贵大的死亡并非她追求的结果,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其它三要件也明显符合。因此,如果认定邓玉娇是防卫过当,应该判决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三、结语
邓玉娇案至今众说纷纭,听闻各种版本的报道分析,不知道我们是在逐步地靠近真相,还是在集体愤青和集体狂欢中被蒙蔽了视野。以防卫过当判处故意伤害罪而免除刑事处罚,这样的结果是否与实情相当,已难以考究。尽管我们在对邓玉娇案的讨论中感到难以入手,甚至限于个人认识的局限而难以自拔,但在这一过程中都将更加熟悉刑法的“游戏规则”,也将坚守刑法学最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的刑法典编撰和刑事司法实务将因为法律人的孜孜不倦而得以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