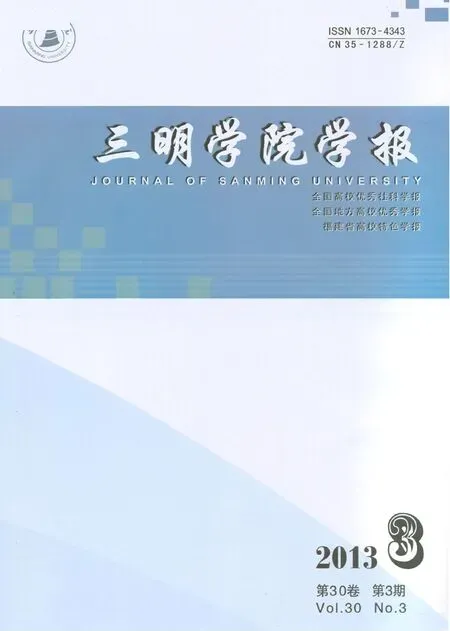宁化客家牌子锣鼓初探
2013-04-11伍荣生
伍荣生
(三明学院 教育与音乐学院,福建 三明 350004)
宁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客家音乐传统,音乐的体裁和题材丰富多样。就其民族器乐和乐种而言,有的来自中原大地的传承和发展,有的是南迁时从沿途传入并加以改造和发展,有的是由本土产生和发展。在融汇、吸收了南北地方戏曲、民族乐器、宗教音乐之所长后,宁化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器乐乐种和演奏形式。[1](P70)牌子锣鼓就是流传于宁化客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吹打乐,广泛应用于祭祀、庆典、灯彩、迎神庙会等场合,深为老百姓喜爱。
一、宁化牌子锣鼓的形成
宁化牌子锣鼓的形成与发展和闽中、闽西北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宁化自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建县,原属古汀州管辖,现隶属三明市。自“永嘉之乱”始,中原汉人延续了九百多年的大迁徙,闽赣边界的宁化成了先民躲避战乱的主要聚散地。客家先民进入宁化定居繁衍的最盛时期,正是客家民系形成时期。后来先民们又以石壁为据点,向外拓殖。客家先民一边播撒中原文明的种子,一边汲取当地文化的营养,无论是在迁徙途中还是在暂居之地,先民们最不会忘记的就是祭拜祖先、供奉神灵,希望祖先能给自己带来平安和温饱。在这种情况下,以祭祀娱神为主要目的音乐形式——牌子锣鼓便应运而生。
据当地老艺人口口相传,宁化牌子锣鼓传承于唐代,繁衍于明代。又据石壁镇唢呐艺人朱某回忆,朱某的师傅曾留一本手抄的工尺谱唢呐曲,该谱用毛笔抄写的线装书,上面书有“明正德XX年”字样。许多资料表明,唢呐是金元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原的吹管乐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唢呐已在我国各地广泛应用。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曾把唢呐用于军乐之中。他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武备志》中写道:“凡掌号笛,既是吹唢呐。”一般认为“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各地民间乐种的形成,不会早于明代初期”[2](P50), 由于宁化牌子锣鼓的主奏乐器是唢呐,没有唢呐就不成为牌子锣鼓。所以,可以由此推断,宁化牌子锣鼓出现的时间不会迟于明正德年间,至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3](P10)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复合体,并且是内部各种成分混合长成,这些成分大部分是自古就有的,也有从别的文化借入的。其次,每个文化倾向发展成特有的组织,这种组织是首尾一致、自成一体的。”[4](P52)宁化地处闽赣边界,与石城、长汀、连城山水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经济的交流,文化的融合势所必然。宁化牌子锣鼓的形成与十番锣鼓、赣南彩灯有着密切关系。
“十番”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合奏乐种,多属于吹打乐,如苏南十番吹打、苏南十番锣鼓、天津十番乐等,也有纯用打击乐器的“清锣鼓”,如上海十番锣鼓等。还有河北承德离宫音乐“十番丝竹”等则属于丝竹乐。[5](P28)此外,十番音乐在其流传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其变体或综合。闽西和清流也有着悠久的演奏十番锣鼓的传统,而且至今盛行。明代沈德富安《万历野获编》和张岱《陶庵梦忆》,清代叶梦珠《阅世编》等著作中,都有十番锣鼓演奏的简略记载,可见这一种乐种至少在明代即在江南流行。十番锣鼓的曲调源于元、明南北曲曲牌和地方民间小曲,所用乐器较多,按演奏形式可分笛吹锣鼓、笙吹锣鼓、粗细锣鼓和清锣鼓等多种编制。而清锣鼓不用丝竹,仅用吹打乐器板鼓、铜鼓、喜锣、齐钹。虽然宁化牌子锣鼓主要用于祭祀、庆典、迎神庙会等场合,从不参与婚丧嫁娶的活动,这与闽西十番锣鼓的使用有明显的不同,但在乐队体制上,牌子锣鼓与闽西十番锣鼓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江西石城,古属楚越,巫风极盛,先民们为祈求家口平安、丰登大熟、时常举灯以消灾避难、经年累月,致使石城民间渐渐形成了“事事当中有规矩,样样规矩不离灯”的说法。客家先民为了满足不同场合、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的不同心理需求,赋予灯彩丰富的内涵。石城彩灯所使用的乐器有板鼓、铜锣、大铙、大锣、小锣、大鼓,以及四面特大的双波锣,两支以上“三节号筒”、若干把唢呐。虽然乐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了宁化牌子锣鼓的规模,但其使用的曲牌如 《将军令》《进城去》《十杯酒》《担子歌》《甩金扇》,却与宁化牌子锣鼓有许多相同之处。
二、牌子锣鼓的乐器和演奏形式
在与多乐种交融、碰撞之中,宁化牌子锣鼓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酝酿,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乐队组织形式,乐器演奏还有一些独特的方式与效果。
宁化牌子锣鼓由唢呐、小鼓、边鼓、拍板、锣、钹等乐器组成。一棚完整的牌子锣鼓乐器不超过九件,乐队人员一般由六至七人组成:大、小唢呐各一人,小鼓、边鼓、拍板共一人,大锣一人,小锣一人,大钹一人,小钹一人(一般不加其他管弦乐器)。
牌子锣鼓主要流行两种唢呐:一是大唢呐,其规格为杆长28.5厘米—36厘米,音色柔和;二是小唢呐,又叫“马蹄子”,规格为杆长19厘米—27厘米,音色嘹亮清脆,常与大唢呐同时演奏,或轮流演奏。唢呐的表现力强,又是牌子锣鼓唯一演奏旋律的乐器,是宁化牌子锣鼓必不可少的重要乐器。
除唢呐外,大锣、大钹在牌子锣鼓的演奏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宁化牌子锣鼓的大锣一般的直径为36厘米左右,多为光锣,或称苏锣(因发音悠长而低沉,俗称苏音)。敲击大锣时,左手提锣或将大锣悬挂于前方,右手持锣捶敲打。大锣的演奏方法有放音、边音和闷音三种,配合旋律的变化,在演奏的过程中,掌控敲击的力度变化。
钹,又称“铙”,民间又叫“镲”。宁化牌子锣鼓常用大钹,直径约32厘米,碗径约15厘米,钹面宽大而厚,发音浑厚而悠长。牌子锣鼓的小钹,直径一半为18厘米,碗径约8厘米,发音清亮,善于表现热烈欢快的场面。在锣鼓合奏中,小钹常打花点为大钹做陪衬,为大锣与小锣起调和作用。由于大锣、大钹的音色低沉厚实,给人于庄重肃穆的感觉。
牌子锣鼓所用的鼓,俗称小堂鼓,鼓面直径约25厘米左右,鼓高15厘米,发音坚实明亮。演奏时,和边鼓并排放置在一个木制的框中,由一人挑着行走,前头挂一面大锣,由挑者打锣。鼓板师傅则跟在鼓板架后面,一边行走,一边演奏。
牌子锣鼓的板鼓是形体矮小的单面鼓,鼓身用硬质木材制作,鼓皮用牛皮,直径25厘米左右。一般用中堂板鼓,演奏时在板鼓的不同部位击打出各种不同的节奏,引导乐队共同表现乐曲所要表达的气氛和情绪。
牌子锣鼓使用的板,又称鼓板,由三块板组成。每块长29厘米、上宽5.5厘米,下宽6.5厘米,厚0.9厘米,两面平,盖板和底板稍薄,由一面中间隆起呈脊状,盖板的平面和中板用丝线缠绕前头,合并为一体。在宁化牌子锣鼓的演奏中,板常在乐曲乐队强拍上击奏。打板鼓的乐手,既打拍板,还要打小鼓、边鼓,还要协调、指挥整个乐队把握好速度与节奏,以及更换乐曲时的转板、续接。
牌子锣鼓多为边走边奏的表演形式。为了便于在行走的同时进行乐器演奏,艺人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简化了乐器种类和件数。二是为了在人员少的情况下,保证吹打乐必须具备的乐器,人们设计制作了一个木制框架,长60厘米、宽30厘米、高20厘米。框架的提把高约60厘米,前头挂一面大锣,(由挑担人按要求敲击)内置小堂锣、边鼓,由一人用扁担挑起。打鼓板的人跟在框架后面,边行走边打鼓板,指挥整个乐队。行进时的乐队排列是:小锣、小钹、大钹、唢呐、鼓板、大锣。
在法事、打醮等活动中,牌子锣鼓则多用坐奏。乐器的排列为神位案桌的两侧与前头:神位案桌前头为鼓板,左侧依次为大钹、大锣、唢呐;右侧围依次为小钹、小锣、唢呐。[6](P30)
三、牌子锣鼓的曲牌
曲牌,在宁化俗称牌子,由南北曲以及民间小调组成。宁化牌子锣鼓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曲牌体系。据调查,在宁化城乡广泛流传着反映不同内容和情绪的曲牌近200个。曲牌的来源有五:
一是唐宋时期遗留的词牌,如《玉楼春》《破阵子》《望江南》《虞美人》《渔家傲》《点绛唇》《风入松》《相见欢》《浪淘沙》等。
二是金元时期的散曲杂剧曲牌有《小桃红》《节节高》《水仙子》《清江引》《朝天子》《得胜令》《普天乐》等。
三是明清以来的民间小调、歌谣俚曲。而曲牌乐大都原为声乐曲,后在戏曲中改为乐器演奏,逐渐演变为器乐曲,后经民间艺人的润色、修改和完善,成为牌子锣鼓的固定曲牌。由于曲牌的来源不一,故其名称繁多,内容复杂,有的以地名命名,如《广东歌》《江州歌》;有的以原命名,如《买花声》;有的因字而传错讹,转义为名,如《朝天子》《醉翁子》;有的出于原曲歌词的部分词句。
四是原民间小戏音乐。如源自客家采茶戏和南词的 《湘子化斋》《卖花线》《牡丹对药》《打八仙》等。[6](P32)
五是红歌和流行歌曲的改编。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宁化唢呐艺人还把《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南泥湾》《纤夫的爱》《好日子》《十五的月亮》等群众广为传唱和喜爱的红歌和流行歌曲稍加变化,纳入牌子锣鼓演奏。这种配上锣鼓经的新编曲牌,让人感到既新鲜又亲切,不但保留了宁化牌子锣鼓的传统风格,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四、牌子锣鼓的音乐特点
(一)结构清晰
宁化牌子锣鼓的曲式结构为联曲、联奏形式,结构清晰,逻辑性强,往往是“大曲”演奏完即奏“小曲”,周而复始、段落分明。除开始的前奏和结尾的尾声外,中间段落全由长短不一的间奏(过门)把各种大、小曲牌串联起来,演奏时一气呵成,形成整体,如流行于石壁一带的“立新牌子锣鼓”就是由 《青光引》《浪淘沙》《怀胎歌》《玉美人》《节节高》《美女进城》《和番尾》《供堂》《点绛唇》《风入松》《急杀松》和《尾声》等大小曲牌组成。牌子锣鼓的长短,一般由司鼓人根据迎神赛会的实际需要而定,可多、可少、可长、可短,演奏时乐手还常常变化演奏、加花等灵活处理。
(二)调式交替
宁化牌子锣鼓的音乐中,调式、调性色彩丰富,但以徵调式和宫调式居多,常常出现五声调式中的“偏音”。如流行于泉上下村一带的曲牌《万年青》,就是在乐段中间通过以“清角为宫”等手法,变换调式,使得旋律风格不断发生变化。而流行于城郊巫坊村、方田朱王村一带的曲牌《凯歌》的中段,旋律中大量出现清角与变宫,通过 “变宫为角”等手法,使调式色彩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交替调式
还大量存在交替调式的现象,其基本特征是首尾调性(主音、音列或调式)不一致,或者首尾与中间段落的调性不一致。以同音列交替居多:构成交替的两个调的音列是共同的,不同的不只是调式主音,调式也是不同的。在这一类的交替调式中,最多见的是具有强烈支持力的四度五度关系的调。徵—宫交替,如 “立新牌子锣鼓”《节节高》;宫—羽交替,如“巫坊牌子锣鼓”《凯歌》;徵—羽交替,如 “巫坊牌子锣鼓”《和番》、“中山牌子锣鼓”《大骨牌》;宫—徵交替,如“南田牌子锣鼓”《耍金扇》;徵—羽交替,如“南田牌子锣鼓”《烟花女告状》等。这些参加交替的前后两调式之间有的出现过渡性质的片段,也有的是在结束处突然发生交替,转换到其他调式。
(四)双终止
在宁化淮土唢呐艺人吹奏的牌子锣鼓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长时值的宫音结束后,紧接着再加吹一个下方小三度的羽音来表示全曲的完全结束。这种具有调式交替功能的双终止,其本质也是交替调式。这种宫—羽交替,新调式出现的时间虽然短暂,使用的音也可能不多,但由于它处于关键性的结束部位,并能完满地结束全曲,因而能够建立起新的调式。[7](P343)
宗族祭祖是客家人最为隆重的古老礼俗之一,以同姓氏族为单位,由乡绅或长老牵头,族人共同捐资,在特定时间,举办隆重的祭典,借以缅怀祖先、团结族众、自娱自乐,具有家族团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特征。由于宁化牌子锣鼓庄重肃穆兼具气势雄壮、欢快活泼的特点,被普遍运用于民间迎神赛会和舞龙灯、装故事、喜庆一类的民俗艺术活动中,特别是为“庙会”等客家传统节俗活动增加喜庆热闹的气氛,至今普遍盛行于客家人聚居地。
牌子锣鼓是三明客家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我国客家音乐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挖掘客家音乐文化的独特风韵,保护和传承民族和地方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是我们这一代音乐人的责任。我们任重而道远。
[1]赖登明.试论三明客家民歌的艺术特点[J].三明学院学报,2012,(3).
[2]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C]//乔建中,薛艺兵.民间鼓吹乐研究.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3]钟宁平.宁化客家牌子锣鼓[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4]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理论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任舒静.中国传统器乐艺术瑰宝十番的起源与流布[J].大众文艺,2010,(20).
[6]王建和,张标发.宁化客家民间音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7]廖开顺.石壁客家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