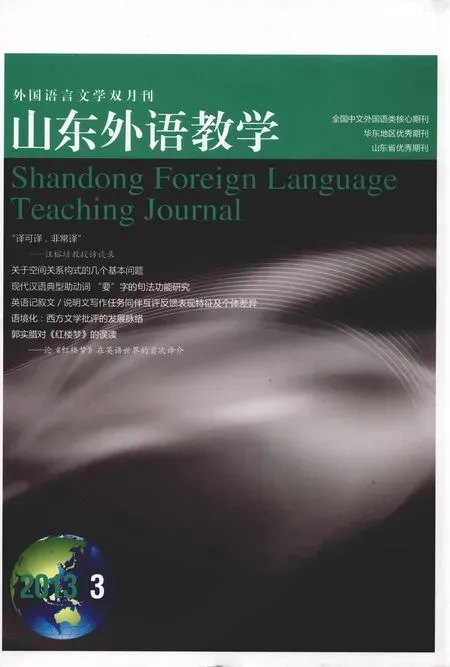《狄公案》的中西流传与变异
2013-04-10何敏
何敏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54)
《狄公案》的中西流传与变异
何敏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54)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伟大的汉学家与作家,他的《狄公案》系列创作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狄公故事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出发,通过高罗佩的翻译进入异质文化并影响到他的创作,而后再次通过翻译返销回中国本土的三个阶段。《狄公案》的流传与变异经历了起点—终点—返回起点的双向交流圆形循环过程,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反映了一种相互交流、反馈、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它代表着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价值与意义。
《狄公案》;公案小说;侦探小说;高罗佩
从19世纪传入英语世界开始,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为英语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古典小说的文学成就在获得国外读者认可的同时,也对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即是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创作的《狄公案》侦探小说系列。高罗佩将一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译入英语世界,又在此基础上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了130万字的侦探系列小说《狄公案》。《狄公案》在海外影响巨大,后来,中国译者陈来元、胡明将此系列小说译回中文,取名为《大唐狄公案》。而后狄公形象被搬上电视屏幕,使西方化了的狄仁杰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狄公案》这一系列的流动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比较文学影响变异学研究范畴内中国的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之间互动式循环交流的最佳案例。
1.0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英译
高罗佩是荷兰外交官,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懂15种语言,尤其精通中文和英文。1945年,高罗佩读到一本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为其中情节所吸引,将它翻译成英文,题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附注“一部中国十八世纪的真实侦探小说”(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译本于1949年于纽约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
高罗佩对《武则天四大奇案》的选材让当时的汉学家惊讶。小说是清代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公案小说,共64回目,以狄仁杰的政治仕途为主线,主要描写狄仁杰于武则天年间所断的四个奇案,属于传统公案小说文类。高罗佩选材翻译的原因是“在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爵士出生之前,犯罪文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很充分的发展”。(Van Gulik,1976:preface)在高罗佩看来,中国犯罪文学已经相当成熟,然而除了偶尔某些汉学杂志上会有零星片段的译文,这些作品没有一部被完整地引入英语世界。于是,他决定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成英文。他认为原作后30回关于狄仁杰仕途部分与断案无关,于是,只翻译了前30回。译本前附有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出场人物索引(Dramatis Personae),译文正文及译后记(Translator’s Postscript)。
高罗佩的译本对原文前30回内容基本忠实。无论是原文本的基本情节、内容、结构手法,或是中国话本小说一些特殊的套路,如章回回目、诗句,他都一一做了翻译。原文是典型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式的开头,开宗明义即是诗词及长篇关于清官的道德说教。高罗佩将这部分内容全部译出。只是做了一个结构的微调,将开篇的诗句翻译移到了对清官的议论之后。
在忠实小说内容的同时,高罗佩也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对原小说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他的译本前言堪称一篇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进行比较分析的平行研究优秀论文。从小说开篇、超自然力、小说细节、人际关系及小说结构上将中西两种相同类型的犯罪小说进行了归纳总结。他采取的修改原则是使译本尽可能贴近西方侦探小说的套路。虽然《武则天四大奇案》在公案小说中是一个特例,小说很适合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并没有在一开始让罪犯现身,作者在小说中没有使用大量封建迷信细节,出现的人物也不算众多,同时,作者的道德说教说辞也显得很节制。(Van Gulik,1976:v)然而,小说作为一部标准的公案小说,毕竟带有传统公案小说的浓郁色彩,因此,高罗佩仍然做了一定的修改。他的修改原则是:
1.1 制造悬念
高罗佩在“译者前言”中指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对小说悬念的处理。“中国犯罪小说无悬念可言”。(Van Gulik,1976:i)从章回回目来看,传统公案小说回目即是对本章内容的预告,读者一览全书回目,基本可明白小说内容。高罗佩出于保留悬念的目的,在翻译中对有些章回回目做了一些修改。“中毒的新娘案”中,新娘在新婚之夜突然中毒暴死,新郎胡作宾成为最大的嫌疑,被县衙收审。狄仁杰明察秋毫,发现真正的杀手其实是一条毒蛇。毒蛇歇息在胡家檐上,胡母烧茶时,蛇涎滴入茶水之中,胡母不觉而使新娘误饮身亡。因此,第23章回目题名为“访凶人闻声报信,见毒蛇开释无辜”。章回题目中明确提示了案情。如果忠实直译,破案过程顿时失去悬念。所以,高罗佩将此回目译为“Judge Dee sends his visiting card to Doctor Tang;In the Hua mansion he reveals the bride’s secret”(狄公拜访唐医生,华府解谜新娘死)。(Van Gulik,1976:163)译名隐藏了凶手是毒蛇这一关键细节,把悬念留给读者在阅读中体会,从而获得阅读快感。
1.2 修改不符合西方文化心理的情节
高罗佩对不符合西方文化心理的部分情节进行了修改。《武则天四大奇案》的“铁钉案”中,周氏通奸杀夫,这在男尊女卑、夫妻关系中丈夫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罪无可恕。因此,原文只要有周氏出现,必然称呼为“淫妇、淫婆”,不但暗示了她的凶手身份,亦是作者道德观的明确体现。高罗佩明显不赞成这种强烈的道德审判立场,他的译本将所有出现“淫妇、淫婆”的对周氏的称谓译为“Mrs.Djou”(周夫人),没有参入个人好恶。如第10回章回标题“恶淫妇阻挡收棺”,他译为“Mrs.Djou refuses to let her husband be buried”(周夫人拒绝收棺)(Van Gulik,1976:74);第15回原文题目为“狄梁公故意释奸淫”译为“Judge Dee allows Mrs.Djou to return to her home”(狄公释周夫人回家)(同上:107),采取了谨慎、客观的翻译措辞。此外,中国人际关系复杂,体现在传统章回小说里,会出现很多人名及各种家庭关系的指称,原文中出现的不少人名,对西方读者而言难以记忆,高罗佩在译本中专门制作了“出场人物索引”,一一介绍了主要人物及案情中所涉及到的人物。
从高罗佩对《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译者前言及翻译策略可以看出,高罗佩已经清楚认识到中西小说的差异。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虽然同为法律题材小说,都与犯罪与侦破有关,具有相同的文学母题,但叙事方法却很不相同。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类型,在“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下,作者首先关注的不是破案过程而是对罪犯的惩罚,以完成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任务。而侦探小说是一种西方文类,注重场面的紧张感,追求刺激的情节、科学的侦探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案件的侦破过程往往是侦探与罪犯的一场扣人心弦的智力较量。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差异正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特点。翻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流,译者常常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进行文化选择。因此,高罗佩翻译策略的选择正体现出他作为一名熟悉并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在跨文明的文学交流过程之中自觉进行文化过滤,对东方文本做出一定改编。这种在面对不同质文学的碰撞和冲击之时,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形与差异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具体印证。
2.0 《狄公案》系列的英文创作
高罗佩在翻译完《武则天四大奇案》后,认为“中国公案小说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刑事案例。因此我觉得,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将是一个有趣的尝试”。(高罗佩,2006a:序言)于是,他仍然以狄仁杰县令办案为线索,使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利用中国的罪案材料,用英语写作了 The Chinese Maze Murder(《迷宫案》)。小说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欢迎。于是,应读者和出版商的要求,高罗佩接连创作了《狄公案》破案系列,创造出狄仁杰这一与中国传统海瑞、包拯式清官形象有本质区别的神探。该系列小说被统称为《狄公案》,共有130余万字,由多个单篇独立的侦探故事组成。可以看出,高罗佩的著作受到《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明显影响,他的《狄公案》系列与《武则天四大奇案》明显一致的地方有如下几处:主要人物的一致,某些情节、人物形象作案手段的一致,结构的一致。
首先,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狄仁杰及其手下4名随员洪亮、马荣、乔泰和陶甘。高著不但使用了4名亲随的姓名,亦借鉴了他们的性格、经历。狄公与4人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断案的人物主线。其次,在案件侦破上,他借鉴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一些具体案例,“我写作的狄公故事情节,很多都有出处”。(高罗佩,2006:678)《铁钉案》中凶手陈宝珍的人物形象及“铁钉杀人”的作案手法,正是以《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周氏为原型。这是高罗佩的小说对原作案例的成功应用及改写。最后,《狄公案》虽然是西洋侦探小说,但在小说的结构方式上借鉴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前30回的结构方式,亦即中国公案小说的传统布局方式。“我在创作中保留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如写个序言或者内容提要,让读者在读全书之前对主要情节有个大概了解。有时我也模仿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在一些书的每个章回开头写两句对偶式的小标题。”(Van Gulik,1997:iii)这一系列西洋读者所不熟悉的小说结构模式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异域特色。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对高罗佩产生影响,让他在创作中成功采用了主要人物和一定的情节、结构。同时,高罗佩借鉴了西方侦探小说技巧,因此赋予了他的小说更多的内容和表现力,这正是一种借鉴与超越,是对其中国“原装货”的再认识、借用与改造的努力。高罗佩从一名西方人的角度出发,跳出原作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主题、古代公案小说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在小说类型、小说承载的价值体系、小说中的具体破案手法的运用方面都赋予了《狄公案》异域文化的特色,两书因此亦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感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狄仁杰法官的形象在两书中有很大差异。公案小说与封建社会的清官崇拜心理密切相关。中国文化传统注重道德,原作描述狄公为“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无名氏,1992:5)在这段对狄公的判断中,正反映出对“清官”强烈的道德诉求,对高尚道德的要求超越对智慧的渴望。亦正如高罗佩所说,“狄仁杰这一类的中国法官都有着高贵的道德品质、知识力量,同时亦是优雅的文人,通晓各种艺术,一句话,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很不幸,中国公案小说很少如我们的小说一样,对人物性格展开深入的分析”。(Van Gulik,1976:xiii)因此,狄公的形象高大全,几乎没有瑕疵,是个全能的人物,也因此显得单薄,脸谱化,某种程度上,狄公与其他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彭公并无区别。而西方文化注重理性与科学实证精神,因此高著强调狄公在破案中展现出来的智慧。狄公系列小说基本围绕着狄公立案、实地查勘及破案过程展开,重点放在狄仁杰的侦探身份上,忽略了其身为古代县令可能具有的其他身份。同时,狄公的形象也显得人性化,与西方小说中总是独自办案的民间侦探也有相当距离,他开朗、智慧、幽默,“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斗几个回合”。(赵毅衡,2003:95)可以说,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成功跨越了不同文化差距,成为一名贯通中西的狄大法官。
其次,就小说类型而言,两书亦有区别。《武则天四大奇案》是公案小说,体现出中国传统公案章回小说的特征,重视道德教化。在叙事上主要使用了说书人的全知叙事视角,大量使用套语和诗词,叙事时间往往选择时间的线性发展,节奏舒缓。断案方式则常常凭借直觉和表面感性认识,常常用严刑逼供迫使嫌疑犯招供。而高著属于西方侦探小说,虽然他对少量全知视角和套语仍然有所保留,但在叙事上采取了现代侦探小说的手法。狄公是故事的主人公,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他与四名亲随的关系一如福尔摩斯与华生,是侦探与助手的关系。断案手段更多借助严密的推理与论证,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注重侦探在破案时的解谜过程。《狄公案》系列往往三案并发,且时时案中有案,节奏显得紧张。整体说来,高罗佩的创作揉和了中西小说风格,在单个案件叙述中,他采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及破案手法。在整部小说的布局中,他采用中国公案小说多线叙事的方式,层层推进,将单个案件串连起来,构成了气势恢宏的小说结构。
第三,两书的文化态度亦有所区别。以对待中国鬼神文化为例,公案小说中常有超自然崇拜描写,公案小说破案过程中常有此类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对鬼神的想象,“法官遇到疑难案件,常常求助于问神托梦,甚至顺着自己帽子偶然被风吹去的方向去寻找罪犯。”(高罗佩,2006:16)这无疑与西方小说的文学旨趣大相庭径,侦探小说讲究逻辑实证,通过推理来排除案件上的重重疑团,给出合理的解释。鬼神想象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故事的真实性。因此,高罗佩的《狄公案》中,虽然案件常为一些神秘的现象所笼罩,然而破案过程仍然以狄仁杰的分析推理及实际调查来发现真相。以《铁钉案》为例,《铁钉案》中故事原型来自《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铁钉案”,在原故事中,为使罪犯招供,狄仁杰布下假地府,最终使罪犯伏法。对中国人而言,阴曹地府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对来世的惩罚想象,有着强烈的震撼。阎罗王、牛头马面对西方人而言,却是新鲜且难以理解的,因此,在高罗佩创作的《铁钉案》中,案犯陈宝珍亦拒不招供,使狄公陷入困境,然而帮助狄公最终得到破案的并非阎罗王,而是狱吏郭夫人,郭夫人帮助狄公明白了陈宝珍的做案手法,最终开棺验明伤情,得以破案。虽然故事从头到尾充满了神秘悬疑的气氛,高罗佩最终给了悬疑一个合理自然的解释。他的诠释是中西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的绝佳例证。
最后,在人物塑造方面,高著亦体现出明显的复杂和多面性。中国公案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脸谱化,作者很少对人物个性及内心加以分析、挖掘,也不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评估,仅简单地对犯罪结果进行道德评判。《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铁钉案”女主角周氏是通奸杀夫的女人,因此,如同潘金莲、阎婆惜一样,她被刻画成嫌贫爱富、见异思迁、荒淫无度,毫无可取之处,让读者极度厌恶,这是非常单一的人物形象。而高罗佩则赋予了以周氏为原型塑造的陈宝珍一个新的面貌。他对人物行为后面的动机进行了挖掘,陈宝珍杀夫是因为没能生儿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受到夫家嫌弃,婚姻生活如同地狱,杀夫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能引起读者的理解与同情。杀夫之后,她认识蓝大魁,与蓝相恋,然而,因为蓝要离开她,她又杀死了情人。这是个有强大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相夫教子贤妻形象有天壤之别。在审讯时,她平静地供述了杀夫的过程,对丈夫的死显然毫无悔意,而在供述杀蓝时,她失去了控制。“他要离开我……我不能没有这个人而活,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杀死他。”(Van Gulik,1977:118)陈宝珍的人物形象至此栩栩如生。她犯了弥天大罪,可恨、可鄙,但亦可悲、可怜。作者把陈宝珍放进了她所处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之中,两个有区别的女性谋杀者形象周氏和陈宝珍体现出两种文化差异,中国传统提倡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女性个人对幸福和爱情的追求基本忽略不计。而西方文化追求个性张扬与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我们可以看出,高罗佩的创作在借用“铁钉杀人”情节时,对周氏进行的改造。陈宝珍既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也聪明、独立、有主见,对蓝一往情深。陈宝珍已经成为一名西方化了的中国旧女性,她中西合璧,显示出性格特征、行为方式的多面性,人物性格也更饱满、更丰富。婚姻不幸造成命案的在传统公案小说中比比皆是,中国作者往往对此类案件中的女主角毫不容情,极尽鞭鞑,以维护封建礼教。而高罗佩在《狄公案》中处理方式则有很多区别,他对因婚姻不幸杀人的女性寄予了同情,但最终会将她们以各种方式审判,维护法律尊严,这亦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法制和理性的特点。
3.0 中译本《大唐狄公案》的特色
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一经出版,即风靡西方,前后翻译成10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且改编成电影。美国就曾经拍过电影《庙祟案》(Haunted Monastry)。鉴于《狄公案》系列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国人又再次把它译回为中文。由陈来元、胡明等翻译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先后由多家出版社出版。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最先推出《四漆屏》,而后,分别再推出《断指记》、《黑狐狸》、《柳园图》、《御珠案》,1985年出版《铁钉案》,而后,198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订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同一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狄公断狱大观》,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推出《狄公探案选》。2006年,海南出版社出版高罗佩《狄公案》系列的全译本,命名为《大唐狄公案》。而在影视界,1986年太原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狄仁杰断案传奇》之后,涌现出不少与狄仁杰有关的电视剧,如《护国良相狄仁杰》、《神探狄仁杰》系列、《神断狄仁杰》、《盛世仁杰》、《月上江南》等。狄仁杰大法官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之上,从此家喻户晓。的确,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的身上有一名欧洲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及文化的独特理解,亦处处可见西方价值文化观念改造过的痕迹,可以说,高罗佩的狄仁杰形象已经中西合璧。而后,中国译者将这已经西方化了的东方神探形象引回本土,并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译者对狄仁杰再次进行了中国式的再认识、借用与改造。
首先,中国译者将英文原著《狄公案》的结构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动。如前所叙,为了尊重中国传统小说,高罗佩的英文原著基本保留了明清小说的章回结构模式。以《迷宫案》为例,高罗佩使用了传统章回小说式的开篇布局,有诗词、判词、说书人套语。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无意中结识狄仁杰后裔,听他讲述了三桩扣人心弦的奇案,而后酒醉睡去,醒来后记录下这三桩案情。而中文译本《迷宫案》则对此做了改写,原文长达数千字的第一章被删节缩写成了短短两段话,直接进入案情。
其次,中译本与高罗佩原文的情节亦有所不同。以《迷宫案》为例,中译本《迷宫案》与原著比较,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写,这体现在对李夫人的处理上。在高罗佩原著中,李夫人是命案凶手,她与倪太守是朋友,倪太守建了一座迷宫,迷宫曲径通幽,不熟悉路线者很难有机会走出来。李夫人通过倪太守了解了迷宫的秘密,迷宫最终成为罪案现场,李夫人利用迷宫囚禁并杀害了白兰。至于谋杀动机,李夫人是一名女同性恋,她爱恋白兰,一见白兰即倾心于她,因此不择手段地将她囚禁,最终杀害。高罗佩在原文中这样描述,“李夫人为人变态,她喜欢年轻美貌的女子……因此,她保守了迷宫的秘密,以备不时之需”。(Van Gulik,1997:126)李夫人见到黑兰时,也赤裸裸地说:“纵然你与白兰不同,有些野性,用不了多久,你自会老老实实听从我摆布。”(同上:145)李夫人对同性的爱恋成为她的谋杀动机,这是《迷宫案》原文的重要细节。而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在性取向方面非常保守,同性恋明显不符合这种价值观,翻译中删去或淡化不符合中国文化考虑的性的内容,是国内译界的一贯作法。因此,中文译本基本删除了明示或暗示李夫人性取向的相关细节,使小说缺失了谋杀动机。为了使故事圆满,译者增添了闲汉牛二这样的角色。牛二是李夫人家奴的朋友,无意发现她通奸杀夫,趁势进行勒索,要求李夫人从此管他吃喝嫖赌,后来,更索性要李夫人送他一绝色美女为妻,因此导致李夫人路遇白兰,认为她可以满足牛二的要求,于是囚禁了她,最终无奈之中杀害了她。在这一情节的处理上,中译本变成了一种改编,因同性情感杀人变成了普通的勒索杀人。
我们来分析造成这种结构和细节上改编差异的原因。“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其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这部作品上打上各自的印记。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同文化的误解和误释。”(谢天振,1999:141)《大唐狄公案》里对原文的改编是有意识地改变原文形态,文化接受国的道德伦理观念对文学翻译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改编在比较文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罗佩热爱中国文化,他的英文创作带有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文化样式的目的,因此保留了明清小说的章回结构模式。而译回中文的《迷宫案》翻译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普通中国读者不但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已经陌生,且已经十分熟悉并接受西方现代通俗小说技法,因此,采用简洁直接的西方小说结构方式具有可行性。而在李夫人细节的改编上,西方犯罪文学中,强烈极端的情感往往成为犯罪动机,各种非常态的恋情并不少见。而在中国,同性恋题材一直受到主流的排斥。侦探小说做为通俗文学需要面向大众,照顾到大众的阅读和审美趣味,同性恋这个话题在译者看来对当时的中国读者不太适宜,因此,勒索杀人比同性恋杀人明显更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因此,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相悖,做了这种改编。正如译者在译本前言中所坦言,翻译中做了一定改编,“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使这部作品更接受中国公案小说本色及更符合国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里的有关情节、诗词、描写及人物对话等进行了适当意译”。(高罗佩,2006a:序言)狄仁杰法官从西方回到故里的过程又一次穿越了不同文化与语言体系,中文译本意味着狄公形象在流传过程中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再一次影响与接受。这种改编是译者面对不符合东方文化的异质文学作品时,对原文本进行的有意识的文化选择、排斥与融化。这是掺入译者本人审美和道德观念后很自然的反应。
4.0 结语
从旧唐书中的真实丞相狄仁杰,到清代公案小说中的“狄梁公”,高罗佩译本中的“Dee Goong”、高罗佩作品中“东方福尔摩斯”式的“Judge Dee”,到最后中译本中的县令侦探,狄公形象在中西文化中穿行,一脉相承又经历着不断地变异,最终作为享誉中西的大侦探,成为中西文学交流史上一朵奇葩。长期以来,中西交流中一直存在文化隔膜,东方形象不断被误传和贬低。高罗佩的写作唤起西方人对东方的热情,引导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形象,纠正误读与偏见。而他的小说又被翻译回中国,令狄仁杰法官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是一种典型的起点—终点—返回起点的影响与接受的双向交流模式,中西双方的影响与接受都不是单向的、绝对的,而是一种共享、平等的对话与互动。它的运动方式排斥着单一、封闭、狭隘的单一文化中心论,体现着一种世界主义的价值。在每一个传播的链条之中,无论是语言翻译,还是文学及文化形象层面,狄公形象都在产生变异,不断地继续、超越和发展,呈现出新的质体。这种从母语文化出发,通过翻译进入异质文化,而后再次通过翻译返销回原文的圆形循环过程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这是一种互相交流、反馈、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它代表着比较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1]Van Gulik,R.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ng An)[M].trans.R.Van Gulik.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76.
[2]Van Gulik,R.The Chinese Nail Murde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3]Van Gulik,R.The Chinese Maze Murde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4]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上、下卷)[M].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5]无名氏.武则天四大奇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6]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7]赵毅衡.名士高罗佩和他的西洋狄公案[J].作家杂志,2003,(2):96-9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irculation and Variation of Judge Dee Myste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West
HE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 610054,China)
Robert Van Gulik is a great Dutch sinologist and writer.His Judge Dee novels have exerted profound impact o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ry culture.Originating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ong’an tale,Dee Goong An entered the Western culture through Robert Van Gulik’s translation and produced influence on his writing.With the effort of Chinese translators,Robert Van Gulik’s Judge Dee novels returned to China with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vernacular novel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ourse of traveling of Judge Dee Mysteri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Being the rare successful cas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xchange history of culture,the circulation and variation of Judge Dee Mysteries experiences a two-way circular movement and reflects an interactive exchange,feedback,symbiosis and complementation.It stands for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udge Dee Mysteries;Gong’an tale;detective fiction;Robert Van Gulik
I046
A
1002-2643(2013)03-0104-05
2012-09-07
本文为2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语世界清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2YJC751021)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ZYGX2011J106)。
何敏(1975-),女,重庆酉阳人,比较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