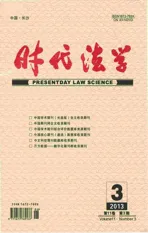非法言词证据之认定标准*
2013-04-10郭旭
郭 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案情简介〔1〕宿迁现首例对“非法证据”不予以排除案件[EB/OL].[2013-01-09].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212/t20121224_1015765.html.:
2012年12月22日,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任元武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该案存在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的请求,但该请求最终被法院予以驳回,这是宿迁市首例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证据”不予以排除的情形。
被告人任元武系未成年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案辩护人提出公安机关在讯问被告人时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要求对被告人庭前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辩护意见。本案经过公诉人的大量举证,同时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质证,最终被告人也明确表示在讯问阶段侦查人员未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因此被告人的供述不是通过非法方法取得,不属于非法证据,故法庭对该证据不予以排除。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本案中,公诉人通过举证证明对被告人的讯问不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法官认为被告人供述的取得并不是通过非法方法,认定了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但是,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在接受讯问时,应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倾斜保护,也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法定代理人未到场的情况下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供述是否应当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应该如何设定,我国应该如何进一步地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
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集中规定了应当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并根据证据材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其中明确指出对“采取讯问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确立了以是否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证据来判断言词证据是否违法的标准。在样本案件的判决理由中,法官也明确表示,被告人的供述并不是通过非法方法取得,因而具有证据效力。
(一)非法方法
各个国家或组织中对于“非法方法”的界定各有不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的“非法方法(取证)”范围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酷刑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这主要是从取得口供的方式来进行界定,判断的内容涵括肉体和精神;美国的概念则包括以违反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获取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宪法性权利集中规定在《权利法案》,即宪法第四修正案、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中,主要是通过法益是否受到侵犯的方式来予以判断;在德国,通过侵犯个人尊严的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并非必须排除,除非违反了宪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非法方法并不会必然导致证据排除,还需要根据综合情况个案判断。
(二)我国刑事法律中的“非法方法”
我国非法证据的认定以“非法方法”为标准,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表述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和“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这样的表述并不清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中的解释为“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式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中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为“适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
我国刑事法律中的“非法方法”以获取口供的方式来作为判断标准,进行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精神或者肉体的痛苦,其二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取得口供。从法律的表述上来看,如果不是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法院将会认可该份证据的效力。这样的规定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非法方法”的范围实在是太过狭小,仅相当于《联合国禁止酷刑》中“酷刑”的范围,这才会出现文章开头对剥夺未成年法定代理人讯问在场权而取得供述的证据效力之认定。
此外,无论是《高检规则》还是《高法解释》,都忽视了刑诉法第50条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对“非法方法”的界定上选择性地遗漏了“引诱、欺骗”等这些更加隐性的非法方式。引诱、欺骗行为并不如刑讯或者暴力、威胁一般赤裸裸地侵犯被追诉人乃至第三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但其危害性和影响力并不会较之更小。随着社会对暴力型取证行为的日益关注,这种隐形的非法取证方式将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替代措施,在样本案件“龙波等人诈骗案”〔2〕说你有“星范儿”,可能是陷阱[N].检察日报,2012-10-15(4).中就得到了体现。该案同案被告人甘某声称“承认诈骗是因为办案民警诱供,说承认后就放她出去”,这实际上是对侦查人员在获取其口供中的讯问方式的质疑。在实务过程中就应该积极区分侦查讯问技巧与引诱、欺骗的区别和界限。但无论是讯问技巧还是引诱、欺骗等方法,在本次刑事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当中都没有被作为认定非法言词证据的标准。
二、我国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之目的
我国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采取“非法方法”为唯一的认定标准,并且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所受之痛苦,以及言词证据取得的强迫性为双重条件。这种标准大大减少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空间,使得法官遵照法律进行裁判得出的结果很有可能与最基本的诉讼理念和价值不符。为了确保“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进一步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探讨,首先需要认清楚言词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其次必须探寻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历来就被认为是“证据之王”,这种观念在法定证据主义时代发展到了极致,尽管当代刑事诉讼推崇自由心证的观念,并不预先要求定案的必须证据以及设定这些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就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在侦查模式和方法当中就是着力于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处获得口供而“不择手段”。再加之侦查水平不高、科技水平的限制,口供就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手段也就层出不穷。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要求日益高涨并写入刑诉法总则,传统的侦查模式即使查明了“犯罪事实”,也很有可能基于非法取证而不予认定,不仅起不到打击犯罪的效果,还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声誉。
本次刑诉法的修订,一方面更加关注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水平和侦查能力,在传统的讯问、询问、逮捕、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尽管这些措施的适用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性限制,但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获取相关证据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对于类似样本案件中的隐秘型、对合型犯罪的侦办活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相关证据的获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做出口供提供了有利条件,即便没有供述,也无需使用非法手段,仍旧可以对其定罪量刑。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导向上来分析,在侦查过程中就应当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加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于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确实有利于实现侦查模式从“供到证”向“证到供”的转变。
(二)美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目的及评述
美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在Weeks案〔3〕Weeks v.United States,232 U.S.383,34 S.Ct.341,58 L.Ed.652(1914)中确立联邦层面的排除规则,并通过Mapp案〔4〕Mapp v.Ohio,367 U.S.643,81 S.Ct.1684,6 L.Ed.2d 1081(1961).将其适用到每各个州司法系统中。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又发展出众多的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况。在理论上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以下两种理由:
1.司法纯洁性说。公平正义应该是司法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公平正义不仅体现在实体层面,还应当包括程序层面。如果对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予以采纳作为裁判的根据,这等于是变相地认可和利用了侦查人员的不法行为,间接鼓励这些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行为,司法的纯洁性就会受到损害〔5〕Elkins v.U.S.,364 U.S.206,222(1960).。
但是,刑事审判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将证据排除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由于证据不足而不得对事实上确实有罪之人做出无罪判决,这也是司法的污点,因此,该观点在联邦最高法院之后的判决中被渐渐抛弃,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为抑制违法侦查说。
2.抑制违法侦查说。排除非法证据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或者诉讼人权,但判断应否适用该规则的依据是能否对警员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关于合法搜查与扣押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6〕The Court has stressed that the“prime purpose”of the exclusionary rule“is to deter future unlawful police conduct and thereby effectuate the guarante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United States v.Calandra,414 U.S.338,347,94 S.Ct.613,619,38 L.Ed.2d 561(1974)。随着证据排除规则的不断发展,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已经不再局限于宪法第四修正案,还包括第五修正案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第六修正案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第十四条“正当程序”的规定,等等。,非法证据排除本身并不能够也不是为了回复被追诉人权利所遭受的侵害〔7〕Application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is neither intended nor able to‘cure the invasion of the defendant's rights which he has already suffered.’”United States v.Leon,468 U.S.,at 906,104 S.Ct.,at 3412.,宪法修正案中并没有关于排除规则的规定,排除规则只是“为了保障修正案权利不受未来(警察行为)侵犯的司法救济”〔8〕We have stated that this judicially created rule is“designed to safeguard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generally through its deterrent effect.”United States v.Calandra,414 U.S.338,348,94 S.Ct.613,38 L.Ed.2d 561(1974).。如果不加区分而一律适用排除规则,除了禁止使用真实可靠的证据影响司法发现事实的功能之外,可能会导致有罪之人逃脱制裁,最终会产生对司法的鄙夷和执法懈怠。判断作为司法救济的排除规则在某一案件中是否适用,与被告人的第四修正案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是两个独立的问题〔9〕Whether the exclusionary sanction is appropriately imposed in a particular case,our decisions make clear,is“an issue separate from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of the party seeking to invoke the rule were violated by police conduct.”Illinois v.Gates,462 U.S.213,103 S.Ct.2317,76 L.Ed.2d 527(1983).,应该通过成本收益法(cost/benefit analysis)来分析证据排除能否对警员未来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在犯罪惩罚与证据排除之间做出抉择。如果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威慑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够适用〔10〕[i]f...the exclusionary rule does not result in appreciable deterrence,then,clearly,its use in the instant situation is unwarranted.Stone v.Powell,428 U.S.465,486,96 S.Ct.3037,3048,49 L.Ed.2d 1067(1976).。
抑制侦查违法说是目前联邦法院审判采用的最为常见的主流观点,但仍旧存在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遏制警察不法取证行为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并不明显,证据排除的案件大量存在。其次,侦查人员比较关心的是破案,也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即使用了非法手段,也不一定会必然导致证据排除。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每个人享有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该权利不得被侵犯”,没有明确的指出侵犯该权利的主体是警察,法官还是立法者。实际上,宪法修正案不仅是权利宣言,还应当是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并不仅仅意旨特定的警察机关或者立法机关。如果立法者立法规定了一个扩大警察对于逮捕、搜查、扣押之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无疑是为了打击犯罪服务的;其次,证据排除的最终目的究竟是“遏制”还是“人权保障”。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大量的先例表明,“遏制”才是证据排除的目的,但这又与该规则产生于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相矛盾,其来源决定了它的性质就是权利保障,是诉讼人权的价值要求和体现。如此,基于是否会产生“遏制”效果来判断应否采用证据排除的分析方式难免会招致责难。
(三)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目的
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为何,但是从文本的表述中可以进行分析讨论。早在2010年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制定宗旨是“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制定宗旨是“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层面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没有明确的表述确立该规则的原因,不过仍旧可以从本次修法的内容出发探求。
刑诉法第1条指明该法的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2条又加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证据一章第50条也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些内容可以被认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制订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也根据该法发布了相关的解释和规则,其中《高检规则》指出制定该规则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正确履行职权,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安部规定》中亦写道“保证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正确履行职权,规范办案程序,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从以上众多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可以归纳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设立有如下之目的:
1.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刑事诉讼是国家公权力行使追诉、定罪权的过程,是犯罪行为与刑罚的纽带。在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尽管在性质上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但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部分司法的职能。这些公权力的行使,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在证据特别是言词证据的取得上,更是要求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遵守法律的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能够以外部制约的方式,对享有国家公权力之司法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通过否定违反程序之诉讼行为效果的方式,确保程序价值的实现。
2.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刑事诉讼作为程序法,既具有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工具性价值,也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一方面是基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可信性不高,即使依照其“定罪量刑”,极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显然无益于刑罚的正确适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人应享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和尊重,这些观点在刑事诉讼中的反映就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得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有辱人格尊严的待遇或惩罚。以上要求已经写入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为我国加入的相关联合国公约所认可。
三、我国非法言词证据认定标准
我国现行法律中以“非法手段”为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如上文所述,将会极大地限制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不利于排除目的的实现。在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进行的言词证据排除判断中,应该采用分层次、综合性的认定标准。
(一)程序合法作为判断之前提
刑事诉讼法就是程序法。在公法领域,程序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力,奉行“法无明文规定则无权”的观念。之所以将程序是否合法作为判断是否存有非法言词证据的前提条件,其根源于公民对公权力的恐惧和不信任。在正常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早就提前设定了如何进行立案、如何开展侦查、如何获取证人证言等一系列的程序性要求,这些要求被认为是确保公民不受到侵犯的保障。任何“循规蹈矩”的诉讼行为都能够被推定为是有效力的、合法的,而任何程序性缺乏或者瑕疵都应该至少被认为是效力待定,在违反强行性程序规定的情况下,就应当被认为是无效的,获取的言词证据自然就没有效力了。强行性法规通常都有一些词语性的标识,比如“禁止”、“不得”、“应当”等等。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这些词语分别出现了2处、50处、362处,这些条文通常是对当事人权利之保障和对专门机关权力的限制。
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法官在判断未成年人在没有适当成年人到场情况下做出的言词证据并不属于非法证据,其依据在于该供述并不是侦查人员采用“非法方法”取得。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该条文在识别上可以认定为强行性规则,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更是要注重对这一权利的保障,在侦查过程中,基于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状态的不成熟,因此需要有相关合适成年人在场代为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这种要求被法律以强行性法规的形式所固定下来,必须要得到刑事诉讼侦查机关的严格遵循。文章开头提到的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以未成年被告人的口供取得不是基于“非法方法”而认定该口供的证据效力,这种做法切断了法条与法条之间的关联,没有将“尊重与保障人权”之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之始终,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证行为,是对诉讼程序的严重违反,取得的被告人之供述,无论是否有效,都不得作为定案之根据。
这种程序性设计安排并不是独立的个案,比如本次刑诉法第121条就明确规定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应该录音录像而没有录音录像的情况存在,那么获取的口供就应该予以排除。
(二)自白规则作为判断之要素
言词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通过“获取证据的方式”进行界定,并不适当,理由有二: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上来讲,很难将这些“方式”一一囊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难免需要进行解释,不同的裁判者同一行为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这未免使得人权保障之要求流于形式;其次,非法取证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行为”做出“交代”,而基于“交代”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后果,被追诉人通常是抵触与反对的,因此,对于口供是否非法取得,应该从被告人的供述行为出发,来判断他的心理活动,究竟是出于忏悔的自愿、权衡利弊的自愿,还是被威胁、引诱甚至是刑讯逼供的后果。
自白规则可以作为判断言词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之标准,其基本含义是“被告人的陈述必须是出于自愿的才可以用为证据,否则不能在法庭审理中采纳”。〔11〕杨宇冠.国际人权法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影响[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250.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自白规则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公诉人作为控方,如果要以被告人的供述作为支持起诉的依据,需要承担该供述符合自白规则之基本要求的证明责任,并可以此来对抗被告人的非法证据排除之申请。
不过,所谓的自白任意或者自愿做出陈述,归根结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控方显然无法对该心态进行直接证明,应该采用相关的间接证据,比如诉讼行为符合法律的程序要求,获得了律师的帮助,明知做出有罪供述的后果仍明确做出该种表述,等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言词证据的自愿性的证明责任必须由公诉人承担,否则就要受到证据排除的后果。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使得追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要收集可以定罪量刑之证据,而且要注意在收集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时,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自愿”之证据。
(三)人权保障作为贯穿之主线
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应该从程序合法和自白规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不能简单以获取证据之“手段”进行界定,因为后者无疑极大地缩小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判断层次上,应首先对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予以分析,考虑是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强行性规定,对这些规定的范围必然导致取证行为的无效,这是程序法的限权价值的重要表现。如果仅违反了一般性之程序要求,则需要考虑是否能够“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其次,基于言词证据特别是被追诉人之供述取得的特殊性,即使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仍旧需要对该行为予以更进一步的探究,只有在自愿、自由、明知状况下做出的陈述,才能当做证据使用。人权保障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应当贯穿于诉讼活动之始终,在非法言词证据之认定中,也应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和施行,是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任务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进步。非法言词证据的正确实施,必须以正确认定言词证据的“非法”为前提。我国法律中以“非法手段”为判断之标准,会使得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非法证据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不仅违背了证据排除制度的设置初衷,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应该以程序合法作为判断之前提、自白规则作为判断之要素、人权保障作为贯穿之主线,综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