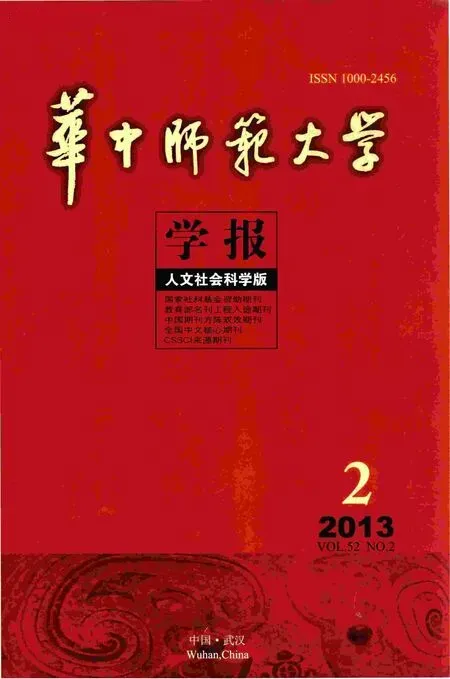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
2013-04-09王乾坤王书婷
王乾坤 王书婷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430074)
一门学科不能不对自己的合法性以终极考问。否则就会像一个人缺乏自我认同意识,不管其活到什么年龄,也不过是他者设定的某种角色,而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成人;无论他做了多少事,这角色多么光鲜,都谈不上自我实现,甚至可能是背离自身。
人的自我认同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伴随一生,因为人总是不断地遗忘自己。同理,一个学科的历史,也是这个学科的自我认同史,因为认同危机总是不断到来,因而需要不断地自我反省,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本来,回归自己。
本文企图取样一个特定时期的若干学术片断,来谈谈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思潮。为与所涉的文本一致,“现代文学”这个词在本文中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
一
正如人的出生并不由自己决定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事件:它既不由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演进而来,也不是外来文学突然“东渐”的结果,而主要为文学之外的因素所诱发。
不管史家将现代文学的诞生定于何时,有一点似无太多的争论: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产物,是“启蒙主义”的产物。没有鸦片战争而来的危机,就不可能有此后的实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和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抬高小说的地位,目的在启蒙。以他为代表的“文界革命”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后人只从这些名称上也能看出现代文学其来所自,姓甚名谁。这种取向不仅是早期“诗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白话运动”或者“五四”文学的取向,而且是一以贯之。此后百年的各种文学变迁,似乎面目各异,实则没离其初,不脱其窠臼:就其主流而言,中国现代文学附属于中国的政治革命、民族解放、文化运动。
参与并作用中国历史,一向被主流学界视作骄傲。这种心理让人们乐于惯性运动。就像劳碌之人很难想到追问“我是谁”一样,主流文学疏于对这种劳碌以怀疑。偶尔的怀疑从来就有,但未成气候。技术意义上文学认同也不能说无,比如流行的教科书中的作家或作品论,后边都有一个“艺术特色分析”的尾巴。还比如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陆续进行的“形象思维”讨论即有合法性辩护的某种因素,但通常不怀疑文学的角色错位。而且,对很多论者来说,强调“形象思维”,“以形象感动人”,是为了更好地行使文学的工具性角色或者现代化的使命,更好地献身。
以主流学界而言,对这种良好感觉以理性怀疑,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标志性的理论事件应该说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中青年学者1985年至1986年间发表在《文学评论》《读书》上的论文与对话(以下统称为“三人谈”)。
他们把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进行整体质疑,认定这个过程“政治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冲淡了一切。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中心环节而展开的,经常服务于它,服从于它,自身的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①于是他们要对这段文学史以重新诠释。
另寻文学“自身的个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意味着告别此前的角色设定而寻找文学的独立身份地位。这是笔者将“三人谈”看作文学认同学术链上第一个环节的依据。“三人谈”是在当时“文化自觉”背景下的“文学自觉”。然而,这个背景对后者并不只有支援之功而是利弊俱在:利在于借势打开思想通道,弊则在于简单化,在于前者以其强烈的社会磁场将后者裹挟进“文化现代化”系统,而轻忽文学的独特身份地位的学理论证。“三人谈”充分利用了前辈学者无缘有过的“新时期”资源,将20世纪文学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大磁场中,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
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②
很有概括力,它迥异于以往文学史的政治归结,有理由成为现代文学史论上的一块重要界碑。问题在于,其所辩护的是否就是文学“自身的个性”?如果不是,便不能算到位的合法性证明,文学的认同危机仍然存在。后来就陆续有人指出,这只是对文学政治革命功能的质疑,是用文学的文化功能代替政治功能,仍然是一种工具化归置。这样的论断也许忽略了“三人谈”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在质的判断上,却是一语中的。
虽然他们“总感到这一段的文学不太像文学”③,并且常常从审美出发对20世纪文学现象提出质疑,但理论自觉不够,尤其没能在本体论上讨论什么才“像文学”。他们眼中的“不像”,恐怕主要是指诸如郭沫若《防棉蚜虫歌》式的那种宣传品。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这也还是对文学宣传功能的清理。
与同时代的学者们一样,他们的学术兴奋点在对“非现代性”的批评,而不在对“非文学性”的检讨,还不能算自觉的文学认同。他们甚至没能注意到“文化”与“文学”的区别。这势必带来如下问题:第一,理不清“文化的现代性”与“文学的现代性”关系而把后者视作前者的部分,已如上述,这在事实上会忽略文学“自身的个性”。第二,轻忽这个时期非主流文学复杂性的考察。他们正确地看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始终不过是对现实积极的或消极的一种抗议而不可能是纯艺术的追求”④,但他们不曾对“纯艺术”的缺失现象以深度的探究。他们在正确地肯定文学使命感的同时却轻忽了文学对自身的承诺。至于现代主义对“文学自身的个性”可能的扭曲与敌对,他们没有察觉,虽然这早已是“世界文学”瞩目的事实。第三,同样的道理,也就很难透过“主流作家”的现代性色调,看到那后边跨时空的艺术之虹。比如钱理群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总是不愿进入后一个层面。(随便提及,这不是对一个学者学术侧重的非议。咬着鲁迅的启蒙思想不放,他本人倒是有意为之,并一以贯之,他从不讳言而且多次重申其“先天性的缺陷”。虽然这种局限妨碍了他对鲁迅思想的深层体认和心理探寻,却构成了他为人为学之品格。在当代中国,这个“品格”在思想和文化意义上是值得辩护的。但这毕竟是另一个问题。)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段,文化的自觉是对个性启蒙的高扬,它可以将人带入文学自觉的门槛。文化个性与文学个性属于同一个家族,前者无疑对后者有开路之功。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功作家,极少不是在个性解放的条件下成为个性作家的,有些则是一身而二任。也正是这个道理,“三人谈”是借着文化自觉向文学自觉的一次重要挺进。
然而文化的这种积极效用是有边际的。因为,即使不考虑文化对文学的冲突关系,文化也不是文学的栖居地,文化不能代替文学回答“我是谁”。正像寻找自我是人的本能一样,此后的现代文学在这种挺进中,越来越感觉到了不自在,于是有人不得不离队而去或转身而去,寻找自己的独立身位。世纪之交以来,何从何去,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茫然失据。有的作家干脆告别这一切主义与价值之争,或标榜“零度写作”,或进入本能性的个人体验,或进入躁动的城市角落和被遗忘的乡村部落。而批评家则开始对历史上的边缘作家发生兴趣,或者对主流作家的非主流层面加以留心。另有一些学者,则对曾经为之激动过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反思和学术清理。
“三人谈”在质疑旧模式的时候曾经正确地指出:
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⑤
现在轮到人们以同样的思想立场把他们置于被质疑地位。最系统而有深度的应是吴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吴文这样指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用“现代性、共同性和技术性”体现的对文学的把握、描述,主要是从文化、思潮、技术和材料等角度对文学的观照,而难以触及文学“穿越”这些要求、建立独特的“个体化世界”所达到的程度,难以触及文学对文化的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特性。⑥
因此他认定:
“20 世纪中国文学”观虽然突破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但并没有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而文化研究虽然不同于政治性研究,文化研究虽然比政治研究视域更为开阔、内涵更为丰富,但根本上说它依然是一种“非文学性”研究。⑦
这就顺理成章给出了一个突破“三人谈”的“文学性”模式。稍后,《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四位学者的笔谈(以下简称“四人笔谈”)就吴论展开讨论。谭桂林等学者肯定了这个运思方向:
通过引入“个体性”的史学观念,从文化影响的思路返回到纯粹文学自身的思路上来,这当然是对“20 世纪中国文学”观的一种反拨,是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一次很有深度的思考。⑧
不能说“三人谈”没有注意到文学性,尤其是黄子平总想把话题向审美方向牵引。但把审美心理(比如所谓“焦灼”、“悲凉”)放在现代化的框架下描述与在文学性的烛照下去考察这个时代的审美特性,还是有区别的。“三人谈”强调“总体性”,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吴炫响应这一号召,注意到了总体性;不同在于,他注意到了历史的森林与文学的森林之不同,他要强调的是后者。他通过大量的古今例证有力地证明,只有在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前提下,才能诠释不同作家的审美个性,而“现代性”、“民族性”或“世界性”等概念对寻找文学“自身的个性”无能为力。
“返回到纯粹文学自身”,是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也是现代文学的合法性辩护。不管吴文对诸问题的分述有着怎样的可商榷处,其眼光无疑达到文学反省应有的深度,那就是文学“穿越”其它要求,建立独特的“个体化世界”。他从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传播和呼应”中,看出“20 世纪中国文学工作者,一直是将文学放在‘从属于什么’的工具性位置上而不自觉。”⑨这个担心是有根据的,他在企图用文学“自身”的眼光重估一切。应该说,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史,吴文是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它标志着这个论域有了到位的理性自律,不再是自发性回归或经验性诉求。
这种理性反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吴文及其后来的申论并没为了所谓“纯洁”,将政治、文化之类从文学中剔出。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不是说文学脱离政治与文化,脱离政治与文化恰恰是受制于政治与文化的逆反性方式。因此‘逆反’不等于‘本体性否定’”⑩他看到“中国学者常犯的错误,是将‘政治权力’与‘政治生活’等而论之,从而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挣脱,推论为不关心政治生活的所谓‘学问’,并以为只有专心于‘学问’才是学术之独立”。⑪他并不否认“文学权利的转让或让渡”,他只是强调在本体论上:文学不可能允许自我外化为非我,从而使原来与自我同一的东西变成异己的东西。
一种理论在雄辩的时候难免对他人构成细节性委屈。“三人谈”更多地是在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模式,未必没有注意到文学的“应然”(什么才像文学)问题,未必就觉得文化问题就等于文学问题。但“三人谈”既然有文学本体论之失,而且这个缺陷构成了思维的短路,以致于“非文学性”,那么吴炫“乘虚而入”,补以新的因子,就有其合理性。何况吴文充分尊重先行者,是继起“三人谈”的“接着说”。
二
吴文的理论结构中有一块基石:“个体性”。他正是在此基础上非议“三人谈”而进行合法性证明的。人们会纳闷,“个体性”何指?它何以可能穿越“三人谈”的文化模式?“个体性”不也是现代启蒙因而是“三人谈”中的一个文化概念吗?没错,但吴炫有一个限定,他讲的个体性是“个体化的艺术世界”。可是这不也是一些老生常谈字眼吗?个体化的艺术世界与个体性的文化世界不是处于同一层面,而且有很大包含关系的术语吗?如果是这样,前者何以能够穿越后者,或进行“本体性否定”?
既然“个体性”是吴文的基石,那么“个体性”何所指谓,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关键。这一点吴炫很清楚,所以行文十分耐心。然而,他虽然有上述的精彩之论,虽然用到了“本体论”这样的思辩范畴,但是在立论方式上,却总是用知性逻辑说事,至少迁就了这种思维,这就很难夯实其基脚。
“文学性”不是看作家是否表现了“人的尊严与权利”,而是看作家如何对这一“共识”产生个体化的理解、体验与表现的,看这种“个体化”是否达到哲学层面上的独一无二。⑫
这是他对“个体化”最好的界说之一。什么是“哲学层面上的独一无二”?他也有一些较好的表述,比如:
“形象——个象——独象”就体现为“文学性”增强的过程,也是对作家要求越来越高的过程。“独象”或“由个体化理解派生的个体化世界”的含义是:真正优秀或经典的作品,不仅是形象生动鲜明或个性风格突出的作品,而且也有作家“自己的”世界观融入,并且由这样的世界观派生出自己的创作方法。⑬
不失理论见地,但是因为限于知性层面上讨论问题,其它学者也就有理由在同样的层面上对他的“独一无二”说加以轻松地反驳。谭桂林如是说: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仅仅引进“个体性”的概念就能解释清楚的。如果我们有兴趣翻阅一下目前国内比较通用的文学史著作,就可以看到,“鲜明的个人风格”、“独特的艺术个性”、“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等等与个体性大致相似的形容语句在史著中俯拾即是,被非常廉价地馈赠给许多有点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作家们。
个体性其实同民族性、现代性等等概念一样,不过是文学史观建构的一种维度,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显示出文学与它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由于这些维度都有赖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才能显现出来,因而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文学本体性的,都不能成为文学史的恒常不变的维度。⑭
谭文不满意吴文对“个体性”的表述,理由是“个体性”已落入大众语而成了廉价的东西,他要用“纯粹的文学本体性”,“文学的恒常不变的维度”代替之。虽然他“因噎废食”地处理了俗语中的“个体性”,但他所用上述语词恰恰是本义上“个体性”的另一种表述,并且与吴炫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谭文的“恒常不变的维度”和吴文的“独一无二”、“个体性”其实是一个指向,他们所要探究的,是文学的最终合法性,因而都是在推进“三人谈”中模糊意识到的“自身的个性”。通过谭桂林的学术接力或补充,“个体性”渐次明朗,可是我们还是不清楚,怎样理解“独一无二”或“恒常不变的维度”?或者说,怎样在此维度把握文学的“自身的个性”?
也许暂离问题略作纯学理考辨是必要的。
“个体性”是形上和形下语域都通用的语词,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思维中如果没有一种分辨,用语中如果不适时根据语域进行概念切换,这些字眼就会乱成一团。谭文看到了用语之乱,但因此不承认“个体性”的“本体论”指谓,断言“个体性”“都不是纯粹的文学本体性的”却是失当的。
二者都讲到了本体论。其实从他们都强调的“哲学层面”上讲,“个体”与“本体”并无冲突。所谓“本体”或“物自体”(二者常常被交替使用)指的都是非关系性的绝对个体。因而可以说,谭文的“纯粹的文学本体性”就是吴文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应该强调的是,哲学本体论上的“个体”不同于大众语中的某个单数,它只是表示先验的“唯一”。就像用individuality来言不可分的“个体”那样,它只是表示不可由他者取代的绝对个体。当然绝对个体一定得现象化地打开自身,不然它就只是一个无。于是就有风格或特色等方面的所谓“个性”,即谭文所说的“有限的个体性”。此意义上的“个性”不过是绝对个体的多样性呈现或展开。
因此,“有限的个体性”不配称本体论上的“个体性”,否则一定是廉价相许。这一点谭桂林看得很准,他意识到,“有赖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才能显现出来”的“个体性”,“不是纯粹的文学本体性”,因为没有恒常的终极的维度。这应该是一种洞见。遗憾的是,他也不愿在此处作应有的逗留,甚至不遑指出,吴炫没有将本体论意义的“个体”与关系属性意义的“个性”作应有的区别。谭文过于匆忙地将终极作了一种经验性处理:“终极维度却是文学的原创性”。⑮他要用“原创性”置换吴炫的“个体性”,认为“文学的个体性、民族性、现代性都应植根于原创性这一基点上,缺乏原创性的个体性只是一种有限的个体性”。⑯
如果按照谭文的驳论路子,“原创性”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词“在文学批评著作中何尝不可以“俯拾即是,被非常廉价地馈赠给许多有点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作家们”?
其实“原创论”是“个体论”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原创”作为一个生成论概念,是“个体”的动态表述。事实上谭桂林不经意间承认了这种关系:“文学的原创性其根底在于文学家生命体验的个人性”。⑰
所以最好将原创性与个体性联系起来,而作出一种本体论理解,不然无以言原创。因为由通常的思路来考察,我们总是可以从任何伟大的“原创作品”中找到非原创因子,找到它的遗传密码,不可能有例外。然而,由本体论视之,“原创”、“独一无二”之类的词并不如它们的汉语字符所暗示的一样,绝不意味个体在经验事实中不与其它因素发生关系。这就正像某棵树一样,我们说它是一个本体,具有唯一性,不在于它不与其父本或母本有着基因上的关联,也不在于它不与泥土、阳光、水分以及周边自然生态发生关系,而在于它不是泥土、阳光、水分,不是别的一棵树,而只是它独立的自身。在其动态的生成中,这棵树不仅不拒绝而且积极摄取其它因素,然而我们可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自足的“个体”,其秘密仅仅在于,这棵树循着它自己的生命目的来取舍万物,不拘一格“原创”着,从而成为它自己。
这样厘定可以解释作家的个体性,也可以说明文学与文化千丝万缕,又何以不是文化而是它自己。吴炫认定文学“性质上与文化不同而分立”,十分正确,但他没有充分借助本体论上的理论支点,所以很容易遇到逻辑学上的质疑,而让他的“分立”不大可能:
在“文化”与“文学”之间,事实上就存在着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等不同的关系角度,而且在不同的关系设定中,概念的指涉也有所不同。在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文化”是一个包括“文学”在内的总体概念,没有任何理由将“文学”排除于“文化”的范围之外,即便把“文化”缩小在“精神文明”的范围内,“文学”也是其中极为重要和极为活跃的一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与文化在性质上不同而分立,显然是不妥当的。倘若是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立论,那么“文化”就只是一个由许多特殊的具体中抽绎出的“共性”,是存在于诸种互不相同的“个体”中的“一般”;而每一个“个体”的生成与存在,也决不可能将这一“共性”的内容全部挤出。⑱
很有说服力。问题是,本体论不是形式逻辑。在逻辑范围内,一棵树当然是森林的一部分,而在本体视域中,一棵树就“如其本来”的只是一棵树,它不属于森林。同样的道理,在形式逻辑中,文学与文化也许能构成种属关系,但在本体论中,文学属于文化这个大前提并不存在,或者说这不是文学本体论思考的问题:本体论视域只是关心对象的“存在”及其生成,而对其关系判断存而不论(说“挤出”也无妨)。然而这种本体上的悬搁并不意味知性判断中不可以有逻辑划分。就像我们说某树是世上独在的个体,并不是说在其它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一棵树。也正像我们在本体论上为一个人神圣的独立性辩护,而不意味着在社会学意义上把人类从这一个体“挤出”一样。吴文并没有违背形式逻辑,说文学可以离开和逃避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并且没有说这些关联都是消极的,他只是对现代文学的合法性进行一种推敲,从而深化文学的个体性认同。但由于其支点有漏,正如他对“三人谈”一样,谭文也可以对其“乘虚而入”,发人深醒。
吴炫在强调本体论上“独一”没有错,将“个体性”当作其立论基石更是其眼光所在,要害在于他没有将这些语词作本体论与关系属性上的区别。其它失误皆由此而来。“四人笔谈”的质疑虽然不是在纵深处用力,却通过一个个横向性质疑,把这些问题给暴露出来(下文还将论及),从而推进了思考。
因“20世纪中国文学”而来的论述很多,这是一场延续了20多年的学理讨论。这样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多见(虽然后来不见下文而断链)。以本文所涉而论,不管作者和编者们自觉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是在艰难地攀爬现代文学的理论制高点,那就是企图在文学本体论视域中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
不期然而然的学术价值还在于,这种讨论具有普遍的文学研究意义。文学史观作为文学的观看立场,本来就是一般问题,没有古代、现代之分。现代文学不过是文学的现代生成,所以这里所谓“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不过是文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法性审视,而与狭隘的专业辩护毫无关系。自我认同问题也关乎古代文学的诠释立场。比如文学性与历史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同样的难题。此外,由于文学本体论问题关乎最一般的文学观,它同时对文艺学理论构成了考问。
这只是逻辑上推论。而在事实上,覆巢无完卵,“无家可归”哪里只是现代文学?
三
然而回家谈何容易?如果我们总是在习惯了的认知论和社会学意义上绕圈子,不管付出怎样的劳动,都可能误把他乡当故乡,甚至错把他人当自己。因此,以文学观文学,由终极处看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吴炫等学者的本体论视野可贵即为此。
然而,终极之维的“纯文学”从来不是可以验证的某种实体,不是经验思维中想象的某个时间段可以致达的终点。它也无法通过逻辑证明,而是一种审美向度。对这样一个向度的不断强调与复习,不过是防止文学异化为他物,防止文学定于一格而进入独断。其目的不是刻意营造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性”,更无意为“鸵鸟主义”辩护。刻意逃离现实生存状态,不能叫纯文学,因为它其实是逃向另一种精神化的功利之途,不能称为审美生活而同样是文学的异化。
缺失审美生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永远不能没有纯艺术追求,这是人类自由本能的要求,而不管人们是不是意识到这一本能。文学的本体论讨论意义在于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这一本能,在超越各种洞穴之见中进行自我认同。
“文学的自我”也不是某种实体,不妨说纯文学的代名词;因此“文学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无穷的过程。与其说它是“一尊”,毋宁说它的要义在于不断地否定“定于一尊”。在这一点上,吴炫并没有充分利用他已然触及到了的理论视域而提防可能的思维泥潭。文学性既然被当作一个本体论术语,那么,正像本体(物自体)不可能是空间中的“客体”,文学性不可能模式化。但他不小心给出了一些确定性判断,并给出了一个“以经典为龙头”的文学性模式。孔范今这样诘难:
当吴文排除了历史发展的内容之后,文学史势必就只剩下他所说的“以经典为龙头”的“不同的空间结构”了。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建构的多样性,但如果像吴文所倡导的这样,它将会是什么状况?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对经典作品的鉴赏和比较研究又有何区别?
本来,吴文的初衷是要反对一种绝对化的思维,但当吴文作者自己又偏向了另一极端时,在思维方式上所走的仍然是过去的老路。⑲
“四人笔谈”中的另两位学者分别指出的,也是其文学性模式的独断之失。指向很明确:《体系化: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弊端》(秦弓),《通向文学史的多元路径》(朱国华)。朱国华借用詹明信的理论指出:
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的办法。⑳
这都是对吴文的有益批评,不过如果只是以詹明信的话作结论,却可能掩盖问题的复杂性而导致另一种独断。其实吴炫注意到了文学哲学的维度并没有错,这是他何以能看到“三人谈”的“非文学性”的一个前提。值得留心的地方在于:哲学的维度不等于传统的体系化,它可能是营造体系,如无数既往的本质主义哲学家那样,但也有可能是“去体系”。现象学本体论就是这样启示的。因此吴炫的那个维度、那些术语是可以通过重审而存的,否则也是一种独断。问题只是在于:“本体论否定”不是“逆反”(这一点吴炫是清楚的);“穿越”也不应是奔向一个特点目标而去建立“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而在于不断指出“非文学性”;哲学上的“纯粹”之思不应是另寻一个“真理”,而不过是“防免误谬”。这是康德的话:
一切纯粹理性之哲学,其所有最大(或为唯一的)之效用,仅为消极的;盖哲学非用为扩大理性之工具,而仅为制限纯粹理性之训练,且其功效不在发见真理,仅有防免误谬之寻常劳绩耳。
谭桂林的“纯粹”应作如是观,吴炫的“穿越”应作如是解。如果以这样的维度去考量各种文学史,只要“分有”了文学性都有存在的理由。吴炫所主张的“以经典为龙头”的文学史当然有其地位,同时,其它的文学史建构,诸如“三人谈”的文学史和朱国华所建议的社会学的文学史、实证主义的文学史、心灵式的文学史、社会史的文学史、接受美学的文学史,“只要能够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或是以独特的方式解释了老问题,均可成一家之言”。笔者还要补充的是,只要不独尊,不仅上述“一家之言”皆可理直气壮,那些让学术家所不屑的怪胎,比如“文革”出品的文学史(假如有的话),也有存目的理由。因为后者没有发现和解决任何新老问题,却以极端的非文学性反衬出文学性,其“防免误谬”之“劳绩”别的文学史不可取代。
最后要补说的是:虽然本体论上的“独一而二”不是关系状态中的“一”,因此它不支持任何“独尊”,但这并不意味在关系性状态中诸类“神仙”全无高下之别(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是一个绝对个体,但不意味每个人“半斤八两”)。只是这高下不为政治、文化等外力来划分,而由他们各自对文学性的“分有”状况而决定。
注释
①②③④⑤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第1页,第37页,第9页,第27页。
⑥⑦⑨⑩⑫⑬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⑧⑭⑮⑯⑰谭桂林:《原创性的文学与文学史的原创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⑪吴炫:《论学术穿越政治》,《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⑱⑲孔范今:《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