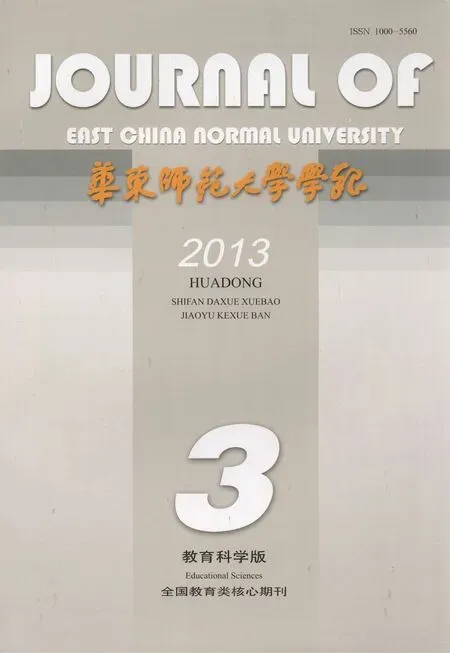百年中国乡村学校教学变迁的历史轨迹*——基于颐村学校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2013-04-08容中逵
容中逵
(杭州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杭州 310036)
晚清至今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学校教学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本文拟在对颐村(湖南省道县雷洞村)自有清以来乡村学校教学进行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基础上,按“环境”、“教师”、“教学”、“学生”四个要素,分“有清一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四个阶段,集中探讨百年中国乡村学校教学变迁的历时轨迹,以期对当下我国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晚清时期:作为传统儒家教育缩影的私塾
晚清时期,尽管国内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出现了保皇与立宪、维新与革命等意识形态之辩,社会各个方面由此也出现不少新的变化,但就颐村而言,该时期的学校教育仍未超出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具有中国传统学校教育固有的各个特征。
其一,从学校来看。这一时期,颐村学校教育的形式主要以私塾和义学为主,据史料载,清代道州私塾主要有“家塾”、“族学”、“门馆”三种形式,①私塾又分蒙馆和经馆,无论哪种形式都有固定馆舍。由于年代久远且村级史料有限,颐村私塾设置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察,但据村中族老学琇、乃煌、乃旷、学琳等诸公反映,颐村自立村以来就设有私塾,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初为家塾,次为族学,后为门馆且多以蒙馆为主的过程。此外还有义学,义学是为教育孤寡贫寒子弟而以公款或集资方式设立的学校,又分“考课班和识字班”两类,当时颐村本身并未设义学,其所属大西乡“义学有二,一设濂溪故里,久废;二设小水洞”,②虽说村中也有不少儿童前往西乡义学就读,但总体而言,入学者仍以本村私塾为主。私塾的规模一般不大,入学者约四、五人不等,塾馆通常都设在富贵人家中。据村中最年长者学琇公反映,他所知道的村中私塾最早设在他二叔家中,其大哥学珢曾在此就读过,时间大致是大清光绪四年(1878)间,上述私塾在行政隶属上均由清光绪二十八年设的劝学所管理。
其二,从教师来看。私塾教师无定员,以一人一馆居多,塾师多为乡村学究或不第秀才,束脩无定准,凭生徒年龄大小和家庭贫富自愿奉送,塾师收入虽高于一般人,但生活仍较清寒,他们常操中医或为人书写状纸。义学师资则通常以秀才、廪生或举人担任,其待遇无统一标准,视义学办学基金和教师水平而定。据史料载,当时官办的2所瑶族义学,教师薪俸为年支银26两,约大米480斗,可解决一家温饱问题。③这一时期,在颐村任教的塾师分别有胡焕文、冷桂馥两位,据《道州教育志》载,“胡焕文,清同治八年(1869)生,1941年卒,原濂溪乡洪家宅村人(离颐村约十里之遥)。光绪三十年取乙等补禀膳生,他终生以教书为业,他把家中水田卖掉,创办濂源书院,除在当地设馆外,还在永明、江华、宁远等地教过书,门生遍及几个县,著《劝善诗文集》曾传诵一时,对移风易俗起到较大作用;冷桂馥,清光绪四年(1878)生,1948年卒,是胡之学生,曾考取府学增生,他文思敏捷,才气十足,长期在大西乡任教,在教学中,除选蒙学教材、四书五经、诗词文赋作教材外,还教学生代数。二者均系当时大西乡的著名塾师”。④被访谈的学琇公(1917年生)声称:
“胡焕文、冷桂馥早了,我哪轮得他们教我,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大西乡有名的塾师,我父亲和祖父他们教过,我的老师是冷桂馥的学生周荷生。”(2008年2月12日访谈)。
按二人的出生年月及从教经历,辅以学琇及其他族老之口述,足见二位确实在颐村私塾任过教,且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要。
其三,从教学来看。这一时期,在教学内容上,私塾或义学均以传统儒学经典读本为主。私塾中的蒙馆和义学中的识字班,其教学内容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格律启蒙》等蒙学教材,达到能读、写、算即可,不参加县试;私塾中的经馆和义学中的考课班,其教学内容除此外,还读幼学、四书、五经、义疏、史鉴,习制义诗赋,修业完毕即应县试、府试、院试。在教学形式上,无论私塾或义学,其学习年限、生源、班级均无定制,一般视学生资质和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从一年到四、五年不等,可个人教学,亦可集体上课。在教学方法上,无论私塾还是义学,均为传统师生授受制,以教师讲授,学生识诵为主,教师要求十分严厉,动辄戒尺惩打,学生也因教师的严厉管教一般都能完成教师当天安排的学习任务。由于村中生于此间且就读过私塾的老人均已过逝,故对私塾中的详细教学情形亦只能了其大概了。
其四,从学生来看。私塾中,蒙馆的生徒多为七、八岁乃至十几岁不等的年幼者,经馆的生徒则多为20岁左右的应童试者,有的甚至已是生员,因不乐于县学教学松散或不被录于书院,故入经馆受业。上述塾生通常为富家子弟,义学的生徒则多为聚居周围方圆几十里的贫困子弟。这一时期,大凡入私塾和义学的学生,无论是否学有所成,不仅在村中族人中均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能通过自己的所学为村中族人的日常生活排忧解难,如写对联、写状纸、读写信函,同时,也为村中大小事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民国时期:私塾对新式学堂的僭越
民国时期,相继颁布《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均要求开办新式学堂并就学制和具体科目进行了规定,但就颐村而言,其学校教育仍以私塾为主。
其一,从学校来看。这一时期,尽管道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玉城书院改为新式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下令将各学堂改为学校,⑤但颐村并未设立新式意义上的学堂或学校,读私塾之风仍然很盛。举凡入新式学堂读书者,无不先是读了私塾再上学校的,有的甚至在新式学堂毕业后仍返读私塾的,上了私塾四年之久的乃旷公(1925年生)在访谈中说:
“到县城濂溪中学读书前,我在家都已读了四年私塾,后来毕了业,我又回来读了两年,我父亲说,啥时候都不能忘本呀”(2008年1月16日访谈)。而据集体访谈的学琇、乃煌、乃跳、乃旷、学琳等诸公反映,此间,颐村私塾先后于1918、1932、1947年设在新村陡砌、老村先杜、学灏家中。上述以私塾为主的情形直至抗战爆发才得以部分改变,1940年4月,为实施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和《保国民学校设施要则》,道县将原有213所乡镇小学改为339所乡镇保国民学校,使一乡有一所中心小学,一保有所一所保校。⑥颐村新式小学堂也于1942年创办,时称湖南省道县尚义乡第三保国立国民学校,设在老村祠堂中,后因1944年日寇入村被毁,搬至村东静水庵中直至1949年解放。在行政隶属及管理上,私塾属民间自发教育机构,由个人或村中自行管理;国民保校属公立教育机构,依次由教育科(1912)、劝学所(1915)、教育局(1927)、教育科(1940)管理。
其二,从教师来看。这一时期,在村中任教的塾师先后为周荷生、廖必仁、容先杜、胡仕先5人,塾师均为饱读传统四书五经的县学生员以上。如周荷生(1891-1959),乃晚清大将军周天翼的儿子、冷桂馥的学生,容先杜为永州府廪生,廖必仁、胡仕先均为县学生员。私塾强调尊师重道,束脩之礼按家庭收入自报奉送,一般为银洋10-20元,学生家长在端午、中秋、春节时都得向先生送礼。1942年新式保校设立后,道县县、区、乡公立小学的教师由校长聘任,只有1个教师的初级小学教师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委派且对教师任职的考核较严,⑦由于颐村属于只有1个教师的初级小学,故其师资由县教育局统一委派。1942至1949年,国民保校的教师分别为朱可耀、容学桂、容乃旷3人,他们均由国民政府任命派遣,具有正规学历和相当威望,如容学桂为当时村中首绅,财富学识均为魁首,朱可耀、容乃旷2人均为湖南省立第七师范毕业生。另据史料载:当时小学教师的薪俸,民初至1935年以银元计,1936至1939年以法币计,1940至1949年以稻谷计;1937年,小学教员的薪俸以学校所在地个人生活之2倍为标准,由区公所拨发,1940年经费改制,小学教师薪俸由筹有田亩的基金保管委员会直接发给,为每期谷12石。⑧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塾师还是保校教员,其待遇均有相当保障,且社会地位和威望也很高,已近九十高龄的乃旷公在回忆当年任教的情形时,不无感慨地说:
“那时候,我们是很受欢迎和尊重的,平日里家长请吃饭自不必说,族人在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时,我们都要被请去坐上宝位的,哪像现在,拿老师根本不当回事?!”(2008年1月16日访谈)
其三,从教学来看。这一时期的私塾,教材及内容通常由塾师视学生情形自由限定,学生没有现成教材,只有靠学生自己抄诵方有文字依据,教学内容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有《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左传》、《古文观止》、《万有文库》、《论说文精华》等,且从发蒙时便以后者教材居多,读过四年私塾的学琳公(1926年生)回忆说:
“我们那时候读的书比较深,用现在的话来说,启蒙时就相当于现在初中的教材,直接就是《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什么的,深得很”(2008年2月15日访谈)。私塾管教十分严厉,上午习字,下午读书,所读之书不能背诵或有其他越轨行为,先生们动辄打手板、跪香、饿饭,家长对此也表示同意。而此时的新式国民保校,实行班级授课制,其教育任务和内容除帮助村民识字、学文化外,主要是向国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三民主义和军国民教育。教师授课前,一般要阅读教材,自定重点难点,凭个人业务水平进行教学,没有写教案的规定,也没有听课的制度,教学方法多为老师讲、学生听,还有适当的课外活动。此间的私塾与新式学堂,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教学内容、方法上都有不小差别。
其四,从学生来看。此时私塾规模较以前更大,一般有子弟8至10人不等,且桌椅排比、坐次有序,但入塾就读者大多为富家子弟,一如被采访的芝龙公(1940年生)一再强调的那样:
“我六岁入塾,所有学生当中,就我一个人是凑傍(陪伴之意),嗬!彬哥佬、兰哥佬、先微、乃意他们哪个不是我们村的财主子弟!他们每人每年要交六、七担稻谷,因我是凑傍的,所以只需交两担就行”(2008年4月25日访谈)。这一时期,曾在新式国民保校就读的学生有学琳、学珉等14人,由于接受了上述学校教育,他们有的考取大中专外出工作,有的则在村中任教,或担任新中国的第一批村干部,成为解放后颐村的首批文化人。按理说,民国时期,由于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私塾应逐年减少,但据相关史料记载表明,“民国10年,道县仍有私塾81所,延师课读,尚无法取缔”,“民国18年,道县有私塾215所,学生2511人”,⑨不仅当时颐村私塾发展势头强劲,而且全县其他各地亦私塾多于新式学校,对此,司洪昌先生在其仁村教育的田野研究中也表明了类似情形。⑩
三、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村小的成长与辉煌
自1949年至1977年,我国先后进行了土改、大跃进、集体化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教育也随之进行了各项改革。尽管此间处于共和国的初创、曲折发展和严重受挫时期,但对颐村学校教育的发展却是一个黄金期,村小得到了巨大发展,在教育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其一,从学校来看。这一时期,由于1944年日寇对全村的武装侵袭,全村被烧,祠堂被毁,所以最初设在老村祠堂的国民保小便暂时迁至村东的静水庵内,当时办学条件极差,没有课桌椅,学生均自带板凳入学,以木为笔,以地作纸,但由于在校学生仍有60余人,故开设年级仍为一至四年级。后经村民重建,1955年村小重新搬回老村祠堂,重建后的祠堂分为两进,前一进为一、二年级,后一进为三、四年级,虽能遮风避雨,但办学条件仍然十分简陋,黑板自制,粉笔紧缺,学生仍需自带板凳,此后六年中,新老村适龄儿童均集中在祠堂村小就学。1962年,为贯彻就近入学方针,全村开始在新老两村分设两个村小,规模较小,开设年级为仅为一至三年级,此种情形直至1971年。1971年,颐村将新老村小合并,在新老村中间的水源头新建三栋六间教学用房,开设一至五年级的完全小学,除一间为教师办公外,其他五间均为教室,1973年,村小在原有基础上,在旁边建立四间公用教师宿舍和一个猪场,1974年,由于公社将下拨1800元小学校舍修理费中的400元拨给了颐村,⑪村小又兴建一个礼堂、一个操场,1974年村小开办初中一年级,原来两间教师宿舍又转变为初中教室,至此,学校初具规模并逐步壮大。1973至1977年间,村小另一难以置信的成就就是小学生入学全部免费,教材课本费都分文不收。另外在管理体制上,村小最初由于只有一个教师,日常事务与教学均为一肩挑,后来教师数量增多,开始采取校长负责制,校长由公办教师担任。
其二,从教师来看。1950年新中国为村小派来了第一位公办教师胡之道,所有校务教学均由其一人负责,1951年村上另推选了一位民办教师查玉美,1959至1961三年困难时期,胡之道调至邻近清塘乡任教,国家委派了另一名年轻的女代课教师李宗桂,1962年,国家又委派来一名公办教师何清荣,此时由于全县广招民办教师,故全村两所村小师资力量扩充,其中新村村小教师为容学珉、容乃谦,老村村小则为何清荣。1971年新老村小合并后,师资力量进一步得到扩充,有教师12人,其中公办4人,民办8人,1977年因2名调走,容从熊、容从彬二位加入民办教师行列。这一时期,村小教师的文化水平,公办教师均为师范学校的正规毕业生,民办教师则为道县一、二中毕业的初、高中生。公办教师均住在村小,民办教师则边做农活边教书。公、民办教师的工资均十分微薄:建国初期,小学教师工资以领取实物(大米)为主,由乡政府拨发,月工资约为大米180-200斤;1952年实行工分制工资,工资约为80-130工分不等;1956年实行货币工资制,月工资为23.5-40元不等。尽管1963、1977、1978三次普调工资,村小教师工资收入有所提高,但仍十分微薄。但村小教师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带领学生勤工俭学,1971年,容学珉、容乃谦、容从彪、卿进4位教师先后在一个暑假为全校学生砍树,锯成木板为学生自制了120套课桌椅,带领学生修建了一个简易操场,并安置了一个篮球架,还请木工做了一面乒乓球桌,解决了村小教室无课桌椅和活动场地的困难。1972至1977年,全校师生自力更生,利用下午放学和星期日拾茶榨油、烧砖卖瓦,努力改善村小办学条件。时任英语教师的容从彪(1950年生)说:
“当时我们起码榨了四、五百斤茶油,共烧了三窑砖瓦,按当时砖每块8分,一千皮瓦48元的价格,每窑出产的砖瓦变卖资金至少有1800元,不是这样,在国家和生产队没出一分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在1973到1977年实行全校学生入学全额免费就读?那时候可真的是连书籍课本费都分文不交的”(2008年2月18日访谈)。
其三,从教学来看。建国初期至1971年新老村小合并期间,由于学校规模不大且师资短缺,故新老村小采用的教学形式均为复式教学和教师个人包班制度。1971年新老村小合并、师资力量扩充之后,开始实行教师分科任教制,此时,全校分为语文、数学、音体美三个教学组。建国初至“文革”前,村小的教学内容以省里统编教材和应用文写作为主,内容虽然简浅,但基本能有据可依、有材可教,并能学习到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同志号召“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全国绝大部分中学开始串联,小学则开始完全停课,⑫故村小的教学内容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兼选一些“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然而,就是在当时其他学校纷纷流行“学习为革命,长大当农民”、“英雄交白卷,好汉打零分”的大气候下,颐村村小坚持了办学方向,始终以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文化为根本,向学生灌输“学生就是学知识,就是要会读、会写、会算”等基本观念,开展了基于毛主席语录的创造性教学。时任语文教师的容从彪(1953年生)说:
“当时所有的学校都不抓教学质量,我想,学生、学生,不就是要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但当时上面规定就是学毛主席语录,我没办法,只好采取这种办法,毛主席语录中,认得的字就教他们组造其他不是毛主席语录中的词句,不认得的字就教他们拼音”(2008年7月18日访谈)。正是在此思想认识指导下,村小师生群策群力,不仅十分重视基本文化知识的掌握,还在当时学校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形下,不惜重金购置了二胡、笛子、小号、鼓锣,以尽可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除维持正常的课堂教学活动外,也因陋就简,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比如,学校在春秋两季还举行春秋游,带领学生到都庞岭上砍柴、入茶树林采磨菇等。
其四,从学生来看。从建国至1971年,村小的生源绝大部分来自本村,1971至1978年,由于颐村小学办学规模变大,质量变好,附近村落的子弟也纷纷来此就读。村小规模也由建国初的40余名扩展到60年代的160余名,再发展到70年代巅峰时期的300余名,入校学生无明显贫富差异,但男孩入学率要远远高于女孩,据时任村小校长的容学珉反映:
“我们那时候(1971-1977年),你不要看学生那么多,真正女生不超过10%”(2008年7月18日访谈)。可见,解放后的女童教育仍然十分薄弱。这一时期,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村上所取得的教育成就是具大的,抛却上述学校基础建设、师资力量及素质等完善与提高外,最明显的就是学生素质的提高。1975年村小在全乡的文艺会演比赛中取得第一名,乒乓球比赛中取得全乡冠军,教学质量也十分突出,只要是统考各年级均为全乡第一,所以在附近乡镇中学中获得了“只要是颐村来的学生,我们都要”的美誉。建国初期村小不仅为全村扫除文盲,培养村干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高级小学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六、七十年代任大队会计的容从龙、容明德均出自村小并得到了全村和全乡人的高度认可。由颐村小学培养的学生,后来通过本乡洞尾完小考入县一、二中并升入大、中专学校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村自建国至1978年恢复中、高考三十年间,共计考取大中专院校24人,其中本科5人,专科10人,中专9人。至此,颐村一下成为全乡闻名的教育名村。另外,这一时期,学生表现出来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刻苦,举凡入校就读的学生,无论最终能否读出来,就读期间都相当刻苦,在当时普遍不学的时代背景和农活本身十分繁重的情形下,这种勤奋刻苦的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四、改革开放后:村小的破败与解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逐渐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迅速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高考制度的正常恢复以及教育事业的全面恢复整顿,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颐村村小逐渐步入破败和走向瓦解的悲剧阶段。
其一,从学校来看。1979年全县调整中小学布局,恢复并成立中心小学和学区,接着进行小学改制,1981年恢复六年制,村小办学规模逐渐变小:1985年,全县小学改五年为六年制,村小所办年级降为一至四年级;1996年,师资缺乏,所办年级为一至三年级;2004年,村小在县里检查时被定为危房,迁至新村大礼堂,所办年级仅为一、二年级;2005年,新村大礼堂也被评定为危房,随即学校撤除停办;停办后,村中适龄儿童或入邻近村小就读,或由家长租房至乡中心小学入读,这一情形引来村中族人极大不满,于是村中两德遂召集一班弟兄,径直找到村支书容修德商量维修村小一事,但因造价昂贵两年未果;2007年,村中出资将在水源头的原村小两间危房稍加缮修后,拟开办一年级,但又没教师愿意来村任教,在村支两委的几番恳求下,在乡中心小学任教的本村教师容从彬才勉为其难地回来教了一段时间。对此,从村小调至乡中心小学任教的容选龙(1952年生)无奈地解释道:
“唉,这种情况也没办法,上面要求三年级开设外语,村小是不可能再办到三年级了,现在中心小学都还缺英语老师,就算村小开办三年级,英语老师这一关都过不了,更不用说电脑等其他课了”(2008年5月12日访谈)。
其二,从教师来看。“文革”结束后,村小师资力量锐减:1978年,学校共有教师欧阳正、容学珉、容乃谦、容从彬、容从蛟、容选龙6人,除欧阳正为公办教师外,均为民办;1979、1984年容学珉、容乃谦二位先后转正调走,于是新民办教师容乃恕、何珍嫒加入,村小教师仍为6名;1984年欧阳正调走后,县里派来何瑞胡,1987年何瑞胡调走,唐运乐复任至1990年;1990年至1996年期间,村小新增3位民办教师容清、容乃恕、容从彬;1996年容学衔、容腾调回村小任教直至2004年,2004年村小只剩容乃恕、容清2名教师,开设一、二年级。这一时期,由于出色的教师纷纷考走或调离,而充任的民办教师又多凭关系上来,所以整体师资实力相对过去要逊色一些。在教师待遇方面,公办教师大致如下:1978、1979年两次调整教师工资;1982年1月执行干部工资标准,凡1978年底前参加工作的教师每人均增加了工资一级;1985年开始发放工龄工资和教龄工资;1987年增加工资10%,实行教师职称评聘制度;1990年实行人均工资普调一级;1993年开始实行工资奖励制度直至1997年。民办教师情形如下:1982年前计发本生产队工分3600分并由财政每月补助5元;1982年按本生产队人均标准分一份土地耕种,另由县财政发补助每月15元、村每年发40-50元不等;1985年工资改革、1987年以职称计;1990年普调增加工资10%,月工资分为三档,由县财政和村财政各支一半;1992年实行工龄补贴(每年1元),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公办教师;1998年底全县实行最后一次民转公。这一时期,尽管县教委采取了诸如听课制度、举办暑期培训班等举措来加强教师教学能力,但就颐村小学教师而言,因部分教师已民转公,许多教师都热心于自家农活,教学责任心薄弱起来,由此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师威望等下降。对此,容选龙分析说: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学生考起来,成绩都很不错,一般都会比其他地方的学生强,后来由于村干部不重视,教师也不负责任,所以就差了起来,我们的名声也差了起来”(2008年7月19日访谈)。
其三,从教学来看。这一时期,颐村村小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部分退化,从1978至1992年,尽管教师数量减少,但随着新增民办教师的迅速补充,村小基本保持了6名教师左右的师资数量,因此,小学的几门主干学科,其师资还有保障,仍能做到教师分科教学,此后由于师资短缺,村小又开始回到民国时期的包班制,一如容从彬(1954年生)所言:
“没办法,老师不够,只能和以前一样,每个教师身兼数门学科的教学任务,否则,你课都开不齐,对学生来讲是很吃亏的,对整个学校也不利,因为课开不齐,你就只有把年级往下降,本来可以开到四年级的,你就要变成三年级或二年级,这样学校就完蛋得更快了”(2008年7月18日访谈)。在教学内容上,教材日渐规范化、多样化,1985年村小改用六年制教材;1996年开始使用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此时因全县按要求编写了地方补充教材《我爱道州》,在小学四年级曾增加了这一乡土内容,但由于当时小升初只考语文、数学、自然三门,故教学亦不作要求。在教学方式方法上,颐村村小仍奉行师授生承的传统模式,因地处农村且学习任务不重,故村小学生的学习生活是自由的,犹如卢梭笔下的爱弥尔,除课堂教师传授的文化知识内容外,平时做做农活,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是一种课堂之外的自然发展状态。
其四,从学生来看。这一时期,颐村村小在生源上发生了较大变化,1978-1988年间,生源均为本村子弟且入学率较高。1988年后,颐村人开始大规模流向广东务工,随着外出人员增多、村小逐年破败、所办年级过低,难以满足儿童入学需求,故此间村小生源锐减。另外,这一时期,村小学生的学习态度上发生了较大转变,1978-1998年间出自村小的学生,其对知识和文化的认同程度依然很高,仍将有知识文化视为个体成长成败的根本评判标准,但1998年以后,随着家长和教师观念的变化,村小辍学率较高,许多学生读到三、四年级便外出广东务工了,1995年就去广东东莞务工的容韶顺(1978年生)说:
“那时候,看到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从广东回来后都穿得洋气了,每个月还有近千元的收入,所以就想‘她们也没读什么书,做死事嘛,在哪里不能做,总比在家里砍柴、放牛、插秧强,在家做这些事,哪个会给你钱哪?’所以98年过了年我就跟着他们出去了,现在虽然每个月也有千把元,见了很多世面,但终究发现没文化还是不行,好想原来多读几年书啊!”(2008年10月3日访谈)。这一时期,尽管颐村村小的学生也有很多考上了各类不同的大中专院校,但其结构与路径已有较大变化:高考制度改革和高校扩招前,颐村村小学生的路径明确单一,均通过小学——乡、县初中——县属高中——大中专院校来实现,学生和村中族人对此路径也高度认可;但1999特别是2004年后,学生及家长开始转变,认为不管是考取还是买取,只要能上个学校就行,故越来越多的颐村生源开始进入高校入读。据统计,1978-2008年三十年期间,全村共计考入大中专院校的109人,举凡在县城一、二中就读过高中的生员都会考入不同高校,此间还有4名获得博士学位,9名获得硕士学位。
五、百年中国乡村学校教学变迁的历时轨迹
纵观百年颐村乡村学校教学变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明显趋势:
其一,学校布点逐渐由大变小。有清一代,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乡村学校教育形式以私塾为主且生源多为富家子弟,但每村基本都会设有好几所私塾,从而确保有点可教。民国时期,除原有私塾外,成立了国民保校,国民保校为全村人而设,只要适龄儿童均可入学,故此时学校规模扩大、生源增多。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为普及初等教育,国家从政治措施上采取了一村一校、将学校下放至大队管理的格局,虽然此间出现了部分极端行为,但乡村学校在基础设施、入学生源、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得以较大扩展,由此许多乡村小学才会从原来只有四、五人的家室搬至可容纳几十人的祠堂或村小,有的还成了代帽中学。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上的改善,村小教学点的规模理应更为扩大,但事实上在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后,却因种种因素出现了反常,乡镇所在地的村小可能会被改造成中心小学,更多的是许多村小越发缩小,所设年级逐级下降直至撤并停办。
其二,传统师道逐渐由强变弱。有清一代,师表上的“君子”和“大人”、师法上的“威恩并重、术有专攻”、师职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和“诲人不倦、清贫乐道”⑬等传统师道得到高度认同,这既表现在村落社会对教师的普遍的尊重与敬畏上,也表现在教师本身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上。民国以降,尽管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私塾的减少,出现了新、旧教师的不同称谓,但人们仍将教师视为道之代表、礼之化身、德之典范。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国家诸种运动一度将教师地位降至“老九”、打成“右派”,人们对教师地位功用的看法也有所下降,但由于传统的惯性及此间教师仍能在诸如代写书信、教育族众等方面发挥实际功用,故传统尊师重教氛围仍较浓郁,人们不会怀疑教师知识的丰富性、伦理的道义性和教学的责任性,更无人会对教师的上述权威地位进行公然攻击。改革开放后,科技的发达、信息网络的挑战和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涨,教师此前那种威严清俊的形象逐渐为人们所淡漠,传统“师表”日益丑化,由于部分教师缺乏敬业进取精神,存有无视法纪、权力滥用甚至以教谋私现象,日益背离传统职业操守,故传统“师法”日益矮化、传统“师职”日益弱化。
其三,教学内容逐渐由土变洋。有清一代,中国乡村私塾的教学内容多为传统儒家道德伦常,与日常生活实践休戚相关,不管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表述的均系国人十分熟悉的“地方性知识”,⑭类似“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坐如尸、立如齐”等内容均源自切己的日常生活,都是“土”的,因而对学生来说,不存在难以认知同化的情形。民国时期,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和“五四”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西方内容开始嵌入课程,但由于乡村仍较封闭,对传统的批判尚未过多侵入乡村中来,故其教学内容基本还是“土”的成份居多。建国三十年间,尽管新的支配阶级对传统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与清除,但在教学内容上仍是“土”者居多,只是此时的“土”是真“土”,土到与乡村生活实践几乎等同,故学生们仍能将当时教材中的“鸡、狗、牛”、“毛主席万岁”等读得朗朗上口而未表现出任何不适感。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生产力的渐次发达和全球化的加速挺进,乡村教育内容开始逐渐“洋”化。此时,启蒙阶段的学生们开卷读到更多的是“斑马线”、“汉堡包”、“磁悬浮列车”、“芭芘娃娃”等,尽管城市儿童对此普遍能够理解,但对广大乡村儿童而言,上述内容却是相对陌生的,故当其读到这些内容时也就难免满脸惶惑。
其四,教学形式逐渐由多变一。有清一代,乡村学校的教学形式传统单一,基本特点是师传生受,识记和背诵是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民国以后,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及普及程度的提高,乡村学校开始采用班级授课制,尽管囿于师资场地等采取的是个人包班复式教学,但随着音乐、体育等科目的增加和诸如捡石子、丢沙包、滚铁环、跳绳等乡土课外娱乐活动的增多,教学形式还是大为丰富了。建国以后,在“教劳结合”的倡导下,乡村小学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重学生的活动,寓教于“做”,于是教学形式又多出了由师生共同参加的勤工俭学集体活动,此间,学校经常在农忙季节组织学生帮助村中困难户进行义务帮工,即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学生们仍可在与教师们的共同劳作中得到言传身教。改革开放后,由于乡村社会生活日渐个体私事化,加之大多数教师本身事务繁忙,尽管仍很重视课堂教学,但已不像往常那样顾及课外的事情,再之后,学校条件逐渐改善、教材日益丰富、所设科目越发增多,但学校教学的形式却越发局限于课堂之内,除因教学科目本身的要求外,鲜有教师再去思考如何营造课堂之外的教育教学形式了,如果村小被撤,可能起码的课堂教学形式也不再有了。
注 释:
①④⑥⑧⑨毛应宾、何如同:《道州教育志》,道县:道县一中印刷厂,1999年,第574页;第575页;第64页;第577页;第577页。
②③《道州志·卷五》,光绪三年修,长沙:湖南日报社资料组,1982年,第37页;第35页。
⑤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615页。
⑦1927年教育厅颁发《检定小学教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教师检定分为无考试检定和受考试检定两种,前者只需呈缴选毕业证即可:中师本科毕业;普高毕业任小学教员一年以上者;中师讲习所毕业且任小学教员三年以上者;大专毕业。后者经考试各科及格者,由省里发给检定书(详见毛应宾、何如同:《道州教育志》,第128页)。
⑩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第98页。
⑪《新车公社关于综合、教育方面的规划通知》,1974年6月18日,全宗号141,案卷号46,道县档案局藏。
⑫关于“文革”期间教育情形的论述,详见《“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全华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方晓东等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之论述。
⑬容中逵:《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关于中国传统“师道”的几点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7年第1期。
⑭[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