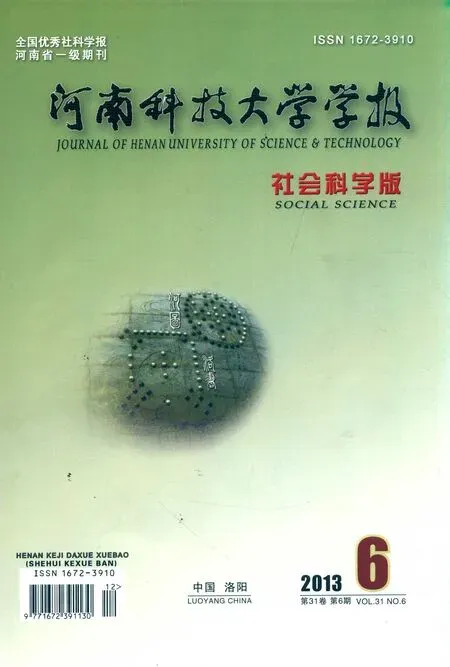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内忧外患与民众舆论诉求
2013-04-08丁健
丁健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安阳455002)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但历史的走向很快由民国初建的勃勃生机转至袁世凯专擅、帝制自为,再至军阀割据混战。习惯上人们把1912年至1928年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对之研究也常常停留在简单批判上,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束缚了研究视野。从价值中立角度看,为还原历史真相,需要多角度地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以展现其鲜活性。本文拟就北京政府成立前后的内忧外患、政局走向及其与民众舆论的互动关系做一粗浅探讨,以补既往研究之不足,并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内忧
(一)财政困难
高劳在民国初年撰文指出:中国向来财政上大弊有三:一、以某项之收入抵某项之支出,各抵各款,破碎支离,无通盘之筹划;二、行政机关,各筹各款,收入支出,各自直接,无提纲挈领之机关;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划界不明,隔阂殊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已紊如乱丝,经过甲午庚子之大役,赔款浩大,国用殷繁。辛壬癸甲间,益紊乱不可究诘。“凡遇筹款要政,大都指令各省摊派”,并增加各种苛捐杂税。[1]新政后,改户部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由于用款激增,清政府不仅加强了监督各省财政编制全国预算的集权措施,而且积极地对财政进行清理。对财政的整理“第一次相对查清了自咸丰军兴以来王朝财政真实的‘家底’”,[2]清政府更有效地控制了全国财政,但并不能改变清末财政危机的困境。
武昌起义前,除赔款外清政府已借了许多外债,这些外债仅以关税为担保,至武昌起义时尚未付清的款项就有八项,数目非常之大。[3]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军费日增,财政库空如洗。由于对清廷不信任,人们争相取款导致银行瘫痪。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田赋、盐课、厘金等,因时局动荡,各省拒不解交中央。海关又被外国公使团把持,拟将“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4]且“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作军费”。[5]收入断绝,清廷不得不发行爱国公债,可应者寥寥。为了维持局面,袁世凯多次秘密商议大借外债,但西方列强以“坚决拒绝向为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而斗争的任何一方贷款,除非证实其中一方已建立了稳定政府”[6]为借口,不愿意为袁世凯提供财政支持。
南方的革命阵营同样面临财政压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军队鏖集需款尤繁,不得不向外国借债。英、法、德、美财团拒绝给予贷款,日、俄为与四国银行竞争,特别是日本为乘机在长江流域发展势力,对南北双方均进行小额借款交涉,其目的主要则在售卖军火。日当时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共计四项:(一)沪军都督陈其美联络日本之大仓,借款数额日金三百万两;(二)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借款总额日金二百五十万元,年息七厘;(三)陆军部军装借款总额日金二百万元,年息八厘;(四)以汉冶萍公司名义借日款二百万元,年息八厘。[7]此外,南京临时政府还曾向其他外国银行借款。据《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6、34号和《中华民国史料》,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分别向华俄道胜银行、四国银行和华比银行等借金磅250万、银 360万两,以借军需和救灾,利率均为五厘。[8]
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正如有论者指出:“武汉起义,各省响应,于是北京与外省之财政关系,彼此断绝,当是时也,各省入款,凡地丁正税,厘课杂捐,或因革命而蠲除,或因战争而短绌,而出款则以征兵筹饷之故,其数陡增,罗掘弥缝,备极困难,其赖以支持危局者,大抵以劝捐及发行军用纸币暨公债票,为挹注补苴之策。”[1]“民国初建,各省独立,中央收入几等于零。”[9]
总之,民初北京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它不得不接收晚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一切债务。尽管当时国民捐款的呼声铺天盖地,人们也大都慷慨解囊,但杯水车薪。
(二)兵变时发
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举行和谈,军事冲突发生较少,但前期各方都招募了大量军队,军费开支极大。南方黄兴为筹措军费,“以空拳支拄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於吐血”。[10]北方为筹集军费也绞尽脑汁,发行爱国公债,利用内帑,甚至变卖珍藏等等。正因双方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才促使和谈成功。[11]革命结束后,如何安置这些军队就成为一大棘手问题,当时南北双方的主流意见是遣散军队,可是完备政策尚未制定,此消息就流布于社会,在南北双方军队中都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导致北方发生兵变。
时人恽毓鼎亲历了北京兵变。他在日记里详述了兵变发生的原因和经过:“甫抵家,即闻东城枪声震地,遥望火光烛天,有第三镇兵变之事……遂肆焚掠,北至北新桥,南至使馆界,东抵城墙,西抵皇城,其中灯市口、丁字街,皆罹其祸。到处纵火,逢门劫掠……排队鸣枪,出正阳门,掠西河沿、大栅栏、打磨厂、前门大街一带。至东车站,登火车,威逼司机人放汽开车,从容遁去。时天已大亮,火犹不息。土匪掠其余。”[12]578-579时人梁济亦有记述:“正月十一日,北京兵变,焚东安门,大掠于市。”[13]36但翌日袁世凯让毅军(姜桂题统领)守西南城时军士扬言:“第三镇兵均发财以去,吾辈独在此苦守,岂非痴人!”“外间又谣传总统放抢三天,西城商民即知大祸在眉睫矣。甫灯上,即闻枪声自南而北,火光时时出现。余知毅军亦肆掠矣,犹冀姜桂题出而靖乱。乃彻夜纵劫,并无一人弹压,巡警和之,地痞附之。”[12]579后来这批乱兵窜至天津,又“煽动天津陆军,四出焚掠,军民商店,多被焚毁”。[14]“保定亦被抢,不论贫富,均存四壁而已。”结果,北京“繁华锦绣场,一夜间变为焦土”。“近数年,天津繁华过于上海,今乃付之一炬。”恽毓鼎对之十分感慨:“北方元气,十年不能复矣……豢兵之害如是!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12]579-580
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抑更加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让人提心吊胆。有时甚至自然界的大风都能让人破胆。兵变后几日,恽毓鼎日记中记载:“夜,风尤狂,合家破胆之余,惴惴不敢安寝。”这在当时是相当一部分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民国初建,需要的是魄力和大胆的尝试,商业发展上尤应如此,可时局的动荡难免为农工商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兵变不仅让普通民众反感,也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在华外交团决议,先由天津调兵1 000人入京驻扎使馆界内以资保护,后各领事又电请本国政府派兵至天津。[15]同时,英、法、日、美各调200名,德、俄各调100名,以加强北京使馆区护卫。各国军队在京大街武装巡逻,间有马队驻扎城内,[16]英、俄、德、法、美五国合兵游街,以耀军威而镇人心,[12]580还增调军舰到大沽,以维持大沽的无线电联系。几天以后,列强军队陆续抵达京津。其中俄国由哈尔滨调兵3个连,进据京津;日本则由旅顺向天津增兵1 200名,其在华北驻军总数达2 400名。[17]并扬言“民国已无自治之能力,将以兵力实行干涉,化界防守,如庚子故事”。[12]580外国干涉的危险再至。
在内外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严肃军纪,接连发布布告、命令,以稳定秩序:“一、除巡警照常站岗,消防队更须准备一切,全城梭巡、防范盗贼等事,统责成毅军办理。二、警告三镇及洪营,听候命令遵行,不得擅自出入。三、如有不法匪徒夤夜扰乱治安,即行格杀。”[18]后又布告各军严守纪律,服从命令:“此后如再敢滋生事端,扰害商民,除重惩该犯外并将该管长官一并惩处,决不姑容。”[19]在强大的威压下,北方秩序逐渐稳定。为安抚民心并对外交团有所交代,袁世凯只得承诺对中外商民进行赔偿。
此外,党派纷争,总统与总理之争,总统与约法之争,复辟派的大肆活动等,都是造成民初内忧不断的根源。
二、外患
清帝退位后,南北统一实现,但北京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令人堪忧。
首先,北京政府必须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对民国的态度。尽管袁世凯先主动通电各国以示好:“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国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20]后又一再努力争取西方诸国的承认,可各国反应冷淡。由于“未得各国之承认,致国际交涉每遇困难”,[21]让袁世凯政府不能不暗中叫苦。
其次,外蒙、西藏和西南边境险象重重。民国成立以来,边疆所发生重要之事件,即为外蒙及西藏两问题。[22]569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外蒙古活佛宣布独立时,俄国就趁机干预。《东方杂志》载:“蒙古库伦活佛者,蒙人所奉之教主也,与清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夙多恶感。闻武昌事起,蒙人遂勃勃欲动。(1911年)10月11日,活佛率蒙兵,至办事大臣衙门,要求兵饷,三多未允,活佛遂宣言如无兵饷,应即出境,蒙人愈聚愈众,声势汹汹,三多乃仓皇出奔。避匿俄领事署,而活佛遂即宣告独立。”[23]后活佛甚至赞同俄人在库伦设立警察队,并训库民警务。[22]507袁世凯面对此情,固然想从速收复,事实上“惟仍拟首以和平手段从事,先行派员劝导,倘执迷不悟,再行另订对待办法”。[24]但由于外蒙古内部关系复杂,统一政府尚未建立,因而外蒙问题一拖再拖。后来,黑龙江蒙人在呼伦贝尔宣布独立,且复暗引俄兵,结果俄兵攻据胪滨府。[14]
在西藏,“清廷派驻西藏之军队,因川路事起,协饷无着。9月23日,驻扎拉萨之兵,首先变乱,涌至兵备处抢劫军火……波蜜、江孜等处,亦相继骚动。”因为英国在西藏问题上一贯作梗,整个民国时期政府为此交涉不断。在西南边境,“腾越厅干崖土司刁安仁,乘滇省响应革军之际,率土勇数千人,取道永昌府黄达铺,进攻大理府,而西南蒙人,亦驱逐清廷将军参赞,拟在乌里雅苏台建国”。[25]真是“以蒙藏之噩耗方来,滇辽之警电踵至;而日皇对于议院之愤言,其心尤为叵测,瓜分之祸,逞于目前”![26]
边境危机已让袁世凯应接不暇,随后又发生一系列棘手的外交事件。1912年2月19日,发生了泗水华侨被虐事件:“旧历元月二日因升旗燃炮事,与荷警察争执,闹起风潮,当场被搥毙三命,理伤十余人,掳禁百余人,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荷兵日日乱掳,全体罢市抵制,复以兵力嗾吓开店,事在危急,乞速解决对付,否则民不聊生。”[27]情况已经很严重,可荷方在法律上的无理规定,更是令人不能容忍:“凡华人因事被逮,不准向寻常裁判所起诉,必先监禁七日,然后提交甲必丹,任意定罪,不准本人或雇律师辩护。定罪后,即为终审,不能上控。此等苛律,只施之于中国人。”[28]因此,王宠惠又电袁世凯:“现在海内外函电纷驰,人心激昂,己臻极点,若无满意之交涉,恐激成他变,更难收拾。乞据此严诘。”[29]袁世凯答应积极处理,言语却透出些许无奈:“念三日即由外部电知驻荷刘使向荷政府交涉,并派员往诘驻京荷使,据云荷官未接荷兰政府承认公文,是以阻拦挂旗或当时彼此小有冲突,亦未可知,并非反对意思,其详情当即电询等语。廿四日迭接各电,当再派员往诘,荷使伊援前未承认葡萄牙之时,葡船挂旗亦不准进口,祗允电荷询问,总之,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援拯,惟现在政府尚缺统一交涉各事,每令人轻视,棘手极多,俟覆电后当再设法。”[30]泗水华侨被虐事件当时在国内掀起一阵风潮,各大报纸都连篇累牍报道,主张维护民族权益而伸国权,不仅给政府施压,也促使荷方态度软化并尽快放人。这表明中国人民参与外交的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日本也发生了干涉华商庆祝共和的事件。“神户华商因庆祝中华民国之成立,举行提灯会……日本警察忽然出街阻止,彼此互有争执。”[31]法国报纸又提“黄祸”之说。《申报》载:“近日,天津法报以中国革命成功曾载长论一篇,略云:中国素称睡狮,今一跃而驱去数千年之专制,此吾人所梦想不到也,故吾辈须知将来为我白种人之劲敌者,终必为黄种之支那人……是故我人对於中国此次之大改革,不可等闲视之,即谓之黄祸一说自今日始可也。”[32]总之,民初外交环境极其险恶。
三、民众舆论诉求
民初虽内忧外患重重,但民主共和思想逐渐在民众心中扎根。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社会思潮纷歧,民众舆论繁杂,虽意见难统一,但思想自由活跃,人们争相表达一己之见。通过梳理,本文姑且将其分为忧时派、乐观派、折中派和悲观派,以说明民初思想的多元化,且通过对不同派别政治诉求的表述,说明民众都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屹立东方。
忧时派对政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希望新政府崇俭,指出“万恶之原起于不节俭”;[33]希望政府破除专制余孽,“破除专制道德之习惯而为共同道德之基础”。[34]对时局他们希望政界:“满清之季,政以贿成……因此结果遂酿革命。今者民国新造,……惟愿勿生意见,勿存党派,对外则巩固国权,对内则尊重舆论。”希望工商界:“惟愿我资本家、制造家及时奋发,各出其心思、财力,专精于实业之一途,改良土产,以发展销路,仿造洋货,以挽回利权,工任其制作,商任其运输,互相维持,即互图进步,无以同业而倾轧,毋贪小利而忘大局。”[35]希望政党:“处今日之时局,乘革新之昌运,宜执行何种政策,始厝国家於不倾之地……于斯时也,非得有力之政治团体,以言论事实从各方面为之向导奖进……政党者,当国民思想浑沌之时,而与之以明灯,以烛幽昏之玄夜,使人心知所趋,而共同以致力于国家者也。”[36]希望国民要“祛虚骄之见”,敦“撙节之风”,宜“联络南北之情愫”,须“预筹南北统一之手续”。[37]忧时派不是仅仅忧时,更是希望国家步入正轨。
乐观派认为,民国成立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必然会带来社会进步。清帝退位后,他们立即提出告别旧时代跨入新时代,不由自主地喊出:“数千年神圣之君权,至此而为一挫,数千年遏抑之民气,至此而为大伸;由专制之国一跃而为共和之国,不谓今年一年中缔造此震古铄今之伟业,获睹此空前绝后之奇观,则今年之岁月有尽期,而今年之留为国民纪念者,将永无尽期也。”[38]有的则认为:“向例阴历年终必将国内大事撮叙要略,列表而系以论,盖所以资结束也。今者义旗一举,全局翻新,共和事业方在进行,则以前种种应以八月十九日之前为一大结束,而以后种种正如春草方生,有一日千里之势。”[39]“我全国人民务勉为共和国人民,而注意于共和精神之所在,组织健全优美之立法机关,建设健全优美之共和政府。”[40]“凌驾各强国,夫复何难。”[41]乐观派的主张在民初复杂的格局里,无疑就是一道亮光,冲刺黑暗。
折中派认为民初社会是一个半新半旧的社会。[42]基于这种认识,在用人方面主张“宜新旧兼收”,“宜南北并用”,进而指出“统一国家既立,本无南北可言,凡在一国之中,俱得参与国政”。[43]折中派的这些主张正适合民初政局,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在新旧矛盾之下很难实现。
悲观派主要是一些忠清的官僚、遗老,如梁鼎棻、梁济等。当时梁济就“慨然叹开创之初,淬砺不闻,暮气已见。以民国为号,而民困欲殆,顾不之恤,则革命云云徒为大盗窃国之资,辜负先朝禅让之盛美”。[13]37他们郁郁寡欢,总认为民国不比大清,消极遁世甚至殉清而死。他们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不能从对亡清的追思中解脱出来。这只是某些个人的思想层面,所占比重很少,其悲观、怀旧情绪并不能阻挡民初多元化时代到来的历史车轮。
总之,尽管当时人们的思想有诸多差异,但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出现,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尽快开展社会各项工作,以巩固东亚民国之丕基。[44]袁世凯北京政府起初也顺应历史潮流,各项事业渐次展开,财政逐渐有所好转,由靠借贷度日,到国库渐有盈余,外交危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遗憾的是,民主共和制度并未有效地贯彻下去,之后称帝、复辟、军阀割据接踵而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逐渐日暮途穷。
[1]高劳.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财政篇[J].东方杂志,1913,(7).
[2]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1851 -1894[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90.
[3][英]魏尔特.自民国元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关税纪实[Z].郭木,校阅.北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印行,1936:207-230.
[4]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911-1931):第2卷[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18.
[5]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M].北京:中华书局,1964:330.
[6]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26.
[7]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1962:88.
[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9.
[9]杨荫薄.民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2.
[1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0:176.
[11]丁健,李金全.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2-126.
[12]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M].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3]梁济.梁巨川遗书[M].黄曙辉,编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6.
[14]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1912,(10).
[15]专电[N].申报,1912-03-04(01).
[16]再记北京兵变情形[N].申报,1912-03-05(02).
[17]纪天津兵变后情形[N].申报,1912-03-07(02).
[18]临时大总统令[N].临时公报,1912-03-02.
[19]临时大总统令[N].临时公报,1912-03-03.
[20]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1912,(11).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26.
[22]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59.
[23]外蒙古独立始末纪[N].申报,1912-03-03(06).
[24]将派蒙古宣慰使[N].申报,1912-03-01(20).
[25]高劳.革命成功记[J]东方杂志,1912,(10).
[26]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53-354.
[27]王宠惠.王宠惠法学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21.
[28]再纪荷人虐待华侨之交涉[N].申报,1912-02-28(02).
[29]罗家伦.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上册[M].台北:国事丛编社,1967:488.
[30]北京袁总统电[N].申报,1912-02-27(02).
[31]日警察亦干涉庆祝共和矣[N].申报,1912-02-27(02).
[32]法报又提黄祸之说[N].申报,1912-03-02(02).
[33]崇俭[N].盛京时报[N].1912-02-01(01).
[34]道德之改革[N].民立报,1912-03-03(02).
[35]对于各界之新希望[N].申报,1912-02-23(01).
[36]吴虞.吴虞日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0-21.
[37]勗哉新共和之国民[N].申报,1912-02-21(01).
[38]辛亥年回顾录[N].大公报:天津版,1912-02-13.
[39]东吴.清谈[N].申报,1912-02-13(03).
[40]国体之解决[N].民立报,1912-02-14(01).
[41]辛亥年之回忆[N].盛京时报,1912-02-15(01).
[42]钝根.半新半旧[N].申报,1912-02-21(09).
[43]临时统一政府之人物[N].民立报,1912-03-17(02).
[44]论今日亟宜建设临时统一政府[N].申报,1912-0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