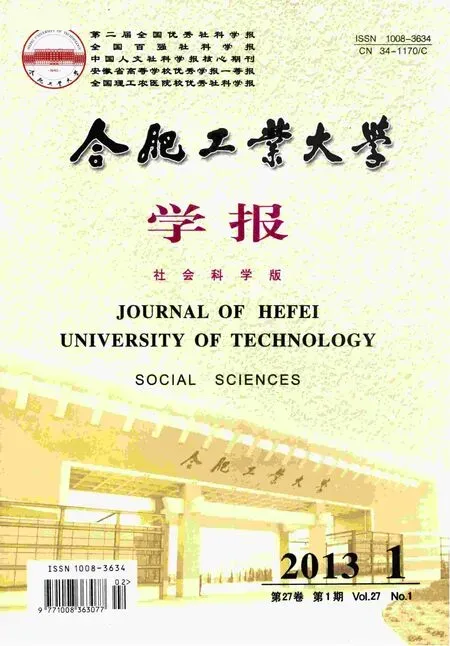汉代四家《诗》文本来源考辨
2013-04-07赵茂林
赵茂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70)
关于汉代《诗经》文本的来源,在汉代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得自私藏。《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1]3319又《六国年表》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1]686其二,讽诵所得。《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1708二说显然对立。如果汉代《诗经》文本出于私藏,则《艺文志》所言就是错误的。那么,汉代《诗经》文本是否出于私藏呢?
一、汉代四家《诗》皆得自讽诵
《史记》之言是以《诗》、《书》盖称“六艺”,非专指《诗》、《书》。不过盖称“六艺”,也自然包括《诗》、《书》。但《史记》只于《书》的私藏有记载,《儒林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1]3124伏生之《书》出于私藏无疑。至于孔氏《古文尚书》,司马迁虽没有明言是否为壁藏,但揆之《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1]3125,也应该是私藏,但于《诗》却没有私藏发现的具体记载。《汉书》记载古书发现之例要多于《史记》,但同样没有《诗》本发现的记载。其他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王充《论衡》、许慎《说文解字·序》等都论及古书的发现,但皆未言有《诗经》写本的发现。
刘毓庆、郭万金猜测《毛诗》“是一部幸存的文字文本”。郑玄《毛诗谱·小大雅谱》“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乱甚焉。既移,又改其目。’”[3]552-553以为由“师移其第”、“乱甚焉”的表述中,是“不难领悟到这是一部与孔壁遗书有相同经历的经典”[4]。但这个猜测实际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郑玄出于“正变”理论解释《十月之交》四篇为“刺厉王”之诗,与《毛诗序》“刺幽王”不同,因而以“师移其第”、“乱甚焉”为自己的解释张本。《十月之交·序》郑注:“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3]718应该是已经断定《十月之交》等篇不是刺幽王的诗,进而寻找《毛诗序》何以把其定为幽王时诗的原因,以“师移其第”、“乱甚焉”来解释,显然是一种推测,并没有什么依据。《十月之交》开篇:“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提到了日食,以及发生的时间,是可以作为此诗系年的重要线索的。据唐代傅仁均及一行推算,幽王六年辛卯朔辰时发生日食[5]611,则《序》所言“刺幽王”,并没有错。而《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6]26“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6]27与此诗“百川沸腾,山冢崒崩”也相合,也可说明郑玄改《序》之“刺幽王”为“刺厉王”不正确。而郑玄之所以定《十月之交》为刺厉王之诗,可能是采用了《鲁诗》之说,本非《毛诗》之义。《汉书·谷永传》载成帝建始三年谷永对策曰:“……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2]3446师古注曰:“阎,嬖宠之族也。扇,炽也。臧,善也。《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阎妻扇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致灾异,日为之食,为不善也。”[2]由师古注释是可以看出《鲁诗》是以《十月之交》为刺厉王诗的。《鲁诗》以《十月之交》为刺厉王诗,而由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也看不出其篇第与《毛诗》有什么不同[7]9。而《韩诗·十月之交》的篇第也是与《毛诗》相同的。《毛诗正义》说:“今《韩诗》亦在此者,诗体本是歌诵,口相传授,遭秦灭学,众儒不知其次。齐、韩之徒,以《诗经》而为章句,口相传授,与毛异耳,非有壁中旧本可得凭据。或见毛次于此,故同之焉。不然,《韩诗》次第不知谁为之。”[3]719说《韩诗》学者“或见毛次于此,故同之焉”,显然是臆说。而由“《韩诗》亦在此”,足以说明郑玄所言是不正确的,那么以此来推测说《毛诗》“是一部幸存的文字文本”,也就是不正确的。
刘毓庆、郭万金还认为《毛诗》中的错简也证实了《毛诗》为古写本。实际《毛诗》的错简并不能说明《毛诗》一定为古写本的,而讽诵、记录更可能导致篇章的颠倒错乱,因为讽诵全凭记忆。再则,前已指出,在汉代,学者多论及古书的发现,从来没有提到《诗经》。《诗经》为“五经”之一,在汉人眼中其地位远远高于《论语》、《孝经》等,但对《论语》、《孝经》尚且有发现的记载,如果有《诗经》写本的发现,学者不会不提。再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来看,也可证明汉代没有《诗经》写本的发现。《艺文志》对古文写本尤其重视,除了在各类经典小序中记载古文写本的来源,而且在各类经传的著录中,总是把古文写本置于最前。但《诗经》小序并没有专门说明《毛诗》文本的来源,而在《诗》类经传的著录中也是先列三家经文,而后为三家传记,最后才是《毛诗》经传。所以,可以肯定汉代没有《诗经》写本发现。
当然,刘毓庆、郭万金之所以猜测《毛诗》是“是一部幸存的文字文本”,还应该来自于对四家《诗》文本性质的传统看法。传统上一般都认为《毛诗》为古文,三家为今文。陈奂说:“《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8]。马瑞辰《毛诗古文多假借考》说:“《毛诗》古文,其经字类多假借。”“齐、鲁、韩用今文,其经文多用正字”[5]23。所以,不少学者基于此,理所当然认为《毛诗》是先秦的古写本。实际,《毛诗》多用假借,三家《诗》多用正字,是私学和官学用字之别,而非古文与今文之别[9]。《毛诗》之所以被看作古文,是由于其学派属性,而非文本性质,对此,王国维在《汉时古文本诸经考》有较为详细的辩证:“《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传》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其所以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幹言‘古文科斗近于实’,下列举《毛诗》、《左传》、《周礼》三目。盖因《周礼》、《左传》而牵连及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10]322
汉代既然没有《诗经》写本的发现,那么《史记》所言,只是就“六艺”而言,并不专属意于《诗》、《书》,也就是说,《艺文志》所谓讽诵所得,是正确的。
二、《诗经》文本“遭秦而全”、不曾残缺
《艺文志》说“三百五篇”、说“遭秦而全”,也就是说汉代四家《诗》虽为讽诵所得,却是完整的,但《毛诗序》:“《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3]609又:“《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3]615则说明三百五篇不是《诗经》完篇,其原本有三百一十一篇。又《毛诗》《小雅·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孔《疏》:“襄十四年《左传》引此二句(即“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诗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记》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则亡。今《韩诗》实无此首章。时三家列于学官,《毛诗》未得立,故服以为逸。”[3]915就熹平石经《鲁诗》残石而看,《鲁诗》确无首章[7]11。
《毛诗》与《艺文志》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前已证明《艺文志》讽诵之说是正确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毛诗》六“笙诗”和《都人士》首章的问题;《艺文志》又为什么会忽视《毛诗》六“笙诗”和《都人士》首章而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呢?要知道比较各类经典传本的异同是《艺文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北史·文苑传》,樊逊议校书事云:“案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11]2789此说由《艺文志》可以得印证。《易》类著录有《易经》十二篇,并指出为施、孟、梁丘三家经文,小序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2]1704《书》类著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原注:“为五十七篇。”[2]1705又著录有:《经》二十九卷,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二)【三】十二卷。”[2]1705小序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2]1706《礼》类著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注曰:“后氏、戴氏。”[2]1709小序说:“《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2]1710《乐记》类著录有《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小序说:“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2]1712。《论语》类著录有《论语》古二十一篇,注曰:“出孔子壁中,两《子张》。”[2]1716又著录有《齐论》二十二篇,注曰:“多《问王》、《知道》。”[2]1716又著录《鲁论》二十篇。《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注曰:“二十二章。”[2]1718又著录有《孝经》一篇,注曰:“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2]1718小序说:“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2]1719只有《诗》类和《春秋》类仅仅著录了各家经文的卷数,没有比较。
陆德明以为《艺文志》之所以说“三百五篇”,是因为知道六“笙诗”已亡佚,故不数。故《经典释文·叙录》说:“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战国之世,专任武力,雅、颂之声为郑、卫所乱,其废绝亦可知矣。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讽诵,不专在竹帛故也。”[12]9说“三百一十一篇”、说“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讽诵,不专在竹帛故也”,看起来是相应的,但六“笙诗”是亡佚的,实际并没有解决《毛诗》与《艺文志》的矛盾。再则,《艺文志》对亡佚之篇章,若其目尚存,也是会注出的,如《春秋》类著录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则其不应该在六“笙诗”篇名、辞义尚存的情况下不注明。
刘歆建言立《春秋左氏传》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移书太常博士,指责博士们“因陋就简”、“抱残守缺”,主要就《逸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立论,故一说“得此三事”,再说“抑此三学”,杨树达以为刘歆不言《毛诗》,是因为中秘没有《毛诗》[13]300。《艺文志》主要依据刘歆《七略》删订而成,其中没有比较四家《诗》异同的文字,也应该是此缘故。但此说也未必得实。《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2]2410献王所得书中虽没有《毛诗》,但既然立《毛诗》博士,则《毛诗》于此时也应该有写本。献王书所归,《汉书》没有明言之,不过,就有关论述来看,入于秘府是无疑的。《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2]1712又《经典释文·叙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12]11①《艺文志》:“《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似皆与此矛盾,但古文出处不一,其实皆是。②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建邦能命龟’以下,皆用成文,未知所出。《传》盖因徙都命卜,连而及之耳。《韩诗外传》:‘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或班引出《鲁诗传》,馀意未详。”陈氏就《艺文志》“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为据,以为此用《鲁诗传》,不见得是的论。再则武帝也大搜篇籍,《毛诗》既为献王所重,也不应不收。《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701
而就《艺文志》来看,刘歆应该对《毛诗》有一定的了解,《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1755王应麟《汉志考证》说:“《毛诗·定之方中传》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也。’”[14]1423王应麟虽没有明言《艺文志》与《毛传》合,但引用《毛传》之语,实际暗含《艺文志》用《毛传》的意思,故程千帆、徐有富认为《艺文志》“传曰”应该在“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后面,乃传写致误,是节引大夫的九能之一的“升高而赋”为说[15]43②。再则《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2]3614对《毛诗》传承叙述清楚,而姚振宗以为《儒林传》也本之刘向《别录》、刘歆《七略》[16]1592,则刘歆对《毛诗》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王应麟《汉志考证》:“汉世毛学不行,故云三百五篇。”[14]1396也就是说《艺文志》所言主要是针对三家《诗》而言。此说也不正确。《艺文志》言“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为一层;“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为一层,前一层的意思是涵盖后一层的,后一层又分为两截,前一截说三家《诗》,后一截专说《毛诗》。再则,汉代没有《诗经》文本的发现,非止三家,也包括《毛诗》。
所以《艺文志》说《诗》“讽诵所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等等也涵盖《毛诗》。然而既然四家《诗》皆为讽诵所得,且三百五篇为其完篇,并没有因为秦火而残缺,那么又如何解释《毛诗》多六“笙诗”、多《都人士》首章呢?这就需要从四家的文本来源和六“笙诗”、《毛诗》《都人士》首章是否在《诗经》中等方面来分析。
三、六“笙诗”、《小雅·都人士》首章本非《诗经》所有
汉代四家《诗》的来源,《汉书》于《鲁诗》有明确的记载。《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2]1922又曰:“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2]1922《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2]3608则《鲁诗》文本为浮丘伯口传,而浮丘伯又传荀子之《诗》本。
《齐诗》、《韩诗》来源,典籍无载,不过《史记·儒林列传》说武帝初即位时征辕固,“时固已九十馀”[1]3123,则年长申公十岁左右①由《史记·儒林列传》“今上初即位,……申公时已八十馀”,故知辕固长申公十岁左右。②“推《诗》之意”,《汉书·儒林传》作“推诗人之意”。由今《韩诗外传》皆依《诗》句推演道理来看,《史记》作“推《诗》之意”更准确,《汉书》加一个“人”字,似乎更合情理,但却与《外传》内容不符。③如《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虽为称述商鞅的做法,实际也是韩非所主张的。④又《礼记释文》引刘瓛说以为《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则其取自《公孙尼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公孔尼子》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子思子》七卷、《公孙尼子》一卷,应该都各有亡佚,但《公孙尼子》散佚甚于《子思子》,也就很难说是沈约所言得实,还是刘瓛所言正确。此姑采沈约之说。。申公学《诗》于浮丘伯,虽在高后时卒业,但在秦焚书前已经就学,那么辕固学《诗》很可能在秦焚书前。汪中《荀卿子通论》以为“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仅因为《韩诗外传》“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17]77,实际是影响之论,并不能说明《韩诗》的来源。由《史记·儒林列传》“韩生推《诗》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1]3124②等语来看,《韩诗》之学可能并非专授,而更多自我发明。其依据《诗》本来自何处,却不得而知。
对于《毛诗》,《史记》无说。《汉书·艺文志》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2]1708又《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2]3614。河间献王刘德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薨,那么毛公年岁可能小于申公、韩婴,他所习《诗》亦可能在秦焚书之后。
四家《诗》创始人习《诗》或在秦焚书之前或在秦焚书之后,即使在焚书之后,其老师也应该为由秦入汉的儒生。而考《诗经》在秦焚书前的流传情况,其流传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儒家引以证成其说,战国其他各家也多引用,即使如韩非敌视“六艺”者③,也有所引用,《韩非子》引用《诗经》就有五篇次。1974年河北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发现一古墓群,其中一号墓的封穴时间约在公元前310年左右[18],其中出土铁足大鼎、方壶、有盖圆壶各一件,上皆有铭刻,铭文皆有套用《诗经》之句之处。此也可说明《诗经》在战国时期流传的广泛。然而遍检《左传》、《国语》及其战国诸子书等,却没有一书引用六“笙诗”之辞。若说某一特定的诗大家都没有引用是可以理解的,而这六首诗都没有人引及就很难理解了。
《毛诗》《都人士》首章典籍倒是有所引及,《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19]932《礼记·缁衣》:“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20]1506《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奏答谓《缁衣》取自《子思子》[21]288④,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竹简都有《缁衣》简,内容和今本《缁衣》基本相同。而郭店楚墓的年代,发掘者推断为战国中期偏晚[22];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为“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23],则沈约之说或为得之。这说明《毛诗》《都人士》首章在先秦是流传的。不过其为逸诗呢还是《诗经》中所有呢?还是需要深究的。因为《左传》、《缁衣》皆有引逸诗之例。
而判断《毛诗》《都人士》首章是否为逸诗,需要拿《毛诗》《序》、《传》与《缁衣》篇和《左传》对比。《缁衣》篇论点与所引诗句贴合得很好,因为“长民者”为民所望,其言行有示范意义,故其“从容有常”,“则民德壹”,也就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就《毛诗》《小雅·都人士》来说,其二章至五章皆表现士、女的服饰以及对士、女的钦慕之情,因而全诗的诉求重点实际不是第一章所言,而《毛诗序》却说:“《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伤今不复见古人也。”[3]915其“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也就没有落脚点了。而在“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两句下,《毛传》曰:“周,忠信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说:“《左传》引诗以明子囊之忠,其实忠信连言而义始备,《传》释‘周’为‘忠信’正本《左传》。”[8]但《左传》说“忠,民之所望”,意思当为因为忠诚,所以为民所景仰,引“行归于周”两句,是说明其受民景仰的程度,故接着说“忠也”。非解释“周”为“忠”。所以王先谦说:“细味全诗,二、三、四、五章‘士’、‘女’对文,此章单言‘士’,并不及‘女’,其词不类。且首章言‘出言有章’,言‘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后四章无一语照应,其义亦不类,是明明逸诗孤章,毛以首二句相类,强装篇首,观其取《缁衣》文作《序》,亦无谓甚矣。《左传》如‘翘翘车乘,狐裘蒙茸’,本有引逸诗之例。《汉书·儒林传》‘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王式谓‘闻之于师’,是鲁家亦本有传逸《诗》之例。”[24]801-802其说应该是可信的。虞万里通过比较竹简本与传世本《缁衣》篇,也认为《小雅·都人士》首章是《毛诗》经师加入《毛诗》的[25]。
既然为讽诵所得,那么遗忘也就不可避免。《毛诗序》说六“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语焉不详,《毛诗》《小雅·南陔》、《白华》、《华黍》《序》下郑玄疏解说:“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3]609又《由庚》、《崇丘》、《由仪》《序》下郑玄说:“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亦用焉,曰‘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山有台》,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亦遭世乱而亡之。”[3]615郑玄说六“笙诗”“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具体情形如何也说得很不清楚。由于汉代四家《诗》皆为讽诵所得,其之所以亡只能是遗忘所致。朱彝尊说:“诗何以逸也?曰: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诵者偶遗忘也”[26]534。但四家《诗》皆为讽诵所得,何以三家皆没有六“笙诗”与《都人士》首章?若说一家“偶遗忘”则可,说三家皆遗忘皆难以说通①或以为《诗经》文本为相合而成,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徐刚《古文源流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刘毓庆、郭万金《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实际是对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误解。刘歆说:“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是说直到武帝时先师单独一个人尚不能解释《诗》全经,非谓单独一个人记不得全经。又举《阜阳汉简〈诗经〉》为证据,但《阜诗》所出之墓已经过盗掘,即使所存《国风》部分和《小雅·鹿鸣之什》部分也残损很严重,很难说原物是不全之物。即使原物为不全之物,也不能说直到文帝时,社会上还没有《诗》之全经。。申公老师为浮丘伯,辕固、韩婴老师尚不清楚,但亦皆为浮丘伯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依据《汉书》关于《毛诗》的说法,毛公为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而河间国也是赵国故地,可知毛公活动范围大致不出赵国故地,而韩婴为燕人,其在文帝时既已为博士,而《史记·儒林列传》说“燕、赵间言诗由韩生”[1]3124,毛、韩二家的文本是有相同来源的可能的,不应该二家文本有如此大的差异。又三国时吴人陆玑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曾身(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27]21同为三国时吴人的徐整又有另一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12]10后人以徐说疏阔,多取陆《疏》之说[28]88。依据陆说,《毛诗》远传自子夏,经荀子传大毛公,则其来源实际与《鲁诗》有相合之处,即其《诗》本亦传自荀子,但何以《毛诗》有六“笙诗”、《都人士》首章而《鲁诗》则无,是浮丘伯健忘呢还是申公粗疏呢?
《毛诗》《都人士》首章王先谦以为是“逸诗孤章”,乃“毛以首二句相类,强装篇首”,也就是说是《毛诗》学者后来加入的,且其来源即为《缁衣》篇。同样,六“笙诗”亦当为后来加入的。六“笙诗”为《毛诗》学者加入《诗经》,由六“笙诗”《序》及其所处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就今本《毛诗》来看,六“笙诗”的篇名,厕身于“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之中,但二什除六“笙诗”外,仍各有十篇,显然尚未正式列入《小雅》之中。而《小雅》中除六“笙诗”中的《白华》外,“鱼藻之什”中还有一篇《白华》,也未加以区分。《小雅》中的诗题没有重复者,主要出于区分。
再则《毛诗序》对六“笙诗”的解释,实际都是从篇题来推演,王质《诗总闻》:“‘有其义’者,以题推之也;‘亡其辞’者,莫知其中谓何也。……《南陔》,南者,夏也,养也;陔者,戒也,遂以为‘孝子之戒养’。《白华》,白者,洁也;华者,采也,遂以为‘孝子之洁白’。《华黍》则以‘时和岁丰,宜黍稷’言之,盖不时和岁丰,则黍无华也。……由庚者,道也,遂以为万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为万物极高大。仪者,宜也,遂以为万物得宜。……皆汉儒之学也。”[29]169
姚际恒《诗经通论》则从六“笙诗”在今本《毛诗》中所处的位置分析,认为是序《诗》者见《仪礼》之文而加入的,他说:序《诗》者“见《仪礼》以《南陔》、《白华》、《华黍》笙于《鹿鸣》之后,故以之共为‘鹿鸣之什’;见《仪礼》间歌,以《由庚》、《崇丘》、《由仪》笙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中,故以附于其后。既不见笙诗之辞,第据其名妄解其义,以示《序》存而诗亡。”[30]①对于六“笙诗”,古今争论不休,或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或以为“有声无辞”,学者各执一词,互不相下。“有其义而亡其辞”见于《毛诗序》,郑玄以为是毛公所言。北宋刘敞首倡六“笙诗”“有声无辞”说,而后郑樵、王质、朱熹等从之。由于郑樵等疑《序》、诋《序》,其观点多不为清儒所接受,故主张“有其义而亡其辞”的学者还是居多。不过,就主张“有其义而亡其辞”的学者,也往往无法解释清楚六“笙诗”何以不入什、《毛诗序》何以只就篇题而推演等疑点,故现代学者多认同“有声无辞”说,如洪湛侯《诗经学史》:“今本《毛诗》,六‘笙诗’的篇名,仅附于《鱼丽》、《南山有台》之末,尚未正式列入《小雅》之中。七什次序仍旧,两篇《白华》亦未加以区分,故其搀入痕迹,尚依稀可见。”中华书局2002年,第47页。周延良《诗经学案与儒家伦理思想研究》:“从《小序》界说三目(《南陔》、《白华》、《华黍》)之文大抵可知,说者是建立在一种社会理想的基础上界定三目,具有明晰的望文生义之嫌。”“至于《小序》对此三目(《由庚》、《崇丘》、《由仪》)之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化心理祈向,突出了秩序观念的文化积淀,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说者确有望文生义之嫌——也与前三目同。”“此六诗所以可能形成在《小序》中明确的伦理界说,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本体是《仪礼》中所载的六诗的礼仪功能,以此为基础,作《序》者以六诗之目字面之义引申,便形成了历史上‘六笙诗’义理范畴有着长久生命力的定义”,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50、452、463-464页。夏传才《诗经讲座》:“六篇笙诗是无词的乐曲,在典礼中与乐歌交叉使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所以郑《笺》所说“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也是臆测。
四、《毛诗》学者入六“笙诗”和《小雅·都人士》首章于《诗经》原因探析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说:“班《志》凡今文经,皆不加今字。凡今文与古文无大异者,皆不记中古文。《书》、《礼》、《春秋》、《论语》、《孝经》皆有古文经,惟《易》、《诗》无之。”[31]13古文经与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有不同,自然是来源有异。但就今文各经各派而言,即使所用经文来源相同,往往存在不小差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学同出伏生,但《艺文志》:“《尚书今文经》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2]1705)此为分卷的不同。熹平石经《尚书》用欧阳本,校以大、小夏侯。则《尚书》三家文字上也有差异。今文《易》皆传于田何,而《艺文志》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2]1704熹平石经《易》用孟氏本,校以施、梁丘、京三家。各家文本上也是有差别的。《仪礼》十七篇传自高堂生,《艺文志》:“《经》十七篇。后氏、戴氏。”[2]1709后氏指后苍,学《礼》于孟卿,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德号大戴,圣号小戴。此戴氏指大戴。戴氏为后氏学生,二家经文已经不同。郑玄《仪礼注》用刘向《别录》本,贾公彦《仪礼注疏》以大、小戴本与之比较,三本篇目次序颇不同。熹平石经《礼经》用大戴本,校之以小戴本,则二者文字上也有出入的。
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弟子员,在利禄的刺激下,各家为了立于学官,背师立说,甚至不惜变动经文。《汉书·夏侯建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2]3159夏侯建之所以能自名其学,就在于善于“左右采获”、“具文饰说”,其所以要如此,是为了“应敌”、为了竞争。比至后汉竟有人“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32]2547,所以皇帝要一次次命儒生校定《五经》文字,熹平石经也因此而立。《毛诗》长期在民间传播自然不至于如此,不过官学既然有利禄的刺激,《毛诗》学者也还是有立于学官的期许的。由《艺文志》“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来看,《毛诗》学者借子夏自重,正是希望立于学官的一种努力。那么,《毛诗》学者为了显示其所传比三家完备而加入六“笙诗”、《都人士》首章,也就可以看作希望立于学官的一种努力。
所以,《毛诗》六“笙诗”、《都人士》首章都应该是《毛诗》学者后来加入的,四家《诗》皆为讽诵所得,三百五篇,为《诗》之完篇,《诗经》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禁语《诗》、《书》而有所残缺。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孔颖达.毛诗正义[C]//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刘毓庆,郭万金.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1):1-5.
[5]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马 衡.汉石经集存[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8] 陈 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
[9] 郭全芝.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J].淮北煤炭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07-110.
[10]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杨树达.汉书窥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 王应麟.汉志考证[C]//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15]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8.
[16]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C]//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17] 汪 中.述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36.
[19]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C]//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 孔颖达.礼记正义[C]//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 魏 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3] 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C]//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 虞万里.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J].文学遗产,2007,(6):4-14.
[26] 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7] 陆 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8]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9] 王 质.诗总闻[C]//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 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1]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 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