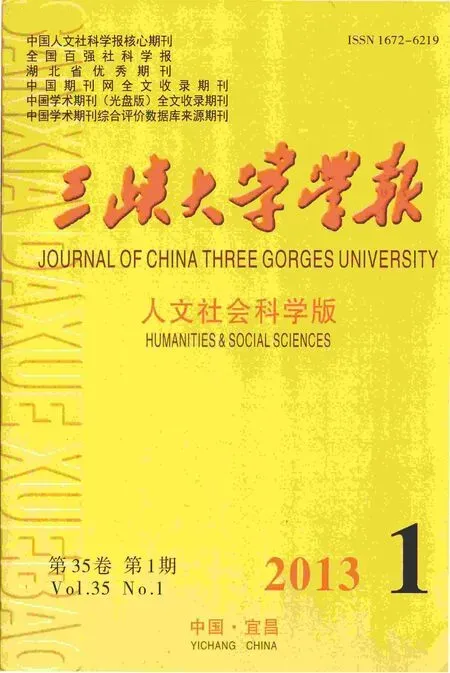生态情怀与生命诉求——郭沫若早期创作再考察
2013-04-07林荣松
林荣松
(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宁德 352100)
郭沫若早期创作通过重返自然的书写,传达了一种亲近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生态情怀。他笔下自然与人的关系更多体现为诗意栖居的生命诉求,其叙事核心是伦理反思。在他的生态情怀和生命诉求中,自然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一种生态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为中国现代文学展示了生态文学的萌芽,是解读郭沫若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人类是从自然世界中走出来的生命形式,人与大自然最初的关系是混沌一体的。英国思想家弗雷在《金枝》一书中指出,原始人眼中世界受超自然力支配,这种超自然力来自于神灵,而神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物的化身。法国思想家布留尔《原始思维》也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和观念中,神灵无处不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由此形成的禁忌、宗教等活动方式,成为原始思想的集体表象。经历了漫长的从依赖自然到征服自然的历史,“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家园”等话题反映出新的生态伦理范型正在建立。
中华传统文化不乏生态智慧,儒学的“仁民爱物”、“天人相通”,道家的“道法自然”、“物我合一”,不仅设定国人的行为方式,而且已经达到生命哲学高度。返朴归真,天人合一,超生死、齐万物,参天地、赞化育,凡此种种对古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道乃人道的根源,要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需要人来实现,人能实践仁心,即体现了天道。但仁心的实践,无法摆脱人本身的种种局限;天道却不受此限制,天道既内在地与仁心合,又超越于人心之上。诚如鲁迅所说:“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根本,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1]
在生态自然观上,中西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默契。胡适发现荀子《天论》中有培根的“戡天主义”思想,而他自己深受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鲁迅指出生物由简至繁,由两栖到爬行动物,又逐渐进化到高等生物,正是大自然“自著之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不过是“抄袭”大自然而已。宗白华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影响下构建了以生命为本的美学体系,明确表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世界观。”[2]在郭沫若那里,王阳明的心学,泰戈尔、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歌德、瓦格纳的浪漫主义等,都被用来作为打破一切束缚、彰显自我个性的强劲精神支撑。他多次谈到自己的泛神论倾向滥觞于传统文化,因为喜欢庄子才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接近”,才受泛神论的思想的“牵引”。《庄子·大宗师》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块”就是大自然。郭沫若《题关山月画》诗曰:“大块无言是我师,陆离生动孰逾之。”正是对此的最好诠释。而以崇尚自然为重要特征的长江流域文化,对郭沫若的精神个性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和发展的基础,加深了郭沫若对大自然执着的偏爱。
置身于五四时期开放性文化结构之中,郭沫若的态度是别致的,他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先见”走向世界,“融化一切外来之物于自我之中”[3],从而构建皈依自然、生命至上的思想立场,泛神论只是其自然观、生命观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表达方式。郭沫若在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中,形成早期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本质即生命与有节奏的情绪世界,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直觉是一个现代生命诗学的概念,诗人把直觉放在诗的公式的首位因素,这种思考无疑触及到了生命的深层奥秘。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精神生生不息,郭沫若深知人类要顺应自然的规律以获得自由,强调对自然的把握是一种充满生命冲动的诗意的把握,进而主张形式上绝端的自由自主,鼓吹“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4]。认为生命与文学同样归属于一个具有本体性质的“Energy”里,因而极力压缩生命意识与文学表达之间的距离。至于“Energy”到底指什么,郭沫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此力即是创造万物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身。”[5]
二
审美从根本上说根植于人与大自然的相通性,体现了自然界的秩序与和谐。中国现代生态文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大自然构成了五四作家个人存在的一个自由空间,它在使生命超空间化的同时,也强化了个体生命那种“处处是家,处处无家”的复杂意识。生态情怀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展示出生命的价值,人与大自然的联系方式由科学认识转变为生命感觉。素有浪漫心性的郭沫若,在“生的颤抖,灵的喊叫”中[6],自然的描摹与生命的书写,互为表里,互相作用。在他看来,生命在物与人之间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要使生命获得无限自由,就要让生命超离现实时空的制约,进入到周而复始、永无穷尽的自然时空。
一般而言,西方人在自然面前更多表现出一种征服与主宰的姿态,而中国人更看重与自然的顺应关系,内心深处更热爱并接纳自然。农耕文化的悠久历史,培育了中国人亲近自然的民族心理,隐居山林甚至成为古代失意文人的行为模式。郭沫若将亲近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和效法自然融为一体,他在《自然底追怀》中写道:“特别是对于自然的感念,纯然是以东方的情调为基音的,以她作为友人,作为爱人,作为母亲。”[7]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鼓吹:“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女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5]。其早期创作中人的本质常常被看作一种人的自然性,这种人的自然性或曰生命的自然性境界,说到底是生命个体的个性和自由获得极大肯定和实现的状态。理想与现实长期不能逾越的障碍被渐次拆除,此岸的现世家园终于和彼岸的精神家园走在一起。来自生命自发的冲动,实际上成了郭沫若早期创作的起点,也是进入其文本精神世界的路标。正如朱自清所说,“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8]。
郭沫若醉心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对皈依自然心有所感,被誉为“自然颂歌者”。“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5]天地有大美,大自然蕴含了人格净化、自我升华的动力。自然是生命的物质载体,生命是自然的精神结晶。有了大自然的启迪与滋养,有了生命的注入与孕育,人才能与大自然化为一体,生命才有超空间化实现瞬间永恒的可能。不论故国山河,还是岛国风光,不论星空、地球、太阳、月亮,还是花草、树木、秋意、残春,都会超越其本身的形象,成为传显生命存在的形式与途径,并由此证明人活着是有意义的。郭沫若所描绘的极富生气的自然王国,是生命本源状态的生动显现,表现了生命力的恣肆伸展。
郭沫若笔下大自然因充满生命感受而变成一种生命的外在呈现,进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描写“自然”就是描写“自我”,回到“自然”就是回到“天真”,赞美“自然”就是“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9],成为郭沫若早期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郭沫若1904年写作第一首五律《屯居即景》,1914年因海滨裸泳诗情“象潮一般涌出来”而作旧诗《白日照天地》,1916年因漫游操山招致“汹涌澎湃的灵感”而作古风《怪石疑群虎》,不难看出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敏感。五四时期的新诗,自然成为最直接的音符用来谱写生命颂歌,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领悟人生真谛,从人与大自然的统一中探索人生意义。
诗集《女神》有不少关涉大自然的诗篇,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倾心大自然的情感。诗人在“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的光海里欢笑(《光海》),在“欢声、群鸟声、鹦鹉声,/……粉蝶儿飞去飞来,/泥燕儿飞来飞往”的晴朝中陶醉(《晴朝》);而《晨兴》中的“耳琴中交响着鸡声、鸟声,/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鸣”,《司春的女神歌》中“红的桃花,白的李花,/黄的菜花,蓝的豆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草花,/散在树上,散在地上,/散在农人们的田上”,展示了一幅幅大自然壮阔美丽的景象。郭沫若小说同样惯于将生命与大自然连为一体,彰显未经修饰的人性,景物衰荣与人生百态交相辉映,体现了物我一体、物心契合的生命宇宙观。《残春》、《落叶》借凋零的自然现象表现生命的短暂,感慨生命的脆弱,流露出一种宿命的伤感;《月蚀》中痛感“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的K君,怀念故乡的江流与山峰,遐想未经斧凿的原野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行路难》主人公饱尝艰辛,仍不忘吟诵陶潜《归去来辞》,此情此景无疑是对皈依自然的最好印证。上述作品的意旨在于使生命获得自由和解放,寻回那失落已久的人的自然的本性,显示了作者对生命存在的自然性的无限向往,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生命冲动和感性体验的内在要求。
三
传统伦理规范中渗透了许多自然因素,或者说对自然的热爱成为人类最初做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头。海德格尔鼓吹人类应该获得一种“诗意的栖居”,阐明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同时设定了文学艺术精神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生命意识的参与改变了人类进入世界的方式,来自灵魂的共鸣可窥见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未来图式。效法自然与咏叹生命相辅相成,尊重生命与善待自然相得益彰,体现了对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的期待。
郭沫若充分意识到只有善待大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必须重新回到自然,才能享受大自然带来的自由畅快,从而进入关于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的伦理叙事之中。《女神》讴歌世界的“大同故乡”,抒发了对世界故乡本源——地球的热爱之情。在郭沫若眼中,自然自有常人无法达到的高尚,每每将自我沉淀在自然的胸怀中情不能已,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会激动地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了。“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地球,我的母亲》)《星空》以超然姿态由人间而天上,由天上而人间,“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点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在“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中关闭了现实思维,找到了心灵寄托。他看到世间一片污浊,“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仰望》),追慕“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南风》),歌颂“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的大禹(《洪水时代》)。在郭沫若看来,一切物质都有生命,大自然具有无限创造的精神和能力,“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4]。只要自觉“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心中本有无限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就可以创造一草一木乃至整个宇宙。如《湘累》所言:“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电,我萃之虽仅限于我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他效法自然造化的精神,崇尚充分自由的创造,对自然的尊崇也不仅限于顶礼膜拜,而在激烈的破坏中构建新的自然,将自身的生命作为自由的自然存在。
郭沫若笔下自然是宇宙的精髓、生命的源泉,自我融化在大自然的律吕中去追寻创造与新生。从这个基点出发,《晨安》越过“常动不息的大海”、“雪的帕米尔”、万里长城乃至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和苏伊士运河,反映出现代人的全人类意识和全新的时空观念。《天狗》带给我们主宰世界的自信与能量:“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底总量!”《凤凰涅槃》已经带有生态预警的意味,梧桐枯槁、醴泉消歇的恶劣环境,逼迫凤凰集香木自焚以获重生,环境与生存的关系就是这么残酷。而“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万物同源”、“万物同灵”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得到了极度张扬。
《女神》有两类重要意象,一类是太阳,一类是大海,某种意义上寄托了郭沫若的生态理想。《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坦言“我崇拜太阳”,《太阳礼赞》直接礼赞太阳。太阳,在郭沫若心中既是普照万物的自然天体,又是蕴含光明与力量的象征意象,同时还是情感充溢、充满活力的生命之物。回归太阳之家的强烈愿望,与太阳同化的至诚之情,可见他对太阳的神圣体认。郭沫若所面对的大海,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的形式,它使你感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充满澎湃生命力的宇宙的主人。《光海》洋溢着“生命的光波”,《浴海》荡涤人的内心尘垢和陈旧的外部世界。他在解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时说:“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这首诗的,或者会嫌他过于狂暴。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罢”[10]。《海舟中望日出》等诗作中,审美空间的恢宏感得益于太阳与大海的交相辉映,无不充溢着郭沫若所称之的“生之力”,使人联想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生生不息,昭示了日月轮回、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
四
文学的生态表达是一种本质需要,亦即对人自身生命的表达。无论从人的社会需要,还是从人的物类生理需要,人类都离不开自然生态。如何才能在大地上获得永恒的精神家园,正是成长中的生态文学所应该承担的重要使命。人类曾因创造反自然文化精神而背离了生态伦理,当人们再次回到自然生态道德时,自然伦理叙事所蕴涵的深刻性,经由文学发现之路再一次悄然复活。努力为现代社会重新寻找新的伦理法则,这种生态情怀的浪漫性反而呈现出更深厚的现实力量,成为现实人生急切寻找的灵魂归宿,并由此获得一种美学上的奇异性。
对文学本己性与本源性的自觉意识,是创造社的灵魂,也是创造社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审美特征。郭沫若一方面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11];一方面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强调“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所吐露出的光辉。”[12]郭沫若认为“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代;是艺术家赋与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代……”[13]自然界存在着取之不竭的美,而自然的美又是最原始、最本质的美。艺术美与自然美某些内在的一致性,拉近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对于自然生态的表达,反映了艺术美与自然美走向内在和谐一致的趋势。郭沫若既然获得了掌控时间流程与生命节奏的感觉,那么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面对自然世界的充足信心。郭沫若早期创作中个体生命与大自然的关系无非有两种:一是用自然的无限来充实和扩张个体生命,二是个体生命向自然与永恒的融入。郭沫若精神深处潜含着一种特殊的心态,崇尚主体自发的冲动,看重独特的个人感受,以及在冲决世俗规范和习俗束缚时产生的高峰生命体验。“无论甚么人,都有他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在郭沫若那里,宇宙观和人生观不是彼此孤立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在精神内质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契合。他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建立自己的文化立场,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朴素的生态情怀,成为最早真切感悟生命自由与自然尊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人类启蒙之初虔诚地崇拜大自然,文学是人类礼赞大自然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西方的亚当、夏娃等神话故事,应该是文学对自然生态最早的关注和表达。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的加深、感受的丰富,文学与自然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关系。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开始了一个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阶段,摆脱了长期以来对自然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济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层面,而重新认识自然的最高价值——生态价值。
长期以来,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从依赖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改造自然,以及对自然的破坏,人类被视为可以独立于自然的存在。生态主义的思想方式解构了人类无限征服自然的神话,自然生存因此成为一种明确的道德理想。自然是人类存在的空间,人类是自然的存在物,无论对自然的能动把握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能超然于自然界之外或之上,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规律。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除了自然生态本身的危机,还有人类如何对待生态资源的价值观的危机。能否化解生态危机不但是对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拷问,更是事关人类生存环境的大问题。
毋庸讳言,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还不具备真正的生态意识,没能预见到人类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困境,没能通过伦理反思真正唤起人类对自然责任的担当。尽管他其时研究过天体的形成和发展,对宇宙因何存在、为何变化发展的原因有过思考,但并没有找到科学的答案,自然观摇摆于唯物唯心之间。不过,郭沫若早期创作探秘和感悟宇宙自然的奥妙,还是蕴涵着朴素的生态思想。郭沫若早期创作的生态情怀和生命诉求,说到底就是自然观、生命观的一种构想。这种构想建立在“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下,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可以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陌生感,让生命从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突围出来。郭沫若早期创作超越了中国文学山水寄情的层面,从亲近自然,到效法自然,再到超越自然;从“生命的洪流”到“有节奏的情绪世界”,从“没我”于自然到要求从自然中解放出“纯粹的自我”,彰显了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希冀,传达出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
[1]鲁 迅.破恶声论[M]//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宗白华.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N].时事新报·学灯,1919-11-12.
[3]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J].创造周报,1923年第3号.
[4]郭沫若.生命的文学[N].时事新报·学灯,1920-02-23.
[5]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M]//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泰东书局,1922.
[6]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0118)[M]//田 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7]郭沫若.自然底追怀[N].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03-04(70).
[8]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9]郭沫若.光海[M]//女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郭沫若.论节奏[M]//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1]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M]//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2.
[12]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N].时事新报·学灯,1922-07-27.
[13]郭沫若.自然与艺术[M]//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