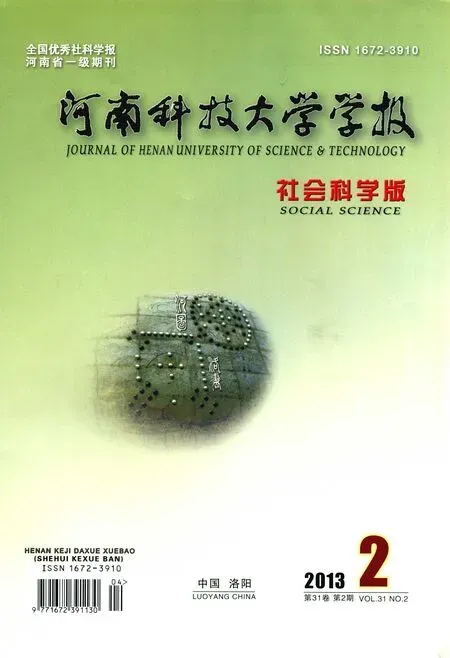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冷思考
2013-04-06王军
王军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合肥 230022)
【法坛论衡】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冷思考
王军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合肥 230022)
将规章以下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研究论文繁多,但是,这些研究对该制度实施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估计不足。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点是个体性的,其影响面相对较小;而抽象行政行为的基本特点是群体性的,影响较大。抽象行政行为被撤消后,行政机关在善后处理群体赔偿时,由于公众证据错综复杂,可能面临巨大的问题,很容易陷入混乱,甚至引起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在行政诉讼法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其审查范围之前,必须有配套的措施保障这些问题的解决。
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群体性事件
自从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讨论就非常引人关注,尤其是规章以下抽象行政行为(以下简称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关系问题,更是研究论文较多。综观这些论文,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抽象行政行为应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呼声已经占压倒性优势。其间,只有个别文章对此提出相反的观点,其声音之弱,鲜以听闻。司法机关对此也是充满期盼,期盼实现权力的有效充实。按此趋势,立法机关采纳该意见,并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体现该观点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主流观点的基本逻辑就会发现,主张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司法审查的观点,大都建立在对其法律属性的抽象分析以及对过往经验的积极反思基础之上,对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估计不足。
一、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会带来公平与秩序的冲突
(一)撤销判决将带来对行政机关的赔偿要求
就目前的审判方式和条件,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不可想象的混乱。这种混乱会发生在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之后。大多数主张抽象行政行为入行政诉讼法的文章对判决结果未曾论及。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通常有两种处理结果:第一,抽象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予以维持;第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予以改变或撤销。
很显然,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人将会提出赔偿要求。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适用赔偿的问题,已有学者论述,如“抽象行政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纳入到国家行政赔偿的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1]而且,从法律逻辑上看,既然存在错误,且该错误的文件还具有拘束力,相对人的损失是因为该错误造成的,那么,对相对人的损失不予赔偿显然是不妥之举。
(二)证据问题可能会导致赔偿偏差
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不利影响主要有两种形式:有的相对人的损失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引起,有的是因为抽象行政行为引起。换言之,大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会选择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愿意等到行政执法机关采取强制性行政行为。如此,凡是经过具体行政行为受到的损失,相对人可以根据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但是,对于没有经过具体行政行为,而选择自愿遵守的,是否需要赔偿就有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应该赔偿:“如果当事人因适用被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遭受损失的,可以在追索期限内要求国家赔偿。”[2]但是,这一赔偿与具体行政行为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结果往往都会有具体的行政程序,因此,一系列的法律文书都会产生;其次,具体行政行为,尤其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都会引起相对人足够的关注和异议,那么,他们也会积极留下,甚至主动寻找相关证据。但对于自觉遵守的相对人而言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面对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过程,往往不能留下什么证据。如此将无法得到赔偿。相反,有些拒绝遵守规则的人,或者心存侥幸之人,却因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未受到损失。这一现象从法律上看,似乎是理所当然,没有证据必然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但是,从社会效果上看就不同了。法院的判决不仅仅要讲求法律效果,而且要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举例而言,2011年乔占祥律师诉铁道部票价上浮的案件,虽然被法院受理,该判例也被引入中国行政诉讼十大经典案例,但法院视铁道部涨价的决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判决是有缺陷的,是勉强的。有文章同样持有此观点,“铁道部的《通知》本身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只不过,该文认为把铁道部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纳入行政诉讼的行为表现了法官的“智慧”。[3]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最高法院在试图明确划分标准的同时,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般尽量将被诉行为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为公民寻求救济的途径。”[4]我们姑且用这一实际上有判例的事情来说明抽象行政行为撤销后的后果。至少,铁道部涨价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反复适用性,其涉及面相当广泛,与抽象行政行为具有相同的效果。所幸的是法院判决铁道部胜诉,如果铁道部败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全国在2001年春运期间购买车票的人都可能获得退还价款的权利。但是,问题出现了:首先,许多人,尤其是农民工,没有必要保留车票,当索赔权产生后,许多人只能望洋兴叹了。其次,还有一些情况,在铁路客运中,许多车站都有在出站口回收车票的习惯,如此,许多人的票不是自己丢失,而是,铁道部门的行为导致其失去了证据,那么,他们当然有理由要求赔偿,但是,哪些人将车票交给了铁路部门又是不能确定的,这时,如果放开了口子,就会出现一些浑水摸鱼的情形,如此,相关铁道部门如何面对?
(三)赔偿偏差可能会带来群体事件
1.赔偿偏差带来政府公信力受损。法律的实施具有导向作用,应能使社会成员知所避就。但是,这种导向并不总是来源于法律字面上的规定,而是来源于事实上的法律,即实施到现实中的法律。赏善罚恶,无论古今中外的法律,都必定因循自己当时的价值观维护这一原则,从而建立自己需要的秩序。但是,如果如上例所推导的事实,就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守规矩的居民受到不利影响,不守规矩的人反倒维护了自己的所有。该现象势必导致社会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不信任,该不信任必将导致更多的抵制,即便是政府规范不存在违法问题,历史的经验也会导致居民遵守的自觉性大大降低,从而使执法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主义法治依赖的不能是行政机关疲于奔命的执行和强制手段的普遍适用,如果该情形出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失败。“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5]成功的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应该因为其内在的说服力从而带来公众自觉的执行,违法者不仅仅受到来自于执法机关的否定性措施,而且更会面对社会鄙视的舆论和目光。赔偿偏差所带来的这种不信任的结果将大大损害公众对法治的支持。
2.赔偿偏差会带来怨恨与不满。赔偿偏差所带来的另一后果可能会是不满与怨恨。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大多数宁可选择私下抱怨,也不愿公开告状,几千年的贱讼观早就在国人血液中种下了不愿诉讼的种子。“在古代中国人眼中,‘讼’特别是打官司就成了不光彩的同义语。古人在说到诉讼行为及其参与者时,常常要加上明显含有贬义的前缀或后缀词,以示鄙弃。如‘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等便是……‘滋讼’、‘兴讼’、‘聚讼’、‘健讼’、‘好讼’、‘包揽词讼’等等几乎成了‘干坏事’的同义语。正因如此,古人才一再倡导‘止讼’、‘息讼’、‘贱讼’、‘去讼’、‘无讼’。”[6]但是,不告状不代表没有怨言。由于怨气没有通过理性的通道表达,就可能会被埋下,并层层积累,是为积怨。积怨的存在很可能在特定的场合突然释放。既然这种怨气本身没有得到理性的疏导,那么,它势必在释放的时候会选择非理性方式。这一释放的方式显然具有不小的破坏力。“这种受心理影响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愤冲突埋下种子。”[7]“从发生动因看,‘利益冲突显见占主导,因深感不公而宣泄情绪的事件则在不断上升’的基本情势是2011年典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8]转型时期,该可能性不能不给予重视。
3.证据问题导致蓄意闹事者有机可乘。还有一种可能性同样不能不予以事先考虑,那就是群体性向行政机关索要赔偿,而行政机关又因为证据问题,不能全面满足。这里面就有可能有浑水摸鱼者,有蓄意惹事者。有研究认为:“有充分证据显示,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确有敌对势力、黑恶势力直接参与和挑动了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骨干作用。”[9]毕竟,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人,天生具有群体性。
(四)对有关质疑的回应
或许会有观点认为,至少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已经间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且,事实上许多案例也证明了判决中在否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并没有因此类判决而出现群体性事件。
其实,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别,过去的审理对象不是直接的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判决也不能直接撤销抽象行政行为,所以,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个案。由于信息传播的有限性,加之有些行政诉讼往往又采取调解的方法,如“长期以来,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理论界几成定律,但行政审判实践中的调解又是公开的秘密”。[10]以至于行政诉讼的结果并不具有爆炸性的宣传意义,或者吸引宣传的注意力。但是,如果将来以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对象,尤其是公众关注的那些规范性文件,那么,该诉讼本身就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群体性意义,而前者,直接的价值是个体的,后者是群体的。这一点也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解决方案——判决是否溯及既往的讨论
(一)有观点认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可不溯及既往
鉴于抽象行政行为对象的广泛性和形势的复杂性,有学者提出了对抽象行政行为撤销判决的效力应界定为不溯及既往,如有学者提出:“法院关于抽象行政行为认定无效以判决形式做出。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抽象行政行为失去效力,为了维护行政管理的秩序,此种判决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11]这一点也被另一学者的研究所支持:“抽象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后,不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据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效力也以不变为宜……如果当事人因适用被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遭受损失的,可以在追索期限内要求国家赔偿,索赔时效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算。”[2]
(二)不溯及既往的撤销不合乎逻辑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是存有异议的。
1.行政行为的撤销从本质意义上看,就应该自始无效。如“行政行为撤销通常使行为自始失去法律效力,但根据社会公益的需要或行政相对人是否存在过错等情况,撤销也可仅使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效”。[12]另一教材持同样的观点:“从行为效力上看,行政行为的撤销对前具有溯及力,它将使社会关系回归到被撤销行政行为之前的状态。这正好与行政行为的废止不同。”[13]有学者提出了无效的判决形式,对于无效判决,和撤销效果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自始没有约束力。
2.溯及既往的例外需要严格限定。撤销行政行为的效力溯及既往是世界上的通例,只是基于对相对人利益的考虑,才可以例外。如我国台湾学者阐述:“若溯及既往使之失效对人民权利及社会公益有害时,则可使撤销之效力仅向后发生,或仅使其一部向后失效。”[14]这一点的基本逻辑在于信赖保护理论,如果需要维持行政行为的既往效力,必须出于对公共利益或者相对人利益的考虑,或者行政行为的错误是相对人引起,而不是出于对行政主体利益的考虑。因此,从世界的实践和理论上看,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中的撤销至少要根据情况,对其是否溯及既往作出确定,且不能违反上述原则。很显然,一般情况下,错误的抽象行政行为不符合这一原则。
(三)在一定范围内,不溯及既往是对目前已存权利保护的倒退
虽然不溯及既往的想法具有较深的思考,但是,如果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判决结果不能溯及既往,那么,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就无法得到支持。因为,这些具体行政行为必定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作出,而后诉至法院审查的。而这些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被法院撤销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当时是有效的。既然,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判决结果不溯及既往,那么,依据当时有效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然是有效的。这就出现这样的悖论:首先,既然抽象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而且该违法行为并不是在判决后作出,判决恰恰是对之前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的判定,但是,结果却是其之后不再具有合法性,之前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这一点,无法获得逻辑支持。其次,判决之前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如果其依据的抽象性行政行为在诉讼中,经间接审查认为不能作为适用依据的,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就会被判定违法,从而被撤销。如果新的不溯及既往的判决形式被引入,就意味着以往可以胜诉的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如今却不能胜诉。那么,在这一点上,诉讼法的修改不仅不能取得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
因此,只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特别的规定,就应该溯及既往,否则只能制造新的不公平。当然,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除外。
三、笔者的建议
笔者以上论述,却也并非反对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问题是,在纳入行政诉讼审查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可能的后果。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从法学理论上看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否能够推行是另一回事,否则,就没有社会科学循序渐进的发展了。所以,法学理论、哲学理论是否正确并不能抽象看待,而是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考察,这也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所倡导的基本原则。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之上,让该制度向着设计者预想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得设计者设定的效果。如果条件不具备,仓促付诸实施,那么可能会事与愿违。所以,公正效果的实现不仅仅是公正理论陈明于纸面,更重要的是,公正效果必须有秩序地落实于实践,也就是说,这种实现必须保证落实在秩序的范围内。因此,该制度的配套设置非常重要。
但是,这无疑是一个难题,涉及到公平和秩序如何兼得的问题。笔者以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对抽象行政行为实行附带审查模式
一种方法是,按照胡锦光教授所倡导的仿照行政复议制度,将抽象行政行为设定为附带审查,[15]而审查后的判决形式,建议不要以撤销或者无效等方式出现,也不宜适用终止这一不溯及既往的判决形式。正如前文所言,不溯及既往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合乎逻辑。作为附带审查的直接好处是,该诉讼的直接对象仍然是个体性的,而群体性的问题属于附带。一般而言不会造成太大的关注,从而也为行政机关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留下了余地。而且,鉴于近年来对行政调解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转而认为,行政诉讼应该也可以适用调解,“植根国情、源于实践的行政诉讼调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16]如此,行政机关在可能引起稳定问题时,可以使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案件。本建议应该也是过渡性质,从长远看,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是大势所趋,但是,在目前改革的过程之中,国家尚处于转型时期,矛盾多发,“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说是由转型期社会变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引起的”,[17]兼顾公平和秩序就非常必要。
(二)设定抽象性行政行为实施前的权利告知配套模式
另一种方法,笔者建议不仅仅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着眼,而且,要与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制定程序配套出台。目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问题较多,不够规范,致使抽象行政行为问题多出。制定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往往没有被审查的经验,以及出于管理的倾向,缺乏接受法律约束的自觉性。因此,必须让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有足够的法律意识,同时,也对利害相关人留下可能错误的提醒,从而为自己留下证据寻求救济作出准备。在此前提条件下,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直接审查对象范围也就为理性方向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
既然欲将抽象行政行为设定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那么,抽象行政行为就要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着同样的要求。况且,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任何行政行为都既是抽象的行政行为,同时又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的统一体”。[18]为了提醒执法机关注意违法行政行为的后果,同时也提醒行政相对人注意自己的权利的存在及其保障方式,行政行为的正式文书一般都要求在行政行为过程中需要向相对人告知异议的权利,并且在具体行政行为的最后,向相对人告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以及相关时限。该程序上的设定显然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做了法律上的提示,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并告知该权利时,必然会思量行为的合法性;而作为相对人,在被告知相关权利后,不仅仅多了一份法律上维权的意识,而且,该维权被因而纳入了理性的法律程序。正是因为被告知权利的存在,其对证据的保留就有了较多的重视和意识。这也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纠纷解决纳入理性范畴铺下了道路。抽象行政行为亦应如此,即便不能履行制定过程的告知和异议程序,那么,也应在颁布时在文件的最后条款或者在颁布通知中,在明显的位置以足以引人注意的字体告知凡是受到该文件调整的人保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如此,在将来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利害相关人要求赔偿却没有保留足够的证据时,面对不利结果就是一个“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了。公正和秩序二者可以得兼也。
两种方案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
[1]陈书笋.抽象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78-81.
[2]马怀德.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J].人民检察,2001,(10):12-15.
[3]唐莹莹,陈星言.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J].法律适用,2004,(11):66-67.
[4]甘文.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J].人民司法,2002,(4):52-53.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3.
[6]范忠信.贱讼:中国古代法观念中的一个有趣逻辑[J].比较法研究,1989,(2):62-65.
[7]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114-120.
[8]张明军,陈朋.2011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及学理沉思[J].当代世界与中国社会主义,2012,(1):140-146.
[9]张传鹤.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最新发展态势、成因及对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0,(5):42-46.
[10]黄学贤.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J].法学,2007,(11):43-49.
[11]王敬波.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J].行政法学研究,2001,(4):45-48.
[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1.
[13]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8.
[14]张正.行政法体系重点整理[M].台北:台湾保成文化出版公司,1996:443.
[15]胡锦光.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9-15.
[16]罗礼平.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论纲[J].当代法学,2011,(1):157-160.
[17]周感华.群体性事件心理动因和心理机制探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6):1-5.
[18]杨解君.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质疑[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1):56-59.
A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on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 Incorporating into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ANG Jun
(Law Department,Anhu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Hefei230022,China)
The idea that judicial practice on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 incorporating into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overwhelming in academic papers while its possible consequences hasn’t been aroused due attention.Collective orientation of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which brings more impact on the society,is different from singular orientation of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After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the concerned administrative organs perhaps can not deal properly with the collective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judicial decision because of complex evidences,which will probably lead to amass incident.This problem should be resolved before the amendme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cope of case admissibility;mass incident
D925.3
:A
:1672-3910(2013)02-0100-05
2012-11-12
王军(1970-),男,安徽阜阳人,副教授,硕士,从事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