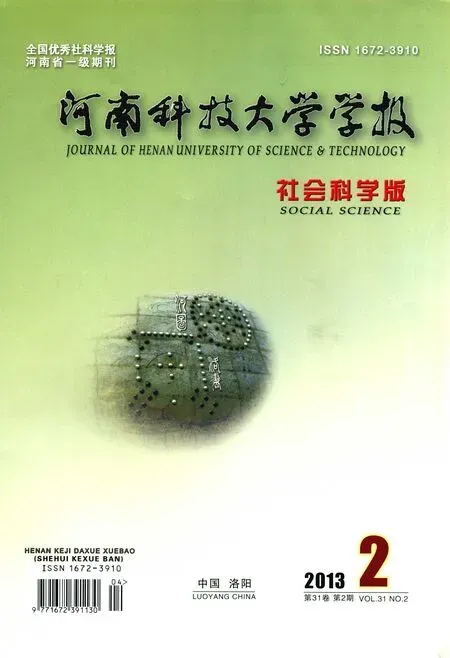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工业文明批判的生态意义
2013-04-06李笑蕊
李笑蕊
(河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是美国重要的剧作家,有关他的传记、专著、各种期刊报纸的评论以及研究论文数不胜数,研究成果视角的多样性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我们发现,生态学的视角绝少被应用于其戏剧研究,网络文献搜索仅显示有一篇论文应用了类似视角,[1]其中曾提到了威廉斯的戏剧,这提示了从生态批评角度探讨威廉斯戏剧的可能性。
一
威廉斯用抒情的笔调刻画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他们郁郁寡欢、离群索居。难怪当代中国批评界曾这样评价说:“威廉斯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2]然而进一步细读发现,这些人物之所以远离社会,并非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细察他们的生活可以看到工业文明价值观是如何一步步把这群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排除出局的过程。通过展现这群人物的境遇,展现工业社会对他们的驯化、排斥、拒绝和排除,威廉斯描绘了整个社会大背景,因而了解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显得尤为重要。
威廉斯戏剧展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生存危机,这些特殊群体常常被称作是“被驱逐者”、“逃离者”、“不遵照规则者”、“不相称者”、“外来者”或者是“错位者”。他们因为与自己所在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常常不容于现实,只好采取逃避的方法回避现实或与现实抗争而最后毁灭。
威廉斯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的精神世界,他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个处于精神危机中的人物,他们或者脆弱、敏感,在现实世界中不堪一击;或者狂躁不安、神经质,在毁灭之前做着垂死挣扎;或者麻木不仁,在酒精或毒品作用下捱延时日。无论哪种状态,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经济拮据,不能控制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只能一败涂地或者濒临失败。他们或仅有单间公寓(如《玻璃动物园》中的温菲尔德一家),或只能寄人篱下(如《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或寄居在小旅馆里(如《鬣蜥之夜》中的汉娜),或蜷曲在吊床中(如《鬣蜥之夜》中的香农)。他们不停地搬家,一直在寻找,寻找失落的世界,失落的信仰或是失落的自我。
二
威廉斯笔下人物的生存危机,具体表现为他们在工业文明中无所适从的生存状态。《玻璃动物园》的剧中人生活在看不到却又似乎无处不在的威胁中,至于是谁居于控制地位,是谁在给他们施加压力,却不能明确说出来。目睹劳拉在打字速度测试时颤抖的手指,这种压力便清晰可感。她的世界充满了弱肉强食的竞争。人们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失败自有一套无情的准则,任何不符合这套准则的人将会被淘汰出局,这套准则就是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剧中三个主要人物劳拉、阿曼达和汤姆在面对这套价值观时,同时感到了痛苦与折磨。劳拉无法融入这种价值观,所以无法在现实中生存,只能躲回自己的玻璃动物园里;阿曼达企图顺应这种价值观,但惨遭失败;汤姆隐忍坚持,最终还是坚持不下,选择了逃逸。《玻璃动物园》如同一首动人的抒情诗,娓娓道出主人公们的希望、失望、痛苦与忧伤,展现了一个笼罩着深深忧伤与失意的人类世界,与这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物质的、机械的、贫瘠的外部世界。因此,这部剧的重要冲突就是敏感、脆弱、温柔的人性与机械、物化、贫瘠的社会的冲突。
《欲望号街车》刻画了两类人物的直接冲突。斯坦利是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化身,作为一名推销员,他有金钱意识,懂得用现存的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布兰琪是旧南方没落文明的化身,她神经质、矫揉造作、没有现实感,缺乏理智。两个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局是布兰琪惨败,斯坦利大获全胜。该剧不仅象征性地展示了一种没落文明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过程,更展示了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势力对一个奋力想要温柔、优雅和高尚起来的灵魂的无情践踏,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展现了工业文明社会所滋生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庄园主大阿爹将不久于人世,遗产争夺战中全家人都使出浑身解数。金钱利益蒙蔽了人的双眼,使人们看不清真相。玛吉一再声称她爱丈夫布里克,布里克却不愿相信她,她“我爱你”的告白在遗产争夺中显得别有用心。大阿爹在临死之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爱大阿妈,那个女人只是他多年积攒财富中的一件而已。他意识到积累财富根本不能让他真正快乐起来。这就是他愤怒和感到挫败的真正原因。该剧深刻揭露了拜金主义价值观对人类灵魂的毒害。在金钱社会里,人们丧失了爱的能力,精神生活极度空虚,从而丧失了诗意栖居的能力。
《鬣蜥之夜》中,处于穷途末路的男男女女暂时逃离自己的困境来到远在他乡的小旅馆。在这里,人们的疏离状态暂时结束,可以互相关心对方的疾苦并提供安慰。剧中尽管照例充满了绝望和疏离的痛苦情绪,然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给这部剧带上了一点温情的色彩。不同于威廉斯前期戏剧的是,这部戏剧指出了不相干的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联系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这部戏剧还指出了“忍耐和接受”的重要性,含沙射影地暗示了美国社会的虚伪性。美国宣称是一个民主的、包容一切不一致的国家,可是在实践中,一切在种族、性取向、信仰等等方面不同的“异端分子”都无法得到公众的接受和包容,都会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戏剧的大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的墨西哥,二战正在进行。貌似平静的旅馆一角被黑暗丛林所包围,耳朵里传来收音机里播着的德国战胜的消息,旅馆里的一家德国人时不时地出来唱点纳粹进行曲。这就是舞台上两个亟待打开心门来互相帮助的人物香农和汉娜所处的大背景。《鬣蜥之夜》更加深了《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剧里所展现的主题,物欲横流的社会,金钱的占有,物欲的满足更加剧了精神的空虚。香农追寻欲望满足的过程中,却陷于更深的迷惘和彷徨,黑暗丛林般的物欲社会,种种无形的压力压向那些敏感而脆弱的灵魂。
威廉斯戏剧深刻揭露了工业文明价值观对人的异化作用。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原始关联性被隔断,人沦为机器的奴隶,金钱拜物教横行,家人之间亲情沦丧,人丧失了爱的能力,人类社会沦为机械化和商业化的冰冷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敏感、脆弱、充满人的欲望和热情的人物难以生存。因而,威廉斯剧中人物的悲剧就具有了深刻的工业文明批判意味。
三
威廉斯的剧中人虽然活在当下,却都在缅怀另一个时空的生活方式。因为他的早期剧本多以美国南部为背景,剧中人多为南方种植园文明的遗老遗少。因此,评论家常常把“另一个时空的生活方式”当成是已经没落的南方文明。然而,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深入了解提示这群人的遭遇不仅代表这个阶层,更多地代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劳动者的普遍遭遇。他们对过去文明的向往,往往是对现实的逃避与憎恶。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的繁荣,这与过去大不相同,旧南方的农耕生活改变了,劳动依赖于机器和技术,产出值大大增加,可精神越来越匮乏。工厂里机械的劳作生活,使劳动者感觉自己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好像沦为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的劳作毫无乐趣可言。剧中人表面上看是在缅怀一种逝去的文明,实质上缅怀过去只是一种寄托,其中主要的情绪是对当下生存方式的不满。他们渴望的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方式”。
人类之所以不能诗意地栖居,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看来,首先归结于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定的环境制约。这种特定的环境始终呈现出严格的等级性,而这种等级性形成了这样的事实: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和权利。严格的环境等级制形成了绝对的权力主义,社会由权力所控制,权力由少数人所控制,社会平等、民主思想不是得到强化和普及,而是走向萎缩与衰落。[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也就是威廉斯剧作的时空跨度中,美国社会包括美国南部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并稳定发展。工业文明在半个世纪之内,席卷整个美国南部,这里的种植园文明迅速衰落。曾经的南部贵族的后代也迅速沦落。在新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他们没有财富,没有权力,徒有一身优雅的风度,然而即使这个也过时了,被人们当成是装腔作势。所以,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为可笑的小人物。工业时代的社会环境限制了这些小人物的自我发展,他们的个性得不到张扬,从而形成了人类自我与其世界性存在的割裂,人与自然、世界、他人的原始关联性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丧失了诗意地栖居生存的能力和权利。
威廉斯在《玻璃动物园》中就展示了狭隘空间中人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生存的困境。第一场的舞台说明这样描述温菲尔德家的居住环境:
温菲尔德家的公寓在一幢楼的后部,这幢楼是许许多多蜂窝状的居民楼中间的一幢,这样的居民楼如瘊子般在城市的中下层阶级聚居的地方蔓延开来。这证明了这个在美国社会中人口最多的、处于受控制地位的阶层避免变化、抗拒差异的需要。他们希望作为集体的一员,融入自动化的制度中。
我们看到,这里空间狭隘,楼房密集如蜂窝,千篇一律的楼房拒绝变化、拒绝个性,一幢幢楼房就像自动化工厂里用模子铸造出来似的。威廉斯用此舞台说明表现了工业化的力量,它可以把美丽富饶的乡村种植园变成水泥森林,当然也可以奴役人的肉体和思想。工业化隔断了人与自然,也隔断了人与人的交流。土地之上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耕种者,变成了工厂中机器的一部分。这里提到的“自动化”不仅仅指的是自动化的机器,也指机器统治下人主动性的丧失,人沦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自动宣传工业文明的盲从者。此剧中的吉姆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罗拉面前充满自信讲了一番话,希望通过上夜校、练习演讲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来摆脱鞋厂仓库这个低级的工作,在工业文明社会的等级制度中一级级往上爬:
我相信电视业的前途。(转向罗拉)我打算从基础学起。其实,我已经找好了合适的关系,剩下的就是靠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了。全速前进——(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知识,啪啪! 金钱,唰唰!权力!民主就是建立在这个循环之上的。(《玻》第七幕)
白手起家,通过知识和个人魅力获得金钱和权力,吉姆这席话在米勒戏剧《推销员之死》中的洛曼那里得到了回响。其实,这就是人们普遍相信的“美国梦”——通过辛勤工作,一步步获得成功,这是工业文明价值观的最佳体现。这样的价值观造就了实际的头脑,强健的肉体,像《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
威廉斯剧作中经常看到工业文明的影子,它们在主人公精神崩溃时出现,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如布兰琪在精神崩溃时,头脑里闪出火车驶过灯光闪烁的影像。火车是工业文明的代表,它的轰鸣声和形象,总给人一种无情和冷酷的联想。工业化社会里容不得诗意。敏感如汤姆这样的人,面对你争我夺的追逐时,只能逃避在诗歌的世界里。而诗歌是资本家们鄙视的东西,这在《玻璃动物园》结尾处得到了印证:汤姆因为在鞋盒上写了一首诗被老板发现,因而被解雇。而脆弱如劳拉和布兰琪的人,更是不能融入这个社会,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劳拉紧张地呕吐;而布兰琪丧失家园,丢失工作,在崇尚技术的工业社会中,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年长色衰,最终落得无家可归。
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我们看到工商业文明的副产品——拜金主义对人的影响。大阿妈在欧洲之行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购物狂,这是人们为物欲奴役的反映。人们为了满足消费的欲望,心灵迷失在外部的物欲中。大阿爹拥有大量的财富,却在濒死时绝望地承认自己一点都不快乐,物欲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反而使人更加患得患失,导致人际关系冷漠,人格得不到升华,对生活的热情丧失,成就感缺乏。在这种环境下,失落、焦虑和彷徨为人们的生活打上灰暗的底色,疏离、孤独和冷漠占据了生活的主导地位。人的自我与其世界性存在割裂,切断了与自然、世界、他人本该有机和谐的亲和关系,因而丧失了爱的能力。
在工业文明中,机器和技术统治一切,人与世界存在的原始关联性被割裂。此时,人与世界的关联必须通过机器和技术作为媒介,而这种媒介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工具,传统的刀斧锤子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操纵,而在大型的机器中劳作的人,不能够看清这个机器的奥妙,一切程序都是设定好了的,人们要做的就是听从它的指令。因此,人本身被物化了,从而出现了物化了的世界观和物化了的整个世界。总而言之,“人在机械的秩序和对机械的依赖以及在物欲的怂恿之中,人在本能地承受机械化的物理暴力的控制并成为这种物理暴力的维护者和强化者”。[4]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精神荒芜如沙漠,丧失了信仰根基,人与神割裂。
《鬣蜥之夜》中香农的故事就反映了人信仰根基丧失后的孤寂、彷徨和无助。香农作为一个牧师,产生对上帝的怀疑,进而追逐肉体情欲的满足。在跟一个又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后,他产生更加深刻的孤独。所以,看似他周围总有美女围绕,汉娜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孤独的:
今天下午在这个走廊里,那个小姑娘让我看到了(你所说的)亲密关系对你来说实际是多么孤独。你和她在冰冷、无情的旅馆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香农先生,那使你鄙视这个姑娘,也更鄙视你自己……不,香农先生,不要骗你自己说你总是有人陪着去旅行。没有,你总是一个人,没人陪同……(《鬣蜥》第三幕)
信仰丧失后,物欲的满足却导致更深刻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实际上,威廉斯剧中刻画了一个个无家可归者。拉着行李箱的布兰琪,总是在路上的香农,浪迹天涯的缺席者(如汤姆和劳拉的父亲),丧失祖父后的汉娜等等。这些剧中人居无定所的状态,正象征了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现代人家园的丧失。其实,家园与人本身的具体所在并非本己相关,家园的所指并非一定是人的住宅,有的人身处豪宅,却无家园;而有的人身在羁旅,浪迹天涯,居无定所,却总感觉在家。正如汉娜所说:
爷爷和我,我们互相给对方一个家。你知道我说的家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家。因为我不认为家是一个地方……一个建筑,一个房子……木头做的,砖做的或是石头做的。我认为家是两个人互相拥有的可以在里面栖息、休憩、居住,我指的是感情意义上的。(《鬣蜥》第三幕)
所以,汉娜和爷爷虽然一直在路上,但他们两个互相支持,因而就拥有温暖的家。借此,威廉斯呼唤人类回归家园。而语言是家园之根基,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于其住处”。[5]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是语言的规定性,正是诗使语言成为可能。“诗人是语言家园的守护人。同时,只有在语言的家园中,才能实现诗意的居住。”[5]归根到底,这里呼唤的是诗意的回归、上帝的重新降临和信仰的重建。《鬣蜥之夜》以诗人农诺谱出最后一首诗后肉体消逝、精神永生结束,似乎寓意着人的精神回归。
综上所述,威廉斯的戏剧通过刻画一个个孤独、郁闷、失意的人物,展示了现代人在工业文明异化作用下的无奈处境,批判了工业文明价值观。这种批判具有鲜明的生态学意义。剧中人的精神危机反映了现代人普遍遭遇的精神家园遗失的境遇。在工业和科技为主导的时代中,人与自然的隔断,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最终导致了人与神的隔离,人类沦为物欲的奴隶,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借此,威廉斯呼唤人类重建精神家园,以诗意人生对抗理性和技术对世界的统治。人与人之间只有重建交流、互相关爱,才能摆脱拜金、拜物等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真正往诗意栖居的归家之路靠近。
[1]刘永杰.当代美国戏剧的生态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17(1):57 -60.
[2]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4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5.
[3]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9.
[4]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
[5]张贤根.诗的本性与人的居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1):136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