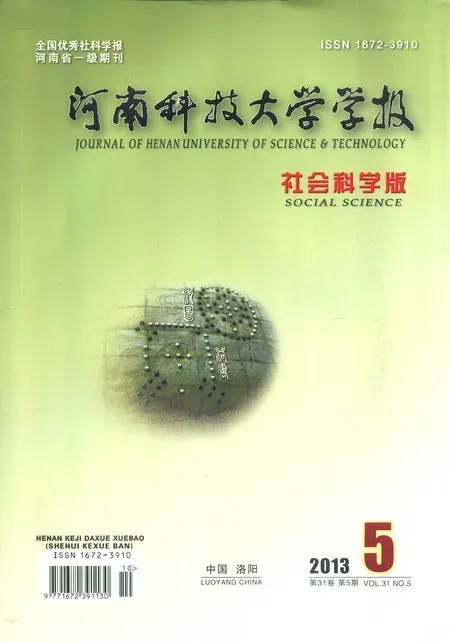新旧时代之交的繁华与沉寂
——20世纪的小诗
2013-04-06刘畅
刘畅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艺文寻珠】
新旧时代之交的繁华与沉寂
——20世纪的小诗
刘畅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20世纪二十年代初和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文学产生重要变革的时代,“小诗体”在这两个时期走在时代最前端,繁荣发展蔚然成风。小诗虽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产生,但其发展中融合了本土的时代背景、主题风格等特色,并在新时期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获得新发展,完善了诗歌民族化建设,将现代派的象征手法灵活运用于创作实践。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小诗将获得新的生机。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小诗
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其先行体式的新诗同样经历了从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到酝酿准备期的近体诗,再到五四新文学大力倡导的现代新诗,白话化和自由化是现代诗体演变的基本趋势。早期白话诗自由语体由于语言欧化、忽视情感、排斥形式美和自身建设不足等原因,造成了诗歌内部结构混乱、日常口语化严重等“非诗”缺陷,并由此导致1923年新诗的中落。新诗中落无形中为新诗体式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反思白话体和自由体的文本形式,力图借鉴外来资源,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小诗体便应运而生。这些诗人并无意以小诗体代替自由体,只是试图通过小诗体弥补诗歌自由化之弊,却未料到“小诗”竟成为一个具有自身诗学内涵和美学特征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坛风靡一时。
小诗是一种形式短小、内容简洁、诗句凝练且思想意蕴和感情集中的自由体新诗,常将诗人瞬间的感悟、体验与零星思想作速写式记录。胡怀琛在《小诗研究》中说,小诗形式上的条件是“将一刹那间的感觉用极自然的文字写出来,而又不要一起说完,使得有言外之余意,弥外余香”,其实质包含了“温柔敦厚的感情”、“神秘幽怪的故事”、“玄妙高超的思想”和“觉悟解脱的见识”。[1]足见小诗是具有独立范式的诗歌体式,不能将其与简单的短诗混淆。短诗仅指诗歌的长短,其特征与其他诗歌大致相同,小诗则是诗人情感迸发的“点”的集合,是对情绪和思想不加渲染的素描和写意,通常不具有叙事的连贯性和循序渐进的情感性表达。
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轫于五四新文学的小诗,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变迁一直延续至今,小诗创作领域收获颇丰。但反观研究领域,关于小诗的专论寥寥,学界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且研究目光大多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很少关注其发展变化,因而关于小诗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和独到价值。特别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20世纪二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两个新文学产生重要变革的时期,小诗创作也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前端并繁荣发展蔚然成风,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本文将立足于这两个时期的小诗创作,将其背景、来源、主题、风格和缺陷作一梳理,试图建构一个小诗发展的清晰框架。
一、发生背景:时代与人文
从时代与文学思潮的角度审视20世纪二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诗,不难发现其相似的诱因:都被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首先,小诗得以在1922年前后蓬勃发展,与“五四”落潮期广大群众——特别是文学青年普遍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革命失败,社会黑暗,知识分子自身的脆弱性和传统文人柔弱的心理使其回避现实转向内心,这时亟需一种能够承载他们突发的感触和喟叹的文学形式,小诗简洁精干的诗体满足了这种心理渴求。因此,20年代的小诗大量弥漫着迷茫哀伤的情绪,着力表现诗人的苦闷、孤独和彷徨。同时,五四时代“是在哲学意义上人的发现、人的自觉,进而对人的自身生存环境和世界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和批判的时代”,[2]因而,以冰心为代表的哲理小诗的广泛出现,体现了诗人在哲学层面对自我和人生的探求。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和文艺漫长的冰封期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解冻,自由的春风温暖着艰难步入新时期的诗人。“文革”中盛行的“假、大、空”的矫情诗(实为非诗)久为人民所厌恶,在新的时代,诗人与读者共同呼唤并期待“说真话,抒真情”的真正意义上的精致诗歌。然而长期的政治和生活磨难,使诗人艺术思维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当他们突然面对新的社会生活时,虽渴望抒发压抑已久的情绪,但艺术准备不太充分,构制长篇显得乏力,此时选择小诗最为合适。因此,小诗以其形体小、内容精、情感真的特点恰好满足了人们当时的审美诉求。
两个时期小诗的繁荣发展都由当时的期刊作为推动力。例如20年代专门刊发诗歌作品的《诗》杂志,从第一卷第四期(1922年7月发行)起,专辟“小诗”栏目,为诗人和评论家提供发表的空间;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小说月报》等杂志,也都发表了不少“小诗”。冰心的《春水》、《繁星》,“湖畔”诗社的《湖畔》,俞平伯的《冬夜》等诗集的出版,形成了小诗创作的高潮。80年代,中国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极具影响力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也不定期开辟专栏推荐新人新作,促使小诗诗人及诗作层出不穷。
这两个时期的小诗,都走在新时期的前端,在大时代的推动下产生,并在满足了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走向繁荣。
二、异域影响:塑形与演进
20世纪20年代是小诗创作的滥觞期,除了企图纠正早期白话诗的贫弱外,其产生还有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受外来思潮和文学体式的影响极深。周作人指出:“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3]除泰戈尔以及其代表作《飞鸟集》的影响外,小诗发展首先得力于周作人对于日本俳句、短歌的译介和对小诗体的介绍推荐。周作人1906-1911年在日留学时,对日本的俳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6年,他的《日本之俳句》第一次把日本诗歌和小诗联系起来;1922年《论小诗》一文,系统阐述了小诗的概念、来源及其与俳句的关系,归纳了小诗的特点。小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赋予一定的美学内涵,以一种区别于旧体诗的新面貌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周作人十分推崇日本诗歌“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3]的特点,而且强调其要点“在于有弹力的集中”,要“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4]这是对小诗诗质特征的概括:既要浓缩凝练,又要意在言外。小诗在与日本俳句发生一系列融合抗争后逐渐发展为自由诗的一种新取向。
80年代的小诗创作是在20年代小诗理论基础上进而丰富生发的,在诗歌形式和核心表达方面延续了前期的诗歌传统,但明显受到当时广泛流行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与20年代相比,新时期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更加全面系统,而“文革”结束后人们普遗存在的怀疑、迷茫情绪和文化失落感,又为接受现代主义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土壤,萨特的文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加深了人们对自我的关注与认知。这种外来的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呼应了部分国人的思想情绪,使人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从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被动接受,变为一种自觉需要的积极迎取。
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表现对象的“向内转”,即由现实主义的客观模仿转向内在体验的主观表达,这与小诗的内涵不谋而合,而其惯用的象征手法在小诗中更是屡见不鲜。代表作家顾城的作品充斥着现代主义的色彩,如著名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表面写“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实指“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教育下的觉醒;备受争议的《远和近》明写“我”、“你”和云的关系,其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社会和生命的关系……埃德蒙·威尔逊评价西方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派的象征通常由诗人选择来代表他自己独特的概念——它们是这些概念的一种伪装。”[5]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诗所运用的象征是一种个人化选择,充分表明诗人对50至70年代明白直露诗风的不满。他们主张诗从独立思索的“自我”出发去寻找个人同现实世界的临界点,通过个人的独特认识、感受和身世去折射世界,包括重大的历史、社会主题。他们主张对精神世界进行多层次开掘,以象征意象的模糊性、朦胧性为手段,使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潜隐性的表现成为可能,同时恢复幻想、想象的艺术功能,将直觉、幻觉和智性潜意识等艺术心理机制注入诗歌,从而大大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当代新诗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三、主题风格:继承与裂变
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诗最大的特点在于扩大了白话诗体的题材,反映了真实的日常生活;除了抒写外在客观世界之外,还表现了诗人的“内生活”。这方面的代表是以自然风景为主题的小诗。小诗本身宜于写景,周作人在《日本的诗歌》中说:“(小诗)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6]俞平伯《忆游杂诗·序》也说:“短诗体裁用以写景最为佳妙,因为写景贵在集中而使读者自得其趣,或疑诗短不能详尽,不知写景物本不是要记路程的。”[7]此期小诗写景的作品众多,例如冰心在《繁星之五十六》中描绘到“夜中的雨/丝丝地织就了诗人的情绪”;冯雪峰的《花影》:“憔悴的花影倒在湖里/水是忧闷不过了/鱼们稍一跳动/伊的心便破碎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此时的小诗在整体风格上大都表现为纤丽柔婉,文笔优美,清隽淡远,同时又因处在五四落潮期而笼罩着忧郁凄迷的情绪。如湖畔诗社的小诗就透露出天真烂漫的青春气息,在《湖畔》诗集中,充满童趣的“孩子气”的描写随处可见:“蛙的跳舞家呵,/你想跳上山巅吗?/想跳上天吧?”(《西湖小诗第十五》)“伊香甜的笑,/沁入我的心,/我也想跟伊笑笑呵。”(《笑笑》)这样的朴素天真、稚气扑人的诗,洋溢着“五四”新文学特有的时代气息。
与之相比,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歌主题则显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此时小诗主题主要是表现对历史和过去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现实社会黑暗面的强烈不满,进而抒发内心的愤怒与郁结。这从80年代的作家构成就能窥见端倪。除了当时活跃在诗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如顾城、北岛、韩瀚、孔孚之外,还有一批以前就从事小诗创作的老诗人即归来诗人,如艾青、流沙河、鲁藜、曾卓、沙鸥等,他们在历史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戕害,在新时期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悲鸣与控诉。例如当时影响力颇大的韩瀚的《重量》:“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首诗作于当年张志新烈士被害后,一经发表立刻家喻户晓,诗歌将触目惊心的“带血的头颅”与“生命的天平”这两个意象相连,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英雄者生命的庄严和苟活者生命的苍白。同样的例子还有北岛的《宣告》:“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诗人将自己所经历的不幸和创伤转化成诗行间痛苦、怅惘、悲愤等多重混合的复杂情绪,将自己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编织成文字,构成诗篇。
80年代的小诗虽然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但仍然是在20年代小诗所传承的重内心、重哲思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的。从20年代单纯模仿外来之作演化成具有独特艺术创造的诗体,小诗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将简洁的诗体、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丰富的哲理和现代派的诗歌技巧融为一体,在诗歌艺术上更为成熟,产生了一大批富于代表性的诗歌佳作。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的小诗创作不仅是在国内,港澳台及海外诗人也纷纷加入其行列,如郑愁予、痖弦、余光中、席慕容等,成为小诗发展壮大的主力,小诗的热潮也由国内向外辐射,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四、衰落缘由:缺陷与桎梏
小诗在2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较短时间就衰落下去,这不得不使人思考其中的原因。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小诗这种诗歌体式在当初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范和独立的诗学内涵,其自身的美学特征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究,从而导致创作小诗的人数虽多,真正领会小诗的诗人却寥寥无几,因此创作很容易流入琐屑和浅陋之中。这一点从当时胡怀琛《小诗研究》中便可看出,书中将小诗的“小”简单理解为诗行的“短”,认为小诗就是“两行或三行的短诗”,是“很容易写成的”。[1]这样的看法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于是,小诗创作良莠不齐,到后期,随意拼凑、艺术水平低下的小诗充斥诗坛,最终使小诗走向衰落。
其次,20年代的小诗主要是受到外来诗歌的影响。外来诗歌带有其民族的特质,译入后难免失其实质,中国诗人学到的只是“神”的层面,在“形”的转换上难免牵强。当时的许多小诗,句式随意,分行很不规则,在诗歌形式上缺乏自觉意识。20年代初大多数作家只是对日本“小诗体”的粗疏理解,而缺乏对诗意的提炼和开掘,导致创作思维散文化和外部格式杂乱化问题,大大削弱了小诗的艺术生命力。
其三,小诗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新诗诞生的初期,诗体解放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传统的负面压力依然不可小觑。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小诗体又没能建构稳定的“体”的自觉与规范,拙劣的效法者越来越多,小诗被大量复制,削弱了自身价值。当时代由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逐渐向“社会解放”发展过渡的时候,仅仅表达个人感受和瞬间情绪的小诗就显得不合时宜,到了20年代中期,处在重重危机中的小诗即走向衰落,鲜有人提及。
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运动,虽然在中国新诗史上初步建立了一种新诗体,但其诗体建设是粗糙简陋的,关于小诗内部的理论没有得到有力的建构,很多问题也没有及时纠正和解决。但是,小诗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小诗的消亡。在60年后,特别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小诗热潮,完善了诗歌民族化建设,并广泛吸收外来思潮,将现代派的象征手法灵活运用于创作实践,这充分说明小诗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是随时代不断变化发展壮大的。在短信、微博盛行的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相信小诗还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1]胡怀琛.小诗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26.
[2]蒋昌丽.中国现代哲理抒情小诗审美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9,(7):23.
[3]周作人.论小诗[J].觉悟,1922,(6):29-30.
[4]周作人.石川啄木的短歌[J].诗,1922,1(5):18-19.
[5]埃德蒙·威尔逊.象征主义[M]//杨匡汉,刘福春.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137
[6]周作人.日本的诗歌[M]//周作人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26.
[7]俞平伯.忆游杂诗·序[J].诗,1922,1(1):3-4.
Prosperity and Silence at the Turn of the O ld and New Eras——Short Poems in the 20th century
LIU C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The early 1920s and 1980s witnessed great changes in literature eras,and“the short verse”becomed more developable and prosperous.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the short verse”came into being and mixed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ackgrounds,themes and styl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With the influence ofmodernism in the new period,short poems gained new developmentand got perfect in nationalization.The symbolic technique ofmodernism was applied in creative practice.It is no doubt that shoet poemswill get new vitality in the digitalized and networking era.
modern literature;contemporary literature;short poems
I206
:A
:1672-3910(2013)05-0062-04
2013-06-14
刘畅(1989-),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