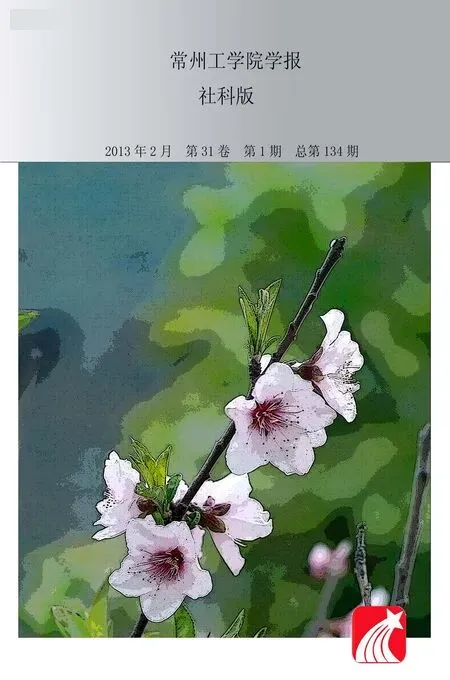物化:香港女作家叙写都市人的命运一种
——以张爱玲、施叔青、西西的小说人物为例
2013-04-02王瑞华
王瑞华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在以香港为叙写对象的小说作品中,似乎都无法回避一类被“物化”的人物形象。张爱玲、施叔青、西西这些以写香港闻名的著名作家作品中,都有涉及。如张爱玲的《连环套》中的赛姆生太太(霓喜),在接连嫁了三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丈夫,并生了一大群孩子却皆被抛弃后,作者写道:
霓喜突然有一阵凄凉的“外头人”的感觉。她在人堆里打了个滚,可是一点人气也没沾……她抬头看看肩上坐着的小孩……是一块不通人情的肉,小肉儿……紧接着小孩,她自己也是单纯的肉,女肉,没多少人气。①
这里,活生生的人,在男性世界里经历一番挣扎劫难后,被物化为单纯的“肉”,没有多少人气的肉,大人如此,孩子也是如此。《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曾是纯洁少女的葛薇龙为了享乐,逐渐沦落为供他人享乐的工具:“就等于卖给梁太太与乔琪乔”,“不是替他们弄弄人就是替他们弄弄钱”,展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逐渐被物化成他人工具的过程。梁太太更是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把自己的青春与爱情当成了物质交易的砝码。而白流苏与范柳原那场看起来浪漫、其实是精于算计的爱情,算来算去,计较的也不过是物质利益的得失。施叔青小说里,英国过气的律师碧加,原是伦敦发霉的律师,几经辗转,当上了香港首席按察司,但他到香港刚下飞机,就“闻到了一股别处没有的味道——金钱的味道”,从此改回本行,大发利市。还有《情探》中的殷枚、《窑变》中的方月、《香港三部曲》中的黄得云等,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被物化的人物名单,这其中,有女人,也有男人。可见,在香港人的被物化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施叔青《维多利亚俱乐部》中的主人公徐槐只有游走在物质世界中,才能找到生存的感觉与意义,这也是他之所以堕落为一个贪污犯的重要原因:
每次出门回来,徐槐必须到他经常流连的商场转过一圈,把他熟悉的名牌店一排看过去,才真正觉得回到家了……采购主任停职不到一个月,徐槐已经跟不上形势了,他吃惊的向四周巡视,那种往日与物连在一起,人在货品中游走,伸手随便可触摸、变成物的一部分的归属感没有了。②
“人”只有游走于物间才能找到回家的感觉,只有在物中才能找到自身的认同与归属感,人,已经不只是自身作为“物质”意义而存在,而是已经内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归属与认同,被演化成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与生存方式,自身变为物的一部分。如果说梁太太、葛薇龙、赛姆生太太她们的物化还有她们的挣扎与无奈,有着现实世界的挤逼与欺压,那么徐槐的物化则是源于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自觉;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人性泯灭,人格的堕落。人被物化到如此程度,已经是十分触目惊心,完全意义上的物质动物了。
人是怎样变成物的?《情探》中的庄水法很清楚地说明他及其他人在香港被物化的过程:
初到香港,庄水法曾经坚决拒绝这种腐蚀人心的空气,轻易不肯到商场流连,早两年为了求得心理的平衡,过海到九龙,故意不开自家车,和人家去挤二等的渡轮。他迎风站在船头,大口吸入浓浊的汽油味,记取从前贫无立锥之地的日子,而致眼眶湿润。然而在这物质过分膨胀的地方住久了,成天价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的,无非是商品,久而久之,人被同化,虚荣了还不自觉,犹自沾沾自喜,相互炫耀。庄水法年轻时节约自律,嫉富如仇的心态,随着他银行日愈高涨的积蓄,早已将之抛诸脑后……③
“空气”中都充满金钱的味道,很决绝坚守的人物都难以自持,香港现实环境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而被物化的人物又是如此之普遍:不仅没有生存能力的弱小者被物化,连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男女社会精英,也陷入物化的追逐与沉沦而不自觉,甚至当成了人生意义的追求,由此可见,香港这个物化的现实环境导致、诱惑着身在其中的人们,甚至是处于其中的一切:土地、文化、艺术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观念、人才培养、人的等级观念等等,香港像一个巨大的物质泥潭,使一切陷入其中的都难以自拔,这不能不是人在香港的悲哀。虽然这也是导致香港商业极度发达的重要原因,然而反过来,这种极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又在诱导、促成着置身其中的一切的进一步物化,使香港成为一个令人堕落的陷阱,人欲、物欲横流的城市欲望投射地。就连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被完全标价了。在香港,土地本身也已成了商品。香港评论家周蕾说:
土地并不是一种至爱的“乡土”,而是彻头彻尾的商品……空间的普遍匮乏意味着创造香港景观的不是土地,而是金钱。④
小说中许多人的发迹主要就是靠经营房地产,如妓女黄得云,就是通过她的英国情人西恩·修洛的关系,帮她贷款买下跑马地的数栋楼房然后抛出,几出几进发达起来的。西西《飞毡》中的普通人家叶重生也是因着她的善良而累积下的房产发家致富的。不只土地,其他的一切,在香港都逃脱不了被物化的命运。如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艺术的沦落在香港更是触目惊心。施叔青的《票房》就演义了一曲典型的文化在金钱世界的沦落。来自大陆京剧团的正宗花旦丁葵芳,想到香港大干一番。然而,在这个金钱主宰一切的世界里,她的梦想注定破产了,沦为陪阔太太唱唱配角的角色。
可见,在这些女性文本中,香港像一个巨大的物质黑洞,把一切都吸纳进去了。金钱在使一切皆被物化的同时,也使人和人性扭曲异化。如《驱魔》中,因为流传穿牛仔裤可以使人看起来年轻,“一个祖母级的女人,就终年一条名牌牛仔裤”。而在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里,她应该是一个言谈举止庄重、儿孙绕膝的忠厚长者。
一切的物化当中,人的物化是最具悲剧性的,也最为令人触目惊心。人的物化的现实条件是:钱与色,这是他(她)们要立足香港的最基本的本钱。钱与色抽离了原来附着于其上的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香港这块化外之地得以发扬光大开来,真正体现了或者是迎合了香港惟钱惟色的消费主义至上的观念。三天三夜炖出的“佛跳墙”,四万港币一席的乳鸽舌大餐,白兰地酒拌鱼翅……钱与色,远离了原来的社会背景,在没有自己历史和文化的香港,反而从原来附着其上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的压制中解脱出来,变得赤裸裸的。从中正可看出香港的社会特征。梁太太牺牲了青春和美貌换来的金钱,使她纵情挥霍,并以此来赢得众多小男生、老男人的爱,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男人既是她们的欲望对象,也是她们的欲望手段;女人更是赤裸裸地变成了男性的欲望对象,人们之间欲望的可悲轮回莫过如此。在这个物质主义至上的殖民地,女人常常是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她们的物化往往就是以性为手段变为男性的玩物,如梁太太,如葛薇龙,如黄得云,如赛姆生太太,如殷枚等;而男性则是通过金钱、物质的手段来满足性欲,纵情享乐。所以他/她们,合二而一,香港就成了一个吃尽穿绝、人欲物欲横流的城市。
英国记者曾这样形容香港这个“自发性移民社会”:
香港一直被视为火车的一个中途站,人们来来去去,你可以跟她偷偷情,尝尝一夜温柔的滋味,可是绝对不可能与她谈恋爱。⑤
这个“偷偷情的地方”就成了除香港本地人而外的大量过客、商人、旅游者竞相奔赴的地方。人们到这里来,纵情享受一番,却绝不为它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香港作为人们欲望投射地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对那些偶尔来偷欢的过客们是如此,对香港自身也是如此。纵情物欲、色欲甚至成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一个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共同追求。香港开埠之初,色情公然成为一种产业。如《香港三部曲》中描绘的当时公开开设的妓院的繁荣热闹。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如黄得云的被劫掠。而且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观念也逐渐按金钱来划分了。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乔其桥:“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而后来成为香港富贵名流的黄得云本是妓女出身,香港的贵族也不过如此,可见在香港社会地位的获得既无传统世袭的贵族,也非西化的名门,而是以钱来重新核定的。这种抽取了种族、血缘和传统的等级观念的社会分层,钱,就成了重新划分人物身份、等级的新标准。钱在香港把传统的一切都颠覆掉了,奠定了它的消费社会本质,这种没有自身思想价值文化观念的消费社会,也正是它这种“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的历史“过客”的身份反映。
香港这个极度物化、放纵欲望的地方还在不停地诱惑着年轻的淘金者,施叔青在她的“匆匆过客”系列的香港故事里叙写了几个世纪末充满着都市梦想与欲望的女性形象,如《一夜游》的雷贝嘉、《驱魔》中的“我”等,她们在世纪末的香港游走于欲望都市的男性当中,追逐放飞自己的城市梦想。她们充满着都市欲望,不停地在名流显贵的成功男人中流浪、游移,从一个男性,流浪到另一个男性,寻求快乐、安慰与庇护,寻求刺激、热烈、富裕的生活,却最终一无所获。如《一夜游》中的雷贝嘉,出于对香港上流社会交际宴会的极度向往与好奇,费尽心机混入其中,然后在一个晚上的盛宴中不停地游走,不停地放飞她的城市梦想。从与她有过一段情的殖民者高官,到刚刚出名的导演,再到国外的著名评论家,个个都成为她献媚讨好的对象,最后却落得一无所获,连她的老情人都被别的女人抢走了。一夜的奔波忙活,最后只落得一个人孤零零地打车回家。《驱魔》中的“我”,怀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心灵的落寞、干涸,游走于男人中间寻求爱情、温情。大学里曾经的浪漫情人找了别的女孩,曾经疯狂地爱上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离婚男人,沙。然而,“沙却只愿随波逐流,一心一意想要逃走……”她现在的情人顾延是一个离过两次婚后,对爱情已经绝望的人,现在过着彻底放纵的生活,“身旁围绕着一群女人,从过气名人的孙女、女学生,到不快乐的已婚夫人……他对他的女人一视同仁,包括我在内,他玩弄种种花妙技巧,却是没有心的,不知是他不愿给,或者根本就没有。”极端的失落、痛苦与忧伤,终于使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声大哭,美好的爱情终究是一个幻想。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与早期的黄得云、霓喜她们不同,她们在都市中漂流、追逐而无所皈依的生活,对爱情、亲情的寻求而不得,充分展现了世纪末香港,繁华之下的都市堕落与无情。
而拒绝物化的品德高尚的小人物便被这个物化的世界挤迫到了边缘,生存日益艰难。这在西西的文本里可清楚地看到。西西小说《我城》里的那些被挤压到生活边缘的普通小人物,如因为精于质量、不求变化的木匠阿北,在商业竞争如此激烈的香港,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关了铺子,去人家家里看门。公园里的看门人,麦快乐终日辛辛苦苦地照料公园,却不料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只好又到电信局做接线员,还被狗咬伤。在这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身上,作者赋予了他们美好的品德和善良的愿望,但他们每况愈下的生活也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这就是普通大众在香港的生活,他们从另一方面见证、控诉着香港这个极度物化的社会。
这些女作家不约而同的共同指涉,从不同的社会层次、时间段验证了香港作为一个城市欲望的投射地的形象,也即一个赤裸裸的欲望都市形象。香港的这种极端物化的社会现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渊源的。香港作为殖民地出现的本身就是大英帝国统治欲望与物质欲望无限扩张的一个产物。英国当初强行割占香港的目的,就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主要在于开拓一个“远东”的入口,而并非在于增加领土。藉着占领香港,所达成的是一个以商业为主而非以领土为主的交易。这在施叔青的《她名叫蝴蝶》曾有述及:
反正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这个亚热带的小岛只不过是船只往来的一个落脚处而已。为了将港、九之间水深港阔的良港占为己有,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自此以后,满载鸦片的船舰从印度出发,在烟波淼淼的南海,不必挤迫在惊涛骇浪的伶仃岛,而能合法堂而皇之的长驱直入,停泊维多利亚港避风,英国已如愿以偿。
香港开埠半个多世纪,殖民地政府无意发展本土建设,他们志不在此。英国人看中的是民丰物埠的中国内陆城市,一心想开辟为倾销英国货品的贸易市场,只希望把香港这转口落脚处清理干净,减少驻军水土不服,感染热病、疟疾、霍乱的人数。⑥
可见殖民者占领这个岛屿的主要的目的是出于商业考虑,这个殖民地没有被视为领土增益;它只是一个容许英国建立必需的机制的最起码空间。它的作用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行政的总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是殖民者设在东方的收税机器。
不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论及到:
无论是殖民者的英国文化还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男性的生殖器崇拜,不但根深蒂固存在于殖民者的意识里,也存在于被殖民的、从封建传统中走来的被殖民者的意识里。殖民事业在大英帝国的意识里一向被认为是男人的事业,是男子汉展现其威力与雄风的疆场,是充满冒险和征服欲的抒写英雄传奇的伟大霸业。
“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排在中国伦理观念的首位,既意味着对国家,对妇女、孩子绝对的权利,也意味着至高的尊严。而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政府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全部都归殖民统治者所有,当地华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参与、保障自己的社会、政治等权利。这种权利的被剥夺,意味着殖民统治者对当地一向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男性的集体阉割。“父亲”这一中国传统意义的强有力的符号功能被剥夺,既失去了传统上的尊严感,也不具有现实的强大的指涉功能,殖民地男性成为被剥夺“父亲”身份的去势男人,甚至连性格都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交际明星周吉婕所谓“杂种的男孩子们,再好的也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带点丫头气”。从而导致现实与精神层面上双重意义上的缺失。这对传统观念中一向依附于他们的妇女与孩子来说,就具有了更大的悲剧意义。孩子们无所适从的焦虑与困惑、后退、麻木、攻击性等特征都给他们的生活、性格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中国传统女性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完全依赖于男性,这对她们而言,就更是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在殖民地香港,在这些作家笔下,中国女性的集体性沦落,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最终的根源,到了殖民统治的后期,香港男性借助于殖民统治的夹缝,依靠经济的才华与能力,重振中国的男性雄风,也都能从这里找到出发点,但这是香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造成香港华人过于或只能在经济中寻求出路的重要原因,无论男性、女性都只能从经济中寻求保障与安全感,所以香港后来发展而成极端的经济主义与消费社会现实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而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发展情况就是验证了这属殖民统治的最终本源。
因此正如评论家周蕾所言:
香港的城市质性——亦即是它的国际都会地位——与造就它的英国商贸帝国主义的暴行是不可分割的……与它的殖民性一直共存的经济与商业,因而就是香港的“根源”:它从来不曾有过另外的社会架构。当评论家为着香港的惟利是图的腐化堕落而摇头叹息时,他们便是忽视和遗忘了这些根源。⑦
香港著名社会学家刘兆佳也认为:
政治途径的封闭很自然导致人民对经济活动全心全意的投入,而这种机会亦多的是。非政治性物质主义的兴起,是香港中国人在他们身处的独特环境中,对政治和经济的不对等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反应。⑧
西方社会学家Ackbar Abbas 在文章中,对香港的“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如此阐述:
一个高效率殖民政权的其中一个效果,就是政治理想主义的全面封杀(至少直至最近而言),其结果是大部分的精力被导向于经济的范畴。历史想象力,人民对自身参与改变其历史的信念——这给地产及股票市场的投机炒卖所取而代之,又或是转移往对时尚和消费主义的沉溺。如果你不能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至少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衣装。于是我们所见的不是一种没落与阴郁的气氛,而是一种似非而是的没落与蓬勃并存的现象:“民主”的诉求越受打击和阻挠,市场便越加生气勃勃。⑨
其实,香港住民当初之所以是作为从大陆过去的移民,正如社会学家刘兆佳形容的,这种大陆移民现象本身就是:英国人和中国人以财富为目标的共同作业。是为香港的这种欲望投射地的角色所需要,并为之提供服务的。这种近似惟一、极端的经济主义也使香港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人才培养等都按照经济利益与观念被重新划分了。与这种极端的物质至上相适应的就是在香港一切都被物化了。首先是人的物化,然后是附着于其上的人性、亲情、爱情、婚姻、艺术、土地全被物化了,同时也被扭曲异化了。到了后期,所谓的香港的精英人物也被物化为单向度的经济人。西西的《飞毡》中曾有过描述,所谓的社会精英是:
肥土镇的大多数精英意识薄弱,欠缺文化修养,没有思想体系可言,只成为成功的经济人。⑩
这种新时期的精英,一方面就是香港的经济至上主义培养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又进一步引导、促成着香港经济的单向度发展。
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因素,是这些女作家叙写香港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以此为基点,我们才能借着小说文本真正理解香港的社会现实与它的“经济主义”的彼此渗透、影响与制约的关系。所以,对香港的解读,对这一物质源头的研究与探讨就成为不可绕过的根深因素。正是这样的客观因素,缺乏精神依存的物质至上,便只能导致感官的放荡与纵情,导致、促使生活其中的许多人物的沦落、物化。
或许,这也不仅是香港,也是世界大都市物质至上的人类命运一种。
注释:
①张爱玲:《连环套》,《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10 页。
②施叔青:《维多利亚俱乐部》,联合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9 页。
③施叔青:《情探》,《一夜游》,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985年,第145 页。
④⑦⑧⑨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0 页,第129 页,第12 页,第122 页。
⑤转引自陈国球:《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91 页。
⑥施叔青:《她名叫蝴蝶》,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52 页。
⑩西西:《飞毡》,台湾洪范书店,1996年,第4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