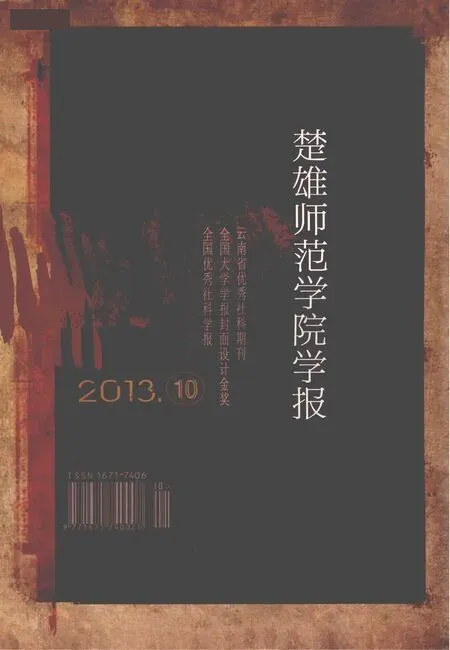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面相与论评*
2013-04-01蓝武
蓝 武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1)
斯大林曾经指出:“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来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1](P3)土司制度正是元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而在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格局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版图之内,为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而实施的一种有别于内地汉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这一与封建大一统制度迥然有别的特殊的地域统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割据性色彩,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论评。
综观学术界,迄今对土司制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者不乏其人,但对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进行专门探讨者实属鲜见。鉴此,笔者不惴谫陋,特就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表现、成因及其评价问题作一专论,藉以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土司制度的真实面貌及其特质,以及历史时期王朝中央与地方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未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正如学者所言:“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多民族而发展不平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封建中央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利用各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分子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继续保留而通过当地贵族分子进行贡纳的征收。”[2](P366)这就明确指出了土司制度的本质。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土司制度的施设,不惟西南边疆地区有之,西北民族地区亦然。[3]作为时代的产物,土司制度无疑是历代王朝中央从封建大一统的角度出发,为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是一种与封建大一统政权迥然有别的区域自治性政权组织形式,有着与封建大一统制度不尽相同的地域特点和本质特征,封建割据性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宏观地看,土司制度既是我国古代封建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种封建性的地方政治制度,它由王朝中央“在自身控制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而推行,因而“具有较高自治意味”,[4](P2)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内容。从历史上看,土司政权实质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土司政治实是“封土建疆”世袭统治的残余。就其性质而言,土司政权实质上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封建政权制度以外的政治实体,属于王朝体制下“中心的边缘”,因世守其土,世代相袭,“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官基”,[5](P41)集权程度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封建割据性。诚如学者所言,在土司制度下,“各土府、州、县、峒均为互相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封建领地,各有自己的地盘、疆界,各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各有自己的武装。而封建王朝为了防止土官势力的膨胀,防止土官势力的联合,亦规定各土府、州、县、峒均不得侵越其他府、州、县、洞的地界,不得干预其他府、州、县、峒的内部事务。违者予以惩治,乃至征剿,有意维持壮族各土司的封建割据。这种封建割据状态持续达千年之久,直到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完成才告结束。”[6](P281)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也是颇有见地的。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割据性显系土司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属性之一。
二
从历史上看,土司制度本身蕴涵的封建割据性特征,早于其原起的羁縻制度时代即已凸显出来。宋人张栻曾于其《议邕管边事》中称:“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十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7]范成大亦称:“比年不然,诸峒不供租赋,故无粮以养提举之兵,提举兵力单弱,故威令不行。”[8]显然,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层面而言,唐宋羁縻制度时代地方土官的割据倾向已经显露。降至元明时代,随着土司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土司势力得以不断伸张和膨胀,部分土官甚至公然与封建朝廷分庭抗礼,“无异古之战国”,[9]“有轻中国心”。[10]据史书记载,元代,以左右两江“羁縻州县,俱属南宁帅府分司管辖,而上下相通,姑息尤甚,夷俗狃于仇杀,往往侵盗边境,莫之能制也。”[11]左江土官黄圣 (胜)许内附,“赐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许雄琚一方,伪立名号,结连交趾,以为外援,聚众二万,劫掠溪峒山寨九十有二,声言将取邕州”,[12]其嚣张之势由此可见。明代,有的土司倚恃力强势大,与封建朝廷相抗衡,割据一方,为害甚烈。有谓:“云南、广西在处,土官割据蛮峒,彼此仇杀,贻患地方。朝廷每下抚巡司府官员抚谕,动经数岁,不得停帖。是虽夷性酷拗,亦抚之者多,贪利之人以养成之。如云南木邦孟养、广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过一狗,乞与一大骨头便去矣。”[13]思恩土官岑濬不仅私自设关征税,“截江道以括商利”,甚至对抗并杀死前来毁其石城的官军。[14]有的土司甚至公开拒绝向封建朝廷交纳赋税,拒不履行封建义务。史称:“土官以理办兵粮为事。今岑应本州税粮,连年不纳,攘为已有。况访得卢辉、黄杰,俱系庆远等卫军丁,避役投入泗城,家赀巨万。故岑应、岑钦乃土官向背之机,而卢辉、黄杰为军兵外逃之囮。若不急行剿除,则他日用兵,又恐难于今日。”[15]显然,地方土司的割据祸乱俨然已成为明代王朝中央无以回避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对此,明人魏濬曾明确指出:“大概土司之形,颇似季周列国,区分畛埒,死力拒守,虽暴寡凌弱、残杀略夺则有之,终莫能越其尺寸。其主或幼弱寡昧,则头目用事,亦略似三家六卿之类。独其人鸷悍鄙俚,无礼乐文章以饰之耳。要之窃中国之威灵,以能保其土地,其贫弱甚者,间或割村为质,亦如诸国割邑割城之例。然有年限,数盈则反,非如瑶僮仇杀驱逐,辄尽其畜产庐亩之属,据而有之者。汉法能行于土司,不能行于瑶僮,何者?力不专,情不急也。”[16]明人谢肇淛亦不无慨叹地说道:土司“虽曰羁縻,然租税不供,文告不行,其人民土物,非中国有也”,“然土司桀骜视昔百倍,见安奢之变,有轻中国心,我能必制其命乎!中途反噬,悔之何及?当事者宜熟思之也。”[10]由此可见,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确实是相当明显的。
三
恩格斯在谈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军队时曾经指出:“这种军队的兵士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的联系更为密切。”[17](P455)此与土司土兵的情形颇相类似。诸土官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法之特权于一身,不仅是其辖区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军事长官。为维护其世袭统治地位,各个土司都拥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谓之土司兵,俗称“土兵”。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称:“土司兵故精劲……以其出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故曰目兵;又以其多俍人,故曰俍兵。”[18]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土兵是土司政权赖以从事封建割据的重要支柱。诸土司往往倚仗自身强大的土兵力量,对内加强保境安民,以求稳守其世袭统治,对外从事劫掠仇杀,以便扩充自身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土司作为王臣,自然负有维护中央王朝统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义务,故必须参与各种形式的军事征调。”[4](P55)
作为土司政权的武装力量,土兵率由土官统领。而诸土司兵受命于土司的意志,接受土司的直接领导,唯土司之命是从。如据史载:“诸土司兵曰俍兵,皆骁勇善战,而内甲尤劲,非土官亲率之,则内甲不出”,“粤右俍兵鸷悍,天下称最……必土官亲行部署才出。”[19]土官对土兵控制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献记载来看,各地土兵数量绝非少数,导致诸土司往往藉此拥兵自重。据学者统计,明代全国土兵有数十万之众,[20](P96)其中尤以湖广、广西、四川土兵最著。史称:“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俍兵,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21]按 《筹海图编》云:“广西俍兵于今海内为尤悍。”[22]史称,明代广西左右两江土司,“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俍兵无虑十数万”;[23]“庆远三土州,各有精兵近万。”[24]思恩府土官岑濬筑石城于丹良庄,屯兵多达千余人。田州常有“精兵数万,呼即应……泗城方千里,兵倍田州。”[25]可见明代土司土兵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诸土司兵不仅数量多、力量大,而且训练有素,作战勇敢,战斗力强,堪称劲旅。史称:“粤右俍兵鸷悍,天下称最”,[26]后因“瑶蛮不靖,往往仗俍兵,急则借为前驱,缓则檄为守御。”[27]明苏濬亦称:“土司兵故精劲,每遇警,辄征召,大者数千计,小者百计。”[28]据史书记载,广西俍兵“于今海内尤悍……东兰、那地、丹州之俍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29]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临大江,地势平坦,沃野方数百里,精兵万人,一呼即应。……南丹差小,而兵悍劲敢死。诸司惮之,二酋忠顺不二。次则东兰、那地,皆有精兵。其它微小,朝贡不绝。”[10]诸土司兵不仅训练有素,骁勇善战,而且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还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术阵法。譬如,田州“岑氏兵法,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郑若曾对“岑氏兵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俍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管见而不之师也。”[30]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鸳鸯阵”,也曾效法于“岑氏兵法”,成为最终战胜倭寇的有力武器。[31]再如东兰、那地、南丹三州俍兵,能以少击众,其部署之法:“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凡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若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者即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走者斩,言惑众者斩,敌人冲而乱者斩,敌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全与军政所载无异。其论功行赏之法:战没者临阵跃马前斗因而催敌破阵,虽不获级而能夺敌之气者,俱受上赏;斩级者论首虏;斩级而能冠同伍者,辄以其人领之。”[32]如此奇特的战术,堪称壮族土司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抑或因此,“其后辗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藉狼兵、土兵,远为驱遣。”[33]在此背景下,当封建朝廷对土司土兵频繁征调之后,“土官自是玩狎军威,骄纵难制,往往治兵相攻,或潜通蛮贼,出没为患,甚则陷城夺印,无异古之战国。”[9]最终造成“当事者既不能节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敛戢其众”,[34]导致王朝中央在土司地区的封建统治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倾向。显而易见,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土兵不仅是王朝中央镇守边疆、保境卫国的主力,也是防卫各地的重要武装力量,还是诸土司长期割据一方的重要支柱。
四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35](P401)我们在分析土司制度封建割据性特征之成因时,理应如此。愚见以为,在土司时代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之内,造成地方土司封建割据的主要原因,当缘于地方土司与封建中央王朝在行政制度上的相异性特点及由此造成的地方土司割据形势。
首先,就地方土司而论,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基础为其从事封建割据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以西南边疆壮族土司为例。诚如学者所言:“由于壮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权,各首领各自统辖一方,不能互相统属。而土司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各土司就是互为独立的小封建主。”[6](P135)而土司制度本身与生俱来的“以其故俗治”的区域自治特点,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与排外性,从而潜滋暗长某种程度的封建割据意识。史称:“土司知州乃世袭,类似古蛮夷小国,自擅生杀。”[36]以致“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37]在土司统治区内,土官“威似王者”,[38]俨然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在行政与司法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视王法于不顾,这或多或少地会助长其离心倾向。从土司制度统治的经济基础来说,土司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强化巩固了这种封建割据状态:土官统治下的壮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官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占有其辖区内的土地、山林、草场和水源。农民都是他的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土官有人身依附”,“各土司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有独立的税收制度。从农奴搜刮来的财富,除了以进贡名义把少量交给中央王朝外,绝大多数都归土官所有。因此,各土司都有自己的粮库、金库,有自己的财政,有较宏厚的经济实力。”[6](P135—13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司统治区的自然经济基础,无疑为其实行封建割据提供了内在基础和必要条件。
其次,就王朝中央本身而言,在自身力有不逮的情况下,若欲巩固其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统治,那么,维持诸土司之间的割据状态与制衡关系以坐收渔利,或许是个不二的选择。以西南边疆壮族土司为例。元明清时期壮族土司制度的确立与推行,本是封建王朝为强化对边疆壮族地区的封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中央王朝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中央王朝为了分散壮族各首领的势力,防止其形成统一的力量,并使他们互相牵制。规定各土司不论其级别大小,辖区的大小,都由中央王朝直接管理,各土司只对朝廷负责,不允许形成隶属关系。因而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独立的封建割据单位。”[6](P135)这就为各土司实行封建割据提供了外在基础和重要条件。
如此一来,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特殊产物,土司制度所蕴涵的封建割据性特征抑或就不难理解了。嘉靖年间,总督两广的王守仁在谈及实行流土分设的缘由时曾称:“今天下郡县之设,乃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者,岂故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39]王氏此言实际上不仅是就王朝中央对壮族土官之认同与倚重及由此形成的土司封建割据形势做了较好的脚注,而且对土司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做了必要的阐释。
五
众所周知,统一和稳定始终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显然是与封建大一统相悖离的,其消极作用当不可低估。对于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之弊端,时人亦多有评论。明人田汝成曾尖锐地指出:“炎徼之政,少催科狱颂之扰,其卒然隳突、惊心骇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犷悍,抗败王略,效尤习恶。逆节比起,法令格阂而不行,骎骎乎尾大不掉之患,虽欲羁縻,渐不可得。”[40]为此,田氏曾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比封建之遗焉”。[41]亦有将其比于古代之分封制、春秋战国形势者。明人邝露曾称:左右江流域各土属,“四府三十七州,形势宛然一衰周战国图。区分畛埒,远交近攻。虽暴寡凌弱,残杀寇略,终莫能越其尺寸。其主幼弱寡昧,则头目用事,似三家六卿之类。寡弱甚者,割村为质,如列国割地献城之例。然有年月刻版,岁盈则反。倾义重士,有似四君。”[42]后人对此亦多有议论:“今之土司,无异古之封建,但古制公侯不过百里,今之土司之大者延袤数百里,部落数万余。抢劫村寨,欺压平民,地方官莫之敢指。如遇投诚归化之生番,辄议令其管辖,一则曰以土治土,再则曰素所畏服,不知日积月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43]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封建割据贻害之大实不可小视,只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基于对自身封建统治力量和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之考量,王朝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全面实施改土归流;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中,王朝中央对广大土司采取了认同与倚重之策,维持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藉以稳固王朝中央在土司地区的封建统治。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土司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全面实施改土归流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土司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的陈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44](P238)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也都是一分为二的,土司制度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无疑同样具有两面性。我们在看到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之弊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建制,土司制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4](P2)作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土司制这一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保障祖国边疆的安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这是应该肯定的。总之,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绝不可因为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而全盘否定其历史地位与积极作用,因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1]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3]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4]彭福荣,李良品.石砫土司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蓝承恩.忻城莫氏土司500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6]谈琪.壮族土司制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7]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45:南宁府部[M].
[8](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9](明)桂萼.论广西峒蛮事宜疏[A].明经世文编:卷 181[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A].粤西丛载:卷24[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11](明)苏濬.土司志[A].粤西文载:卷 12[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元)金华先生文集卷25:刘公神道碑[M].
[13](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寰宇一[M].
[1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传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明)秦纮.议泗城州土官岑应罪状疏[A].粤西文载:卷5[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6](明)魏濬.官司治徭僮不如土司能用其众[A].粤西文载:卷61[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5·广西一[M].
[19](清)汪森.粤西丛载:卷24·土兵[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20]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2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M].
[23](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73[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明)苏濬.土官用兵议[A].粤西文载:卷 56[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25](清)汪森.粤西丛载·广西土官[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26](明)邝露.赤雅:卷上·俍兵[M].
[2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17·广西土司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明)苏濬.土兵征戍论[A].粤西文载:卷 57[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29](明)胡宗宪.筹海图编·附录客兵:卷十一[M].
[30](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 (下)杂著[M].
[31]谈琪.瓦氏论略[A].覃彩銮,黄明标主编.瓦氏夫人论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32](明)魏濬.峤南琐记:卷下[M].
[33](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广西土司:志十一[M].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明)储巏.寄费国老[A].明经世文编:卷96[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5]列宁选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6](清)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土州[M].
[37](乾隆)蔡毓荣.筹滇第二疏[A].云南通志:卷29·艺文[M].
[38](明)邝露.赤雅:卷上·土司世胄[M].
[39](明)王守仁.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A].王文成公全书:卷14·别录·奏疏六[M].
[40](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序[M].
[41](明)田汝成.广西土官论[A].粤西文载:卷57[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2](明)邝露.赤雅:卷1·形势[M].
[43]朱批谕旨:卷89,“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条,黄焜奏.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