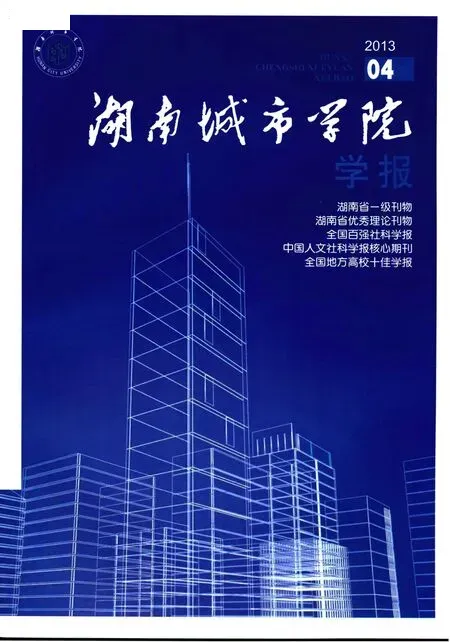网络文化自觉维度下的网络行为规范建构
2013-04-01陶鹏
陶 鹏
(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 科教信息中心,郑州 450002)
随着人类行为活动在网络世界的日趋活跃,网络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并以此为纽带推动了虚拟社会的迅速繁荣。于是虚拟空间集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为一体,演进为一种社会文化空间。然而虚拟社会毕竟有着诸多迥异于现实社会的特性,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出现了异化现象,对社会和个体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英国学者尼尔·巴雷特对虚拟社会中的行为规范性做出过论断,虚拟社会“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一个不用现实社会中法律、条例、警察和军队约束的独立王国。”[1]网络文化自觉蕴含了建构网络行为规范所必需的多种内在意识,是网络行为实现自省、自律、自觉的基础。因此,从网络文化自觉的维度来建构与网络行为相关的各种规范,能够从根本上消解网络行为的失范现象。
一、网络文化自觉不足导致的网络行为失范
(一)文化选择的方向性误判
借助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性优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突破了传统的文化传播障碍,开始把网络空间当作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网络中的行为主体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汇与交融,代表着不同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的文化类型引发了多种文化思考和社会思潮,经常会出现因彼此间完全相悖而引发冲突,使网络行为产生失范。
由于网络文化自觉程度的不足,部分网络行为主体无法在多元文化面前做出正确选择,方向性的误判使得他们不能辨识文化冲突潜在的风险威胁。他们忘记了全球化语境下应该秉持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文化选择与发展根本原则,对本国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价值视而不见,在虚拟社会的网络文化实践活动中主动放弃了应有的责任。受到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的制约,这部分网络行为主体认为选择传统文化就意味着选择落后,只有完整经历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的文化才是成熟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类型,试图以外来文化为主导来改造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有部分群体盲目的把虚拟与现实完全割裂,认为网络文化是超越国家界线和意识形态的纯文化,对具有内在精神约束力量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心存抵触。
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所导致的文化选择方向性误判,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极端化现象,部分群体意识到了媒介同质化带来的全球文化同质化风险,他们高度推崇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出现了一些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文化行为,导致网络中的文化割据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等文化思潮涌动,反而制约了国家与民族的文明进程。
(二)政治参与的无序
网络文化的政治功能拓展了政治参与体系,与现实中的政治参与相比,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治话语权利。正如英国学者亚历山大(C. J. Alexander)和帕尔(L. A. Pal)所说,“网络政治参与正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基础、政治制度和过程,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等诸多方面。”[2]
受到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的影响,虚拟社会公民对网络文化政治功能的应用方式和控制能力有所欠缺,导致虚拟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出现无序性的混乱。网络文化相对自由宽松的氛围增强了人们政治参与的安全感,现实世界里一些被压抑的社会情绪得以释放,网络中的政治参与经常会表现出反权威特征,注重通过自我赋权进行自我权威形象塑造。但是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会让网络文化的个性化因素失去抑制,容易产生过度的自我赋权。一些参与主体没有用严谨的态度对待网络政治参与,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认同,其政治参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功利性特征。当政府做出的公共决策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需求时,他们经常会使用刺激性、偏激性的方式和语言进行网络社会动员,试图以此对政府决策施加社会压力。部分群体为了把个体的政治表达最大限度地输入到决策体系当中,开始以政治参与为目的寻求网络结社,这种非制度化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混乱无序状态,极易诱发网络群体事件,使政府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众的政治权益受到双重损害。
(三)意见陈述的非理性表达
网络文化的裂变式传播让个体的意见陈述有了难以计数的受众群体,为个人声音的最大化提供了最佳实现途径。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弱化了网络行为主体的意志,使得网络行为主体在意见陈述过程中情绪失衡,理性屈从于非理智性情感所带来的欲望和需求。网络行为主体会因此陷入情绪化的焦虑、焦躁状态,自我品格的丧失导致个体出现自我认同危机,部分群体的意见陈述甚至会在人格分裂的极端化状态下进行。网络文化自觉程度不足往往还会让网络行为主体的意见陈述局限于自身利益,并且将社会整体利益抛之脑后。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会争取成为意见领袖,通过制造强势化的网络舆论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不惜使用虚假和煽动性的言论,使个体的非理性表达演变为群体性的非理性表达。在这种群体非理性表达的裹挟之下,社会公众对政府权威性声音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明显降低,政府形象极易受损。这种非理性表达也会作用于普通社会个体,一旦网络中出现与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相悖的某些热点事件,部分网络行为主体会在虚拟社会各种特性的催化下充当狂热卫道者的角色,进而转变为非理性表达的主体,用非理性的语言、行为和热情来捍卫自身的既定标准。然而非理性表达越激烈负面影响越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也就越深,事件中的普通社会个体成为了非理性表达的直接受害者。这些非理性表达主体的本意是要捍卫社会道德,可是非理性的意见陈述却对社会规范与道德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加重了社会整体的焦虑心态。
(四)群体行为的破坏性倾向
网络文化加强了网络人际关系的互动式沟通,使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交流变得直接且深入,新媒体的大量应用更是为个体迅速集结成群体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文化自觉程度的不足,以及尚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促使社会公众为了达到共同的诉求目的而聚集为临时性的网络群体,他们希望用群体行为实现个人力量的倍增。但是网络群体行为往往会不自觉地摆脱和逾越理性,使本就失范的个体行为扩大化,而群体性的参与又增加了个体的心理安全感,导致个体的失范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网络中的群体行为通常在开始之初就带有极大的情绪化倾向,其行为主体围绕共同的诉求目的不断进行各种努力,他们把网络文化的传播渠道和文化形式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背离了网络文化的应用初衷和其中蕴含的社会责任。各种类型的虚拟社交空间是网络中群体性行为的最佳孕育场所,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相近的行为主体相互吸引,在虚拟社交空间中聚集,经过交流讨论后形成较为一致的群体意见并采取群体行为。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他们会拒绝采纳外来意见修正群体偏差,敌视不同的意见和异己力量,并采用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等群体破坏性行为加以攻击,破坏了虚拟社会原有的秩序和规范,一些原本细微的社会问题被迅速放大。这恰恰印证了凯斯·桑坦斯的观点,“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3]
二、基于网络文化自觉建构网络行为规范
(一)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道德规范的建设
高度的网络文化自觉可以强化网络道德,满足网络道德规范建设的内在道德情感需要。虽然网络文化属于后喻文化,但网络道德却是传承于现实社会和传统道德。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道德规范建设,应注重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融合,把具备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美德根据虚拟社会的特点进行时代再造,使之符合信息时代社会行为规范的需要。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将会因此被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借助互联网提升自身的生命力和辐射力,改善网络文化与网络道德文化根基相对脆弱的现状。网络行为主体应自觉承担起网络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主动选择蕴含高尚道德品质的文化产品,并以此为标尺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检视自身的网络行为是否存在失范。与此同时,网络行为主体应通过学习实践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清醒地辨识网络中的低俗行为和失德行为,克服网络中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自觉抵制那些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网络炒作,从文化自觉走向道德自觉、道德自律,为最终实现行为自觉创造条件。在目前网络文化自觉程度和网络道德水平尚不理想的情况下,需要有除了虚拟社会个体之外的其它外部力量介入,政府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应充分发挥在道德监督、道德引导方面的作用,把虚拟社会的外部控制与网络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结合起来,通过褒扬善举德行、鞭挞失德失范的方式,为虚拟社会营造出良好的道德氛围,促进网络行为的规范化。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道德规范建设,能够取得文化和谐和道德自觉的双赢局面,是建构网络行为规范的有效方法。
(二)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文化规范的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网络文化在内容形式、传播应用方面的规范不健全,导致大量网络文化负面产品充斥在网络空间当中,许多网络行为的失范与此有着重要关联。网络行为主体应自觉紧跟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从自己精神思想深处意识到网络暴力文化、网络色情文化、网络黑客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把互联网用于汲取先进文化和知识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满足负面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的不良途径。网络行为主体应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因虚拟世界的隐匿性就放宽对自己的行为标准要求,尽量降低负面网络文化产品对自身网络行为的影响,真正在网络文化面前做到慎独自省。面对社会公众心理宣泄的需要,所有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应致力于建立理性的网络文化规范,使现有的网络文化具备更强的包容能力,帮助社会公众有节制地适度宣泄情绪,在不破坏社会运行秩序的前提下为现实社会减压。用这种方式能够消解极端化的不良情绪,避免因心理异化而诱发网络行为失范,逐步培育出理性、和谐、包容等良好的社会心态。为了让公众意见得以有序表达并及时获得反馈,还应从网络文化自觉入手,完善网络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高网络文化的规范化程度,使多元化的社会治理获得长效化、制度化的实践基础。网络媒体作为网络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应自觉担负起构建网络文化规范的社会责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信息传播,正确对待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充分发挥对失范网络行为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个体的价值规范建设
网络文化在强调多元文化共享性的基础上淡化了各种异质文化的差异性,网络行为主体不易察觉文化差异背后价值规范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使用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价值取向来引导自身的网络行为,自然就会引发网络行为失范,并且网络行为主体通常不会觉察到失范的发生,这就需要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个体的价值规范建设。与现实社会不同,虚拟世界中的价值观冲突暗流汹涌,多元价值观的冲突非但没有减弱,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反而在信息技术的催化之下变得更加深刻,主流价值观面临着多重网络文化安全风险。以网络文化自觉引领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关键在于强化主流文化在网络空间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兼收并蓄汲取各种思想文化之长,以持续的文化创新确立主流文化在网络文化冲突中的主导地位,促使网络行为主体主动去选择主流文化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并以此来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在此基础上,在虚拟社会中建立与主流价值观相符的价值评价体系,结合网络文化的特点逐步扩大主流价值观的适用性和引导性,从而实现对网络行为失范现象的有效规制。虚拟社会中个体价值规范的构建,还需要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行为主体树立正确的自我价值实现预期。受到网络文化个性化因素的影响,网络文化主体较为注重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但过高的实现预期或偏离实际情况的实现预期会导致网络行为的异化。强调网络文化自觉中蕴涵的社会责任,能够让网络行为主体意识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促使他们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网络生态文明规范建设
网络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涵盖了虚拟社会中的所有行为主体。大量的网络生态文明危机表明,外部的控制体系固然必不可少,但虚拟社会内在的自治性特点,决定了网络生态文明规范更多的是要依靠内在的精神力量建设和维系,而网络文化自觉则是这种精神力量的内生源泉。政府作为构建网络生态文明规范的主导性力量,既是网络生态文明外部约束机制的执行者,也是内在的参与主体之一。政府应以高度的网络文化自觉提升自身对网络文化的运用效果,提高信息技术与施政手段的融合度,为社会公众提供制度化的参政渠道,使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规范且有序。在推进网络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应避免新型问政方式的政绩化和名利化,减少因此而出现的虚拟社会资源浪费,真正发挥电子政务、网络问政的实际作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加速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面对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网络民主监督体系,政府行为主体应自觉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防止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社会矛盾被激化为网络群体事件,在网络生态文明规范的构建中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市场、非政府组织也属于构建网络生态文明规范的参与者,同样需要以网络文化自觉提升内在的综合素养,努力与不断扩展的网络生态文明体系相契合。尤其是要克服工具理性扩张对价值理性的抑制作用,自觉用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他人和社会,成为网络中文明行为准则的建设者和践行者。
(五)以网络文化自觉促进虚拟空间社交规范建设
虚拟社交领域是网络行为主体进行群体性交流的主要空间,在群体极化效应和社会流瀑效应的作用下,容易出现群体性的行为失范,扩大了个体行为失范的危害性。因此,需要以网络文化自觉为切入点,针对这一新型社交领域加强规范建设。处于群体交流应用空间的网络行为主体,应通过网络文化自觉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倾向、心理情绪、身份角色加以客观的自我评价,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虚拟社交准则,以此为基础进行自我检视和自我调控,防止自身成为非理性群体中的一员。每一位虚拟社交的参与者,都应该用正向行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制定虚拟空间社交的语言规范、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选择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网络文化作为网络社区文化,自觉抵制低俗网络文化产品对虚拟社交领域的侵蚀。网络空间的社会化演进,允许网络行为主体可以根据自我需要,在虚拟社交空间中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但要以不违背道德规范和不触犯法律法规为前提,每一种虚拟角色都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并遵守相关的行为规范。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学习扮演社会角色,即依照社会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学会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实现角色期待与角色实现的整合”。[4]虚拟社交的参与者也应该看到虚假网络信息和非理性情绪借助“情感链”传播的危害,在网络交往中以清醒的头脑、审慎的态度对待各种信息,建立虚拟社交领域诚信规范,使虚拟社交在善意无害的原则下健康发展。
网络行为规范的建构涉及到多方面的规范内容,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着多重障碍。基于网络文化自觉建构网络行为规范,体现了网络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理性反思,也反映出了虚拟社会对网络文明的内在追求。最终网络行为主体将通过网络文化自觉实现行为自觉,从而推动虚拟社会形成和谐有序的良好氛围。
[1] 尼尔·巴雷特. 数字化犯罪[M]. 郝海洋,译. 辽宁: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99.
[2]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249.
[3] 凯斯·桑坦斯.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0.
[4]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46.
[5] 费孝通. 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7] 云杉.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J]. 红旗文稿,2010(15):4-8.
[8] 尹海洁. 网络行为规范建设的障碍因素分析[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1(06):73-75.